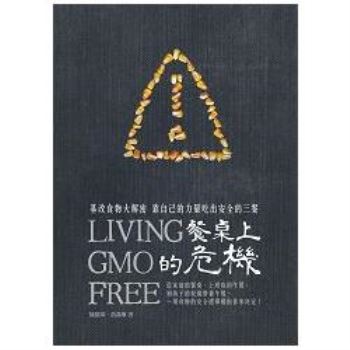序─
用相機蒸餾時代
如果我們想了解 20 世紀中國的形象,以及在此基礎之上關於中國的想像是如何在海外被建構起來的,那麼有四個攝影師的記錄無法繞過: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38 年中國之行期間所記錄的抗日戰爭;亨利·卡蒂埃 -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鏡頭下 1948—1949 年間國共兩黨政權的更迭;馬克·呂布(Marc Riboud)的數次中國之旅所見證的毛澤東時代;劉香成鏡頭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 20 世紀下半葉中國開放之前,在數字影像和社交傳媒徹底改變圖像生成機制之前,這四人的攝影是在國際情境中最廣為傳播的圖像(後來它們又成為無數中國藝術家創作借鑒的來源)。四人之中,其他三人都是瑪格南圖片通訊社(Magnum Photos)的歐洲成員,而劉香成則先後為美國《時代》週刊(Time)和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服務 16 年。其他三人都是外國人,而劉香成雖然總被標籤為美籍華人,但因為父親是左派報人的緣故,他出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香港,在福州度過童年後,又返回香港至 16 歲,隨後再去美國受教育。1978 年,不到 30 歲的他被《時代》週刊派駐北京,並協助建立了北京辦公室。因此,劉香成的人生閱歷不僅跨越中美兩個國家,更重要的是他對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亦有着親身體驗— 這種特殊的體驗造就了劉香成攝影與其他人不同的特質。也正因此,當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後,他憑着驚人的直覺預感到中國的歷史巨變即將到來,而他有責任身處中國記錄這個時刻。
蘇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曾 經 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不無尖刻地說「攝影一直對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着迷不已」。自有攝影術以來,中國就是滿足西方中產階級獵奇心理的對象。1949 年之後的中國因意識形態原因與西方社會呈隔絕狀態,但政治上的隔絕不僅沒有消除獵奇心態,反而促使文化和景觀的獵奇演變為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獵奇。毛澤東時代被允許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多半因其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親近感,雖然不再充斥着早期傳教士照片那樣基於人類學視角的窺察,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他們的攝影中覺察到來自中國文化之外的關注,它是親熱而溫情的,卻又的確是殘存着少許獵奇感的「他者的眼光」,然而劉香成的攝影與這些作品完全不同。
在他以往出版的攝影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劉香成的攝影主題不再如其他外國攝影師一樣,關注着羣眾運動與大幅宣傳畫,或者如中國官方攝影師那樣刻意美化領袖及工廠、農田中揮汗如雨的勞動者。劉香成的鏡頭指向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變化。他關注真實日常中的普通人,而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正在悄無聲息地發生改變。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劉香成能夠疏離充滿時代標誌的景致,相比其他攝影者,他的長處在於對中國人肢體語言和日常場景這些細微之處的敏感:公園裏一對情侶正襟危坐,但他們的雙腳卻扣在一起;婦女們在新髮廊裏燙頭髮— 這一切都暗示一個時代正在成為過去。多年浸潤於正統美國圖片新聞訓練的劉香成在拍攝中國時,其視點卻不再是「他者」,而是浸入到被拍攝對象之中。他的鏡頭和拍攝對象是平等關係,既不獵奇也不美化,一切都顯得自然而平靜。這既與他的身份有關,也與他的經驗有關。在東方與西方雙重文化經驗交織影響下,劉香成既是一個「融入者」,又是一個「中間人」,因此他有能力發現和抓取特定時期的中國人與他們日常生活中難以察覺卻又非常「酷」的一面— 從會見美國企業家時注意力偏離鏡頭的政治領袖,到握着可樂瓶子開懷大笑的普通人— 他們保有最珍貴的人性魅力,對此種魅力的觀照賦予劉香成攝影良好的幽默感和趣味性,正是基於此,他的攝影能夠消解獵奇的濾鏡,從而幫助世界逐步理解更真實的中國,也讓中國人更加理解自身。
在觀念上,這種平等恰恰隸屬於他在美國學習和工作所建構的知識譜系。劉香成曾經在由亨利·盧斯(Henry Luce)創辦的《時代》週刊工作多年,作為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後裔,亨利·盧斯先後創辦的《時代》週刊和《生活》雜誌幾乎奠定了 20 世紀圖片新聞報道的主流。基督教信仰奠定了亨利·盧斯對於平等的追求,不同於蘇珊·桑塔格所說的那種對於上層和底層的特殊興趣,他強調的是平等看世界的眼光。亨利·盧斯在描述《生活》的目標時這樣說:「看生活,看世界,目擊大事的發生,撞上貧窮的臉頰,感受自豪的手勢與陌生的一切— 機器、軍隊、人羣、投在叢林中與月亮上的陰影;看人們的工作……看千里以外的萬物,隱藏於牆後與屋內的一切;看危險襲來,男歡女愛與膝下嬰兒纏繞……(我)看見了,所以我心生愉悅、困惑或茅塞頓開……」多年之後,劉香成總是會在不同場合談到這段文字對於他的啟發;當我們將這段文字與劉香成的照片對照起來觀看的時候,我們會相信這種關聯是完全成立而絕非信口開河的。
在 1936 年《生活》雜誌創辦之前,或許與傳統照相機的脆弱和龐大體積有關,傳媒的照片通常都是擺拍的。隨着便攜式照相機的面世,攝影者們可以迅速捕捉瞬間的影像。正是這種新型相機給了盧斯創辦圖片雜誌的新理念,也催生了新聞攝影和紀實攝影,以及瑪格南這樣的圖片機構。某種程度上,是盧斯的《生活》雜誌將瑪格南風格在美國和全世界推廣開來。但是在手法上,劉香成卻和前面提到瑪格南的攝影師們有着明顯的區別。他首先是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新聞攝影師,他有着非常強烈的新聞敏感度。無論人民大會堂裏的會議,還是發生在北京街頭的前衞藝術展覽,劉香成總是能捕捉到這些事件的新聞點。但對於新聞攝影而言,所謂的「關鍵瞬間」往往依附於經驗,無論是戈爾巴喬夫發表完辭職演說後將講稿扔到桌上的一瞬間,還是尼克遜在從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上手搭毛巾、拎着青島啤酒送給隨行的記者,他都精確地抓住了那個關鍵的瞬間。劉香成提過,當時《紐約時報》的頭條上每天只安排一張國際新聞的圖片,正是如此激烈的競爭造就了劉香成的一種能力,就是要讓一張圖片除了成為關鍵時刻的見證之外,還有足夠多的細節可供閱讀,這種能力賦予劉香成攝影新聞和紀實兩方面的魅力。從性質上說,這是典型的紀實攝影的方式。劉香成花了更多時間進入到中國的現場,將自己當作拍攝對象的一分子,從而記錄改革開放以來各個社會階層的生存狀況,消除了單純新聞報道可能具有的偏見。在紀實攝影層面,瑪格南攝影師們常常通過編制攝影畫冊、圖片散文,勾勒出故事線,而很多時候圖片是在故事線上彼此依存的。但是在劉香成這裏,如果我們仔細打量這些照片,就會發現每張照片的細節,或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刺點」,都是如此豐富並自成體系。由於劉香成的跨國文化經驗,他們幾乎作用於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閱讀者。他的攝影直截了當,即便持續關注某個主題,故事線卻並不明顯,同時每張照片都有着脫離故事線而獨立存在的品質,也因此,他的照片總是具有發散的記憶特質和非線性的敍事魅力。
正是因為這種獨特魅力,我們似乎很難機械區分劉香成大部分的攝影到底屬於新聞攝影還是紀實攝影,它們往往兼有新聞攝影的直接見證,又有紀實攝影的豐富信息。這種個人化的風格又和劉香成平等而細緻入微的拍攝觀念相得益彰。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劉香成關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四十餘年的記錄。當我看到,從 1981 年大連理工學院毛澤東像前滑旱冰的人,到 2021年演員楊采鈺在上海北外灘兜風時身後略過的風景是東方明珠的時候,彷彿感到這些被拍攝的對象從未因鏡頭的封存而停滯,相反,這些對象及其背後的事件、人物、生活、歷史、現實一直是生機勃勃的。或者說,無論是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普通人,還是市場經濟時代的新貴和精英,在劉香成的鏡頭下,他們從來不是歷史的消極的承受者,而是積極的行動者。劉香成的攝影幾乎成為機械圖像在 21 世紀數碼技術和網絡自媒體氾濫時代最後的輓歌。他攝影的主體和客體具有永恆的尊嚴,它們或許不能告訴我們最絕對真實的歷史和現實,但是它們卻成為我們記憶的地標,激發我們的好奇,並指引着通往過去和當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