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的札記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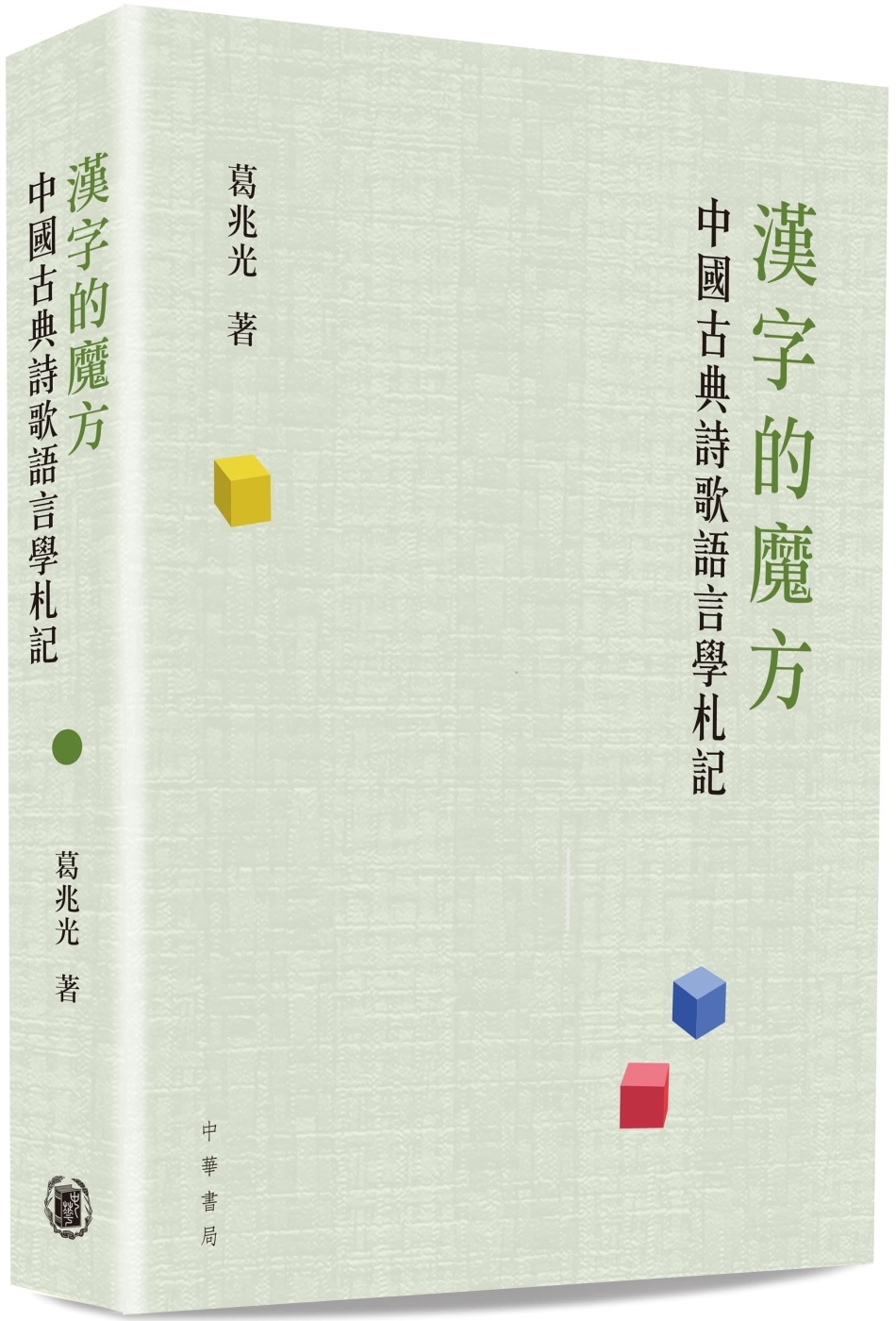 |
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中華 出版日期:2024-04-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軟精裝/ 320頁 / 14 x 23 x 1.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的札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葛兆光
- 出版社: N/A 出版日期:1998-06-26 ISBN/ISSN:9789622311282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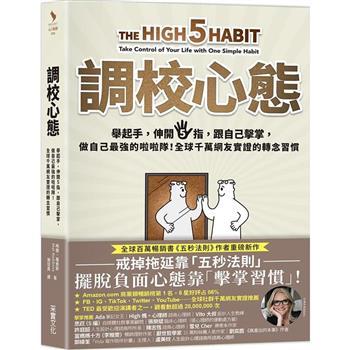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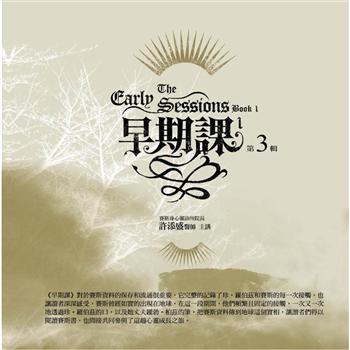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