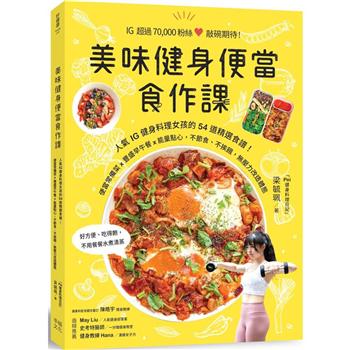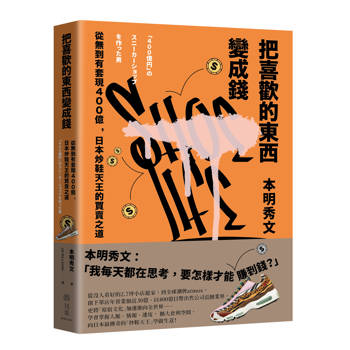前言
本書擬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做一個邏輯梳理。我認為,從執政黨的建國方略、發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 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路徑經歷了五次選擇,即實行新民主主義、仿效蘇聯模式、追尋趕超之路、發動繼續革命和轉向改革開放。這五次選擇呈現兩個過程,即從走入傳統社會主義(或稱蘇聯模式)到走出傳統社會主義,走上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本書試圖說明以下問題:中共何以放棄原本認真考慮過的新民主主義,急於仿照蘇聯模式,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覺察蘇聯模式弊端並嘗試走中國自己的路之後,為什麼引導出一場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標誌的烏托邦運動?對「大躍進」的調整和反思,為什麼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不歸之路?「文革」結束後,又是哪些社會力量推動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1953 年為什麼提前結束新民主主義政策?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和新民主主義政策之間存在內在的緊張關係。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新民主主義本來就是一個變通的理論,一種階段性的制度安排。在毛澤東那裏,相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一切都是過程,都具有策略性。這是決定毛澤東取捨新民主主義的一個根本的原因。具體說,有三個因素促使新民主主義政策很快地結束了:第一,就是對「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擔憂。特別是在農村,各級領導擔心,假如農民特別是農村幹部靠個人發家致富了,他就不會嚮往社會主義了,黨在農村的力量就可能發生動搖。第二,就是力量對比的變化,或者說對力量對比的估計。1952年土改以後,可以說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對新政權提出挑戰。在經濟結構上,國家不僅已經控制了經濟命脈,國有工商業所佔比重也超過了私人工商業,私人企業的一半以上也已經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國家有力量對它實現和平改造。第三,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型」工業化,必然導致對市場的排斥和對計劃的依賴,這正是蘇聯走過的道路。
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錯誤,引發毛澤東等領導人「以蘇為鑒」、走中國自己道路的思考,並在經濟改革與擴大民主兩方面進行了嘗試。然而,這種探索被一場來自外部的危機—波匈事件和國內的一場反右派運動所打斷,從擴大民主轉向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不過從1956年到1958年,在一個根本問題上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強烈的趕超衝動。如果要找一個毛澤東心目中的中國模式,那就只能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它具有雙重趕超的含義:一是用全民動員的辦法創造增長奇跡,趕超英美;一是通過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蘇聯,建立一種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模式。「大躍進」是政治壓力與政治激情的雙輪驅動。政治壓力來自於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及1958年黨內批評反冒進等一系列反右傾鬥爭。用「搞發動羣眾、搞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搞經濟建設,造成了從上到下的緊張氣氛,壓制了黨內外的不同意見。政治激情來自於「強國夢」願望與烏托邦理想,黨的高層幾乎沒有頭腦不發熱的,各級幹部急於建功,敢於冒險,許多想法和做法出自他們的「發明創造」,「大躍進」的失控顯露出運動式經濟的巨大風險,「大躍進」滑向大饑荒與一些基本制度安排也有很大關係。
1960年代初從對「大躍進」的反思和調整為什麼轉向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軌道,這與兩件大事有關:一是「大躍進」失敗引出的黨內分歧,一是冷戰背景下的中蘇分裂。從意識形態考察,這兩件事都涉及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黨內分歧的實質是什麼?就是在大饑荒面前,黨內許多高層領導幹部已經從1958年那種狂熱情緒中冷靜下來,回歸到常識理性:社會主義首先要讓老百姓吃飽
肚子。基於這種意識,許多人認為應該採取更加靈活的政策,包括包產到戶,雖然只是權宜之計。這越出了毛澤東所允許的底線。毛澤東認為一些人在暫時困難面前發生了政治動搖,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政治傾向,必須站出來進行強力干預。中蘇分裂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視意識形態因素。中國批評蘇聯是修正主義,蘇聯批評中國是教條主義,實質上是經典社會主義同社會主義改革的一次激辯。在毛澤東看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了我們身上,當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變修,從國際反修到國內防修,是符合邏輯的延伸。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權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大批人,一個階層,一個
派別,要改造整個黨;「文革」也是一場社會大試驗,在這一點上與「大躍進」一脈相承,只是路徑不同,「大躍進」以經濟為進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為進路;「文革」最有號召力的口號是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文革」以反修防修相號召,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反對,中共高層沒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文革」發生的力量。如此多的民眾帶着宗教式狂熱投身於運動,反映出羣眾對官僚特權化的不滿和對革新社會制度充滿幻想,
紅衞兵及其他羣眾組織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機造反」。「文化大革命」這場以理想主義為標榜的政治運動異化為三個東西,一是普遍的暴力,一是持續的派性鬥爭和動亂,一是詭譎的黨內權力鬥爭,使「文革」的解釋體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們的思想覺醒,「文革」培養了反「文革」力量。
19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啟動,肯定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文革」帶來的後果有兩個:一是傷人太多,把所有階層,特別是過去的既得利益階層都傷害了,誰都不願意再回到「文革」。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問題已經成為很重大的政治問題。這兩個問題就促使了黨內和知識界對於我們過去所走過的道路一種深刻的反思。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主要有三種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幹部。從希望擺脫「文
革」噩夢這點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幹部都是改革派,這一點很重要,如果黨內沒有基本的改革共識,改革就很難推動。當然不是所有老幹部都始終一貫支持改革,隨着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持續的爭論。但是從中央到省市、到地縣,各級領導層確實出現了一批銳意改革的領導人。第二種力量是知識分子。1980年代知識分子都是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歷次運動給知識分子造成的創傷,更主要的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目標激起了知識界的熱情。還有一個改革力量來自基層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農民很難說認識到他們選擇包產到戶與一場改革有什麼聯繫,但是農民的選擇確實成就了中國的改革。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走這麼遠,有一個大背景,它是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進行的。開放本身就是改革,開放又推動了改革。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在引進外部資金技術的同時也引進了新的觀念、規則和制度。當然,中國決策層始終堅持了自主選擇的原則,沒有接受任何「一攬子」方案,不是依據某種理論邏輯而是訴諸「試錯」式改革實踐。
當今中國,對於當代中國史的看法分歧很大,尤其網絡上兩極化的說法俯拾即是。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者,應當避免為某種主觀情緒所左右,把追尋真相作為自己的任務。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着看」、「倒着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研究歷史,首先應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本書的學術態度是: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可靠堅實的材料之上,收斂過度解讀的衝動,對歷史的複雜性抱持一種敬畏;着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而不是做簡單的道德和價值評判,拒絕用某種既成框架來框定歷史。本書的考察自然要涉及領袖人物的意志和黨內分歧,但更注重於分析在個人意志和黨內分歧背後起作用的歷史的、制度的和觀念的因素。通過這種梳理,為人們思考中國未來走向提供某種歷史經驗的支持。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精裝光邊)的圖書 |
 |
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精裝光邊) 作者:蕭冬連 出版社:開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1-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精裝 / 328頁 / 13 x 19 x 4.59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精裝光邊)
本書以簡明清晰的文字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做了邏輯梳理。作者認為,從執政黨的建國方略、發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路徑經歷了從實行新民主主義開始,途經仿效蘇聯模式、追尋趕超之路、發動繼續革命和實行改革開放的五次歷史選擇。
作者簡介:
蕭冬連,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東縣人,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邀研究員。1978—1986年間,先後在南開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主修中國近現代史和經濟學。1979—2000年,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國防大學任教,從事中共黨史和當代中國史教學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史、中國改革開放史。著有《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五十年國事紀要·外交卷》《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三次危機與中國改革的緣起》《篳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等。
作者序
前言
本書擬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做一個邏輯梳理。我認為,從執政黨的建國方略、發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 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路徑經歷了五次選擇,即實行新民主主義、仿效蘇聯模式、追尋趕超之路、發動繼續革命和轉向改革開放。這五次選擇呈現兩個過程,即從走入傳統社會主義(或稱蘇聯模式)到走出傳統社會主義,走上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本書試圖說明以下問題:中共何以放棄原本認真考慮過的新民主主義,急於仿照蘇聯模式,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覺察蘇聯模式弊端並嘗試走中國自己的路之後,為什麼引導出一場以「...
本書擬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軌跡做一個邏輯梳理。我認為,從執政黨的建國方略、發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 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路徑經歷了五次選擇,即實行新民主主義、仿效蘇聯模式、追尋趕超之路、發動繼續革命和轉向改革開放。這五次選擇呈現兩個過程,即從走入傳統社會主義(或稱蘇聯模式)到走出傳統社會主義,走上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本書試圖說明以下問題:中共何以放棄原本認真考慮過的新民主主義,急於仿照蘇聯模式,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覺察蘇聯模式弊端並嘗試走中國自己的路之後,為什麼引導出一場以「...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 i
第一章 實行新民主主義
一、「新民主主義」的源流 - 3
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建國構想 - 8
三、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實行 - 14
四、理想與政策之間的張力 - 21
五、醞釀放棄新民主主義 - 31
第二章 仿效蘇聯模式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 - 40
二、統購統銷的深遠影響 - 49
三、高潮是如何出現的 - 59
四、「舉國體制」的形成 - 76
第三章 追尋趕超之路
一、蘇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 90
二、1957 年的「大轉彎」 - 101
三、趕超模式的大實驗 - 115
四、滑向大饑荒 - 130
五、思想和體制透視 - 147
第四章 發動繼續革命...
第一章 實行新民主主義
一、「新民主主義」的源流 - 3
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建國構想 - 8
三、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實行 - 14
四、理想與政策之間的張力 - 21
五、醞釀放棄新民主主義 - 31
第二章 仿效蘇聯模式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 - 40
二、統購統銷的深遠影響 - 49
三、高潮是如何出現的 - 59
四、「舉國體制」的形成 - 76
第三章 追尋趕超之路
一、蘇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 90
二、1957 年的「大轉彎」 - 101
三、趕超模式的大實驗 - 115
四、滑向大饑荒 - 130
五、思想和體制透視 - 147
第四章 發動繼續革命...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