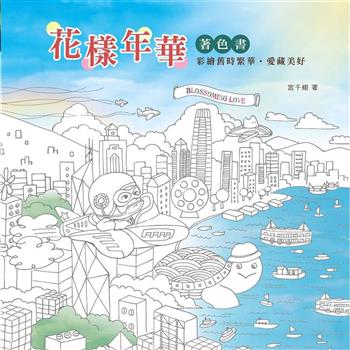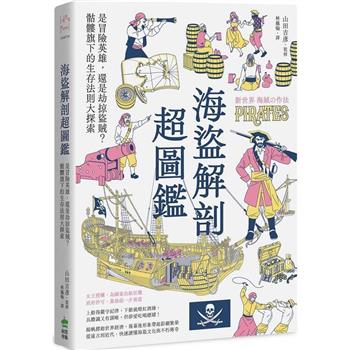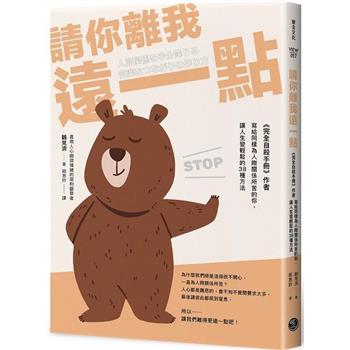前言: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
文明的臨界點
四十五億年前,我們居住的地球誕生。
四萬至五萬年前,我們祖先的足跡,開始遍布非洲以外的歐亞大陸和大洋洲。
四千至五千年前,地球各處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文明,帶來了宗教、國家、文字和貿易。
四百至五百年前,歐洲人展開全球化的冒險,人類接連經歷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踏入現代化的階段。
四十至五十年前,在經過兩次大戰之後,人類文明又再邁向新的階段,還迎來了資訊、通訊科技和智能革命。
若把地球四十五億年歷史比作廿四小時,則過去的四萬至五萬年,只不過是最後的一秒;過去四十至五十年,更只是最後約0.001秒。幸運的是,我們共同見證了人類歷史上、以至地球歷史上轉變最迅速的一剎那;不幸的是,在我們之後,人類文明不知還能否延續下去。
從歷史極長河的角度來審視,人類文明只不過剛剛誕生。正如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家William MacAskill指出,地球一般哺乳類動物通常能繁衍五十萬年以上, 以人類擁有遠超其他物種的潛能,繁衍一千萬年以上絕非不可能。地球作為一個宜居的星球,最少仍有十幾億年的歲月。假如人類有能力移民其他星球,則文明還可大幅延續下去。
然而,大約自一百年前起,隨著尖端科技的突飛猛進,再加上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從大戰、流感、種族屠殺、原子彈、軍備競賽、環境污染、基因改造、複製生命、氣候危機、物種滅絕到人工智能…..人類滅絕的陰影便一直如影隨形,人類文明似乎已走到它的臨界點。尖端科技為改善人類生活和福祉,帶來了異常巨大的正面影響;但亦正因如此,人類對科技的潛在毁滅能力,往往便加以輕率地視而不見。
若從五萬年前作為起點計算,過去已有逾一百億人曾經在地球上生活過,現在仍然活著的也有七十多億人。香港擁有七百多萬人口,約佔現時全球人口的千分之一。不幸的是,我們共同見證了香港迅速的衰敗;但幸運的是,我們仍遠較地球上的絕大部分人,過著豐盛的物質和非物質生活。
香港人早已習慣了營營役役,耗費畢生精力盡情「搵食」。只會在很偶然之下,才抬頭關心一下我們的社會,然後很快又再躲回私人領域之中。那怕只有百分之一的香港人,能長期、持續和有意識的投入公共事務,香港的歷史已經斷然改寫。假如再有千分之一的香港人,願意再進一步放眼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未來的世界同樣可以很不一樣。這種期望,也不算太過奢侈吧?
烏托邦的丕變
「烏托邦」一詞的出現和其意義的演變,頗能反映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想像和疑慮。一五一六年,即距今超過五百年前,摩爾(Thomas More,1478-1535)出版了《烏托邦》(Utopia)一書,影響力至今仍歷久不衰。不無諷刺的是,utopia一詞希臘文的原意是no place,反映作者對烏托邦的理想世界能否在現實中實現,持保留、懷疑、甚至可能是否定的態度。
摩爾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人,畢生反對英國的新教改革,最終並且被英國政府處死。摩爾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卻抱有強烈的人本主義精神,期望教會朝向更人性化的道路發展。但對於人的理性和良知的局限,摩爾自始至終保持著清醒的態度。
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人定勝天的時代樂觀精神漸成主流,人們開始相信烏托邦實現的可能。十九世紀冒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更奉「烏托邦」概念為最早的理論泉源。但踏入二十世紀,通過人的智慧和能力創造人間樂土的幻想,卻在兩次大戰期之間徹底破滅。「敵托邦」(dystopia)一詞,遂作為烏托邦這個銅幣的另一面,應運而生。
最廣為人所熟悉的敵托邦描寫,可以在《美麗新世界》(1932)和《一九八四》(1949)兩本小說中找到。它們和更早的蘇俄小說《我們》(1921),並稱為「敵托邦三部曲」。三者均提及在不遠的將來,由獨裁政府全面掌控的社會將會出現,先進科技將大大提高管治效率,公民自由則會徹底被剝奪。不問可知,法西斯主義和史太林主義等極權思想的崛起,正是幾位作者的寫作藍本所在。
一九二六年,即距今接近一百年前,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73)因為對抗法西斯,被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關進監牢長達十年,直至臨終前方獲假釋,期間他卻寫下了不朽的《獄中札記》。在葛蘭西看來,當時歐洲冒現各種極端的思想,皆源於對英美資本主義衝擊的回應(同期中國面對的處境又何嘗不是一樣)。但不同國家民族的歷史路向,卻並非宿命地已被決定的。歷史存在極大的可變性和多變性,端視乎人們的集體抉擇。
一整個世紀過去了,人類歷史的悲劇,此刻驚人相似地重複搬演著。當尖端科技與威權民粹、官僚體制、地緣衝突等結合,人類文明將走向怎樣的未來?
電影中的未來世界
本書嘗試勾勒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在討論過程中,有三齣可被歸納為敵托邦類型的電影——《太空奇兵:威E》(Wall-E,2008)、《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2018)和《蝙蝠俠:俠影之謎》(Batman Begins,2005)——特別具有參照價值:
《太空奇兵:威E》:雖然地球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盡,但人類仍能生活在衣食豐足、無憂無慮、「堅離地」的太空船「公理號」(Axiom)上,卻接受電腦的全權統治和嚴密監控,可以稱為一個「快樂愚人」社會
《挑戰者1號》:在地球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盡後,人類生活在赤貧的狀態,但仍能在虛擬真實的「綠洲」(OASIS)中尋找自我,並且繼續與權貴階級進行絕境抗爭,可以稱為一個「網絡游擊」社會
《蝙蝠俠:俠影之謎》:在地球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盡後,政治極度腐敗和黑幫勢力當道,人類只能活在由壟斷資本掌控的葛咸城(Gotham City)中,可以稱為一個「自毁資本主義」社會
正如陳冠中在《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2018)一書中指出,荷里活往往反覆製造烏托邦與惡(敵)托邦式的想像,同時加入英雄浪漫的元素——邪惡入侵和諧社會,烏托邦被毀,幸而在鐵屋子的大門關上、邪惡全面勝利前的最後一刻,少數人特別是主角發揮正面價值的意志,力挽狂瀾,扭轉乾坤。「沒有惡托邦認知, 不吸收歷史教訓,不以寓言故事來敘說惡托邦,不僅很難體會邪惡到底有多麼邪惡,說不定還會眼看著歷史變態重演。但現在除了騙徒及無知的人,其實誰都提不出烏托邦藍圖。」
電影描繪的二元對立、黑白分明的世界,往往亦是主流民眾的庶民常識,傾向把問題簡化和理想化地看待。在此我們大可先把各種電影,想像成組成一幅大拼圖中的一片片小方塊,它們各自偏重和突出整體現實的某些方面,但卻容易以偏概全,見樹不見林。若把這些小方塊不斷重新組合,又會令我們一點點逐步加深對現實的認知,同時發現單一敍事以外的各種不同可能性。
在本書引述的眾多著作中,以英國社會學家Peter Frase的《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2016),最能提供各類敵托邦的情景設定,以及人類面對的集體命運和選項,並通過不同科幻電影的例子呈現出來。他把這種方法稱為「社會科學幻想」(social science fiction),我實在深有共鳴。
關於上述三齣電影的討論,和我稱為「公理號模式」、「綠洲模式」及「葛咸城模式」的各種未來路徑,在此容許我先賣一個關子,到了第五章才作詳細探討。在此之前,且先讓我們回首過去,追溯這些路徑出現的不同背景和因由。在第一章的提綱挈領之後,本書第二至四章將分別探討知識(非物質)權力、政治權力和物質權力的失衡,是如何在我們身處的這個世代,一步步令敵托邦從想像變成可能。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敵托邦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敵托邦
「人工智能(A.I.)能夠偵測人臉上表情的微小變化,又或說話聲調和遣詞用字的微妙差異,從而預測人的心理以至行為變化⋯⋯它全面掌握個人的所有數據,進行無處不在的介入和誘導,覆蓋範圍遠超行為心理學鼻祖斯金納(B. F. Skinner)實驗設定的有限範圍。也就是說,它足以把社會生活的整體情景,變成一個無邊無際、碩大無比的實驗室,而人則彷如生活其中的白老鼠。」
—— 鄒崇銘《敵托邦》
智能革命徹底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形態。然而當人類把未來拱手交給人工智能時,通向的是烏托邦還是敵托邦?
科技影響歷史進程,卻絕非單一具決定性條件。當它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資源以致病毒等元素混雜偶合,會構成曲折的歷史路徑。香港學者鄒崇銘分別從知識權力、政治權力和物質權力三方面,探討智能革命大潮下人類將邁向怎樣的未來。
作者簡介:
鄒崇銘,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注經濟社會學研究。曾與韓江雪合著《香港的鬱悶》、《用消費改變世界》、《僭建都市》、《以銀為本》、《這一代的鬱悶》、《後就業社會》等。相信資源和權力分布才是主宰人類未來的關鍵。
作者序
前言: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
文明的臨界點
四十五億年前,我們居住的地球誕生。
四萬至五萬年前,我們祖先的足跡,開始遍布非洲以外的歐亞大陸和大洋洲。
四千至五千年前,地球各處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文明,帶來了宗教、國家、文字和貿易。
四百至五百年前,歐洲人展開全球化的冒險,人類接連經歷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踏入現代化的階段。
四十至五十年前,在經過兩次大戰之後,人類文明又再邁向新的階段,還迎來了資訊、通訊科技和智能革命。
若把地球四十五億年歷史比作廿四小時,則過去的四萬至五萬年,只...
文明的臨界點
四十五億年前,我們居住的地球誕生。
四萬至五萬年前,我們祖先的足跡,開始遍布非洲以外的歐亞大陸和大洋洲。
四千至五千年前,地球各處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文明,帶來了宗教、國家、文字和貿易。
四百至五百年前,歐洲人展開全球化的冒險,人類接連經歷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踏入現代化的階段。
四十至五十年前,在經過兩次大戰之後,人類文明又再邁向新的階段,還迎來了資訊、通訊科技和智能革命。
若把地球四十五億年歷史比作廿四小時,則過去的四萬至五萬年,只...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
第一章 啟蒙運動打造的「想像的秩序」
第二章 網絡壟斷:非物質或知識權力的失衡
第三章 威權民粹:政治權力的失衡
第四章 生態、城市、資源和病毒:物質權力的失衡
第五章 終站?重生?未來的四種路徑
後記
圖片來源
版權頁
第一章 啟蒙運動打造的「想像的秩序」
第二章 網絡壟斷:非物質或知識權力的失衡
第三章 威權民粹:政治權力的失衡
第四章 生態、城市、資源和病毒:物質權力的失衡
第五章 終站?重生?未來的四種路徑
後記
圖片來源
版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