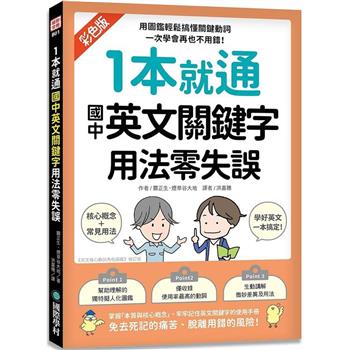胡風是魯迅晚年親密的弟子和友人,在魯迅去世之後被看作其批判精神的重要承襲者,通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影響很大的《七月》和《希望》雜誌,培養了一代新文學的闖將,並作為「同路人」,幫助共產黨做了很多宣傳工作。1949年之前,共產黨曾經通過兩輪有組織的批評,嘗試團結和爭取胡風,但是他無法放棄自己的文藝理念、遵從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最終釀成「新中國最大的文字獄」。
本書透過對84位受訪者的口述、從各家搜集的圖文資料以及對報刊文本的解讀,嘗試用多重聲音和視點,呈現政治風暴的各個層面,描摹五四之後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為他們的詩人理想付出的代價。
1925年秋,三個來自不同省份的年輕人同時入讀北京大學文預科。在動盪的時局中,他們選擇了三種不同的革命道路:王實味留在黨內,胡風一直是黨的同路人,而王凡西則轉向為黨的反對派。「北大三人行」這部歷史三部曲,以王實味、胡風、王凡西的生命脈絡為中心,借用紀錄片的手法,以多重視點組織材料,重塑三人之間遙遙相望又息息相關的顛沛命運,折射中國知識分子追求革命的歷史變奏,冀為讀者提供一部時間跨度大、同時可讀性強的中國知識分子通史。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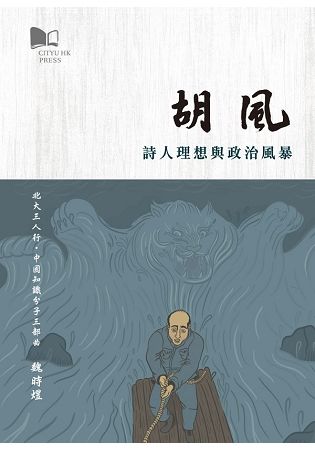 |
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7-01 規格: / 精裝 / 876頁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40 |
社會人文 |
$ 721 |
中國當代人物 |
$ 753 |
中文書 |
$ 753 |
華文文學人物傳記 |
$ 770 |
中國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魏時煜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電影學博士、卡爾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2001年起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業餘從事電影創作,劇本作品包括《明明》(2007)和《五顆子彈》(2007),紀錄片作品包括在海內外媒體好評的紀錄長片《紅日風暴》(2009)和 《金門銀光夢》(2014)。近年出版的專著包括《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2016)、《東西方電影》(增訂版,2016)、《開始學動畫》(2010)、《女性的電影:對話中日女導演》(2009)和《紅日風暴:介紹、劇本、評論》(2009)。
魏時煜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電影學博士、卡爾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2001年起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業餘從事電影創作,劇本作品包括《明明》(2007)和《五顆子彈》(2007),紀錄片作品包括在海內外媒體好評的紀錄長片《紅日風暴》(2009)和 《金門銀光夢》(2014)。近年出版的專著包括《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2016)、《東西方電影》(增訂版,2016)、《開始學動畫》(2010)、《女性的電影:對話中日女導演》(2009)和《紅日風暴:介紹、劇本、評論》(2009)。
目錄
第一章 眼中天地久沉昏
第二章 烽火連天創《七月》
第三章 鎖鏈不能屬於我
第四章 延安講話和《希望》
第五章 時間真的開始了
第六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七章 忍看朋輩成新囚
第八章 弄文罹禍可銷骨
第九章 我花開罷百花殺
第十章 我饑渴勞累困頓
第十一章 無端狂笑無端哭
第十二章 見我鬚髮醉嵯峨
第二章 烽火連天創《七月》
第三章 鎖鏈不能屬於我
第四章 延安講話和《希望》
第五章 時間真的開始了
第六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七章 忍看朋輩成新囚
第八章 弄文罹禍可銷骨
第九章 我花開罷百花殺
第十章 我饑渴勞累困頓
第十一章 無端狂笑無端哭
第十二章 見我鬚髮醉嵯峨
序
序
我是因為拍紀錄片才接觸到五四之後的文學的,而我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就是聚焦胡風事件的《紅日風暴》。這部電影是上海導演彭小蓮邀我和她一起完成的,因此可以說我最初的動機僅僅是給朋友幫忙。我和我的同輩人是在文革出生,在文革之後成長起來的,不要說在 1955 年就被打倒的胡風,我們對文革至多也只有如碎片一樣的記憶。我有同窗好友看了《紅日風暴》之後說,這部紀錄片把原來他們零散聽到和讀到的人名、概念、政治語彙,透過一個個人視點串聯起來了。在這部 138 分鐘的影片的過程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政治運動的影像和親歷者們的生動講述,能夠把觀眾帶入歷史現場;但是彭小蓮的旁白所表達的家庭的離散、成長的夢魘,才真正令這部作品有別於「客觀」的、BBC式的紀錄片。下面的文字,既是回憶、也是備忘;既是對我為什麼會寫這本書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我寫書過程中受到的影響的一個歸納。
自由養成的頭腦
我早年記憶中第一件歷史大事,是毛澤東去世。剛上小學沒幾天,有天早上,和同學們排著隊站在去往學校的馬路邊。等了很久,我其實不知道在等什麼,直到奏著哀樂、掛著毛主席遺像的「靈車」開過。那天下雨,但老師不許我們戴草帽、打傘、穿雨衣,覺得那是對偉大領袖的不敬。我媽媽用塑膠袋剪成一個「背心」,套在我的白襯衣下面,叮囑我不能告訴其他人。第二天很多小朋友都病了,我卻無恙。學校裏掛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像,後來華主席的像拿掉了。三年級開始學英語,我才漸漸知道,不是全世界人民都像外國譯製片中那樣,說著洋腔洋調的中文。小學快畢業,我才知道我小姨和姨父分別是西安外語學院的西班牙語、法語教授,而我舅舅楊德友,雖然在山西大學裏教英文,但是他懂七國外語,可以互譯。80年代起,與世界隔絕很久的中國大陸,有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潮發表,我們家的三位教授也翻譯了不少著作;我看到他們爬格子的辛苦,還曾經立志長大不做翻譯。但是他們不用坐班、有寒暑假的生活,給了我啟發,我在16歲就給自己手寫了一張名片,表明「志向」:「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系魏時煜博士」。名片我媽媽至今保留。
童年時沒有兒童讀物,認足了三四千字,在小學畢業的暑假看完了四大名著,只喜歡《紅樓夢》一部,後來每年一遍,又讀了十幾遍。因為媽媽的書架是按照世界文學史買書的,外國經典倒是讀了不少,我和妹妹還夢想過做勃朗特姐妹。80年代,魯迅、老舍、茅盾、巴金、曹禺的作品都再次被搬上銀幕;家裏訂的《收穫》、《當代》、《小說月報》上面,有很多「傷痕文學」,寫的都是物質貧乏年代,上山下鄉的青年們的故事。同時,社會上最響亮的口號是「走向世界」,連我們師大附中的童聲合唱隊,都要向獲得三連冠的女排姑娘們學習,後來在西安的校際比賽中獲得三連冠。轉眼到了高中要分文理科,父母不贊成我讀文科,大學只好讀了科技英語,竟然完全沒讀過現當代文學,印像深的課文只有莊子的《逍遙游》。教大學語文的老師對我說:「你不出國就完了。」大一時我已經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錄取,不過那時中國父母還供不起一個留學生,於是我大學畢業之後才出國留學。1992 年第一次坐飛機就去了渥太華,到卡爾頓大學讀比較文學。一位從東北來的學姊正在寫論文,題目是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她的理論框架是女性主義;還有一位學兄從北京來,不論哪一課的研究報告題目都是魯迅。我當時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到外國做中國文學,因為我只想學習西方文論。我從小念書基本只是班上中上,出了國卻幾乎功課全A,倒不是因為我英文有多麼漂亮,而是因為我有自覺、也有能力表達自己的觀點。同學們寫文學作品的報告主要是分析情節、人物,我認為這樣的分析生活閱歷豐富的教授們會覺得很幼稚;秉承工程師父母的邏輯思維的我,得A靠的是分析故事的「結構」、比較不同理論的核心概念,以及跳出慣常的思維框架。
找到了表達形式
在一年八個月都會下雪、卻常常陽光普照的埃德蒙頓,我愛上了電影,並轉讀電影學博士。我靠直覺和常識行事,老師們都很開放,沒有誰要來影響我的思維,或有意帶我進入到某個領域的深層。2003 年我在香港任教之後,開始跟隨彭小蓮拍攝胡風紀錄片,同時又跟司徒兆敦教授學習了紀錄片拍攝;現在想來,這兩位可能是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老師,因為他們引領我找到了迄今為止我最有力的表達形式。司徒老師 2003 和2005年兩次來到我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學教紀錄片,我配合他教學同時,學習了各種搜集「視聽證據」的方法。古人說:「耳聽是虛、眼見為實,」但是紀錄片的最高境界,則是在聲畫同步和聲畫分立中、在眾聲喧嘩和獨立思考中,呈現情感和思考。我的第一個紀錄片習作拍的就是司徒老師,他曾在文革中坐牢五年,多少受到父親司徒慧敏的牽連。司徒老師熱愛電影、為人誠懇,我在最初的拍攝中對他的記憶沒有懷疑,直到他自己開始在我的攝影機前糾正記憶的偏差。司徒老師說,因為記憶不可靠,所以我們需要紀錄片。巧的是,1978 至1982 年在小蓮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期間,司徒是小蓮的班主任。在履行攝影和錄音的職責的同時,我變成了一個擅長傾聽的人;通過傾聽和對話,我理順了很多對歷史的觀念,並給我的學術訓練找到一個創意出口。
在胡風紀錄片六年的拍攝、剪接過程中,我認識了五四之後中國最為開放的一個時代,認識了數十位既有激情又很率性的詩人、作家,他們大都是魯迅的追隨者。通過和他們的對話,我又重新認識了魯迅、認識了革命、認識了知識分子。從拍紀錄片起,我和很多人建立了非常特別的聯繫,在傾聽人生故事的過程中,獲得了很多師友。小蓮對於五六十年代可怖的記憶,讓我感受到政治可以給家庭帶來的災難;而對於這個災難的理解,我又通過後來接觸到的二十多個胡風分子的家庭得以深入。我單純給小蓮幫忙的動機,可以說在第一次拍攝之後就改變了,因為我首次拍攝的對像,是幽默、博學、睿智的賈植芳。他講故事的戲謔語氣和對歷史現場的幽默描繪,和我從傷痕文學中讀到的太不同了,他比很多後輩知識分子都更開放、豁達、可親,卻不自憐、不自戀。回頭去看,像李輝、周燕芬、王麗麗、路莘、張業松這些後輩學者,從胡風或七月派開始,進入開始各自的研究之路,和胡風友人這個群體的人格魅力有很大關係。因為拍攝的關係,我會坐在鏡頭旁,要求對話者看著我講故事;後來有人問,人家怎麼能和你如此暢所欲言,我想因為真誠是看得見、感受得到的!
找到「民主」的入口
人們對於「民主」這個字眼,一般都有寬而泛的理解,但要深入思索,就需要一個切實的入口。對於我在香港的學生而言,這幾年的社會動蕩,讓他們紛紛進入到這個原本並不熟悉的領域。我父親讀大學的時候,經歷了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他是讀地質的,但是同學中仍有文采飛揚、善於表達者,在運動中被送去青海;二十年後從青海回京,反因不能適應平原氣候而早世。父親是福州人,祖輩有中國最早留法學造船的魏瀚(1851–1929),還有幾位出洋留學的外交官。除了讓我遠離文藝,父親一直希望我和妹妹出國留學,我們也都獲得了博士學位。我從小愛文學,但遠離政治,即便在周圍同學們都罷課、絕食時,我也只輕輕地說,「你們這麼做也改變不了貪污腐敗。」到香港後看到許鞍華導演的九七紀錄片《去日苦多》,發現她大學時也不關心政治,1967 年她如常去期末考試,老師宣佈外面已經戒嚴,她才知道同學們的行動升級到「暴動」。70年代末她導演生涯伊始,就有「越南船民三部曲」,成為眾人心中的「政治導演」。機緣巧合中,我拍攝的首部紀錄片竟是《紅日風暴》,是關乎「20世紀中國的政治與精神事件」(林賢治語),也證明不論我說自己多麼不關心政治;但是用生命中十多年的時間追尋一段歷史,卻是當初沒有想到的。整個過程中推動我的,除了基本的民主意識,主要還是對於人性和命運的探尋。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剛開始就胡風事件查找資料時,搜索《人民日報》從 1948 年起的數據庫,看到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艾青、何其芳、劉白羽等眾多被收入過我的中學課本的著名作家,還有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甚至橋梁專家茅以升、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等人批判胡風的文章,真是有些匪夷所思。1955 年之後,胡風等人的名字,顯然有計劃地被從文壇、歷史中抹去了;50年後,一無所知的我,看到那麼多我從中學課本中認識的文學家,批判一個我從來沒聽說過的評論家,我感到的不只是驚訝,簡直是震撼。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文學家們大都與胡風相熟,思想上原本並沒有太大的分歧。然而到了運動中,私人情感都要讓位給政治立場,黨員們接受任務寫批判文章,很多人被迫公開和他劃清界線。很多人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寫批判文章的情勢,我能夠理解和想像,但我還是忍不住去檢視每個人抗壓的程度,想探究每個人在捍衛真理時,付出了多少代價。於是,沒有寫過批判胡風文章的賈植芳、蕭軍,在兩千人面前替胡風辯護的呂熒,敢於告訴審訊員「真相」的詩人阿壠,伴囚二十多年的胡風夫人梅志,在監獄裏自學了德文的詩人綠原,為避免整人而自定右派的曾彥修,還有許多為胡風鳴不平而被劃右派的大學生,都在我心中變得高大了……
拍攝梅志時,她說起第一次見到魯迅,是在一個木刻展上,她默默地跟在先生身後,隨著先生的腳步前移,一幅一幅地看木刻作品。她後來常常跟胡風一起去看望魯迅,但最初的記憶仍舊清晰如昨。在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我特別喜歡蕭紅的散文〈回憶魯迅先生〉和聶紺弩的長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蕭紅的文字,看似碎片式的日常描述,卻把我們心目中原本遙遠的魯迅,像電影鏡頭一樣,中景、近景、特寫,展示在我們面前。而聶紺弩的文字,則有效地帶我們回到 1936 年10月那萬人送葬的現場,讓我彷彿聽到當時青年們對先生的呼喊:
我們是一條悠長的行列—
饑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頭的背影倒了!
……
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
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第一個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個冒著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民倒了!
一個人民倒了!
我讀胡風、蕭紅、蕭軍、聶紺弩、馮雪峰等人在先生去世之後的文字,看到他們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以自己的生命延續魯迅的生命:魯迅是他們心中高大的背影,永遠的引領。賈植芳先生曾對胡風說:「『老先生』懂政治,我們不懂,」勸胡風不要上書。「老先生」指魯迅,而我們訪問過的人,幾乎每家都有一整套《魯迅全集》。2009 年初我到滬出差,和小蓮一起看望住在醫院的賈植芳先生,他把新書《歷史背影》簽名送我,而書中他回憶了一生遇到的奇人奇事。賈先生去世時,我看著電腦中,他舉著一支煙,笑眯眯地在說笑話,我沒有感到悲痛,因為潛意識根本不相信他去世了。
我讀胡風案中人的故事時,感動於友人之間的誠信和深情,感動於他們受難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仍然選擇一起守護真理。80年代初,曾經像農民一樣健壯的胡風,曾經以旺盛的熱力支撐起半個文壇的胡風,在出獄後精神分裂了。他曾經培育過的青年作家們,卻在花甲之年煥發新的創作生命。寫這本書時,我眼前有魯迅高大的背影,也有一群追隨魯迅的高大背影,雖然很多人已經遠去,但是沒有一個在我心中倒下。
眾聲喧嘩的歷史
在研習西方文論時,我非常喜歡一個理論概念叫複音(Polyphony)。它來自於巴赫金,是講小說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不同人物的聲音,包括帶有各自的社會階層、性別、教育所導致的雜和言語,或曰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共同參與敍事。這個概念在音樂中的實現形式,是交響;在小說之中,要求作者打破不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絕對權威,讓每一個聲音都能夠自主。這個概念,與胡風文論中的兩個關鍵詞—現實主義和主觀戰鬥精神,有相通之處;但是強調一種更多元的眾聲對話,甚至可以說接近真正意義上「百家爭鳴」的概念。因為「百家爭鳴」在中國歷史上含義太多,我還是用「眾聲喧嘩」,也因為喧嘩的目的未必是爭鳴。
結合到歷史研究中,我覺得「眾聲喧嘩」的實現,在於要同時重視文脈與人脈是很重要的:文脈是公開的,對公眾開放相同的「權限」;人脈卻並非公開,但卻主導了很多具體事件的發生。我接觸到的歷史研究者中,大部分人的職業是教授或編輯,善於搜索、處理、分析文獻,也有工作帶來的縱向和橫向的人脈。他們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朱正、錢理群、林賢治三位先生。朱正先生記憶力強大,重視材料和人脈研究,不急於說服讀者,善於用細節說話;他提示我要注意考證歷史背景。錢理群注重文脈、自覺守護自己的「獨立」;他提示我們,歷史不能由受害者來寫,不要以道德評判來作為歷史書寫的目的。深入研究過胡風和王實味的林賢治,從文字和為人中看人的品格,敦促我在研究中注重對像的人性和生命。這三位都沒有特別用主觀、客觀的字眼,但是他們的深度和廣度相輔相成。
我和小蓮遍訪胡風分子之後,完成了《紅日風暴》。我接著又想進一步了解共產黨文藝整風,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起源,於是又訪問了一些在延安經受了整風洗禮的人,並完成了《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和紀錄片《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我在《王實味》書中所做的嘗試,是希望把口述、書寫、圖片、思考都納入同一個文本,以生動、易讀的文字,呈現出王實味和他的時代;心中希望如果有人翻開這本書,可以基本讀懂延安。對於王實味的理論基礎,對於與他論爭的黨內理論家們的哲學概念,我雖有研究但無意著墨太多。這本書讓我收穫的驚喜之一,是章詒和老師對我說:「我是看了你這本書才讀懂了延安。」看到我的驚訝,章老師說:「我們是民主黨派的!」事實上章老師的書我是凡出必買,而且全家傳閱,我不敢奢望能獲得她那麼多的讀者,但是的確是把書寫給普通的,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因此她的評語對我震動和鼓舞都很大:「我們更需要這樣普通人也可以讀的歷史。」
我雖然秉承同樣的態度來書寫胡風,但是這一次的挑戰不同。寫王實味時,材料稀缺,要考古、要追問;寫胡風時,材料龐雜,要精簡、要理順。84 位受訪者的口述、300 多張從各個家庭相簿中掃描的圖片,幾千萬字的文獻,我只能完成幾個人物的生命線索。但是我希望通過本書中所呈現的人脈,讀者能夠延伸閱讀。事實上,幾乎所有受訪者,若干年來都在不停地閱讀和思考,在我拍片和寫書的十多年中,他們每個人的思想都在深入。比如把自己劃成右派的曾彥修先生,文革之後又創辦了《南方日報》,他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別處不能出版的重要書籍。2015年他去世之後,我看到他與何方先生的幾封通信,驚異於他對於延安、對於共產黨的認識的不斷深入。
記得到加拿大時,上文學理論第一課,一位智利來的教授就說,「客觀是廢話!」對我來說,做這本書和做紀錄片是一樣的,因為材料的選取已經難免「主觀」,我對「主觀」的平衡有三點:一、博采眾家之言,不從作者的角度去給任何一位歷史人物作道德評判;二、兼顧口述和發表的文字,呈現政治帶來的情感激蕩;三、盡量搜集每個受訪者的照片,讓讀者「看見」他們不同時期的精神狀態和風貌風采,以便對每個人的性情氣質,多一層直觀感受。這三點之目的,都是以我作為後輩的感受和認知,希望能把歷史傳遞給更多普通讀者,特別是比我更年輕的讀者。
我是因為拍紀錄片才接觸到五四之後的文學的,而我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就是聚焦胡風事件的《紅日風暴》。這部電影是上海導演彭小蓮邀我和她一起完成的,因此可以說我最初的動機僅僅是給朋友幫忙。我和我的同輩人是在文革出生,在文革之後成長起來的,不要說在 1955 年就被打倒的胡風,我們對文革至多也只有如碎片一樣的記憶。我有同窗好友看了《紅日風暴》之後說,這部紀錄片把原來他們零散聽到和讀到的人名、概念、政治語彙,透過一個個人視點串聯起來了。在這部 138 分鐘的影片的過程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政治運動的影像和親歷者們的生動講述,能夠把觀眾帶入歷史現場;但是彭小蓮的旁白所表達的家庭的離散、成長的夢魘,才真正令這部作品有別於「客觀」的、BBC式的紀錄片。下面的文字,既是回憶、也是備忘;既是對我為什麼會寫這本書的一個總結,也是對我寫書過程中受到的影響的一個歸納。
自由養成的頭腦
我早年記憶中第一件歷史大事,是毛澤東去世。剛上小學沒幾天,有天早上,和同學們排著隊站在去往學校的馬路邊。等了很久,我其實不知道在等什麼,直到奏著哀樂、掛著毛主席遺像的「靈車」開過。那天下雨,但老師不許我們戴草帽、打傘、穿雨衣,覺得那是對偉大領袖的不敬。我媽媽用塑膠袋剪成一個「背心」,套在我的白襯衣下面,叮囑我不能告訴其他人。第二天很多小朋友都病了,我卻無恙。學校裏掛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像,後來華主席的像拿掉了。三年級開始學英語,我才漸漸知道,不是全世界人民都像外國譯製片中那樣,說著洋腔洋調的中文。小學快畢業,我才知道我小姨和姨父分別是西安外語學院的西班牙語、法語教授,而我舅舅楊德友,雖然在山西大學裏教英文,但是他懂七國外語,可以互譯。80年代起,與世界隔絕很久的中國大陸,有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潮發表,我們家的三位教授也翻譯了不少著作;我看到他們爬格子的辛苦,還曾經立志長大不做翻譯。但是他們不用坐班、有寒暑假的生活,給了我啟發,我在16歲就給自己手寫了一張名片,表明「志向」:「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系魏時煜博士」。名片我媽媽至今保留。
童年時沒有兒童讀物,認足了三四千字,在小學畢業的暑假看完了四大名著,只喜歡《紅樓夢》一部,後來每年一遍,又讀了十幾遍。因為媽媽的書架是按照世界文學史買書的,外國經典倒是讀了不少,我和妹妹還夢想過做勃朗特姐妹。80年代,魯迅、老舍、茅盾、巴金、曹禺的作品都再次被搬上銀幕;家裏訂的《收穫》、《當代》、《小說月報》上面,有很多「傷痕文學」,寫的都是物質貧乏年代,上山下鄉的青年們的故事。同時,社會上最響亮的口號是「走向世界」,連我們師大附中的童聲合唱隊,都要向獲得三連冠的女排姑娘們學習,後來在西安的校際比賽中獲得三連冠。轉眼到了高中要分文理科,父母不贊成我讀文科,大學只好讀了科技英語,竟然完全沒讀過現當代文學,印像深的課文只有莊子的《逍遙游》。教大學語文的老師對我說:「你不出國就完了。」大一時我已經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錄取,不過那時中國父母還供不起一個留學生,於是我大學畢業之後才出國留學。1992 年第一次坐飛機就去了渥太華,到卡爾頓大學讀比較文學。一位從東北來的學姊正在寫論文,題目是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她的理論框架是女性主義;還有一位學兄從北京來,不論哪一課的研究報告題目都是魯迅。我當時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到外國做中國文學,因為我只想學習西方文論。我從小念書基本只是班上中上,出了國卻幾乎功課全A,倒不是因為我英文有多麼漂亮,而是因為我有自覺、也有能力表達自己的觀點。同學們寫文學作品的報告主要是分析情節、人物,我認為這樣的分析生活閱歷豐富的教授們會覺得很幼稚;秉承工程師父母的邏輯思維的我,得A靠的是分析故事的「結構」、比較不同理論的核心概念,以及跳出慣常的思維框架。
找到了表達形式
在一年八個月都會下雪、卻常常陽光普照的埃德蒙頓,我愛上了電影,並轉讀電影學博士。我靠直覺和常識行事,老師們都很開放,沒有誰要來影響我的思維,或有意帶我進入到某個領域的深層。2003 年我在香港任教之後,開始跟隨彭小蓮拍攝胡風紀錄片,同時又跟司徒兆敦教授學習了紀錄片拍攝;現在想來,這兩位可能是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老師,因為他們引領我找到了迄今為止我最有力的表達形式。司徒老師 2003 和2005年兩次來到我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學教紀錄片,我配合他教學同時,學習了各種搜集「視聽證據」的方法。古人說:「耳聽是虛、眼見為實,」但是紀錄片的最高境界,則是在聲畫同步和聲畫分立中、在眾聲喧嘩和獨立思考中,呈現情感和思考。我的第一個紀錄片習作拍的就是司徒老師,他曾在文革中坐牢五年,多少受到父親司徒慧敏的牽連。司徒老師熱愛電影、為人誠懇,我在最初的拍攝中對他的記憶沒有懷疑,直到他自己開始在我的攝影機前糾正記憶的偏差。司徒老師說,因為記憶不可靠,所以我們需要紀錄片。巧的是,1978 至1982 年在小蓮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期間,司徒是小蓮的班主任。在履行攝影和錄音的職責的同時,我變成了一個擅長傾聽的人;通過傾聽和對話,我理順了很多對歷史的觀念,並給我的學術訓練找到一個創意出口。
在胡風紀錄片六年的拍攝、剪接過程中,我認識了五四之後中國最為開放的一個時代,認識了數十位既有激情又很率性的詩人、作家,他們大都是魯迅的追隨者。通過和他們的對話,我又重新認識了魯迅、認識了革命、認識了知識分子。從拍紀錄片起,我和很多人建立了非常特別的聯繫,在傾聽人生故事的過程中,獲得了很多師友。小蓮對於五六十年代可怖的記憶,讓我感受到政治可以給家庭帶來的災難;而對於這個災難的理解,我又通過後來接觸到的二十多個胡風分子的家庭得以深入。我單純給小蓮幫忙的動機,可以說在第一次拍攝之後就改變了,因為我首次拍攝的對像,是幽默、博學、睿智的賈植芳。他講故事的戲謔語氣和對歷史現場的幽默描繪,和我從傷痕文學中讀到的太不同了,他比很多後輩知識分子都更開放、豁達、可親,卻不自憐、不自戀。回頭去看,像李輝、周燕芬、王麗麗、路莘、張業松這些後輩學者,從胡風或七月派開始,進入開始各自的研究之路,和胡風友人這個群體的人格魅力有很大關係。因為拍攝的關係,我會坐在鏡頭旁,要求對話者看著我講故事;後來有人問,人家怎麼能和你如此暢所欲言,我想因為真誠是看得見、感受得到的!
找到「民主」的入口
人們對於「民主」這個字眼,一般都有寬而泛的理解,但要深入思索,就需要一個切實的入口。對於我在香港的學生而言,這幾年的社會動蕩,讓他們紛紛進入到這個原本並不熟悉的領域。我父親讀大學的時候,經歷了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他是讀地質的,但是同學中仍有文采飛揚、善於表達者,在運動中被送去青海;二十年後從青海回京,反因不能適應平原氣候而早世。父親是福州人,祖輩有中國最早留法學造船的魏瀚(1851–1929),還有幾位出洋留學的外交官。除了讓我遠離文藝,父親一直希望我和妹妹出國留學,我們也都獲得了博士學位。我從小愛文學,但遠離政治,即便在周圍同學們都罷課、絕食時,我也只輕輕地說,「你們這麼做也改變不了貪污腐敗。」到香港後看到許鞍華導演的九七紀錄片《去日苦多》,發現她大學時也不關心政治,1967 年她如常去期末考試,老師宣佈外面已經戒嚴,她才知道同學們的行動升級到「暴動」。70年代末她導演生涯伊始,就有「越南船民三部曲」,成為眾人心中的「政治導演」。機緣巧合中,我拍攝的首部紀錄片竟是《紅日風暴》,是關乎「20世紀中國的政治與精神事件」(林賢治語),也證明不論我說自己多麼不關心政治;但是用生命中十多年的時間追尋一段歷史,卻是當初沒有想到的。整個過程中推動我的,除了基本的民主意識,主要還是對於人性和命運的探尋。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剛開始就胡風事件查找資料時,搜索《人民日報》從 1948 年起的數據庫,看到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艾青、何其芳、劉白羽等眾多被收入過我的中學課本的著名作家,還有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甚至橋梁專家茅以升、著名婦產科醫生林巧稚等人批判胡風的文章,真是有些匪夷所思。1955 年之後,胡風等人的名字,顯然有計劃地被從文壇、歷史中抹去了;50年後,一無所知的我,看到那麼多我從中學課本中認識的文學家,批判一個我從來沒聽說過的評論家,我感到的不只是驚訝,簡直是震撼。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文學家們大都與胡風相熟,思想上原本並沒有太大的分歧。然而到了運動中,私人情感都要讓位給政治立場,黨員們接受任務寫批判文章,很多人被迫公開和他劃清界線。很多人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寫批判文章的情勢,我能夠理解和想像,但我還是忍不住去檢視每個人抗壓的程度,想探究每個人在捍衛真理時,付出了多少代價。於是,沒有寫過批判胡風文章的賈植芳、蕭軍,在兩千人面前替胡風辯護的呂熒,敢於告訴審訊員「真相」的詩人阿壠,伴囚二十多年的胡風夫人梅志,在監獄裏自學了德文的詩人綠原,為避免整人而自定右派的曾彥修,還有許多為胡風鳴不平而被劃右派的大學生,都在我心中變得高大了……
拍攝梅志時,她說起第一次見到魯迅,是在一個木刻展上,她默默地跟在先生身後,隨著先生的腳步前移,一幅一幅地看木刻作品。她後來常常跟胡風一起去看望魯迅,但最初的記憶仍舊清晰如昨。在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我特別喜歡蕭紅的散文〈回憶魯迅先生〉和聶紺弩的長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蕭紅的文字,看似碎片式的日常描述,卻把我們心目中原本遙遠的魯迅,像電影鏡頭一樣,中景、近景、特寫,展示在我們面前。而聶紺弩的文字,則有效地帶我們回到 1936 年10月那萬人送葬的現場,讓我彷彿聽到當時青年們對先生的呼喊:
我們是一條悠長的行列—
饑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那走在一切人前頭的背影倒了!
……
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個—
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第一個有自己底思想的人民,
第一個冒著風吹雨打和暗夜底一切,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這第一個人民倒了!
一個人民倒了!
我讀胡風、蕭紅、蕭軍、聶紺弩、馮雪峰等人在先生去世之後的文字,看到他們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以自己的生命延續魯迅的生命:魯迅是他們心中高大的背影,永遠的引領。賈植芳先生曾對胡風說:「『老先生』懂政治,我們不懂,」勸胡風不要上書。「老先生」指魯迅,而我們訪問過的人,幾乎每家都有一整套《魯迅全集》。2009 年初我到滬出差,和小蓮一起看望住在醫院的賈植芳先生,他把新書《歷史背影》簽名送我,而書中他回憶了一生遇到的奇人奇事。賈先生去世時,我看著電腦中,他舉著一支煙,笑眯眯地在說笑話,我沒有感到悲痛,因為潛意識根本不相信他去世了。
我讀胡風案中人的故事時,感動於友人之間的誠信和深情,感動於他們受難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仍然選擇一起守護真理。80年代初,曾經像農民一樣健壯的胡風,曾經以旺盛的熱力支撐起半個文壇的胡風,在出獄後精神分裂了。他曾經培育過的青年作家們,卻在花甲之年煥發新的創作生命。寫這本書時,我眼前有魯迅高大的背影,也有一群追隨魯迅的高大背影,雖然很多人已經遠去,但是沒有一個在我心中倒下。
眾聲喧嘩的歷史
在研習西方文論時,我非常喜歡一個理論概念叫複音(Polyphony)。它來自於巴赫金,是講小說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不同人物的聲音,包括帶有各自的社會階層、性別、教育所導致的雜和言語,或曰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共同參與敍事。這個概念在音樂中的實現形式,是交響;在小說之中,要求作者打破不論是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絕對權威,讓每一個聲音都能夠自主。這個概念,與胡風文論中的兩個關鍵詞—現實主義和主觀戰鬥精神,有相通之處;但是強調一種更多元的眾聲對話,甚至可以說接近真正意義上「百家爭鳴」的概念。因為「百家爭鳴」在中國歷史上含義太多,我還是用「眾聲喧嘩」,也因為喧嘩的目的未必是爭鳴。
結合到歷史研究中,我覺得「眾聲喧嘩」的實現,在於要同時重視文脈與人脈是很重要的:文脈是公開的,對公眾開放相同的「權限」;人脈卻並非公開,但卻主導了很多具體事件的發生。我接觸到的歷史研究者中,大部分人的職業是教授或編輯,善於搜索、處理、分析文獻,也有工作帶來的縱向和橫向的人脈。他們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朱正、錢理群、林賢治三位先生。朱正先生記憶力強大,重視材料和人脈研究,不急於說服讀者,善於用細節說話;他提示我要注意考證歷史背景。錢理群注重文脈、自覺守護自己的「獨立」;他提示我們,歷史不能由受害者來寫,不要以道德評判來作為歷史書寫的目的。深入研究過胡風和王實味的林賢治,從文字和為人中看人的品格,敦促我在研究中注重對像的人性和生命。這三位都沒有特別用主觀、客觀的字眼,但是他們的深度和廣度相輔相成。
我和小蓮遍訪胡風分子之後,完成了《紅日風暴》。我接著又想進一步了解共產黨文藝整風,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起源,於是又訪問了一些在延安經受了整風洗禮的人,並完成了《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和紀錄片《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我在《王實味》書中所做的嘗試,是希望把口述、書寫、圖片、思考都納入同一個文本,以生動、易讀的文字,呈現出王實味和他的時代;心中希望如果有人翻開這本書,可以基本讀懂延安。對於王實味的理論基礎,對於與他論爭的黨內理論家們的哲學概念,我雖有研究但無意著墨太多。這本書讓我收穫的驚喜之一,是章詒和老師對我說:「我是看了你這本書才讀懂了延安。」看到我的驚訝,章老師說:「我們是民主黨派的!」事實上章老師的書我是凡出必買,而且全家傳閱,我不敢奢望能獲得她那麼多的讀者,但是的確是把書寫給普通的,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因此她的評語對我震動和鼓舞都很大:「我們更需要這樣普通人也可以讀的歷史。」
我雖然秉承同樣的態度來書寫胡風,但是這一次的挑戰不同。寫王實味時,材料稀缺,要考古、要追問;寫胡風時,材料龐雜,要精簡、要理順。84 位受訪者的口述、300 多張從各個家庭相簿中掃描的圖片,幾千萬字的文獻,我只能完成幾個人物的生命線索。但是我希望通過本書中所呈現的人脈,讀者能夠延伸閱讀。事實上,幾乎所有受訪者,若干年來都在不停地閱讀和思考,在我拍片和寫書的十多年中,他們每個人的思想都在深入。比如把自己劃成右派的曾彥修先生,文革之後又創辦了《南方日報》,他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別處不能出版的重要書籍。2015年他去世之後,我看到他與何方先生的幾封通信,驚異於他對於延安、對於共產黨的認識的不斷深入。
記得到加拿大時,上文學理論第一課,一位智利來的教授就說,「客觀是廢話!」對我來說,做這本書和做紀錄片是一樣的,因為材料的選取已經難免「主觀」,我對「主觀」的平衡有三點:一、博采眾家之言,不從作者的角度去給任何一位歷史人物作道德評判;二、兼顧口述和發表的文字,呈現政治帶來的情感激蕩;三、盡量搜集每個受訪者的照片,讓讀者「看見」他們不同時期的精神狀態和風貌風采,以便對每個人的性情氣質,多一層直觀感受。這三點之目的,都是以我作為後輩的感受和認知,希望能把歷史傳遞給更多普通讀者,特別是比我更年輕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