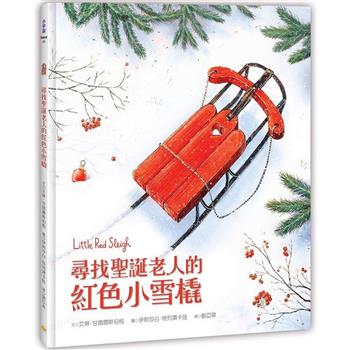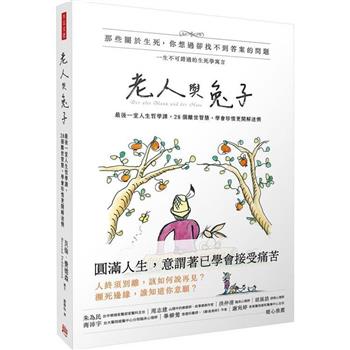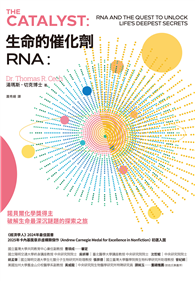兩甲子前,中國戰敗於日本,儒家士大夫遂尋求全面制度變革,行之數千年的堯舜周孔治理之道被棄如敝屣。此後百年,雖有仁人志士守護道統,復興儒學,唯多局限於精神、道德、文化領域,以為儒家未曾塑造、維護良好秩序,更不可能行於當世。
本書作者卻力排眾議,為當前中國之制度變革提出「儒家憲政」方案。作者認為,一國憲政當扎根於自身文明,儒家在中國文明中具有特殊地位,這决定了中國憲政必為儒家憲政。
本書上卷「義理」,參考中國數千年的治理實踐,疏解儒家經典,闡明常在常新的中國治理之道;下卷「更化」,探討當下中國通往儒家憲政之路。作者並不準備提出整全的憲制方案,反而保持充分開放的心態。作者認為,唯有歸宗道統,中國之政治秩序才可趨於良善、穩定,但「人能弘道」,當世君子不能不因時而立制,為此不能不廣泛參照西方的法度。
故「儒家憲政」既不同於自由民主憲政或社會主義憲政,亦有別於「儒教憲政」。作者以為,前者無視中國文明傳統、憑空立憲,而失之於「不及」;後者「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而失之於「過」。儒家憲政中道而行,或可供有志於治國平天下的賢明君子採擇一二。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儒家憲政論的圖書 |
 |
儒家憲政論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 出版日期:2016-07-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8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全彩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60 |
社會人文 |
$ 616 |
社會人文 |
$ 702 |
政治 |
$ 725 |
中文書 |
$ 725 |
中國哲學 |
$ 741 |
政體/政治制度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儒家憲政論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姚中秋
筆名秋風,陝西蒲城人,弘道書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 曾致力於譯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普通法憲政主義,譯著十餘種 。 近年致力探究中國治理之道,闡發儒家義理,探索儒家復興並更化天下之道,著有 《 華夏治理秩序史 》 第一卷 《 天下 》 及第二卷 《 封建 》、《 儒家式現代秩序 》、《 國史綱目 》、《 治理秩序論 : 經義今詁 》等 。 2013 年夏創辦弘道書院,組織各種思想對話,拓展當代儒學研究之新議題,推動中國思想學術之儒家化 。
姚中秋
筆名秋風,陝西蒲城人,弘道書院院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 曾致力於譯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普通法憲政主義,譯著十餘種 。 近年致力探究中國治理之道,闡發儒家義理,探索儒家復興並更化天下之道,著有 《 華夏治理秩序史 》 第一卷 《 天下 》 及第二卷 《 封建 》、《 儒家式現代秩序 》、《 國史綱目 》、《 治理秩序論 : 經義今詁 》等 。 2013 年夏創辦弘道書院,組織各種思想對話,拓展當代儒學研究之新議題,推動中國思想學術之儒家化 。
目錄
上卷 義理
第一章、儒家憲政之形而上本源
一、敬天之確立
二、天不言
三、天文與人文
四、人文之治
五、結語
第二章、儒家憲政之根本原則:天下為公
一、公平: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二、公有: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三、公民:人皆為治理之主體
四、公論:言論自由
五、共和:君主制只是權宜之計
六、公治:選賢與能
七、公政:王道不偏,全民政府
八、公義:見義勇為,積極政府
九、公天下:和而不同的天下情懷
十、餘論
第三章、儒家憲政之義理與制度
一、周秦之變:國家權力統治及其困境
二、第二次立憲:從統治到治理
三、多中心治理之儒家義理
四、文化復興,治理重建
五、結語
第四章、儒家憲政之歷史大勢:第二次立憲
一、秦:錯失第二次立憲
二、董仲舒—漢武帝更化:第二次立憲之典範
三、第二次立憲之周期性出現
四、歐美之第二次立憲現象
五、第二次立憲之基本模型
六、結語
下卷 更化
第五章、八二憲法與儒家憲政
一、《共同綱領》創立革命憲法範式
二、繼續革命的憲法精神及其困境
三、八二憲法之歷史文化條款
四、歷史文化條款之寫入與闡釋
五、憲法序言第一段與中國故事、文明復興
六、結語
第六章、通往儒家憲政:論憲法修訂
一、憲法須守護道統
二、憲法語言之中國性
三、憲法價值之中國性
四、憲制架構之中國性
五、結語
第七章、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一、作為秩序構建之道的通三統
二、儒家之作為中華性之本
三、儒家的憲政主義傳統
四、儒家的民生主義傳統
五、反復其道,天行也
第八章、儒家憲政論申說
一、何以只是儒家的憲政?
二、儒家憲政不是儒教憲政
三、儒家憲政無違政教分離原則
四、儒家何必憲政?
五、儒家憲政與心性儒學
六、何以是憲政,而非民主
七、義理:儒家之憲政理念
八、歷史:中國之憲政傳統
九、現實:憲政之中國形態
十、開放的儒家憲政規劃
十一、結語
第一章、儒家憲政之形而上本源
一、敬天之確立
二、天不言
三、天文與人文
四、人文之治
五、結語
第二章、儒家憲政之根本原則:天下為公
一、公平: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二、公有: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三、公民:人皆為治理之主體
四、公論:言論自由
五、共和:君主制只是權宜之計
六、公治:選賢與能
七、公政:王道不偏,全民政府
八、公義:見義勇為,積極政府
九、公天下:和而不同的天下情懷
十、餘論
第三章、儒家憲政之義理與制度
一、周秦之變:國家權力統治及其困境
二、第二次立憲:從統治到治理
三、多中心治理之儒家義理
四、文化復興,治理重建
五、結語
第四章、儒家憲政之歷史大勢:第二次立憲
一、秦:錯失第二次立憲
二、董仲舒—漢武帝更化:第二次立憲之典範
三、第二次立憲之周期性出現
四、歐美之第二次立憲現象
五、第二次立憲之基本模型
六、結語
下卷 更化
第五章、八二憲法與儒家憲政
一、《共同綱領》創立革命憲法範式
二、繼續革命的憲法精神及其困境
三、八二憲法之歷史文化條款
四、歷史文化條款之寫入與闡釋
五、憲法序言第一段與中國故事、文明復興
六、結語
第六章、通往儒家憲政:論憲法修訂
一、憲法須守護道統
二、憲法語言之中國性
三、憲法價值之中國性
四、憲制架構之中國性
五、結語
第七章、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一、作為秩序構建之道的通三統
二、儒家之作為中華性之本
三、儒家的憲政主義傳統
四、儒家的民生主義傳統
五、反復其道,天行也
第八章、儒家憲政論申說
一、何以只是儒家的憲政?
二、儒家憲政不是儒教憲政
三、儒家憲政無違政教分離原則
四、儒家何必憲政?
五、儒家憲政與心性儒學
六、何以是憲政,而非民主
七、義理:儒家之憲政理念
八、歷史:中國之憲政傳統
九、現實:憲政之中國形態
十、開放的儒家憲政規劃
十一、結語
序
序
止於儒家憲政的學思之路
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演進之最可能方向,且我相信,唯有依據儒家義理建立良好政制,中國之社會政治秩序才能保持長久穩定。 然而,當筆者提出儒家憲政論,學界、尤其是公共輿論界,批評之聲居多。對這些懷疑,我很少直接回應,而以之為動力,盡自己之心力,更為深入、細緻地思考,以求儒家憲政義理之完整和融貫。 本書算是近年來對儒家憲政之義理探索之總結;借此機會,也交代一下自己從思想上走入儒家憲政之路,或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之論說。
一、河殤一代
80 年代中期,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之所以主動選擇讀歷史專業,乃為弄清縈繞心頭的疑惑:中國何以至此貧窮、落後、混亂境況,又何以走出此種局面?故當時身在歷史系,卻有強烈現實關懷,尤其喜愛理論思考。由此難免在文化上成為激進分子。 此乃時代使然。這時代之弄潮兒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主宰思想文化界的「80年代知識分子」,其人生經歷普遍如此:生在紅旗下,長在毛主席的懷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又被迫「上山下鄉」;70年代,成為「批林批孔」的主力,大寫所謂理論文章;鄧小平復出,復得以上大學,所謂「老三屆」是也。這一代人可稱為「紅衞兵一代」。我上大學時,他們已畢業,並掀起文化思想之大潮,其基本傾向是激進反傳統。 他們之前的兩代人,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也持反傳統立場,但畢竟,幼年受過家庭、社區風俗之熏染,對傳統尚能手下留情;或者雖反傳統,身上仍可見傳統之遺韻。在這批 80 年代知識分子身上,傳統則蕩然無存,其對傳統之態度是激烈而粗暴的。可以說,中國思想學術與傳統的真正斷裂,最早發生在這代人身上,而風雲際會,他們主宰70年代末以來之中國思想文化界長達三十年之久。好在近年,他們終於到了退休年齡。 身在此環境中,血氣未定之青少年,自易受其影響,故當時認可「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之類高論,告別黃土文化、走向藍色海洋文明的吶喊,也聽之無疑。猶記得1988年在大學宿舍之活動室與同學觀看電視政論片《河殤》之激動心情。故我這代人大體可稱為「《河殤》一代」,精神成長時期完全籠罩在紅衞兵一代之下,「被激進」是不可逃避的,其文化傾向也基本上是激進反傳統;而因為閱歷不多,見識較少,比之紅衞兵一代,實際上更為膚淺。
二、錢穆先生
命中注定經歷一次轉變。考上研究生之後,查出患有慢性疾病,乃休學一年,回陝西老家農村養病。有此生命經歷,思想發生較大變化。故 1989年秋季學期返校之後,不再那麼激進了。 決定畢業研究方向時,選擇錢穆先生之歷史文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為此,在北京圖書館港台閱覽室研讀錢穆先生的著作。如今,二十多年過去,當年讀書景象,仍歷歷在目。當時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因為,錢穆先生提供了全然不同的中國歷史敍事:既不同於已令人生厭的官方歷史學,也不同於當時最為時髦的文化激進主義歷史敍事。當時,對錢穆先生所倡導的對自身文明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未必全然理解,但轉回自身文明歷史之思想種子已然種下。而今回首自己十幾年來的思想學術努力,其實大體在錢穆先生範圍之中:重視歷史,但重在求歷史之常道;此道在經中,故而同樣重視經。儒家憲政之論,即由經史參讀、互證,逐漸浮現、顯明。 近幾年,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從事通識教育、開設中國文明文化史課程之需,重讀先生《國史大綱》,又有很多收穫;為教學便利,乃以此書為本,而予以擴展豐富,作《國史綱目》(海南出版社,2013 年),從中國內部視角重述中國歷史;同時,重讀《政學私言》等先生論政之書,卻猛然發現,原來先生就是儒家憲政論者!故 2015 年先生誕辰兩甲子紀念日,乃以弘道書院名義,發起在常州大學召開學術研討會,專門討論錢穆先生之政治思想。而檢索一番之後發現,這是當年唯一紀念錢穆先生的會議。
三、哈耶克
90年代初畢業之後,因服務於公眾媒體,寫作時事評論,乃關注當時正在大陸興起之自由主義思潮。但經過錢穆先生之熏陶,已有保守心智,故當時即自我標榜為「古典自由主義」。於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人物中,最為偏愛出生於奧地利、活躍於英美學術界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世紀之交那幾年,曾投入相當精力譯介哈耶克思想,如翻譯《哈耶克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繁體字版,台北:康德出版社,2005;修訂再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並推動成立「華人哈耶克學會」,每年召開一次思想學術會議,討論哈耶克思想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其中在香港舉辦兩次,在台灣舉辦一次。 哈耶克當然是自由主義者,此為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肯定,哈耶克在經濟方面的論述甚至已成為不可懷疑之教條。不過,尊崇哈耶克教條之人士通常忽略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面:肯定傳統。在20世紀激進主義甚囂塵上之思想氣氛中,哈耶克哲學思考之主要貢獻在於堅定反對「理性至上主義(rationalism)」,在他看來,極權主義之哲學源頭正是理性至上主義。他提醒人們注意理性之限度,重視傳統之於自由之重要意義。據此,在美國,哈耶克被歸入「保守主義」譜系。 對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引發我深入中國傳統,從而有儒者之自覺。說起來,這樣的轉向有點可悲:身為中國人,卻不能不借西人思想為中介,返回自身思想文化傳統。當然,錯不在我,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自身的知識傳統斷裂,學校所教授者就是西學,自身思想文化傳統被取消,乃至於遭到批判。凡接受過較好教育的學人與各領域社會精英,在知識上都是非中國人。只有幸運者,因某種特殊機緣,才有可能轉回,大多數則處在扭曲的生存狀態:身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卻近乎本能地反感、排斥。我想,自己尚算幸運者,在激進反傳統幾乎是本能之文化政治大環境中,得以碰到哈耶克,最終返回中國。但現在想來,碰到哈耶克,也非偶然,而須感謝錢穆先生所埋下的心智之種子。 當然,正是我的回歸傳統,讓很多過往的思想同道斷定我背叛了自由主義。若自由主義以激進反傳統為其核心訴求,那我要說,經錢穆先生熏陶之後,我從來就不是此類自由主義。這類自由主義其實與其所反對的思想政治,比如毛澤東之「文化大革命」,共享相同之觀念:你說傳統是封建的、專制的、落後的,主張全盤西化,為此而主張摧毀傳統,毛氏文革不正做此事嗎?余英時先生說,文革的思想根源在新文化運動,確為不刊之論。正是由於哈耶克,讓我與此類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事實上,自研究哈耶克之後,我對現代中國之自由主義傳統多有批評,後來結集成書:《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
四、奧派經濟學與普通法
不過,我的學思並未停留於哈耶克: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心智總喜歡追根溯源,研究哈耶克的我希望了解哈耶克思想之源頭何在。對此,哈耶克本人倒是再三再四之說明其思想之源頭:於經濟學方面,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政治理論方面,在英國保守主義傳統、蘇格蘭道德哲學,以及英格蘭普通法傳統。 於是,首先做了幾年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工作,比如組織翻譯《奧地利學派譯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華人哈耶克學會也是重要的平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大陸影響逐漸擴大,自己也有一份功勞─以至於偏左的人士說,對於極端經濟自由主義教條在中國的傳播,你要負責任。不過,我自己又一次逃跑了:此類奧派經濟學,有時被稱為「國奧」,很快把某些思想、觀念教條化為不可懷疑的真理,大張旗鼓地宣傳。我向來厭惡這種「真理黨人」,乃退身而遠之。圈子裏紛紛說,我背叛了,其實,我只想靜靜。 在另一個線索上,我進入英國思想和制度傳統中。一度,喜歡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義,又研讀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之論說。浙江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蘇格蘭道德哲學傳統代表人物的著作,參加過其中若干次討論,雖然未作專門研究。 下功夫較多者為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重要源頭:英格蘭普通法傳統,尤其是1600年前後現代轉型過程中基於普通法傳統之法律與政治思想創新,其代表人物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曾動念頭翻譯其三卷本文集,並已翻譯出其中一部分,只是判例集充斥法律英語,翻譯難度太大,況且時間不敷,只好作罷。不過,圍繞着這一主題,翻譯過幾部相關著作,據此提出過「普通法憲政主義」概念,既是對英美憲政傳統之概括,也有意運用於中國。唯這方面思考始終不成體系,只是零散談論而已;高全喜教授在闡明其政治憲法學理論過程中反覆予以批評,但這個概念有人援用。 我的西學歷程到此也差不多結束,因為得到了深入理解儒家義理之鑰匙。
五、儒家憲政論的提出
孔子思想,可用「仁」、「禮」二字概括。仁之大義易明,禮之內涵不彰。古人謂三代皆行禮治,在儒家之社會治理體系,禮治也至關重要,五經中有《禮經》。然而,禮究竟是什麼?禮治究竟如何運作?古人知其然,現代人幾無生活經驗,不知其然,要麼迴避,要麼扭曲,比如批判、破壞禮教就是新文化運動之核心內容,今人也不斷拾此牙慧。 對普通法的研究,讓我得以理解三代之禮的性質及其運作機理。簡而言之,普通法就是禮,兩者都運作於封建制中,三代之禮治,即類似於英格蘭普通法下之法治。由此認識上的突破,得以理解三代歷史之關鍵;而洞悉三代禮治之機制,也就能理解儒家何以在禮治趨於瓦解的時代依然主張禮治;後世儒家也確實在新的制度環境下,盡可能重建禮治。 由此,自己對中國歷史形成一番全新認識,乃撰寫《華夏治理秩序史》,計劃寫作多卷本,首先出版了前兩卷:第一卷《天下》,敍述中國之誕生;第二卷《封建》(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探討封建制之架構及其運作機理,側重於疏解禮治之大義。由於此書規模龐大,一時半會兒無法完成,乃作《國史綱目》。這樣,歷史的研究暫告一段落。 正在此歷史研究階段,逐漸提出並論證儒家憲政論,由三部分論說組成: 第一部分,從義理上闡明儒家的社會治理構想有憲政之義,也即:論證儒家尊重個人自主,主張社會自治,致力於規範和約束國家權力。 但受反傳統之傳統和扭曲的歷史敍事之影響,人們難以相信這種說法,故有第二部分工作:論證歷史上儒家曾建立過憲政制度。龐大的歷史書寫計劃即為此而展開。 完成上述義理和歷史論證後,展開第三部分工作:論證儒家憲政可行於當世。歷史上儒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值得今日創制立法者參考,比如以教育為政制之基礎,選賢與能,由此形成士人政府。當然,儒家憲政也對西人發明之各種制度開放,只是反對全盤引入西方政制。 之所以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儒家憲政論,或許是因為自己畢竟出身歷史專業訓練,習慣從歷史看制度之流變;恐怕也是因為在上述三部分研究中,對制度之歷史性研究實屬關鍵:憲政有賴於有效制度之運作,僅有義理是不够的,唯有從歷史上證明儒家曾發明諸多制度能收今日所言憲政之效,儒家憲政論才能成立。按孔子所指示的創制立法之道,今日儒家憲政設計各項制度,恐怕必須參照歷史上的各種有效制度,予以組合、發展─雖然,有不少制度,「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也即,依儒家義理,參照西方制度,自行創制。
六、儒家憲政論的深化
上述歷史研究旨在為儒家、為中國歷史、為中國文化正名。有了這一歷史確證之後,我主要轉入經學領域,致力於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識解讀經典。過去幾年,先後出版《治理秩序論:經義今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等著作。目前完成《論語大義淺說》、《堯舜之道:尚書帝典、皋陶謨大義淺說》等著作,2016年陸續出版。接下來還會繼續解讀經典。 由此,對聖賢開啟之成人之道、合天人之大義有所體認,對中國治理之道的理解更為深入、細緻,並將儒家憲政置於天人之際進行思考。由此確信,儒家憲政之精神基礎是敬天,治理機制是人文之治,宗旨是《周易》〈乾卦彖辭〉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各種社會治理主體在多個維度上創造合適條件,讓每人生命向上成長,彼此間形成良好關係。 天人之際的儒家憲政,不似中國以西諸民族兩三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做法,把社會治理奠基於神教信仰;也不似現代西人那樣,以政治神話如「人民主權」為憲政之預設。儒家憲政相信,敬天之人可「明明德」,自明其德,從而可「里仁」、「克己復禮」。由此,人可組織起來,自我治理,「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故儒家憲政之起點是平實的,而又有向上提撕之力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比華人世界目前所行之各種體制更為優越,比西人目前所行之主流體制更為優越。 凡此種種,或可視為圍繞儒家憲政論之第四部分論說:作為政制的儒家憲政置於整全的天人秩序中,以見其直抵生命本源之獨特意義。這是儒家憲政有別於、或者超越於當下中國種種憲政論說之處。那些基於外來思想和制度所構建的憲政論說是純政制的,無法照顧身在中國之共同體成員的安身立命,如《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貫通無礙。唯有儒家憲政,徹上徹下,整全而圓融。 基於這一點,我對儒家憲政之前景充滿信心。儒家憲政也是走向「和而不同」的天下秩序之較優政制方案。
七、人能弘道
重建儒家憲政之最大障礙,是歷史終結論的思維方式。震懾於西方之富強,現代中國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精英,幾乎都是歷史終結論者:中國文明已死,歷史正在終結於歐美現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盤自我改造而歐美化。今日諸多憲政論說均有這一傾向,儘管其所嚮往之歷史終點,各有不同,但都在西方。 歷史終結論造成了可怕的心智封閉。歷史終結論者總是呼籲人們開放。也許,這種呼籲在20世紀初是有益的,但晚近以來,此所謂開放日益成為自我封閉,因為他們所謂開放,只是照抄,完全放棄思考之重負,不斷重複西來之咒語,坐等良好秩序之神跡降臨;此神跡對文化無知之中國精英群體有很大吸引力。 儒家憲政論者曾花費很多精力自我辯解,試圖喚醒處在現代神話蒙昧狀態中的這些可憐人。還好,歷史終結論正在被誰也未曾預料到之歷史進程所終結。21 世紀以來,諸多巨變讓歷史終結論神話走向瓦解,連福山也改了口風。儒家終於得以喘了口氣,在大陸快速復興,構建儒家憲政之可能已隱約顯現。儒家憲政論或許將進入第二個階段:一如今日之儒家整體,將不再是批判、反駁、辯解,而是構建、推進和踐行。 故本書只是儒家憲政論第一階段之成果。其論證是初步的,還須細化、深化、調整;最重要的是,對儒家憲政論者,前面還有極為廣闊的理論空間有待拓墾、耕種。筆者在此願意聲明:在儒家憲政論中,無所謂政治的真理;儒家憲政論者不相信人可設計出完備的、從而終結歷史之政制;儒家憲政論者只是致力於「推明治道」,也即確定關於優良治理之大方向和若干基本原則。此義理體系類似於持續成長的生命體,它長成什麼樣子,取決於人作出多少努力。子曰「人能弘道」,以此自勉。
八、關於本書
立憲者,國之大事也。本書收錄筆者近年來圍繞儒家憲政所撰寫之主要論說,多已公開發表,具體發表媒體如下: 第一章,原以〈中國治道探源:敬天與人文之治〉為題刊《人大法律評論》,2015 年第2 輯,總第19輯(2015)。 第三章,原以〈治理之儒家義理、中國傳統及其重建〉為題刊俞可平主編:《中國治理評論》,第七輯(2015)。 第五章,原以〈從革命到文明:八二憲法序言第一段大義疏解〉為題刊《法學評論》,第 2 期(2015)。 第六章,原以〈論憲法的中國性〉刊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6 月號(2012)。 第七章,其删節版刊《開放時代》,6月號(2011)。 第八章,下篇刊《天府新論》,第 3 期(2013)。 後序,原刊《中國法律評論》,第 2 期(2016)。 以上諸篇收入本書,其主要論說一仍其舊。為保持全書脈絡貫通,增補若干字句,予以串聯,有些篇章略有增補。為使全書結構完整,另撰寫兩章,即第二章和第四章。以上八章,編為上、下兩卷: 上卷「義理」,疏解儒家經典關於社會治理之大義,參照歷史經驗,以揭明儒家社會治理之道,也即儒家憲政之初步義理。第四章特別指出,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之常道,但在漫長歷史中多有反覆,此為中國歷史之顯著特徵;過去百年中國人破繭而出之政制嘗試,不過是反覆出現的歧出之最新一次,而今日中國正處在又一次回歸常道的過程中。 由此轉入下卷「更化」,探討當下中國通往儒家憲政之路。自以為第五章較為重要:現行中國憲法〈序言〉第一段構建「文明中國」敍事,確立「歷史」為基本的憲法和政治方法論,確立「文化」為國家塑造和維護良好秩序之根本。本段統攝憲法〈序言〉,進而統攝整部憲法,赫然有回歸文明中國之大義在。也就是說,即便激進革命的領導者,也在中國文化籠罩下,尤其是鑒於「文化大革命」之慘痛教訓,而於自覺不自覺之間回歸中國文化,並將歷史、文化寫入憲法,從而打開本書所討論的「第二次立憲」之大門。此義甚為深遠,筆者已就此展開研究。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教授邀約,此書得以面世。期待學界批評指正。創制立法者若能參考其中一二,幸莫大焉。
歲次乙未,時在仲冬,蒲城姚中秋自序於北京陋室。
止於儒家憲政的學思之路
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演進之最可能方向,且我相信,唯有依據儒家義理建立良好政制,中國之社會政治秩序才能保持長久穩定。 然而,當筆者提出儒家憲政論,學界、尤其是公共輿論界,批評之聲居多。對這些懷疑,我很少直接回應,而以之為動力,盡自己之心力,更為深入、細緻地思考,以求儒家憲政義理之完整和融貫。 本書算是近年來對儒家憲政之義理探索之總結;借此機會,也交代一下自己從思想上走入儒家憲政之路,或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之論說。
一、河殤一代
80 年代中期,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之所以主動選擇讀歷史專業,乃為弄清縈繞心頭的疑惑:中國何以至此貧窮、落後、混亂境況,又何以走出此種局面?故當時身在歷史系,卻有強烈現實關懷,尤其喜愛理論思考。由此難免在文化上成為激進分子。 此乃時代使然。這時代之弄潮兒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主宰思想文化界的「80年代知識分子」,其人生經歷普遍如此:生在紅旗下,長在毛主席的懷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又被迫「上山下鄉」;70年代,成為「批林批孔」的主力,大寫所謂理論文章;鄧小平復出,復得以上大學,所謂「老三屆」是也。這一代人可稱為「紅衞兵一代」。我上大學時,他們已畢業,並掀起文化思想之大潮,其基本傾向是激進反傳統。 他們之前的兩代人,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也持反傳統立場,但畢竟,幼年受過家庭、社區風俗之熏染,對傳統尚能手下留情;或者雖反傳統,身上仍可見傳統之遺韻。在這批 80 年代知識分子身上,傳統則蕩然無存,其對傳統之態度是激烈而粗暴的。可以說,中國思想學術與傳統的真正斷裂,最早發生在這代人身上,而風雲際會,他們主宰70年代末以來之中國思想文化界長達三十年之久。好在近年,他們終於到了退休年齡。 身在此環境中,血氣未定之青少年,自易受其影響,故當時認可「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之類高論,告別黃土文化、走向藍色海洋文明的吶喊,也聽之無疑。猶記得1988年在大學宿舍之活動室與同學觀看電視政論片《河殤》之激動心情。故我這代人大體可稱為「《河殤》一代」,精神成長時期完全籠罩在紅衞兵一代之下,「被激進」是不可逃避的,其文化傾向也基本上是激進反傳統;而因為閱歷不多,見識較少,比之紅衞兵一代,實際上更為膚淺。
二、錢穆先生
命中注定經歷一次轉變。考上研究生之後,查出患有慢性疾病,乃休學一年,回陝西老家農村養病。有此生命經歷,思想發生較大變化。故 1989年秋季學期返校之後,不再那麼激進了。 決定畢業研究方向時,選擇錢穆先生之歷史文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為此,在北京圖書館港台閱覽室研讀錢穆先生的著作。如今,二十多年過去,當年讀書景象,仍歷歷在目。當時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因為,錢穆先生提供了全然不同的中國歷史敍事:既不同於已令人生厭的官方歷史學,也不同於當時最為時髦的文化激進主義歷史敍事。當時,對錢穆先生所倡導的對自身文明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未必全然理解,但轉回自身文明歷史之思想種子已然種下。而今回首自己十幾年來的思想學術努力,其實大體在錢穆先生範圍之中:重視歷史,但重在求歷史之常道;此道在經中,故而同樣重視經。儒家憲政之論,即由經史參讀、互證,逐漸浮現、顯明。 近幾年,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從事通識教育、開設中國文明文化史課程之需,重讀先生《國史大綱》,又有很多收穫;為教學便利,乃以此書為本,而予以擴展豐富,作《國史綱目》(海南出版社,2013 年),從中國內部視角重述中國歷史;同時,重讀《政學私言》等先生論政之書,卻猛然發現,原來先生就是儒家憲政論者!故 2015 年先生誕辰兩甲子紀念日,乃以弘道書院名義,發起在常州大學召開學術研討會,專門討論錢穆先生之政治思想。而檢索一番之後發現,這是當年唯一紀念錢穆先生的會議。
三、哈耶克
90年代初畢業之後,因服務於公眾媒體,寫作時事評論,乃關注當時正在大陸興起之自由主義思潮。但經過錢穆先生之熏陶,已有保守心智,故當時即自我標榜為「古典自由主義」。於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人物中,最為偏愛出生於奧地利、活躍於英美學術界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世紀之交那幾年,曾投入相當精力譯介哈耶克思想,如翻譯《哈耶克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繁體字版,台北:康德出版社,2005;修訂再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並推動成立「華人哈耶克學會」,每年召開一次思想學術會議,討論哈耶克思想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其中在香港舉辦兩次,在台灣舉辦一次。 哈耶克當然是自由主義者,此為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肯定,哈耶克在經濟方面的論述甚至已成為不可懷疑之教條。不過,尊崇哈耶克教條之人士通常忽略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面:肯定傳統。在20世紀激進主義甚囂塵上之思想氣氛中,哈耶克哲學思考之主要貢獻在於堅定反對「理性至上主義(rationalism)」,在他看來,極權主義之哲學源頭正是理性至上主義。他提醒人們注意理性之限度,重視傳統之於自由之重要意義。據此,在美國,哈耶克被歸入「保守主義」譜系。 對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引發我深入中國傳統,從而有儒者之自覺。說起來,這樣的轉向有點可悲:身為中國人,卻不能不借西人思想為中介,返回自身思想文化傳統。當然,錯不在我,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自身的知識傳統斷裂,學校所教授者就是西學,自身思想文化傳統被取消,乃至於遭到批判。凡接受過較好教育的學人與各領域社會精英,在知識上都是非中國人。只有幸運者,因某種特殊機緣,才有可能轉回,大多數則處在扭曲的生存狀態:身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卻近乎本能地反感、排斥。我想,自己尚算幸運者,在激進反傳統幾乎是本能之文化政治大環境中,得以碰到哈耶克,最終返回中國。但現在想來,碰到哈耶克,也非偶然,而須感謝錢穆先生所埋下的心智之種子。 當然,正是我的回歸傳統,讓很多過往的思想同道斷定我背叛了自由主義。若自由主義以激進反傳統為其核心訴求,那我要說,經錢穆先生熏陶之後,我從來就不是此類自由主義。這類自由主義其實與其所反對的思想政治,比如毛澤東之「文化大革命」,共享相同之觀念:你說傳統是封建的、專制的、落後的,主張全盤西化,為此而主張摧毀傳統,毛氏文革不正做此事嗎?余英時先生說,文革的思想根源在新文化運動,確為不刊之論。正是由於哈耶克,讓我與此類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事實上,自研究哈耶克之後,我對現代中國之自由主義傳統多有批評,後來結集成書:《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
四、奧派經濟學與普通法
不過,我的學思並未停留於哈耶克: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心智總喜歡追根溯源,研究哈耶克的我希望了解哈耶克思想之源頭何在。對此,哈耶克本人倒是再三再四之說明其思想之源頭:於經濟學方面,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政治理論方面,在英國保守主義傳統、蘇格蘭道德哲學,以及英格蘭普通法傳統。 於是,首先做了幾年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工作,比如組織翻譯《奧地利學派譯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華人哈耶克學會也是重要的平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大陸影響逐漸擴大,自己也有一份功勞─以至於偏左的人士說,對於極端經濟自由主義教條在中國的傳播,你要負責任。不過,我自己又一次逃跑了:此類奧派經濟學,有時被稱為「國奧」,很快把某些思想、觀念教條化為不可懷疑的真理,大張旗鼓地宣傳。我向來厭惡這種「真理黨人」,乃退身而遠之。圈子裏紛紛說,我背叛了,其實,我只想靜靜。 在另一個線索上,我進入英國思想和制度傳統中。一度,喜歡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義,又研讀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之論說。浙江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蘇格蘭道德哲學傳統代表人物的著作,參加過其中若干次討論,雖然未作專門研究。 下功夫較多者為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重要源頭:英格蘭普通法傳統,尤其是1600年前後現代轉型過程中基於普通法傳統之法律與政治思想創新,其代表人物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曾動念頭翻譯其三卷本文集,並已翻譯出其中一部分,只是判例集充斥法律英語,翻譯難度太大,況且時間不敷,只好作罷。不過,圍繞着這一主題,翻譯過幾部相關著作,據此提出過「普通法憲政主義」概念,既是對英美憲政傳統之概括,也有意運用於中國。唯這方面思考始終不成體系,只是零散談論而已;高全喜教授在闡明其政治憲法學理論過程中反覆予以批評,但這個概念有人援用。 我的西學歷程到此也差不多結束,因為得到了深入理解儒家義理之鑰匙。
五、儒家憲政論的提出
孔子思想,可用「仁」、「禮」二字概括。仁之大義易明,禮之內涵不彰。古人謂三代皆行禮治,在儒家之社會治理體系,禮治也至關重要,五經中有《禮經》。然而,禮究竟是什麼?禮治究竟如何運作?古人知其然,現代人幾無生活經驗,不知其然,要麼迴避,要麼扭曲,比如批判、破壞禮教就是新文化運動之核心內容,今人也不斷拾此牙慧。 對普通法的研究,讓我得以理解三代之禮的性質及其運作機理。簡而言之,普通法就是禮,兩者都運作於封建制中,三代之禮治,即類似於英格蘭普通法下之法治。由此認識上的突破,得以理解三代歷史之關鍵;而洞悉三代禮治之機制,也就能理解儒家何以在禮治趨於瓦解的時代依然主張禮治;後世儒家也確實在新的制度環境下,盡可能重建禮治。 由此,自己對中國歷史形成一番全新認識,乃撰寫《華夏治理秩序史》,計劃寫作多卷本,首先出版了前兩卷:第一卷《天下》,敍述中國之誕生;第二卷《封建》(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探討封建制之架構及其運作機理,側重於疏解禮治之大義。由於此書規模龐大,一時半會兒無法完成,乃作《國史綱目》。這樣,歷史的研究暫告一段落。 正在此歷史研究階段,逐漸提出並論證儒家憲政論,由三部分論說組成: 第一部分,從義理上闡明儒家的社會治理構想有憲政之義,也即:論證儒家尊重個人自主,主張社會自治,致力於規範和約束國家權力。 但受反傳統之傳統和扭曲的歷史敍事之影響,人們難以相信這種說法,故有第二部分工作:論證歷史上儒家曾建立過憲政制度。龐大的歷史書寫計劃即為此而展開。 完成上述義理和歷史論證後,展開第三部分工作:論證儒家憲政可行於當世。歷史上儒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值得今日創制立法者參考,比如以教育為政制之基礎,選賢與能,由此形成士人政府。當然,儒家憲政也對西人發明之各種制度開放,只是反對全盤引入西方政制。 之所以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儒家憲政論,或許是因為自己畢竟出身歷史專業訓練,習慣從歷史看制度之流變;恐怕也是因為在上述三部分研究中,對制度之歷史性研究實屬關鍵:憲政有賴於有效制度之運作,僅有義理是不够的,唯有從歷史上證明儒家曾發明諸多制度能收今日所言憲政之效,儒家憲政論才能成立。按孔子所指示的創制立法之道,今日儒家憲政設計各項制度,恐怕必須參照歷史上的各種有效制度,予以組合、發展─雖然,有不少制度,「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也即,依儒家義理,參照西方制度,自行創制。
六、儒家憲政論的深化
上述歷史研究旨在為儒家、為中國歷史、為中國文化正名。有了這一歷史確證之後,我主要轉入經學領域,致力於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識解讀經典。過去幾年,先後出版《治理秩序論:經義今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等著作。目前完成《論語大義淺說》、《堯舜之道:尚書帝典、皋陶謨大義淺說》等著作,2016年陸續出版。接下來還會繼續解讀經典。 由此,對聖賢開啟之成人之道、合天人之大義有所體認,對中國治理之道的理解更為深入、細緻,並將儒家憲政置於天人之際進行思考。由此確信,儒家憲政之精神基礎是敬天,治理機制是人文之治,宗旨是《周易》〈乾卦彖辭〉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各種社會治理主體在多個維度上創造合適條件,讓每人生命向上成長,彼此間形成良好關係。 天人之際的儒家憲政,不似中國以西諸民族兩三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做法,把社會治理奠基於神教信仰;也不似現代西人那樣,以政治神話如「人民主權」為憲政之預設。儒家憲政相信,敬天之人可「明明德」,自明其德,從而可「里仁」、「克己復禮」。由此,人可組織起來,自我治理,「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故儒家憲政之起點是平實的,而又有向上提撕之力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比華人世界目前所行之各種體制更為優越,比西人目前所行之主流體制更為優越。 凡此種種,或可視為圍繞儒家憲政論之第四部分論說:作為政制的儒家憲政置於整全的天人秩序中,以見其直抵生命本源之獨特意義。這是儒家憲政有別於、或者超越於當下中國種種憲政論說之處。那些基於外來思想和制度所構建的憲政論說是純政制的,無法照顧身在中國之共同體成員的安身立命,如《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貫通無礙。唯有儒家憲政,徹上徹下,整全而圓融。 基於這一點,我對儒家憲政之前景充滿信心。儒家憲政也是走向「和而不同」的天下秩序之較優政制方案。
七、人能弘道
重建儒家憲政之最大障礙,是歷史終結論的思維方式。震懾於西方之富強,現代中國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精英,幾乎都是歷史終結論者:中國文明已死,歷史正在終結於歐美現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盤自我改造而歐美化。今日諸多憲政論說均有這一傾向,儘管其所嚮往之歷史終點,各有不同,但都在西方。 歷史終結論造成了可怕的心智封閉。歷史終結論者總是呼籲人們開放。也許,這種呼籲在20世紀初是有益的,但晚近以來,此所謂開放日益成為自我封閉,因為他們所謂開放,只是照抄,完全放棄思考之重負,不斷重複西來之咒語,坐等良好秩序之神跡降臨;此神跡對文化無知之中國精英群體有很大吸引力。 儒家憲政論者曾花費很多精力自我辯解,試圖喚醒處在現代神話蒙昧狀態中的這些可憐人。還好,歷史終結論正在被誰也未曾預料到之歷史進程所終結。21 世紀以來,諸多巨變讓歷史終結論神話走向瓦解,連福山也改了口風。儒家終於得以喘了口氣,在大陸快速復興,構建儒家憲政之可能已隱約顯現。儒家憲政論或許將進入第二個階段:一如今日之儒家整體,將不再是批判、反駁、辯解,而是構建、推進和踐行。 故本書只是儒家憲政論第一階段之成果。其論證是初步的,還須細化、深化、調整;最重要的是,對儒家憲政論者,前面還有極為廣闊的理論空間有待拓墾、耕種。筆者在此願意聲明:在儒家憲政論中,無所謂政治的真理;儒家憲政論者不相信人可設計出完備的、從而終結歷史之政制;儒家憲政論者只是致力於「推明治道」,也即確定關於優良治理之大方向和若干基本原則。此義理體系類似於持續成長的生命體,它長成什麼樣子,取決於人作出多少努力。子曰「人能弘道」,以此自勉。
八、關於本書
立憲者,國之大事也。本書收錄筆者近年來圍繞儒家憲政所撰寫之主要論說,多已公開發表,具體發表媒體如下: 第一章,原以〈中國治道探源:敬天與人文之治〉為題刊《人大法律評論》,2015 年第2 輯,總第19輯(2015)。 第三章,原以〈治理之儒家義理、中國傳統及其重建〉為題刊俞可平主編:《中國治理評論》,第七輯(2015)。 第五章,原以〈從革命到文明:八二憲法序言第一段大義疏解〉為題刊《法學評論》,第 2 期(2015)。 第六章,原以〈論憲法的中國性〉刊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6 月號(2012)。 第七章,其删節版刊《開放時代》,6月號(2011)。 第八章,下篇刊《天府新論》,第 3 期(2013)。 後序,原刊《中國法律評論》,第 2 期(2016)。 以上諸篇收入本書,其主要論說一仍其舊。為保持全書脈絡貫通,增補若干字句,予以串聯,有些篇章略有增補。為使全書結構完整,另撰寫兩章,即第二章和第四章。以上八章,編為上、下兩卷: 上卷「義理」,疏解儒家經典關於社會治理之大義,參照歷史經驗,以揭明儒家社會治理之道,也即儒家憲政之初步義理。第四章特別指出,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之常道,但在漫長歷史中多有反覆,此為中國歷史之顯著特徵;過去百年中國人破繭而出之政制嘗試,不過是反覆出現的歧出之最新一次,而今日中國正處在又一次回歸常道的過程中。 由此轉入下卷「更化」,探討當下中國通往儒家憲政之路。自以為第五章較為重要:現行中國憲法〈序言〉第一段構建「文明中國」敍事,確立「歷史」為基本的憲法和政治方法論,確立「文化」為國家塑造和維護良好秩序之根本。本段統攝憲法〈序言〉,進而統攝整部憲法,赫然有回歸文明中國之大義在。也就是說,即便激進革命的領導者,也在中國文化籠罩下,尤其是鑒於「文化大革命」之慘痛教訓,而於自覺不自覺之間回歸中國文化,並將歷史、文化寫入憲法,從而打開本書所討論的「第二次立憲」之大門。此義甚為深遠,筆者已就此展開研究。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教授邀約,此書得以面世。期待學界批評指正。創制立法者若能參考其中一二,幸莫大焉。
歲次乙未,時在仲冬,蒲城姚中秋自序於北京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