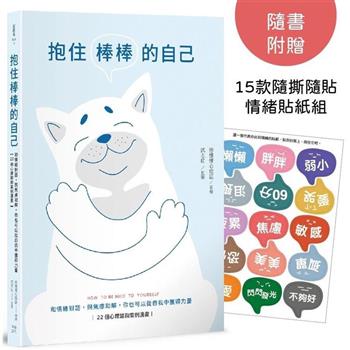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迄今,雖保留了英殖民者遺下的西敏寺民主政制運作,卻普遍不被視作民主政體,而是一種介乎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半民主」狀態。其執政聯盟聚合各族群代表,歷一甲子至今不曾下野,與新加坡一道成了東亞民主化浪潮下,長期政治穩定的異例。微妙敏感的族群、宗教關係,往往是執政者捍衛政權的利器:局勢對己不利時,就往挑撥的方向操作;局面對己有利時,則訴諸和諧;屢試不爽。不過1990年代末以降,馬來西亞公民社會開始躁動,在野政治力量更屢見選舉突破。本書即嘗試回答以下探問:
一、聯盟 / 國陣政權憑什麼長期穩定地維繫此「半民主」政體?
二、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展望如何?困難何在?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的圖書 |
 |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作者:王國璋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 出版日期:2018-01-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24頁 / 13.5 x 22.5 cm / 普通級/ 雙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11 |
社會人文 |
$ 463 |
亞洲史地 |
$ 468 |
政治 |
$ 483 |
中文書 |
$ 484 |
政治 |
$ 494 |
文化評論/社會觀察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國璋
馬來西亞北海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香港大學博士(亞洲研究)。曾在台北、澳門、香港的研究機構和大學擔任過研究助理、兼職導師、專任導師、副研究員等職,現為獨立研究者。研究興趣主要在族群政治、語言政治及海外華人。著有《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1997)及《菲華商聯總會之興衰與演變,1954-1998》(2002,與張存武合撰)等書,近年時評則散見於馬來西亞、香港和新加坡三地。
叢書主編簡介
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社會科學系副系主任,《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總編輯。
王國璋
馬來西亞北海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香港大學博士(亞洲研究)。曾在台北、澳門、香港的研究機構和大學擔任過研究助理、兼職導師、專任導師、副研究員等職,現為獨立研究者。研究興趣主要在族群政治、語言政治及海外華人。著有《馬來西亞的族群政黨政治,1955-1995》(1997)及《菲華商聯總會之興衰與演變,1954-1998》(2002,與張存武合撰)等書,近年時評則散見於馬來西亞、香港和新加坡三地。
叢書主編簡介
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社會科學系副系主任,《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總編輯。
目錄
第1章
獨立前的政治秩序與華巫博弈
第2章
政體性質與獨立前期的族群政治
第3章
五一三之變:馬華政治的轉折
第4章
伊斯蘭復興大潮下的馬來政治
第5章
2008年及2013年大選:轉型起點?
第6章
抗變的馬來社會與盼變的馬華社會
獨立前的政治秩序與華巫博弈
第2章
政體性質與獨立前期的族群政治
第3章
五一三之變:馬華政治的轉折
第4章
伊斯蘭復興大潮下的馬來政治
第5章
2008年及2013年大選:轉型起點?
第6章
抗變的馬來社會與盼變的馬華社會
序
序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迄今,雖基本上維繫了英殖民者留下的西敏寺民主政制運作,卻普遍不被視作民主政體,而是一種介乎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半民主」狀態,與新加坡一道,同是東亞民主化浪潮下長期政治穩定的異例。其執政聯盟─1974年前的三黨「聯盟」(Alliance)及1974年後擴編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 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包含了國內所有主要族群的政治代表,歷一甲子至今,竟然不曾下野。
馬來西亞社會多元複雜,不僅族群多元、文化紛陳、語言混雜,宗教上也是各教各派並存,遑論各族群內部,都還存在不少次族群的分歧。敏感微妙的族群、宗教關係,遂往往是執政聯盟維繫其政權的利器:局勢對己不利時,就往挑撥的方向操作;局面對己有利時,則訴諸和諧;屢試不爽。不過1990年代末以降,馬來西亞公民社會開始躁動,在野政治力量在晚近的2008及2013年兩屆全國大選,更屢見選舉突破。馬來西亞貌似已經邁入民主轉型階段,但與此同時,族群與宗教議題的典型操作手法未見失效,國陣政權的根柢,似乎也沒有崩解跡象。這段民主轉型的歷程,最終會邁向民主鞏固,還是隨時可能回歸舊貌?本書即嘗試回答以下探問:
一、聯盟/國陣政權憑什麼長期穩定地維繫此「半民主」政體?這類要素,如今是否已經逐漸消逝?
二、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展望如何?困難何在?
馬來亞(Malaya)是於1957年8月31日自英殖民者手中獨立,當時的國土範圍,僅馬來半島或「馬來亞半島」一地。所謂「馬來亞半島」,即強調不含半島以南的新加坡島,而新加坡原是英屬馬來亞的重要一環。至於馬來西亞(Malaysia),則是馬來亞、新加坡自治邦和英屬婆羅洲的砂拉越(Sarawak)、北婆羅洲(今日沙巴Sabah)四地合併的產物,成立於1963年9月16日。不過合併未及兩年,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就因故被逐出了馬來西亞聯合邦。
馬來西亞基本上可視為馬來亞的東擴版。西馬的馬來半島,相較於東馬的沙巴、砂拉越兩州,地理面積雖然較小(約四比六),人口卻多得多(約四比一)。西馬的工商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也遠較東馬優越。此外,西馬和東馬中間,隔了個不大不小的南中國海,交流其實不便,兩地的族群構成與歷史發展,也頗有差異。簡言之,馬來半島至今仍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的重心所在,所以討論馬來西亞政治,難免會重西馬而輕東馬。
回顧馬來西亞由英殖民時代迄今的政治發展,大致不離三條主線,即族群、伊斯蘭、階級。族群政治可謂馬來西亞的根本現實,迄今猶是。伊斯蘭政治原可視為馬來政治一環,1970年代後,卻逐漸反客為主,份量直逼族群政治。階級政治則至今未成氣候,但也難謂無關痛癢,總會在階級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隱晦地發揮某種跨族群的政治力量。話雖如此,基於階級政治在馬來西亞始終不敵族群與伊斯蘭政治的現實,本書基本上輕前者而重後兩者的討論。
族群與伊斯蘭政治的根本,源於一個建國六十年後,依然沒有共識的提問:馬來西亞究竟是誰的國家?這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即所謂 Tanah Melayu / the Malay Land,或更廣義之Nusantara / the Malay World 的概念),還是所有馬來西亞公民─不論其族群背景為何─的馬來西亞?本書即據此開展。
行文將首先回顧馬來亞獨立前的政治秩序,舖陳該國今日政體與社會結構的演進脈絡。這當中,我會特別回顧獨立前夕,影響深遠又極具定調意味的一場政治博弈。限於篇幅,相關討論將偏重於馬來西亞最具政治能量的兩大族群─馬來人(或巫人)和華人,而較少兼及相對弱勢的其他族群,如西馬的印度人社群及東馬的非穆斯林土著群體。
其次,我會概述馬來西亞的政體性質,並分析其獨立前期的族群政治。關於馬來西亞的政體性質,學界議論多年,究竟這是個威權、民主政體,還是哪一類的雜色品種?政體性質的討論是宏觀視角,有助我們思考其政治發展的總體路向。至於該國獨立前期的族群政治,值得觀察的,一是它早年的「雙族群」社會型態,如何為其政治定調?二是本時期的左翼力量,看似鼎盛,卻為何難成氣候?
其三,我會突出1969年的分水嶺事件─五一三族群暴動對馬來西亞民主進程的傷害,尤其是對馬華政治的深遠影響。其四,我當素描伊斯蘭政治於1980年代後興起的輪廓,並探討族群、宗教兩因素的互動。其五,我會簡析晚近兩屆全國大選,即2008年及2013年大選以來的馬來西亞政治發展,藉此探討該國民主轉型的困境。至於結論,除了總結,亦將展望未來。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迄今,雖基本上維繫了英殖民者留下的西敏寺民主政制運作,卻普遍不被視作民主政體,而是一種介乎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半民主」狀態,與新加坡一道,同是東亞民主化浪潮下長期政治穩定的異例。其執政聯盟─1974年前的三黨「聯盟」(Alliance)及1974年後擴編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 Barisan Nasional,簡稱國陣),包含了國內所有主要族群的政治代表,歷一甲子至今,竟然不曾下野。
馬來西亞社會多元複雜,不僅族群多元、文化紛陳、語言混雜,宗教上也是各教各派並存,遑論各族群內部,都還存在不少次族群的分歧。敏感微妙的族群、宗教關係,遂往往是執政聯盟維繫其政權的利器:局勢對己不利時,就往挑撥的方向操作;局面對己有利時,則訴諸和諧;屢試不爽。不過1990年代末以降,馬來西亞公民社會開始躁動,在野政治力量在晚近的2008及2013年兩屆全國大選,更屢見選舉突破。馬來西亞貌似已經邁入民主轉型階段,但與此同時,族群與宗教議題的典型操作手法未見失效,國陣政權的根柢,似乎也沒有崩解跡象。這段民主轉型的歷程,最終會邁向民主鞏固,還是隨時可能回歸舊貌?本書即嘗試回答以下探問:
一、聯盟/國陣政權憑什麼長期穩定地維繫此「半民主」政體?這類要素,如今是否已經逐漸消逝?
二、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展望如何?困難何在?
馬來亞(Malaya)是於1957年8月31日自英殖民者手中獨立,當時的國土範圍,僅馬來半島或「馬來亞半島」一地。所謂「馬來亞半島」,即強調不含半島以南的新加坡島,而新加坡原是英屬馬來亞的重要一環。至於馬來西亞(Malaysia),則是馬來亞、新加坡自治邦和英屬婆羅洲的砂拉越(Sarawak)、北婆羅洲(今日沙巴Sabah)四地合併的產物,成立於1963年9月16日。不過合併未及兩年,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就因故被逐出了馬來西亞聯合邦。
馬來西亞基本上可視為馬來亞的東擴版。西馬的馬來半島,相較於東馬的沙巴、砂拉越兩州,地理面積雖然較小(約四比六),人口卻多得多(約四比一)。西馬的工商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也遠較東馬優越。此外,西馬和東馬中間,隔了個不大不小的南中國海,交流其實不便,兩地的族群構成與歷史發展,也頗有差異。簡言之,馬來半島至今仍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的重心所在,所以討論馬來西亞政治,難免會重西馬而輕東馬。
回顧馬來西亞由英殖民時代迄今的政治發展,大致不離三條主線,即族群、伊斯蘭、階級。族群政治可謂馬來西亞的根本現實,迄今猶是。伊斯蘭政治原可視為馬來政治一環,1970年代後,卻逐漸反客為主,份量直逼族群政治。階級政治則至今未成氣候,但也難謂無關痛癢,總會在階級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隱晦地發揮某種跨族群的政治力量。話雖如此,基於階級政治在馬來西亞始終不敵族群與伊斯蘭政治的現實,本書基本上輕前者而重後兩者的討論。
族群與伊斯蘭政治的根本,源於一個建國六十年後,依然沒有共識的提問:馬來西亞究竟是誰的國家?這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即所謂 Tanah Melayu / the Malay Land,或更廣義之Nusantara / the Malay World 的概念),還是所有馬來西亞公民─不論其族群背景為何─的馬來西亞?本書即據此開展。
行文將首先回顧馬來亞獨立前的政治秩序,舖陳該國今日政體與社會結構的演進脈絡。這當中,我會特別回顧獨立前夕,影響深遠又極具定調意味的一場政治博弈。限於篇幅,相關討論將偏重於馬來西亞最具政治能量的兩大族群─馬來人(或巫人)和華人,而較少兼及相對弱勢的其他族群,如西馬的印度人社群及東馬的非穆斯林土著群體。
其次,我會概述馬來西亞的政體性質,並分析其獨立前期的族群政治。關於馬來西亞的政體性質,學界議論多年,究竟這是個威權、民主政體,還是哪一類的雜色品種?政體性質的討論是宏觀視角,有助我們思考其政治發展的總體路向。至於該國獨立前期的族群政治,值得觀察的,一是它早年的「雙族群」社會型態,如何為其政治定調?二是本時期的左翼力量,看似鼎盛,卻為何難成氣候?
其三,我會突出1969年的分水嶺事件─五一三族群暴動對馬來西亞民主進程的傷害,尤其是對馬華政治的深遠影響。其四,我當素描伊斯蘭政治於1980年代後興起的輪廓,並探討族群、宗教兩因素的互動。其五,我會簡析晚近兩屆全國大選,即2008年及2013年大選以來的馬來西亞政治發展,藉此探討該國民主轉型的困境。至於結論,除了總結,亦將展望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