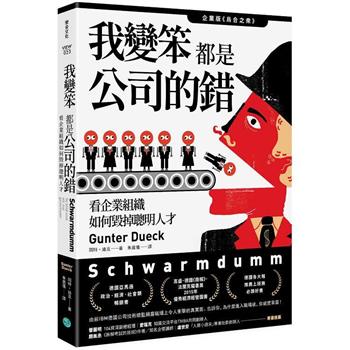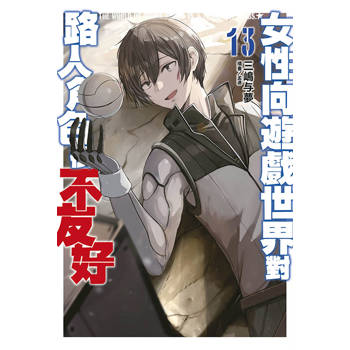夏志清
1965年2月23日,先兄夏濟安因腦溢血去世,年僅49歲。噩耗傳到台北,眾友人紛紛在當地報紙期刊撰文,紀念他作為一位教師和作家的成就。由於還不曾讀到他的英文近作,對於他在美國度過的最後六年裏如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聲譽日隆的傑出學者,人們只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不過,他對當前的台灣文學創作發揮過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點卻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一個弟子在《現代文學季刊》(1965年7月)紀念專輯裏這樣寫道:「自大陸淪陷後,不管在海外或在台灣,在保持中國文學命脈,在栽培中國新作家方面,貢獻之大,近人無出其右者。」1這一論斷恰如其分,儘管濟安兄只是在創作的道路上孑孓獨行。作為台大外文系的講師(後來升任教授),先兄一直鼓勵有資質的學生進行創作,在這一點上他比任何老師都要積極。同時,作為《文學雜誌》(1956–1960)的創辦者和主編,他會反覆要求學生對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評並進行修改,然後才拿去發表。這批年輕作家就是這樣慢慢成熟和獨立起來的。為匡正審美偏失,鼓勵優秀創作,他自己也寫了不少影響深遠的評論文章。不過據學生們回憶,他所做的還不止於此:無論是向他尋求指導或只是輕鬆地聊天,他都會欣然答應,從不擺架子。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濟安在台灣年輕作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非凡影響,乃是因為除了他自己的朋友外,即使是對他的短篇小說〈耶穌會教士的故事〉(載《黨派評論》1955年秋季號)2和其它英文作品推崇備至的西方讀者,仍可能未曾注意他在台灣(以及早先在大陸的光華大學、西南聯大和北大任教時)扮演的關鍵角色。作為一名學者,濟安著述最多的時期確實要到1959年3月來美國以後才開始,但他的英文論著中表現出的那種睿智與熱忱,其實正是他早年身為教師、編輯、批評家以及偶爾客串小說家和詩人時已經具備的特徵。假如下點工夫把他的英譯漢作品和原文作一下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他是那個年代中國最敏銳、最成熟的譯者之一。他翻譯過一本美國經典散文集(其中包括歐文、梭羅、霍桑等人的作品),3不僅不失精準地再造了抑揚頓挫的節奏,還為白話文帶來了另一種形式的暢達。
注意到濟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對於準確理解這部書大有助益。長期深入的研究當然是本書得以完成的前提條件,但若不是滿心牽掛中國文化的未來,那是絕不可能寫得出來的。生於1916年的濟安兄不可避免地受到「五四」理想與願景的洗禮;他先是在當下的文學現場積極發力,然後轉而研究對他產生過直接影響的文學傳統,為的是還原前一時期充滿悲劇性和複雜性的歷史真相。他本可以直截了當、就事論事地描述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運動,或選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來書寫傳記,或對他們的作品進行點評。諸如此類的研究皆可自成體系,也頗有意義。但對先兄而言,這樣的做法是對整個文化圖景的簡化和歪曲。雅克.巴贊(Jacques Barzun)在《達爾文、馬克思、瓦格納》一書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這種類型的文章顯然不是純粹的傳記、歷史或評論,而是三者的融會貫通,有時被稱為『文化批評』。」4在我的印象裏,沒有幾部研究近代中國的著作像先兄的研究那樣大量採用文化批評的多重視角,並賦予其種種文學特徵。
上述方法理想地實現了濟安的寫作目的。為了論述左翼文學運動,濟安挑選了魯迅、瞿秋白、蔣光慈,以及原本名不見經傳但死後被譽為「五烈士」的五個作家。在這些人中,只有魯迅堪稱大家,其作品之精湛,哪怕不熟悉人物生平和歷史情境也可以讀得津津有味。但即使是魯迅,他在生前最後十年裏之所以創作枯竭,亦不無深厚的文化意義──除非我們將其視作各種論戰與政治活動導致的思維混亂。濟安兄認為,蔣光慈的價值正是他在文學上的無價值,而「五烈士」乃是因為在特定情境下遇害,研究他們的生平才有價值。類似的評語並不只是幾句悖論而已:這說明對於很多左翼作家,只有完整重現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政治活動,才能凸顯他們在中國文化轉型關口的代表價值,才能展現他們意味深長、多愁善感,同時也的確悲慘的文人形象。雖然這些作家的文學天賦和教育程度各有差異,但他們當年都是「五四」傳統的堅定支持者,比如要求個性解放、社會公平,和民族復興。他們的願望依然真實,儘管他們在寫作中很少去把握這種真實。他們用筆來反抗傳統──其中不少人甚至願意放下筆桿,採用更激烈的方式與敵人作鬥爭。不過,哪怕是早年擁護共產主義的人,也很少會懷疑他們遲早要面對的敵人正是那個一再破壞他們個人品行與愛國情操的人,正是那個不擇手段利用他們滿腔抱負的人,正是那個將他們的文學事業引向毀滅的人。共產黨的革命如今居然成了「五四運動」理所當然的延續,這真是中國近代史上充滿諷刺性的悲劇。但至少對左翼作家本身來說,當他們後來對共產黨感到幻滅,終於試圖拒絕出賣自己的天賦來達到政治目的時,早年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只不過給他們多添了一些痛苦。「五烈士」死於共產黨的奪權鬥爭而沒有進一步走到幻滅的階段,何其幸也!
不過,我還是得讓先兄自己來評價這本書的性質。1964年6月,他寫出了〈一部關於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書稿序言〉。當時他正準備去西雅圖作一年一度的夏季旅行,同時希望能對這部書的內容作進一步研究。他打算把這篇起草於柏克萊的序言帶在身邊,給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羅斯研究中心」的同事看看,以備正式發表。他在寫給我的信裏一再表示對這篇序言並不滿意,他說要寫一篇更長的導論來介紹左翼文學運動。但是到了秋天,他回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後擔任了「中國研究中心」的語言學助理研究員。於是,他只能把一部分精力放在書稿上,同時還要為中心的當代漢語研究項目撰寫專題論文。這篇序言一直沒有能夠動筆修改,直到1965年2月21日──那是一個星期天,濟安兄像往常一樣去辦公室工作,卻突發中風去世。儘管如此,這篇文章還是帶有先兄風格鮮明的印記,而且言簡意賅地說明了該書的寫作目的。茲引全文如下:
一部關於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書稿序言
在中國,「左翼文學運動」這個說法可能會讓讀者想到兩件事。第一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近代中國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理論。「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作家被說成是具有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的命運:他們必須在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之間作出選擇。那些參與左翼運動的人實際上只是幫助了毛澤東的革命,但他們被視為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他們不單是預見到「解放」的先知,他們還是戰士,用包括筆桿在內的武器去締造未來。雖然左翼作家的數量一直不多,創作水準也至少可以說是參差不齊,但他們被認為代表了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支創作流派,而這些人的重要性是由他們對革命的貢獻,而不是由作品的審美價值來決定的。
這套意識形態框架內的理論簡潔明瞭,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的解釋。其中還包含一條從艱難抗爭到取得勝利的線索:它講述一群知識分子如何從摒棄舊中國開始,為了追求革命理想向一切開戰。他們在文學場域內的出現被說成是歷史的必然:在以毛澤東的最後勝利為巔峰的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中,上述行動只是其中一環。既然毛現在大權在握,那麼由他授意所做的一切就都被解釋成了左翼作家的理想自覺,他們為這種理想付出了三十年的鬥爭。
但是,對於那些經歷過這一時期的人,或者是能擺脫馬克思主義的片面影響來閱讀和思考這段歷史的人來說,還存在另一條可能的線索。這條線索充滿更深層次的情感問題,有時甚至因其複雜的動機而讓人感到費解。首先,共產黨員要和無黨派作家聯合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導致運動內部發生衝突的常常不是關於政策的爭論,而是涉及到的原則問題。但凡對良知──無論是人道的還是藝術的──有所珍視的人,大概都不可能和專心致志於一個目的的職業革命者共事。況且,中國的經驗並非偶然。同一時期,美國和歐洲也有一批才華出眾的作家被吸引到類似的運動中去。他們記錄了社會良知的覺醒和背叛,還留下一大堆水平低劣的文學作品,這些作者今天或許會因為覺察到這一點而感到羞愧。在中國以外的國家,此類運動的最終失敗,往往會因為人們的幻滅而帶來一定的教育意義,這有助於作家心智的成熟。中國的經驗裏也包括幻滅,可是當中國左翼作家擺脫天真的時候,或許也已經失去表達的自由了。
在中國,對左翼作家最激烈的批判正是舍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出的。他所採用的評價標準包括洞察力、感受力、對人生的獨到見解、動機分析,以及在明知無法實現的熱切希望和人性的弱點之間保持平衡的智慧。當然,大部分左翼作家在這些方面都不合格,志清宣告了他們的失敗。他的批評觸怒了捷克學者普實克(Průšek)先生,後者對志清貶損的那些作家抱有很高的評價。志清和普實克先生的爭論由《通報》刊載之後,大概激起了漢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這個迄今為止乏人問津的課題的興趣。對我來說,這場爭論的意義在於志清不僅證明了他的批判立場是正確的,還要求人們重新審視上述領域內常常發生的學術和政治宣傳的混淆。
但是,由於志清這本書旨在批判,因而忽略了左翼文學運動的某些特定方面。他對左翼作家在論述方式上的激烈性給予足够的關注,卻沒有充分注意到他們在文學以外的活動中表現出相同程度的激烈性。我所關注的是全世界範圍內很多左翼作家都曾經歷的兩難困境,即政治和藝術的衝突,也正是這種衝突注定了運動的失敗。1930年代,共產黨對作家的個人生活、個人信仰和個人創作道路橫加干涉,徹底導致這些被利用的對象對它的疏遠。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直到今天都沒有多大改變,但卻日趨強勢。
然而正是在黨變得強勢以前,這種兩難困境才更容易被感覺得到,因為個人還保留著一點尊嚴去對抗黨的力量。我討論的這些左翼作家,在他們的人生中有這樣一條心路歷程是值得注意的:這些作家發現自己在「五四運動」以後面臨巨大的自由和巨大的責任。巨大的自由是因為舊中國的社會體系瓦解了,巨大的責任則是因為他們有大好機會去創造理想的未來。對於當時的狀況,他們當然是不滿意的。1911年以來,革命思想讓不少知識分子著迷,1917年俄國樹立的榜樣堪為革命的理想範式。很多人自願擁護共產主義,他們找到了配得上自己的事業,他們願意為此奉獻自己的才華──必要時甚至奉獻生命。但是,起初的自覺獻身最終淪陷於共產黨的運作體制。每個人都要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個人對於改變現狀的意願、對於自由的聲張以及挑釁和反抗的姿態,在集體意志和統一行動中消於無形。要相信「科學」社會主義許諾的烏托邦可能沒有多大困難,但同時還要相信主導集體意志、指揮統一行動的幹部們百無一失則需要作出極大的犧牲,因為在某些情况下這意味著犧牲自己的原則。
集體運動中的個人命運可能會很悲慘,而我這本書就是要揭示其中的悲劇。假如把共產黨員也看成個體,那麼也應給予他們體諒,因為除了搞政治,他們同樣有思考的能力。在我關注的那個歷史關口,中國共產黨還很弱小。在它成立之初的頭十年裏,內部的權力鬥爭拋棄了不少同志,他們有的困惑不解,有的心生厭惡,還有的則徹底心灰意冷。參與派系鬥爭的人所展現出的卑鄙,完全揭穿了那些激動人心的宣言。中國的混亂局面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由莫斯科一手造成的,出自同一來源的指令獨斷專橫,又常常自相矛盾,反映出蘇聯內部的爭鬥。所有這一切對於很多中國同志來說是痛苦的,他們的入黨動機或許是夢想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奉命在文藝界從事地下活動的幹部們陷於「右傾」和「左傾」之間的兩難境地,常常不知何去何從。對於1927年後國民黨為平定叛亂而採取的高壓措施,他們既要抵抗又要躲避,處境也就更加艱難。
我要寫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歷史,卻沒有親身經歷可談,我與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都毫無關聯。既然心中沒有燃燒後的餘燼,也就沒有斬斷舊愛的必要。我做的研究是傳記性的和歷史性的,並不是自傳性的。所有材料都是調查所得,亦即在圖書館閱讀所得。全書並無任何個人經驗,除了我自己的觀察和評價。我沒有機會採訪書裏的主人公,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世,但不幸的是中國一直沒有出現像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那樣的人,出來講述自己走向左派的過程。本來胡風、丁玲和馮雪峰都是細述中國左翼作家心路歷程的理想人選,但他們始終保持沉默。我的這本書或許可以滿足上述要求。我無法以親身經歷取勝,但希望讀者能在我的超然態度或學術立場中得到補償。
按照原計劃,濟安兄這本書由一系列研究左翼作家及其與共產黨之關係的論文組成。〈魯迅與左聯的解散〉以及關於瞿秋白、蔣光慈和「五烈士」的章節都屬這個系列。先兄還打算收入兩篇分別在《亞洲研究期刊》和《中國季刊》發表的論文:〈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雖然這兩篇文章在形式上和其餘章節多少有些不同,但對於理解左翼文學運動至關重要。〈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不僅對魯迅傳記那一章作了補充,而且詳細闡述了先兄在討論其他作家時隱含的批評原則,即:假如一個作家未能充分利用自己內心的資源,那麼他就是膚淺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通過對作家的研究,如實地概括了左翼創作的趨勢,並再現了文學獨裁者否定這種趨勢和召喚共產主義文學新時代的歷史場景。
假如先兄活得够長,能看到本書付梓,他是否會對其中的章節進行修訂呢?讀者當然有權了解這一點。1964年6月以前,濟安兄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不多見的獨具創意又博學多聞的學者。他出版了兩本研究共產黨治下的中國社會和語言的大作,書名為《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以及《下放運動術語研究》。第三本是《從術語和語義看公社的潰敗》,定於當年夏天出版。他在學術會議上宣讀過不少論文,也在權威刊物發表重要文章。5
尤為重要的是,現在的這本書裏除了蔣光慈的部分,其它章節他都完成了。這些文章在單獨發表時(〈五烈士之謎〉一章原先是作為獨立研究成果在柏克萊發表的)得到學界讀者的交口稱讚和高度評價。6先兄在華盛頓大學的同事們受此鼓舞,紛紛敦促他盡快完成研究,反正全書規模已相當可觀。那年6月濟安兄抵達西雅圖後,同意再寫一章和一篇導論就交付出版。但他打心底裏覺得自己還應該再多寫點,6月24日他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坦言:
眼下,當務之急就是完成左聯那本書。還有兩章要寫,蔣光慈一章我打算在這兒花兩個月時間完成。……另一章是對左聯的概述,這個題目牽涉面太廣(比如其中就涉及我以前研究過的周揚),一直拖到現在都沒寫。不過,我還是希望在聖誕節之前──甚至在感恩節之前能完成。還有一章〈魯迅與左聯的解散〉,我打算重寫……並大幅度地加長。我想仔仔細細地描述魯迅與共產黨和無產文學擁護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胡風和馮雪峰的經歷(要還原當時的真實狀况很困難,但不這麼做我會覺得虧待了這兩個「正人君子」)。此外,我還想詳細討論徐懋庸在1956–1957年間發表的諷刺雜文,我認為這些文章可以看出作者繼承了魯迅的衣缽(在文學天賦上,無論胡風還是馮雪峰都無法和他比肩)。完成這個任務大概要花上一些時間。
四個星期後,濟安在7月18日的一封信裏設想對這本書作進一步擴充:
我在華盛頓大學(的朋友們)希望我寫完蔣光慈一章後就將全書出版。他們當然是一番好意,但我自己還是覺得慚愧:首先,我還想對1928年的反魯迅和反茅盾運動作一番徹底考察。那年,創造社和太陽社捲入了論戰,但我對個中議題還不甚了了。似乎創造社擁護普羅文學,而太陽社擁護革命文學。這兩個社團在文學觀念上到底有多大分歧(當然,大量證據表明它們只不過在同時利用這種對抗),他們是否代表當時蘇聯作家中兩大陣營的觀點──這些問題都值得仔細研究。我可以把這些問題組成一章,名為〈左聯的形成〉。
第二,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左聯剛一成立,早先的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的影響力就大為衰减。後者的式微在蔣光慈被開除出黨後表現得尤為明顯。魯迅有很強的「自負感」,想到這些時他肯定會摸一摸鬍子,露出笑容──數年後,當馮雪峰寫到這一時期時,同樣充滿了溢於言表的自我滿足。可能就是在周揚獲得(在左聯的)權力時,魯迅失去了他的權力。但沒過多久胡風就出現了,魯迅領導在野的左聯派別,而「新貴」周揚則領導掌權的左聯派別。這種狀况是怎麼發生的?我現在還不大清楚,但魯迅在早期左聯表現出的得意洋洋(他一直挖苦創造社和太陽社,毫不顧忌他們已是同一戰線的同志──托派的王獨清在寫到自己蒙受耻辱而得不到創造社的保護時,顯得頗為憤怒)和後期的鬱憤也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這一章要論述左聯內部的權力如何易手。(或許馮雪峰掌權的時候對魯迅惟命是從,事事請示,而周揚則他不够尊重。)
第三,我還要好好研究一下與左聯解散密切相關的徐懋庸。1956年時,他說自己沉默了二十年,但「雙百」期間忽然來了靈感,寫出一大批諷刺文章。這些文章相當優秀,真的應該輯成一本書,讓人看看魯迅的風格還沒死。
第四,魯迅譯介蘇俄文學功不可沒,理應給予肯定。蘇聯在二十世紀也經歷過「百花齊放」的階段,當時湧現的各派作家後來都遭到斯大林的清算。魯迅所感興趣的是:(1)蘇俄文學的多樣性……;(2)「同路人」作家──這些作家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以及對風格和技巧的關注很可能是延續了沙俄文學的光榮傳統。魯迅可以說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學習者,哪怕他根本讀不懂馬雅可夫斯基的未來主義、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象徵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他看到了蘇俄文學和沙俄文學之間的緊密聯繫,這種認識和處在後斯大林時代的我們大不相同。「魯迅與俄國文學」是個不錯的題目。……
假如要徹底研究清楚,恐怕還得再花好幾年時間。
可惜濟安兄英年早逝,無法繼續按計劃完成對左聯作家的全方位考察。但其實他不是真的要把上面這幾章併到現在這本書裏(他打算另寫一本)。假如由他來編排,全書內容還是會和現在差不多,只不過他會寫一章導論用來替換序言或加在前面,左聯解散那一章則會有大幅度的增補。他可能還會對蔣光慈一章作些微細的改動。他把能找到的蔣光慈的作品全都讀了,但還是有幾篇沒看到。不過蔣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的,多讀些額外的材料主要是滿足先兄作為一名學者的責任感,對於這一章所刻畫的作家形象其實不會有甚麼影響。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精裝)的圖書 |
| |
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精裝) 出版日期:2016-03-0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74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765 |
文學作品 |
$ 765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790 |
中文書 |
$ 791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精裝)
夏濟安先生所著《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自1968年英文版問世以來,便在英文世界產生極大影響,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研究領域一本劃時代的傑作。儘管該書部分篇章曾翻譯成中文並以單篇論文形式發表,遺憾的是此後近半個世紀之久,中文讀者始終無緣窺其全貌。此次中文大學出版社對英文版全書重新翻譯,增錄夏濟安先生另一篇相關的重要論文,並邀請翻譯學研究專家王宏志教授對譯稿全文審訂,首次推出這本經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
本書細緻梳理文學與時代政治的糾纏,深入揭示左翼文學運動的兩難境地。書中所論作家包括魯迅、蔣光慈、左聯五烈士以及瞿秋白等人,他們都是1949年以前共產黨理念的同情者乃至實踐者。在1960年代國際上反共仇共的大環境中,夏濟安下筆敏銳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滿耐心,既給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一個恰當公允的評價,更為他們身上的悲劇意義而深深歎息。
作者簡介:
夏濟安(1916-1965)教授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曾任教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外語系和香港新亞書院。1950年赴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為早期小說作家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葉維廉等人的啟蒙老師,1956年與吳魯芹、劉守宜等創辦《文學雜誌》並兼任主編,在雜誌上主張「樸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學,對文學新人盡心栽培呵護,也深刻地影響了一代華語文學的風貌。1959年濟安教授赴美,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改治中國共產黨黨史。The Gate of Darkness就是他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的一個精彩呈現。
TOP
推薦序
夏志清
1965年2月23日,先兄夏濟安因腦溢血去世,年僅49歲。噩耗傳到台北,眾友人紛紛在當地報紙期刊撰文,紀念他作為一位教師和作家的成就。由於還不曾讀到他的英文近作,對於他在美國度過的最後六年裏如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聲譽日隆的傑出學者,人們只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不過,他對當前的台灣文學創作發揮過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點卻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一個弟子在《現代文學季刊》(1965年7月)紀念專輯裏這樣寫道:「自大陸淪陷後,不管在海外或在台灣,在保持中國文學命脈,在栽培中國新作家方面,貢獻之大,近人無出其右者...
1965年2月23日,先兄夏濟安因腦溢血去世,年僅49歲。噩耗傳到台北,眾友人紛紛在當地報紙期刊撰文,紀念他作為一位教師和作家的成就。由於還不曾讀到他的英文近作,對於他在美國度過的最後六年裏如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聲譽日隆的傑出學者,人們只有一個大概的印象;不過,他對當前的台灣文學創作發揮過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點卻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一個弟子在《現代文學季刊》(1965年7月)紀念專輯裏這樣寫道:「自大陸淪陷後,不管在海外或在台灣,在保持中國文學命脈,在栽培中國新作家方面,貢獻之大,近人無出其右者...
»看全部
TOP
目錄
筆權和政權(王宏志) vii
導論(夏志清) xxv
第1章 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 3
第2章 蔣光慈現象 51
第3章 魯迅與左聯的解散 95
第4章 魯迅作品的黑暗面 129
第5章 五烈士之謎 145
第6章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 211
附錄 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239
注釋 267
中文版校譯後記(王宏志) 317
導論(夏志清) xxv
第1章 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 3
第2章 蔣光慈現象 51
第3章 魯迅與左聯的解散 95
第4章 魯迅作品的黑暗面 129
第5章 五烈士之謎 145
第6章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 211
附錄 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239
注釋 267
中文版校譯後記(王宏志) 317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夏濟安
-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3-04 ISBN/ISSN:978962996684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6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