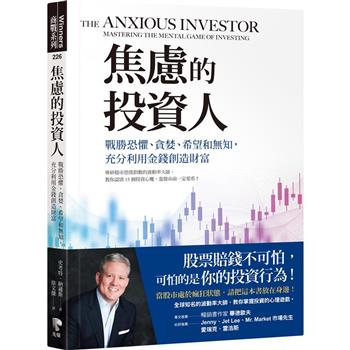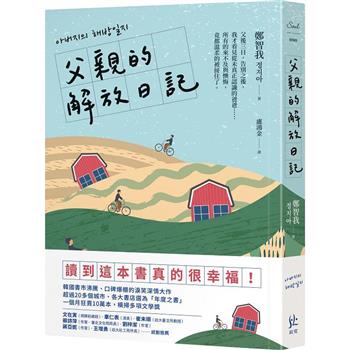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係一部有關道教修心煉性的清代道經。據經文說,斗姥元君和孚佑上帝純陽呂祖於嘉慶初(大約在三年至八年間,1798–1803)在北京一個奉祀呂祖為主神的道教乩壇─覺源壇上降示了這部經典。《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包含兩個主要的部分,「斗姥降經」(稱本經)和「呂祖疏解」(稱疏解)。本經共有九個章節,由斗姥於九皇寶誕的慶祝期間,敕令紫微星君降示予覺源壇弟子,目的是希望在壇弟子能夠繼承天仙派修煉金丹的傳統,並能以此真經廣化度人。至於「疏解」部分,則是出於呂祖的降示,為本經的每章內容進行梳理解釋,使經文的旨意更加清晰明白。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特色是一改以往丹經的深邃難解,運用平實簡易的文字,強調人本來擁有尊貴的靈性,可惜被塵世中各種欲望蒙蔽,不過仍可通過自我修煉,重獲靈妙真性,並一一指出道教心性修煉而致玄通微的真正功法。
本書白話註譯《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使用的底本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清代嘉慶《道藏輯要》。加上全新註譯的白話版本,本書希望能為當前充斥著物欲利益、社會階層之間衝突與不和諧,以及種族和宗教紛爭的人類社會,帶來一點如經文裏所指出的修煉本心、求得清淨的道理。本書為精裝甲、乙兩冊本、 甲部包括註譯使用的經書版本簡介、原經影印本、經文常用繁體字標點本、常用繁體字與原經異體字對照表。乙部主要是白話註譯《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 以便讀者將原經與白話註譯進行對照閱讀。真經貴重難得,註譯平易明晰,藏用皆宜。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修心煉性:《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 甲、乙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418 |
宗教類 |
$ 1669 |
中文書 |
$ 1669 |
佛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修心煉性:《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 甲、乙部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主任、《道教研究學報》主編及《中國文化研究學報》副主編。研究領域包括六朝道教史、天師道經典、道教科儀、清代《道藏輯要》、廣東地方道教史。著有《宗教研究與詮釋學》(2003)、《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2007)、《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2007)、《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2010)、《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2014)、《了解道教》(2017)等。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主任、《道教研究學報》主編及《中國文化研究學報》副主編。研究領域包括六朝道教史、天師道經典、道教科儀、清代《道藏輯要》、廣東地方道教史。著有《宗教研究與詮釋學》(2003)、《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2007)、《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2007)、《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2010)、《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2014)、《了解道教》(2017)等。
目錄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版本簡介(黎志添) 1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原經影印本 7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常用繁體字標點本 59
常用繁體字與原經異體字對照表 103
序一 (善玄精舍研經小組) vii
序二 (黎志添) ix
凡例 1
導讀 3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 23
1.朝禮斗姥 25
2.靈妙真經第一章 緣起品 40
3.靈妙真經第二章 持心品 45
4.靈妙真經第三章 解脫品 52
5.靈妙真經第四章 精進品 56
6.靈妙真經第五章 布施品 62
7.靈妙真經第六章 離欲品 70
8.靈妙真經第七章 清淨品 80
9.靈妙真經第八章 煉虛品 90
10.靈妙真經第九章 超昇品 99
11.收讚.三皈依 110
12.斗帝敕演九品靈妙真經疏解後跋(蔣予蒲) 115
後跋(黎志添) 119
附錄一 香港善玄精舍簡介 123
附錄二 香港善玄精舍助印善信芳名 127
參考書目 131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原經影印本 7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常用繁體字標點本 59
常用繁體字與原經異體字對照表 103
序一 (善玄精舍研經小組) vii
序二 (黎志添) ix
凡例 1
導讀 3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 23
1.朝禮斗姥 25
2.靈妙真經第一章 緣起品 40
3.靈妙真經第二章 持心品 45
4.靈妙真經第三章 解脫品 52
5.靈妙真經第四章 精進品 56
6.靈妙真經第五章 布施品 62
7.靈妙真經第六章 離欲品 70
8.靈妙真經第七章 清淨品 80
9.靈妙真經第八章 煉虛品 90
10.靈妙真經第九章 超昇品 99
11.收讚.三皈依 110
12.斗帝敕演九品靈妙真經疏解後跋(蔣予蒲) 115
後跋(黎志添) 119
附錄一 香港善玄精舍簡介 123
附錄二 香港善玄精舍助印善信芳名 127
參考書目 131
序
序一
善玄精舍研經小組
二〇一四年秋,善玄精舍慕道班榮幸地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親臨精舍講道。蒙教授慈悲引導,善玄弟子如沐春風,認識了道教文化的浩瀚淵博、廣闊深遠。令弟子們擴闊眼界、玄關開啓。
翌年,慕道班再次邀請到教授講道,並了解到善玄弟子對經教的渴求,尤其以全真義理修善心性而又易明易讀的經書最能契合善玄弟子的需要。二〇一五年秋,教授再臨精舍講道。為了滿足善玄的訴求,此次講道,他特地為善玄選擇了一份寶貴的禮物,也送給善玄一個無價的寶藏──他為我們帶來及講解了《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
在緊迫的兩個課節中,教授為我們講述了「真經」的源起、派別、註疏、每一品的內容和義理。對於我們這一群從來沒有真正研讀過經書的道子,教授自然要多費心神去說文解字,為經文加入標點符號,並對一些難懂的文字、詞語、句子加上白話註釋,使我們讀經時不如想像中困難,也改變了我們以往見到經書便望而生畏、敬而遠之的態度。
這改變可見於壇內的師兄師姐,對「真經」愛不釋手。一有空閒,便兩兩三三一起研讀,遇到難處就互相討論。尤其難得的是,有弟子將教授的錄影重看,一遍又一遍,本來打算做點筆記,沒想到學得越來越起勁,後來竟有師兄師姐將教授的講解逐字記錄,並將功課送呈教授修改、校正。由此可見善玄弟子對《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重視。有見及此,研經小組希望將這份重要的功課與善玄所有同修分享,於是向理事會提出了印經的構想。
替恩師闡道,是善玄弟子最樂意做的。既得嘉賓傳送寶經,應當珍之重之,參研深究。理事會同寅,認為善玄得此瑰寶,應與分享,讓經書流通,廣結善緣,方不負呂師教誨。研經小組與黎教授接觸,商討合作出版事宜,並蒙教授允諾負責編輯,將全經用白話文註釋,使讀者更容易明白。此外,其他繁瑣的校正和刊印等工作,亦得教授一力承擔,令此寶經可於丁酉年,善玄成立第二十年之呂祖先師寶誕前出版,是黎教授和善玄弟子慶祝恩師誕辰而送給恩師的最佳賀禮。
序二
黎志添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本身就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中國宗教文化寶庫。在中國社會,道教歷來就是一個具有精神影響力的本土宗教傳統,其影響力滲透至社會的各個階層,從王朝的統治者、精英知識分子到民間百姓,並形成獨特的中國本土宗教精神傳統。
道教不像西方宗教那樣要求信眾認信其「教義」的真確性,也不執著於向其他文化傳播其「普世價值」。道教不會刻意劃定信徒身份,皈依或信仰轉換在道教世界中並非主要問題。可以說,道教的宗教信仰特色在於其落實於本土各個階層對超越生活世界束縛的追求。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道教是以科儀立教的。因其「土生土長」的身份,道教在齋醮儀式之中已經自然而然地表達了中國人祈願、懺悔、赦罪、解脫及拯救等宗教精神。可以說,道教是屬於儀式型的宗教。其齋醮儀式裏所包含的宗教信仰非常豐富,而且也密切地滲透於民眾的生活習俗之中。
另一方面,道教又是一個重視對自我身體和精神進行修煉的宗教。道教的內丹修煉不囿於純粹思維領域的超越,反之,它更看重一種精神和形體兩者並重的實踐性修煉。因此之故,道教的內丹修煉常被稱為「性命雙修」,即是常說的性功和命功。事實上,道教性命雙修的實踐意義在於打破、消解和突破了「精神-肉體」、「物-我」和「個體-自然」等二元對立的思維,從而建立一個具有道教所追求的靈妙、無為、虛靜、清淨、超越、形神俱妙等主體價值的豐富人生。
道教內丹修煉具有清晰的人本主義色彩,這也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色。本書選錄的《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本書簡稱《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或《靈妙真經疏解》)反覆強調人本有的靈性是尊貴的─「靈踰萬物,至寶內含」。但是,如果人這本有而靈妙的真性一朝被塵世中各種慾望蒙蔽,好像被淤泥所掩蓋一樣,那麼結果便是不能分辨人與禽之間的區別。道教內丹修煉的實踐提出:縱使人的真性被掩蓋,但仍然可以通過自我的修煉,找回、返還、獲得本來性命的根源。這種區分人禽的本原真性並非作為一種現存事實而存在,而是必須經過綿綿不斷的修煉過程,才能通達、體察和參證,並達到那種與大道契合、內外相通的境界。換而言之,性命修煉的功法和關鍵仍然繫於自我的堅持、參透和驗證,這即是該經所說的「惟功惟實,自證自參」的生命轉化過程。
筆者過去一直從事道教齋醮科儀的研究,並且深深認識到,道教將與民眾禍福命運有關的宗教信念融入於齋醮科儀的實踐中。然而,自五、六年前開始,筆者因機緣轉入清代《呂祖全書》及《道藏輯要》的研究領域,結果發現,明末清初以後,道教信仰傳統在全真宮觀道教和正一齋醮科儀傳統以外有所發展,即由在家皈依信眾組成的扶乩道壇及其傳承下來的內丹修煉,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而且影響深遠。近代以來,大部份這類扶乩道壇供奉的是呂祖孚佑帝君。可以說,這些主祀呂祖的乩壇是道教第三種重要的存在和傳播的形式。若是不認識或不承認扶乩道壇的角色和貢獻,便不能準確及全面了解近代道教發展的特色。雖然,今天的扶乩活動常被誤認為低下層的民間宗教活動,但是其實不然。自明清至民國初年,許多精英分子、士大夫及文人所組成的道教乩壇成為幾百年來保存和推廣道教文化的重要力量。例如本書所介紹的《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便是在清代嘉慶年間,由一群創建於京城的呂祖乩壇──覺源壇的弟子,通過扶乩活動編撰、刊刻出來的一部道教內丹修煉經典。該壇的弟子是一批儒生精英,學問好,有科舉功名,同時又有道教信仰。他們得到呂祖的乩示,奉命傳播和編輯呂祖乩文。
關於覺源壇與《呂祖全書正宗》及《道藏輯要》的關係,本書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莫尼卡(MonicaEsposito)、森由利亞及筆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贅述。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覺源壇的降鸞活動在蔣予蒲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辭世之後,便迅速失去了蹤影。至於與覺源壇直接相關的《道藏輯要》的命運,正如莫尼卡的感言所說:「遺憾的是,這一偉大的計劃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蔣予蒲死後,這部本應得到公認的清代新《道藏》,卻只為少數收藏家所珍視。」不僅是《道藏輯要》的出版得不到預期的成果,更令人遺憾的是,蔣予蒲和其他覺源壇呂祖弟子的編纂功勞更被隱沒於後人對成都全真道觀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的認可之後。事實上,除了閔一得於道光十一年(1831)在其刊刻的《古書隱樓藏書》裏所收載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中,提及過《道藏輯要》的「〔經〕板在京邸,及送板歸南,而〔蔣〕先生又北上,卒於京師」之外,直到1922年,丁福保(號守一子,1874–1952)在其編輯的《道藏輯要總目》中,重證閔一得的說法,指出:「是書清嘉慶間蔣元庭侍郎輯。」然而,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二仙庵閻永和方丈主持重刻、賀龍驤(活躍於1891–1908)校勘的《重刊道藏輯要》,卻有意採用了《道藏輯要》的編者為康熙彭定求(1645–1719)的說法。例如賀龍驤在其所撰的〈《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中說:「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書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另外,賀龍驤又在〈欽定道藏全書總目序〉中稱:「相國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出於頒行本者半,出於坊間本者亦半。雖坊本,亦皆純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由於二仙庵《道藏輯要》的光緒重刊本主張彭定求為編者的錯誤說法,蔣予蒲和覺源壇的歷史進一步被埋沒。以致現今仍有一些學者支持彭定求為《道藏輯要》第一編纂者之說,且由於缺乏對覺源壇的研究及完全不知有《呂祖全書正宗》存在的前提下,卻主張說:「事實上,蔣元庭〔蔣予蒲,字元庭〕增補的《道藏輯要》本身,並未就蔣元庭與《道藏輯要》的關係作任何說明。」
因為有機會重新研究蔣予蒲、覺源壇和《道藏輯要》的緣故,筆者得以發現並受益於由呂祖及其他上界仙真降鸞覺源壇而新出的道經,包括:《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玄宗正旨》及《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等。以《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為例,雖然這是一部講論道教性命修煉的內丹經書,但是它一改以往丹經喜用龍虎、鉛汞、坎離、水火等隱晦譬喻及辭藻,以致深邃難解的積習;反之,其運用平實簡易的文字,一一指出了道教心性修煉而致玄通微妙的真正功法。該經的開首已經明言此丹經的宗旨:「此經九品,實為金丹妙典,洗盡從來譬喻隱秘之詞,使人人共由大道,直證天仙。」
二〇一五年秋,筆者有幸與香港善玄精舍呂祖弟子結下道緣,受邀至該壇教授道教經典。筆者選擇了自己也有所體驗及獲益的《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與該呂祖扶乩道壇弟子一起閱讀。相信他們與覺源壇弟子一樣,都能讓自己的修道信仰與呂祖性命修煉精神和功法契合,結果,正如他們所說:「壇內的師兄師姐,對《真經》愛不釋手。」善玄精舍的弟子不僅具有如此「經教」的反應,在乩壇上受稟呂祖恩師的旨意後,他們又發道心,積極支持筆者推動道教信仰現代化的夙願,通過白話註譯道經的學術功夫,俾讓道教的精神智慧能以平實易懂的文字方式,重新傳揚於現代華人社會之中。以上是本書緣起的背景、意義和目的。
白話註譯《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工作乃是從去年十月開始的,並且是集體努力而得的學術成果。筆者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和在讀的道教研究博士生們的幫助,共同討論、註譯、修訂及編輯全書的內容,包括賀晏然、陳文妍、高麗娟、胡劼辰和祝逸雯等,在此特別感謝他們的參與和襄助。最後,筆者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為當前充斥著物欲利益、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與不和諧,以及種族和宗教紛爭的人類社會,帶來一點如經文裏所指出的修煉本心、求得清淨的道理。
善玄精舍研經小組
二〇一四年秋,善玄精舍慕道班榮幸地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親臨精舍講道。蒙教授慈悲引導,善玄弟子如沐春風,認識了道教文化的浩瀚淵博、廣闊深遠。令弟子們擴闊眼界、玄關開啓。
翌年,慕道班再次邀請到教授講道,並了解到善玄弟子對經教的渴求,尤其以全真義理修善心性而又易明易讀的經書最能契合善玄弟子的需要。二〇一五年秋,教授再臨精舍講道。為了滿足善玄的訴求,此次講道,他特地為善玄選擇了一份寶貴的禮物,也送給善玄一個無價的寶藏──他為我們帶來及講解了《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
在緊迫的兩個課節中,教授為我們講述了「真經」的源起、派別、註疏、每一品的內容和義理。對於我們這一群從來沒有真正研讀過經書的道子,教授自然要多費心神去說文解字,為經文加入標點符號,並對一些難懂的文字、詞語、句子加上白話註釋,使我們讀經時不如想像中困難,也改變了我們以往見到經書便望而生畏、敬而遠之的態度。
這改變可見於壇內的師兄師姐,對「真經」愛不釋手。一有空閒,便兩兩三三一起研讀,遇到難處就互相討論。尤其難得的是,有弟子將教授的錄影重看,一遍又一遍,本來打算做點筆記,沒想到學得越來越起勁,後來竟有師兄師姐將教授的講解逐字記錄,並將功課送呈教授修改、校正。由此可見善玄弟子對《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重視。有見及此,研經小組希望將這份重要的功課與善玄所有同修分享,於是向理事會提出了印經的構想。
替恩師闡道,是善玄弟子最樂意做的。既得嘉賓傳送寶經,應當珍之重之,參研深究。理事會同寅,認為善玄得此瑰寶,應與分享,讓經書流通,廣結善緣,方不負呂師教誨。研經小組與黎教授接觸,商討合作出版事宜,並蒙教授允諾負責編輯,將全經用白話文註釋,使讀者更容易明白。此外,其他繁瑣的校正和刊印等工作,亦得教授一力承擔,令此寶經可於丁酉年,善玄成立第二十年之呂祖先師寶誕前出版,是黎教授和善玄弟子慶祝恩師誕辰而送給恩師的最佳賀禮。
丙申年冬月
序二
黎志添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本身就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中國宗教文化寶庫。在中國社會,道教歷來就是一個具有精神影響力的本土宗教傳統,其影響力滲透至社會的各個階層,從王朝的統治者、精英知識分子到民間百姓,並形成獨特的中國本土宗教精神傳統。
道教不像西方宗教那樣要求信眾認信其「教義」的真確性,也不執著於向其他文化傳播其「普世價值」。道教不會刻意劃定信徒身份,皈依或信仰轉換在道教世界中並非主要問題。可以說,道教的宗教信仰特色在於其落實於本土各個階層對超越生活世界束縛的追求。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道教是以科儀立教的。因其「土生土長」的身份,道教在齋醮儀式之中已經自然而然地表達了中國人祈願、懺悔、赦罪、解脫及拯救等宗教精神。可以說,道教是屬於儀式型的宗教。其齋醮儀式裏所包含的宗教信仰非常豐富,而且也密切地滲透於民眾的生活習俗之中。
另一方面,道教又是一個重視對自我身體和精神進行修煉的宗教。道教的內丹修煉不囿於純粹思維領域的超越,反之,它更看重一種精神和形體兩者並重的實踐性修煉。因此之故,道教的內丹修煉常被稱為「性命雙修」,即是常說的性功和命功。事實上,道教性命雙修的實踐意義在於打破、消解和突破了「精神-肉體」、「物-我」和「個體-自然」等二元對立的思維,從而建立一個具有道教所追求的靈妙、無為、虛靜、清淨、超越、形神俱妙等主體價值的豐富人生。
道教內丹修煉具有清晰的人本主義色彩,這也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色。本書選錄的《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本書簡稱《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或《靈妙真經疏解》)反覆強調人本有的靈性是尊貴的─「靈踰萬物,至寶內含」。但是,如果人這本有而靈妙的真性一朝被塵世中各種慾望蒙蔽,好像被淤泥所掩蓋一樣,那麼結果便是不能分辨人與禽之間的區別。道教內丹修煉的實踐提出:縱使人的真性被掩蓋,但仍然可以通過自我的修煉,找回、返還、獲得本來性命的根源。這種區分人禽的本原真性並非作為一種現存事實而存在,而是必須經過綿綿不斷的修煉過程,才能通達、體察和參證,並達到那種與大道契合、內外相通的境界。換而言之,性命修煉的功法和關鍵仍然繫於自我的堅持、參透和驗證,這即是該經所說的「惟功惟實,自證自參」的生命轉化過程。
筆者過去一直從事道教齋醮科儀的研究,並且深深認識到,道教將與民眾禍福命運有關的宗教信念融入於齋醮科儀的實踐中。然而,自五、六年前開始,筆者因機緣轉入清代《呂祖全書》及《道藏輯要》的研究領域,結果發現,明末清初以後,道教信仰傳統在全真宮觀道教和正一齋醮科儀傳統以外有所發展,即由在家皈依信眾組成的扶乩道壇及其傳承下來的內丹修煉,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而且影響深遠。近代以來,大部份這類扶乩道壇供奉的是呂祖孚佑帝君。可以說,這些主祀呂祖的乩壇是道教第三種重要的存在和傳播的形式。若是不認識或不承認扶乩道壇的角色和貢獻,便不能準確及全面了解近代道教發展的特色。雖然,今天的扶乩活動常被誤認為低下層的民間宗教活動,但是其實不然。自明清至民國初年,許多精英分子、士大夫及文人所組成的道教乩壇成為幾百年來保存和推廣道教文化的重要力量。例如本書所介紹的《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便是在清代嘉慶年間,由一群創建於京城的呂祖乩壇──覺源壇的弟子,通過扶乩活動編撰、刊刻出來的一部道教內丹修煉經典。該壇的弟子是一批儒生精英,學問好,有科舉功名,同時又有道教信仰。他們得到呂祖的乩示,奉命傳播和編輯呂祖乩文。
關於覺源壇與《呂祖全書正宗》及《道藏輯要》的關係,本書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莫尼卡(MonicaEsposito)、森由利亞及筆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贅述。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覺源壇的降鸞活動在蔣予蒲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辭世之後,便迅速失去了蹤影。至於與覺源壇直接相關的《道藏輯要》的命運,正如莫尼卡的感言所說:「遺憾的是,這一偉大的計劃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蔣予蒲死後,這部本應得到公認的清代新《道藏》,卻只為少數收藏家所珍視。」不僅是《道藏輯要》的出版得不到預期的成果,更令人遺憾的是,蔣予蒲和其他覺源壇呂祖弟子的編纂功勞更被隱沒於後人對成都全真道觀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的認可之後。事實上,除了閔一得於道光十一年(1831)在其刊刻的《古書隱樓藏書》裏所收載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中,提及過《道藏輯要》的「〔經〕板在京邸,及送板歸南,而〔蔣〕先生又北上,卒於京師」之外,直到1922年,丁福保(號守一子,1874–1952)在其編輯的《道藏輯要總目》中,重證閔一得的說法,指出:「是書清嘉慶間蔣元庭侍郎輯。」然而,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二仙庵閻永和方丈主持重刻、賀龍驤(活躍於1891–1908)校勘的《重刊道藏輯要》,卻有意採用了《道藏輯要》的編者為康熙彭定求(1645–1719)的說法。例如賀龍驤在其所撰的〈《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中說:「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書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另外,賀龍驤又在〈欽定道藏全書總目序〉中稱:「相國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出於頒行本者半,出於坊間本者亦半。雖坊本,亦皆純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由於二仙庵《道藏輯要》的光緒重刊本主張彭定求為編者的錯誤說法,蔣予蒲和覺源壇的歷史進一步被埋沒。以致現今仍有一些學者支持彭定求為《道藏輯要》第一編纂者之說,且由於缺乏對覺源壇的研究及完全不知有《呂祖全書正宗》存在的前提下,卻主張說:「事實上,蔣元庭〔蔣予蒲,字元庭〕增補的《道藏輯要》本身,並未就蔣元庭與《道藏輯要》的關係作任何說明。」
因為有機會重新研究蔣予蒲、覺源壇和《道藏輯要》的緣故,筆者得以發現並受益於由呂祖及其他上界仙真降鸞覺源壇而新出的道經,包括:《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玄宗正旨》及《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等。以《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為例,雖然這是一部講論道教性命修煉的內丹經書,但是它一改以往丹經喜用龍虎、鉛汞、坎離、水火等隱晦譬喻及辭藻,以致深邃難解的積習;反之,其運用平實簡易的文字,一一指出了道教心性修煉而致玄通微妙的真正功法。該經的開首已經明言此丹經的宗旨:「此經九品,實為金丹妙典,洗盡從來譬喻隱秘之詞,使人人共由大道,直證天仙。」
二〇一五年秋,筆者有幸與香港善玄精舍呂祖弟子結下道緣,受邀至該壇教授道教經典。筆者選擇了自己也有所體驗及獲益的《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與該呂祖扶乩道壇弟子一起閱讀。相信他們與覺源壇弟子一樣,都能讓自己的修道信仰與呂祖性命修煉精神和功法契合,結果,正如他們所說:「壇內的師兄師姐,對《真經》愛不釋手。」善玄精舍的弟子不僅具有如此「經教」的反應,在乩壇上受稟呂祖恩師的旨意後,他們又發道心,積極支持筆者推動道教信仰現代化的夙願,通過白話註譯道經的學術功夫,俾讓道教的精神智慧能以平實易懂的文字方式,重新傳揚於現代華人社會之中。以上是本書緣起的背景、意義和目的。
白話註譯《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的工作乃是從去年十月開始的,並且是集體努力而得的學術成果。筆者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和在讀的道教研究博士生們的幫助,共同討論、註譯、修訂及編輯全書的內容,包括賀晏然、陳文妍、高麗娟、胡劼辰和祝逸雯等,在此特別感謝他們的參與和襄助。最後,筆者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為當前充斥著物欲利益、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與不和諧,以及種族和宗教紛爭的人類社會,帶來一點如經文裏所指出的修煉本心、求得清淨的道理。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