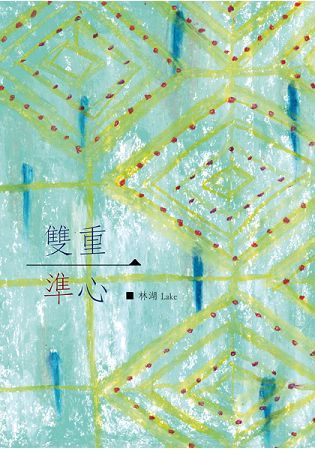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雙重準心》原創個誌展首發新書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 圖書簡介
《雙重準心》原創小說╱約5萬字╱約120P╱A5彩封
七名星際人被派往未知的原始星球開創生命,他們各自著陸,在生命茁長的關鍵地點「自由水塔」集合才能執行任務並返回母星。
但當七人終於到達集合地時,狙擊手意外死亡,若是少了其中一人就無法完成任務,而狙擊手能協助大家分辨未知事物背後的真實,對任務十分重要,隊長「刻印者」楊昏只好通知母星派遣新的狙擊手替補。
六人分散開來,在一個全然未知、只在夢境裡顯形過零碎片段的星球等候新成員,帶著失去夥伙的巨大痛苦,各懷心思,並為了完成任務各自行動。
而楊昏知道,他所尋找的新狙擊手那蒙,能夠把所有破碎和分離再度聚合起來,但他必須先跟那蒙重新磨合……
【閱讀手冊──關於本書的有趣設定】
1. 那蒙(狙擊手):
對應眉心輪,職責為看穿表象後的真實、破除幻覺。作為新的狙擊手出現在楊昏面前時,有著跟其餘隊員截然不同的任務意識。性格好強,強烈警戒心背後有著純真的一面。
2. 范陷(觀測手):
對應心輪,職責為感受環境波動、把自身持有的情感複寫到其它人事物上,或把別人的情感吸收到自己身上。性格謹慎、敏感,能用各種方式細膩地表達情感。私底下是美食家。
3. 藍淋(召喚者):
對應喉輪,職責為呼喚、聯絡隊員,也能對星球上的物質發送信號,移動速度非常快,極度專注使用能力時會暫時失去視力。性格有些溫吞,執行任務以外的時候是不擅言詞的,喜歡冰涼的東西。
4. 顏陡(挖掘者):
對應胃輪,職責為挖掘地面找出可用或需排除的物質,亦有戰士的天賦,性格直率、爽快不糾結,喜歡蒐集人類文明的裝飾品。
5. 王夙(破壞者):
對應臍輪,唯一被賦予「反抗」機制的隊員,會在重大危機發生時啟動。性格溫和,有使人感覺幸福的天賦,是動物們的好友。
6. 楊昏(刻印者):
對應海底輪,七人小隊的隊長,職責為監督其餘隊員及把夏海的投影落實在星球上。高大、有極好的體能和傷口復原能力,很愛哭,沒有狙擊手對他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任務中一直戴著面罩。
7. 夏海(投影者):
對應頂輪,職責為匯集六人蒐集的情報與工作進度,投影在星球上。是唯一不直接著陸星球進行任務的隊員,有先知能力,性格淡漠。
8. 自由水塔:
七人的意識連結後才會產生,用於創造生命,亦需憑藉七人的存在運轉。
9. 溝通方式:
七名外星人以類似存在於四度空間裡的意識,以暫用的肉體著陸原始星球,主要以意念傳心來進行溝通。
★全新視野的史詩奇幻小說,「脈輪擬人」帶你探索神祕未知的世界!
首創將印度瑜珈的七大脈輪擬人化,七人小組要前往原始行星創造生命,
蒙太奇般的敘事手法,拼湊出一段不可思議的冒險旅程,打造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他們還來不及創造新生,就面臨死亡傷痛……
突如其來的死亡造成組織崩壞、平衡失序,倖存的六人各自面對心靈創傷,
有的人重新獲得愛人的力量,有的人卻只想毀滅一切,
他們最後能撫平自己的傷口,重新集結,完成任務嗎?
★「原創個誌展」首發新書!
獻給身處崩壞時代的人們,今年不可錯過的療癒系奇幻故事,書展首發! - 作者簡介
林湖Lake
新手人妻,興趣是種田和抓蟲,但沒有寫過種田文,也不擅長為文章抓蟲。
自己也看不懂的故事常常從天上掉下來,為了解釋給別人聽而傷透腦筋。
但是無論如何,浪漫是最重要的!
個人網站:https://marslake.weebly.com/ - 序
【作者序】
我想講述一個像星星在耳朵旁說的床邊故事
這是一個出自星星光芒的故事。
我在晚上凝視著星星,然後入睡、做夢,新的一天做著毫無相干的活兒時突然心想:啊,有這樣一件事啊!
最先出現的是楊昏和那蒙兩人相遇的故事。不過在這個階段,他們還沒穿上海底輪和眉心輪的色彩,而是像兩個「很有緣分」的夸克那樣的存在。
宇宙中的相遇有太多太多次了,最後浮現的是脈輪之間的關係,於是其他夥伴就跟著一一出現,湊齊七脈輪戰隊,大家要手牽手一起實現一個願望。
我在很多地方讀過脈輪的知識,也試著自己體會,從字面上看來,脈輪就好像是一套不可見的身體器官,和人類的身心健康平衡,以及這個世界息息相關。
以我的文字表達能力,沒辦法簡單條理地解釋這個深奧的知識,但是我覺得,脈輪這個系統的存在,一定是跟愛有關的。
我想盡可能柔軟、真誠地講這樣一個故事,像星星在耳朵旁說的床邊故事。如果能讓大家對脈輪知識有點興趣,或者感覺到愛,那就是最棒的事了。
林湖Lake
二○一八年冬 - 目次
第一章 崩潰
「若是死亡將我們集結起來,那寧願永不相見。」
第二章 復甦
「我會攻擊你的話語,不攻擊你的聲音;攻擊你的模樣,不攻擊你的臉。」
第三章 融合
「可是你看吧,雖是有形的、硬實的韻文,也可供排列,能在背叛中矗立不搖。」
第四章 破壞
「不再渴求回家、不再視離別為傷害、不再獨自佇立流淚、不再流放真實的自己於黑夜。」
第五章 重逢
「這些是在地上的星星?」
「不,是百合花。」 - 書摘/試閱
雙重準心 試閱
【第二章】復甦
最開始,任務成形的時候,是沒有狙擊手的。
顏陡醒來,這是他第一個念頭,記憶中的狙擊手,在夏海的書房裡,向他投來一眼,他覺得像看見另一個自己,像水邊倒影,有不同的光澤。他要再看的同時,狙擊手走過他身邊,就如他小心翼翼掛在摩擦光亮的錫架子上的絲巾,呼地拂過去了。他看到夏海坐在他帶來的那張高腳椅上,慢慢地,花朵綻放時的顏色轉變那樣,抬頭笑著看他。如果他問夏海那是不是他喚來的,夏海會說不是。那麼狙擊手是自己來的嗎?一定也不是。
夏海依舊笑著看他。這是必要讓顏陡見到的一刻,夏海會說是的。沒錯。比顏陡蒐集的任何樂器聲音都更好聽。
顏陡睡去的時候,身體裡生出的根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他一邊收回這些根,一邊思考是去了哪裡。時常他會用此方法挖掘與準備和他想要的物件相遇。障礙是從來不缺的,碰觸到、敲擊出清脆或沉重的聲音,他便高興地全身一亮。遭受阻擋,在根上留傷痕,發生一次,他的儲藏空間就更大一些。但他回想如根的回收一般順利,再多分支也沒使其受傷,什麼也沒遇到,什麼也沒找到。他坐起來,大龜還在,不必選擇。
即使是在夢中,狙擊手的降落也穿透夢境。沒有誤差,在所有人之中。夏海也知道,顏陡心想,但總不出手。他所管護的四角地略略變形,朝外擴充,像一隻伸出虛擬肢體的蟲,這使他站在原地的視野嘩地張大,升高,空無一物的感受更深了。已經去了那麼遠,卻不夠。顏陡站著,呆呆望著。會出現的,會占領的,在廣大中,要他一一去注視。光線是不一樣了。
楊昏在顏陡無限的凝視裡動起,先是胳臂,才是頸子。他用完了在這星球應有的動作,本來不能再有。隨之而來,新的空氣與色彩,冰冷、陌生,將他托起來。他的呼吸化成白煙,從身體裡出來,往某個方向去。他知道顏陡為何凝視,不是要挖開空中。是那穿來的視線,他們也要回應。在楊昏面前,那非常混沌,近乎盲目。他呼吸,在心裡呼喚范陷。范陷不在原本的地方,也並未出聲。他聽到范陷正走去一條狹窄的路徑,有事要做。
狙擊手的光線照在楊昏身上,他還看不見,就像一條太細的線黏在他的胸口。但他不禁想起,彷彿不久之前,狙擊手還在,注視他時,一雙眼睛像是意識的全體。一潭清涼的水池,帶給他快樂。楊昏沒注意,快樂出現時,所有人都停頓了一下子。
他在霧霾中移動腳步,這亦和過去的行走有區別,跟著發亮的白煙走,現在他知道范陷為何走離。如果受到控制,應該拒絕。他這麼想。他在乎的、愛著的植物在土裡察覺他,有些讓他的腳底吸附,修補他身體的坑洞。
狙擊手離開書房後,顏陡對夏海說。我以為,狙擊手是為我而來。說著伸出手讓夏海看。手環與珠鍊叮叮噹噹地滑到手臂上方。顏陡漂亮的手指比這些裝飾都還堅不可摧,使最亮的寶石也看來遙遠。我知道不是為了對抗。他說。對抗也有其必要,一直是我為你帶來。
夏海對他點頭,躺在椅裡,長髮隨著瀉在地面。
范陷撿起了藍淋丟在地上的圍巾。那也是顏陡的禮物。
在那之後,也許就是前往執行任務的旅途上,實際上很久,又只像一會兒。平常顏陡會說「是吹熄一個寶物所需的時間」,這次他只是躺著,翹著腿,仔細地想,若要送狙擊手什麼,從他的蒐藏品裡,是不是不容易?像爬樓梯似的,他把所有物件都數上一遍,連不屬於他的都數進去了。只有他和夏海見過進入任務前的狙擊手,他對此極有自信,而降落的狙擊手該有多令他目眩神迷,卻無從得知。狙擊手正是他寶貴蒐藏品成形前的模樣,他不由得全心地喜愛上。
他身旁的大龜,緩緩溶解,骨骼變得透明,他看著,臉上出現一種有區隔的笑容,像是把信心和愛分開來顯露。這一定會發生,因為這一次的狙擊手,乍看凹陷,比一口氣還不成模樣。他想。那大龜的溶液讓土壤盛著,並未流入隙縫。在顆粒間,原先不能見的,新與逝去狙擊手的碎片溶液相吸,流如細小水脈。
有毒。范陷抬起腳,讓流來的水蜿蜒而去。他把藍淋的圍巾揣在懷裡,和水流保持距離,就像和其他人保持距離,這不是太難的事,他原本擅長。要找到藍淋,又比現在更不同些,要找不是藍淋的藍淋,和使自己不和任何人相似,是不同的。他又看了楊昏所在處一眼,有數條強硬的、明晰的線條飛隨,楊昏卻未受操控,向著以為是操控的路走去。他暫時不能再看楊昏了,這一眼之後,他要實行諾言。
可是,楊昏在夢中見到他了。在行走的路途上累得只能這麼做,在圓狀橘紅色的一個房間,楊昏是本來的楊昏,對他展開笑容。強壯,輪廓如金的楊昏,當他們在旅途中短暫相見時,傳達到他身體裡的,比花朵還精巧的變形,他知道有種果實也是如此,纍纍而不沉重,使他的意識更強固。他曾有一瞬對楊昏感到抱歉,因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他。但楊昏在落地時第一個見他,遠遠跑來,沒有遲疑,知道他就是范陷,並以全部的自己擁抱他。要不是他們先前相遇,范陷恐怕是脆弱地無法承受。楊昏在水塔落下眼淚時,他發現那張臉上竟有個面罩,所有曾令他或他們快樂的,都成了面罩。他想拿過來扔掉,曾經的記憶們,而後他失去了聲音。
在這之前,誰在乎過說不說話?本來,聲音不是太多,就是全然沒有。一個人說話,也就像是無數鈴鐺響起,是所有人共有的。他遇見狙擊手時正是在那些聲音裡,彷彿舉起弓矢般尖銳的一段顏色,帶起令人思鄉的歌聲,很多事情范陷都忘了,因此被判定不必在此想起,但狙擊手令他想起最好的事。他認為是「巧合」,是一個掩飾過的字,他用這個字督導自己不可沉迷回憶。「巧合」到了藍淋那裡,就被用於編織新的歌聲,又分別回到他們七人身上。他模仿著,並用於尋找藍淋。
在幻覺中如火苗一般的聲音來自楊昏。那出現得太早,變形太快,真正的火焰根本還沒出現,已經留下了。在未來的某個「永遠」,也許有空間前進,也許沒有,這缺憾在楊昏身體裡裡,像一個秤。他走著,以為會看見一座湖,或海的一部分,他是那樣被指引的,最純粹的,最漆黑的,都在那裡。
但狙擊手並未使用任何替身或者憑藉,是他們已許久不見的赤裸,在這裡,值得畏懼。楊昏的腳趾間,在他該停下腳步的時候,生出灰色芽苗。
狙擊手應該要在高處的,連楊昏都這麼想,雖然,星球上的高與低時常變動,又或可能他太高大,把狙擊手看小了。那人坐在流動的旱雲上,要移遠時就走到另一片,好像他擁有一個不動的中心,那也是他們還不能確信的。在他周圍有一圈很淡的光澤,有人接近也無變化。
楊昏記起了,以第二次甦醒的意識。他們都未同第一任狙擊手說過話,在他死亡之前。他知道狙擊手的家鄉,和他曾經刻印的事物部分重疊,最初是一個接一個的三角丘,斜度極小,像溫和海浪。從三角的頂端看過去,有一條路可走,在那盡頭創造了狙擊手的星球意識,像一面大珠簾,圓珠子照耀周遭。楊昏猜想那是絢麗多彩,能將人輕易穿透的,因為他只是很遠很遠地遙望過而已,在夢中亦是。
旱雲升高,稀薄了,在不必承載重量後,楊昏想他再一次看錯了,不是旱雲,一下子拉近,本該比星球另一側還遠的色彩逼在鼻子前,新的狙擊手像在一幅畫裡,薄薄的,這是全部。楊昏感覺到自己的呼吸,自從降落後,很久沒有這樣緊繃的振動。
給我一點光。那人說。楊昏沒仔細聽,他似乎連汗水都要滴在地上。沒感受過的意識,被他的思考擠壓到危險那一方,可本不該如此的,他的判定方法不是這樣的。
那人等了一會兒,比劃一個像是點火的手勢。給我一點兒光,不要接近火焰的,要你自己那種的。他歪著頭看楊昏,像在確認雙眼的位置。他的個子確實小,但佔滿了楊昏的視野。
當你在火球裡時,光很多,我能看到你。那人說,垂眼沉思,拍拍自己胸口,再指向他。我,看到你。可是不能用那些光,你知道吧?你自己的光呢?
楊昏要開口,好像兩顆石子卡在喉嚨,這個意識出奇地年輕,和第一任狙擊手完全不同。一陣刺痛爬上他的後頸。他伸出手指,做出像在模仿方才對方做的動作。一點點微弱的光浮在指尖。
那人望著他的臉,走上前來握住他的兩隻指頭,呼地吹口氣。楊昏的光芒亮了一點,把他倆都照清楚。
這是狙擊手,與他們相繫,楊昏不敢相信也沒辦法。顏陡在他的那一角地嘆口氣,他的地被撐開,工作增加,他決定不問緣由,要去挖下一角。在那有機會見到有蹄動物,是的,只要狙擊手在,刻印速度會加快的。但楊昏的時間像停止一樣,狙擊手為他吹亮的範圍,逐漸擴大,彷彿摘下一副灰色眼鏡,換上另一副前,短暫地,他見到逝去的狙擊手的光澤,液體玻璃般,將他的色彩吸走。那人站在他面前,距離變得正常,五官也逐漸成形,他一驚,摸自己的臉,面罩還在。
你以為自己沒有臉。那人說。是誰讓你覺得?
他搖搖頭,緊壓面罩。
你們不說話,很長時間。那人說,放開他的手。我攻擊你的火焰,之後,聽到有人唱歌。在這裡可以感覺的方式,變得很粗糙,藏得很深。
顏陡大笑幾聲。現在他真的開心了,把土橫翻,並不往下挖。
你們不碰觸彼此,會痛嗎?那人說。
楊昏搖頭。
看到嗎?用我的眼睛。狙擊手指向右方。還有一個人會在那裡粉碎,因為那裡是仿製的。然後再重組。等到七個人聚集,會有新的水塔,對不對?
楊昏點點頭。
我會攻擊你的話語,不攻擊你的聲音。攻擊你的模樣,不攻擊你的臉。這就是我所被命令的。那人說著,漸漸走離他。一會兒他才跟著過去,越過新河流,往前走,會有一叢銀色線條,像骨架一樣立著。他揮下的一點汗,這是還未有過的,滴向土壤石塊,穿過孔隙直往下。
你能刻印自己的臉嗎?狙擊手沒回頭,走路時,風幾乎掀起他的面罩,或者早已割破他的面頰。他走得有點吃力,回想之中,一個被阻礙的夢境,他哪兒都不能去,死亡的臉沖落下來。
如果刻印這條河,行嗎?會有一張毒河流的臉嗎?狙擊手繼續問著,小但清晰的聲音針一般刺著他的眼周。聲音呢?刻印聲音,比如一隻蟲子展翅的聲響,非常脆,有些悲傷,因為透過牠,事物有被看透的角度。你想過嗎?
楊昏氣喘吁吁地走在後方。狙擊手的聲音很快,留下的路線他未曾見過。但是,可以推測。他閉起眼,停下來彎著腰換氣。再不到夢裡去,恐怕再也走不動。狙擊手愈走愈遠,他看見的,再堅持一段路,就能讓這裡開一整片的花。實在不行了。狙擊手為他張開的弧度,又收縮起來,要貼在他身上。像滑了一跤那樣摔進夢裡,或真正的地層裡,楊昏在來之前見過的,分散成顆粒的紅色,流在液體裡。這在旅途中遇見,得馬上避開,現在,好像要奔進他身體裡,又嘩地一下直直透過他的眼後去了。他驚得一下站直起來。他的夢成了不同的密度,物質縮小,彷彿是他變大。一會兒他發覺這是有狙擊手後的夢境。
他聽見顏陡在外頭大聲說「是的!」,鏗鏘擲地,感覺很舒服。當然,你來看看更好,親眼瞧瞧。這是對夏海說的。楊昏記得的畫面和顏陡不同,他見到許多個三角,不等邊地,要完全進入沉靜才能再組合。可是它們完全碎了。
楊昏睜開眼,紅花近在額前。不是看到的,景色先擁抱他的身體,柔軟的草,還未能長得翠綠,更像一片陰影,紅花因而燦爛地像整個世界的原貌。狙擊手也在紅色裡,藏在花紋稜角裡,從甫誕生的形樣,到終點的些微揭露,他竟看見了,像拋棄這個被給予的身軀,重新用真正的視覺看見。狙擊手是坐在躺臥的他旁邊等待著,目不轉睛地凝視他。
對了,笑容是紅花的一部分。楊昏想著,在撲面的花間找狙擊手的笑容。那夢裡縮小的物質退在後頭,就像星星,也有人利用它們來安睡,一種非常熟悉,充實的觸感來臨,他看見狙擊手細細的髮梢,那是軌跡。
你經過無數次旅行才新生於此。楊昏說,說出聲來。
無數也就是唯有的一次啊。狙擊手說。
你自己決定來的嗎?楊昏問。
怎麼會呢?狙擊手回答。
你認得我們?
一個都不認得。
楊昏點點頭,像接受了。狙擊手移開目光,在側耳傾聽。
好漫長呀!一會兒他說。楊昏聽不見,但想那說的是歌聲。本來是歌要成為河流,現在河流成了無知。
若是攻擊河流,真正的河也會死。狙擊手說。他們分別想著這件事。你想粉碎什麼時候來,歌何時唱完?
楊昏的手臂被拉住,以一份不可能的力氣被拉起來。狙擊手眼中累積的東西是用於發射的,為了他們被留住的。他受住手的突然一痛,照理說,不該會痛的。狙擊手冷淡地望著他。
時間掉在這裡。要花多少時間創造時間?還是說和植物一樣,一瞬間而已。狙擊手沿著草地走。你看,那要多少時間創造我?
要把狙擊手的面孔看清,讓他頭痛欲裂。楊昏的眼淚又大顆大顆地掉下來,並沒有被看見。他知道,因為有毒的河流,植物也變得有毒。若是水塔再次出現,這構築的一切又將毀去。這不是他所希望,不是只要完成任務而已,他不要再見到毀滅,或隨之遺留的氣息。倏地他抬起頭,看著刻意走出他視線的狙擊手。
從來都沒有新生,還沒有,全然沒有發生。他說,咬緊牙齒。事情確是如此。狙擊手無聲地垂下頭,接著笑了。獨立地,不在任何事物之中的。
歌聲從范陷的身體流出,即使他不開口,不打開身體的孔隙,歌也繼續存在。說到底有什麼屬於這身體呢?但此刻所行,就像去挽留住屬於它的東西。范陷走著,有時從河流裡濺出,活的水銀狠狠咬他的小腿,他不理會,覆在身上單薄的衣物血跡斑斑――就連楊昏要消滅在幻覺裡時,血都還沒被召喚出來――他想一個被稱為「自己」或「我」的形式有很多種,血液是其中一個,但分離出來,對這星球另有他意,他不管,沒閒暇管。
你何不像那人一樣放手不顧?狙擊手說。
這卻令楊昏十分憤怒,不畏電流之痛,捏住狙擊手的肩頭。還帶有母星特質,未和肉體完全融合的浮游層從他指縫間逸出,閃出花朵枯萎的色澤。狙擊手的臉色變得較像他們,但楊昏看來,像尖刻的幾何與無秩序的顏色。
狙擊手被他抓住,並無防備,疼痛於他還只是一種界線的薄弱,這狀態傳到楊昏身上,像所有悲傷的記憶湧進頭顱,他放開對方,伏在地上,抓住土壤。些許小型植被從他身周長出,不能長高。他見到,把那些長起的都捂住。別長,還不行。葉片便吸進他軟弱的手掌中。
許久他才想起狙擊手還在,可是他真想一個人走,沒想過是這樣的,即使有延遲的快樂,他也感覺無力面對。抬頭時狙擊手不見蹤影,楊昏爬起,極力阻擋著後悔。他多半已偏離任務的意義很遠了。不尋找,也不刻印,如此他還有什麼用處?他想起范陷,又要哭泣,現在范陷是不得不斷絕連繫,他討厭這樣。討厭范陷的身分,討厭這顆星球。
我也討厭。狙擊手的聲音從前方傳來。
不要你同意!楊昏心想。聲音被截斷。
我討厭血液。聲音從另一頭傳來。楊昏正要發怒,卻發覺那來自范陷。來自范陷,由狙擊手發出。
為什麼不能說話?聲音換成了狙擊手。除了不觸碰,也不說話。我討厭這樣。
他說「討厭」時帶著笑意,好像在贊許這個字的出現,而不在於展示意圖。楊昏對此要氣也氣不起來,狙擊手並未延續他的怒氣,像個玻璃瓶般滑開。
但是,感覺不到我,聽不見我,是應該的。狙擊手說。我卻聽得到,用穿透的方式。你將我打倒在地,我也不反抗,不攻擊。我還沒擁有那麼多,夏海是唯一告訴我名字的人,在你們全部之中。自己持有的,我不在意。那離我太遠。
楊昏向前走去,看見狙擊手首先轉向他的一雙眼睛。
曾經是有的,曾經甚至不必接近,就能擁抱。他說。在我們一無所有的時候,不必集結,就在一起。
(此為精采節錄,更多內容請見《雙重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