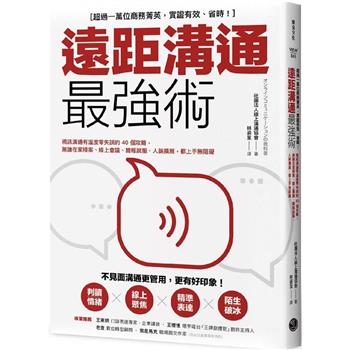棲身書寫
殷宋瑋
自序
歪河上的黑鎮(Hay-on-Wye)是位處英格蘭與威爾斯邊界的小鎮,人口僅有一千五,卻因擁有約三十間二手書店和人文薈萃的文學節而聞名於世。在英國生活多年一直想造訪,唯其地處偏遠,交通亦不便;遷徙英格蘭西南角的 E 城後,終於在二○一○年的九月中旬,乘搭火車至 H 城再轉搭班次并不頻密的公車,輾轉逾四小時才一償夙願。
迷林型的小鎮,幾條街道半個下午即可逛完。書局多但大小皆無當,一般讀者或許能有收獲,較專業或品味殊異的書種則乏善可陳。唯有一專售詩集的小書店令我們欣喜若狂,J 尋得捷克詩人賀洛布(Miroslav Holub)英譯本如獲至寶,和書店店長亦相談甚歡。
那一年自一月起大學放我半年研究假,進入暑假仍在撰寫《蔡明亮與緩慢電影》英文書稿,但間中也斷斷續續寫些中文散文。此行乃十月開課前給自己放個小假,卻也帶了些原稿用紙以備不時之需。
租了兩晚民宿,小鎮書局盡覽,一個下午我突然想有個自己的空間,遂和 J 分道揚鑣,獨自往一家老字號的大型書局,在二樓落地窗前的沙發坐下。此二樓亦是頂層,極高的天花板,原木的地板,樓層此端窗戶面向狹窄的馬路,兩張長型紅絨布沙發排成直角,其間一條傳統花紋大地毯,靠另一面牆的大書桌上擺有零星書本。空無一人。
下午近四時的秋陽低低斜斜透窗而入,滿滿灑在一張沙發上,我坐下。另一張無陽光斜照的沙發上躺著一隻貓。
我坐下,閤上雙眼,吸納陽光的暖意,身心漸漸平息。我打開雙眼,取出稿紙,開始書寫。
我開始書寫,用一頁五百字的稿紙,以大開本雜誌為底,在沙發臂墊上,持藍色原子筆,一個字接一個字,無中生有地填寫方格子。好奇的貓滑下沙發,緩步踱來,躍上這一張沙發,若無其事繞過我身後椅背,然後在我身邊蜷曲,繼續睡眠。我瞄了牠一眼,繼續書寫。
我並非愛貓之人,但那個下午的畫面,髣髴就是「書寫」的化身,詞典內此字條旁只需附上定格光影,不用說文解字。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存有」:我的存在有實體物質的陽光、沙發和睡貓,我的存在亦棲身於右手握筆在方格子上書寫的每一個中文字。
我寫,故我在。這不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命題,而是時空中具體可觸摸可感知的實物和行動。
無論是英文的學術論述或中文的散文創作,行至中年,我倏然發現書寫此一行動乃界定我存有與身份的最明確指標。學術研究固然是專業工作的一部份,舞文弄墨也難免風花雪月的附庸形象,但逾三十年來書寫不僅是我生活中唯一不可或缺的行動,那個下午的那一刻,由斜陽、沙發和睡貓共同組成的畫面,實則是我生命本質的凝結。從新加坡起始,行經台北和劍橋,L 城和 E 城,到此地處偏遠人煙稀少書店林立的小鎮,我走到那裡,寫到那裡——其他事我可以不做,但我不能不寫作。
棲身書寫的光影定格,那一刻我感覺無比幸福。
感覺幸福,因為書寫此一行動是如此單純,只要有筆、有紙,便可以走到那裡寫到那裡。難的是年歲漸長後生活不由人,物質上縱使能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要同時保有自己的時間和自己的心情來煮字療饑,卻不是容易的事。但無論如何,比起其他藝術形式,書寫仍是輕便簡易、經濟實惠,堪稱最民主的創作媒介。
感覺幸福,更因為書寫的那一刻總能讓我氣定神閑、心智清澄,髣髴置身於另一個世界。日常生活是如此繁瑣而庸俗,蠅營狗苟惶惶不可終日;書寫則具有提煉和沉澱的作用,讓平庸的生命彰顯深邃的意義。若沒有書寫的軌跡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些記錄,回首前塵,或許僅剩一些生活照的影像而已。畫面也許能清晰留住時空,但文字卻更能準確捕捉心情。
「對於一個已經沒有家園的人來說,書寫變成了棲身之所。」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名言似乎對現實中家園的喪失有喟嘆之意,書寫的棲身之所髣髴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這是我的第五本文集,兩本寫於出生地的新加坡,一本於唸大學時的台北,一本於唸研究所的劍橋,這本則是博士畢業十年來長居英國的結果,書寫之地涵蓋台北和英國。台北的記憶洶湧澎湃,幾番因研究或開會回返總會奮筆疾書;英倫的天氣陰晴不定,四季的輪替為文字增添異質的風景。遠離家園於我並非現實中的不得不,卻也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台北四年,英倫十四年,三十餘年不停的書寫,原來一個一個的空白方格子才是極樂世界。棲身書寫,不是因為現
實中的失樂園,它實則乃生命中的尋夢園。
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潮汐靜止之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4 |
文學作品 |
$ 324 |
小說/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5 |
高等教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潮汐靜止之處
本書收集2003年至2010年的十一篇散文,分為“台北的記憶洶湧澎湃”
以及“英國的天氣陰晴不定”。
〈台〉收錄的四篇散文:〈潮汐靜止之處〉、〈從四百擊到一○一──給楚浮的一封信〉〈築夢者──2003/4秋冬電影筆記〉、〈許多許多年以前,許多許多年以後〉,乃作者兩度訪問台灣期間所撰寫的篇章,篇章以台北為基地,思考文化、電影、教育等課題,并廣及華語文化圈,尤其是中文在新加坡的處境,觀察入微,反省深刻,乃新加坡作家中少見兼具知性思維、理性批判和感性情懷的作品。
而〈英〉收錄的七篇散文:〈格蘭騫士德〉、〈啟程,以及抵達的謎團〉、〈遠方〉、〈拂雪〉、〈冬季的遊牧者〉、〈仲夏夜〉、〈慢走〉,為作者旅居英國、踏上學術生涯的心路歷程。 這系列文章可稱之為「與青年學者的對話」,以在劍橋唸研究所的學生為對象,進行一系列關於學問、知識和研究生活的討論。其中寫景部分尤其細膩,呼應寫〈再別康橋〉的徐志摩,從四季的氣候到景物的變化,絲絲入扣,引人入勝。
作者簡介:
殷宋瑋,本名林松輝,一九六五年生於新加坡。台大中文系畢業,英國劍橋大學漢學系碩士、博士。出版有文集《晚風莫笑》(華初文叢,1985)、《名可名》(1989年台北自印版,1994年華初文叢版)、《無座標島嶼紀事》(草根書室,1997)、《威治菲爾德書簡》(青年書局,2004)。現旅居英國。
作者序
棲身書寫
殷宋瑋
自序
歪河上的黑鎮(Hay-on-Wye)是位處英格蘭與威爾斯邊界的小鎮,人口僅有一千五,卻因擁有約三十間二手書店和人文薈萃的文學節而聞名於世。在英國生活多年一直想造訪,唯其地處偏遠,交通亦不便;遷徙英格蘭西南角的 E 城後,終於在二○一○年的九月中旬,乘搭火車至 H 城再轉搭班次并不頻密的公車,輾轉逾四小時才一償夙願。
迷林型的小鎮,幾條街道半個下午即可逛完。書局多但大小皆無當,一般讀者或許能有收獲,較專業或品味殊異的書種則乏善可陳。唯有一專售詩集的小書店令我們欣喜若狂,J 尋得捷克詩人賀洛布(M...
殷宋瑋
自序
歪河上的黑鎮(Hay-on-Wye)是位處英格蘭與威爾斯邊界的小鎮,人口僅有一千五,卻因擁有約三十間二手書店和人文薈萃的文學節而聞名於世。在英國生活多年一直想造訪,唯其地處偏遠,交通亦不便;遷徙英格蘭西南角的 E 城後,終於在二○一○年的九月中旬,乘搭火車至 H 城再轉搭班次并不頻密的公車,輾轉逾四小時才一償夙願。
迷林型的小鎮,幾條街道半個下午即可逛完。書局多但大小皆無當,一般讀者或許能有收獲,較專業或品味殊異的書種則乏善可陳。唯有一專售詩集的小書店令我們欣喜若狂,J 尋得捷克詩人賀洛布(M...
»看全部
目錄
棲身書寫(自序)
鳴謝
當下,也在遠方:讀後感代序 / 林高 (新加坡)
穿行者 / 黃慧芬 (台灣)
寫給遠方的信 / 張經宏 (台灣)
(一)台北的記憶洶湧澎湃
潮汐靜止之處
從四百擊到一○一 給楚浮的一封信
築夢者 2003/4秋冬電影筆記
許多許多年以前, 許多許多年以後
(二)英國的天氣陰晴不定
格蘭騫士德
啟程,以及抵達的謎團
遠方
拂雪
冬季的遊牧者
仲夏夜
慢走
代後記:中文作為能力(而非身份)
鳴謝
當下,也在遠方:讀後感代序 / 林高 (新加坡)
穿行者 / 黃慧芬 (台灣)
寫給遠方的信 / 張經宏 (台灣)
(一)台北的記憶洶湧澎湃
潮汐靜止之處
從四百擊到一○一 給楚浮的一封信
築夢者 2003/4秋冬電影筆記
許多許多年以前, 許多許多年以後
(二)英國的天氣陰晴不定
格蘭騫士德
啟程,以及抵達的謎團
遠方
拂雪
冬季的遊牧者
仲夏夜
慢走
代後記:中文作為能力(而非身份)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殷宋瑋
- 出版社: 八方文化創作室 出版日期:2012-01-01 ISBN/ISSN:978981428273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7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