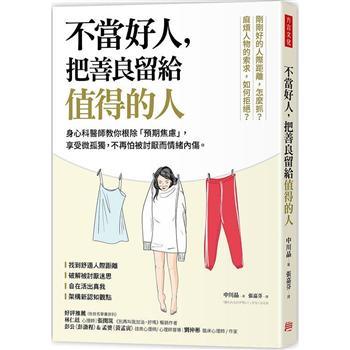編者序
陽光追想曲
「青少年台灣讀本散文卷(3)」《希望有一天》,計收錄二十三位作家二十三篇作品,多音交響,聚合成一部台灣作家的「陽光追想曲」;希望有一天,陽光在台灣上空和暖臨照,長住久安。
本卷的編輯策略,揚棄以作者年齡排序的方式,而以議題分類、統整、串織、參照的型態呈現,期望能夠展現當代台灣作家的多重關懷面向與對話線圖。本卷包含三大主題面向:歷史記憶、族群關係、民主化與本土化歷程。這三大主題面向,串織出台灣當代社會的歷史圖像,而在這些文字背後,則流動著台灣當代知識份子的精神魂體;整體而言,本卷或者可以視為台灣當代精神史的一個切片。
本卷在作品選擇上,包括幾個考量要素:議題性、多元性、文學性。在世代的跨越性方面,遠較其他選本更大,有超過八十歲的葉石濤先生,也有才二十歲出頭的李怡道;而族群、性別的多元性也是一大特色。再者,以書寫手法而言,本卷所選載各篇章,都具有理性思辨、知性知識、感性情感的多重流動特質,在文學技巧與藝術美學方面,編者亦未曾輕忽,希望不致有「議題掛帥.文學稀薄」的問題。
一般而言,這些篇章可以歸類為所謂「知性散文」的範疇。知性散文在散文書寫中,難度頗高,必須關注的面向與細節較複雜,而且這些面向或有相互矛盾拉扯的可能;在知識性方面,若不知節制與再造,則易流於百科全書式的過度賣弄;在理性批判方面,收放之間,拿捏困難,或者深度不足,或者論理過硬,都非佳作;在情感性方面,要如何與知識材料與理性思辨相互結合,達致互滲交融的境界,都考驗著寫作者的智慧、才華與功力。當然,這也成為本卷在編輯上所遭遇的最大難題與挑戰。
若再以議題的聚焦性而言,本卷所選諸篇章,或者可以稱之為文學性較強的「台灣文化論述」。「台灣」,是一個地理空間的名稱,也是一個文化載體與象徵符號;台灣這個地理空間,長期歷經由外部移徙而來的不同政權統治,「台灣文化」成為一個複雜多元的實體,也是一個各方解釋的「象徵符號」。
以歷史記憶的書寫而言,本卷所選作品彰顯出作家在追溯自我身份、家族身世、族群記憶的生命履痕。台灣在各個世代政權的統治經驗中,在地的文史教育長期缺席,台灣住民一度嚴重罹患「台灣歷史失憶症」,無論是對於地理空間的台灣、抑或文化載體的台灣,都認知稀薄、陌生疏離。這些作家們也無法置身其外,他們的成長、受教育歷程,經常正是與故鄉母土裂離的過程;然而,成長之後,在各種內外在契機與衝擊之下,他們深刻反省自己的無知與傲慢,並且以謙卑的靈魂,返身走進曾被自己離棄的幽暗歷史長廊,逐一審視這塊土地的時間鑿痕,重建自己的身世。
扣緊這樣的思惟脈絡,陳芳明〈相逢有樂町〉中,父親孤獨蒼涼的身影,與蹲踞在牆角的歷史身影相互疊合,而傲慢的兒子,竟然必須在繞過地球的另一端之後,才在異鄉打開自己故鄉的歷史書頁。李筱峰〈走入悲情〉,說的則是揮棄悲情的唯一路徑:如何不曾走入、了解、感知、體會歷史,如何能夠找到真正走離悲情的陽光心路。林世煜〈椰子樹的長影〉一文中的「走入」,則是更深的歸鄉行旅;他所走入的,不是個人的歷史記憶,然而,他所召喚的,卻是超出個人的、台灣住民的集體身世。唯有將國族的悲情歷史視為「集體記憶」,才有超越悲情,共赴未來的可能。
人類總是自我標榜迥異於其他動物,有超越個人的襟懷,然而,在這座小島中,他們卻為了一個悲情事件的「受害者」、「非受害者」身份,劃清楚河漢界。事實上,集體歷史記憶的意義,並不在於「記憶」的同質性,而在於「記憶」互涉共感的可能性。邱坤良的〈坐火車向前行〉、賴舒亞〈挖記憶的礦〉,寫的既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卻也是一座城鎮、一個世代、一群人的歷史畫像。而陳文彬〈青春已死,青春不死〉則恰好相反,他寫的固然是自己無緣參與的「抗日史」,卻也暴顯出一名新世代知識青年對自我生命意義與理想的追尋。自我與他者、此刻與彼時、此地與他鄉,在他們的作品中,既分線而走,又融鑄一體;這正是文學的能量。至於郭力昕的〈執著與叛逆的味道〉,更是一則記憶追想曲,他透過自己對攝影的學習、感動與實踐經驗,凝視一些攝影家熱情實踐的身影,追想七0年代台灣,那曾被自己遺忘的動人氣味。
追索台灣歷史記憶,必然發現台灣的族群關係與族群文化是如此複雜多元。田威寧的〈沒人寫信給爺爺〉寫出國共鬥爭所造成的兩岸分隔,當年跟隨國民黨來台的少年,經過漫長的等待,卻以垂老的身軀返鄉,寫出外省第一代流離、無所歸著的精神圖像。同樣是離散經驗,台灣原住民族的「在地離散」則是另一則故事;孫大川〈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透過母親堅毅鮮明的生存姿顏,重返母族歷史記憶,希望找到昔日的豐美文化,重寫一則屬於這座島嶼的繁複史詩。這樣的想望,在利格拉樂.阿的〈血與屈辱的烙印〉中,似乎還未露出可能實現的曙光;因為,即使可以找回自己的名字,但名字背後的屈辱烙印,仍然可能要歷經漫長的時間才得以刷洗乾淨。族群共和共存是當前台灣人的集體意識,葉石濤〈族群和諧共存的新風貌〉就比較樂觀,他認為這個理想是一個有希望的進行式。這樣的希望,在呂美親〈無仝階段,猶原堅定的滾陣〉中清楚流露;族群文化的「重建」,必須以比「流失」加倍的時間和努力才得以完成,而自我族群文化的主體與自信,正是台灣各族群文化得以把手言和的前提。紀駿傑的〈原住民,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則提示另一種「共和」的可能性;從一個更寬廣的文化視野切入,最美好的「共和」不是抹消差異,而是發現、保留各種差異,讓台灣文化成為繽紛的萬花筒,而不是一塊標準化的鐵板。
撥開歷史迷霧,尋回土地姿顏,建構一個自主、和諧、百花齊放的美麗新世界,可以說是現當代台灣社會的基本課題;而這樣的想望,都必須透過具體的實踐來完成;對威權體制的批判、對社會文化的關懷,都是前往新世界的路徑。散文中,有關民主化、本土化,書寫台灣政權轉型的篇章不少,王定國的〈叫總統太沉重〉,從父親、母親不同的角度觀察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企圖在惡夢中找尋一絲亮光;小野的〈七年淋漓〉也同樣閃動光亮;他認為民主總須經歷陣痛,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民主化看似混亂的現象,其實是充滿生命力與無限可能性。
李敏勇〈另類塑像,文化解放〉則提示我們,希望的泉源在於掙脫舊有威權體制的桎梏,拆除象徵威權的符號,才有獲致文化解放的出路。這樣的希望,是許多人以青春和鮮血換取而來;魏貽君的〈向權力說真話〉,寫親族叔叔正義不屈的風骨,為台灣民主花圃的繁美灌注清泉。江文瑜〈我們正在描繪台灣的未來〉中,核四公投的環島苦行,也是一樣的身體實踐,一步一履,描繪一個未來實景。而年輕的張鐵志,也就循著前路走去,以〈從美麗島到美麗之島〉一文,檢視「音樂」如何照亮島上的陰暗角落。更年輕的李怡道,以〈我們把這個標幟給搶回來吧〉,用新世代的聲音,指出一般民眾的失憶與迷思,認為民主化是累積的,並且需要持續灌溉。向陽對媒體文化的反省,廖永來對文學作家的反思,都指向林義雄對台灣未來的想望;希望有一天。
希望有一天,歷經漫長的共同努力,島嶼上空的雲霧得以撥除,台灣春天的陽光綻現,歷史的悲情得到撫慰與救贖,威權體制的魅影被陽光蒸發,喜樂的詩歌傳響島上每個角落,你我,在希望的國度裡,一起微笑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