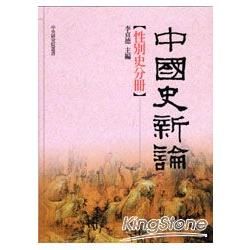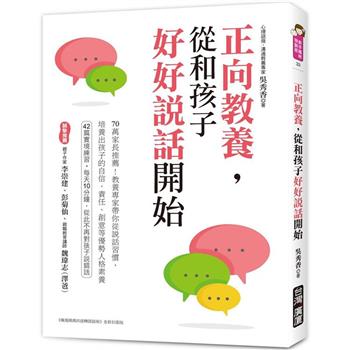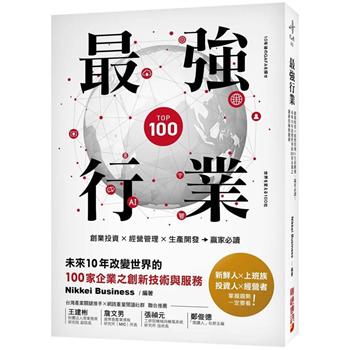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中國史新論》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2008年10月22日
史語所八十周年所慶日
導言
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
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男人在海邊釣魚,釣到一條美人魚。美人魚為了脫困,提出條件,答應每個男人各許一個願,換取她重返大海的自由。男人們表示可以接受,便由第一位提出要求:「希望我的智力變成現在的兩倍!」美人魚回應:「成了!」轉眼間,這個男人開始演算數學公式、觀測天文物理,儼然是個科學家。第二位見狀,趕緊加碼:「希望我的智力變成現在的三倍!」美人魚回應:「成了!」說時遲、那時快,這個男人突然搖頭晃腦起來,不但吟詩誦詞、縱論古今,並且侃侃而談,分析人心幽微、時局世變,似乎是個人文大師。第三位心中竊喜,決定更上層樓:「原來如此!那麼請將我的智力變成現在的四倍!」美人魚建議他三思,因為這個願望引起的變化太過劇烈,還是選擇金銀財寶等物質享受吧!然而,男人不依,堅持所許的願望。美人魚見他情詞懇切,便答應了他的請求:「成了」。
……
頓時,這名男子,變成了一個女人。
1990年代中期,網際網路發展得如火如荼,各種笑話在電子郵件之間流竄,國外友人為了慰勞我案牘勞形的學者生涯,轉來上面的小品 。就像傳統「從前有三個人」之類的故事,或新興氾濫的網路訊息一般,美人魚的笑話有各種版本。然而,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最終,引人入勝的,仍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驚奇,而這個驚奇挑戰了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
婦女史的出現和發展,毋寧也是抱著量變的修辭匍匐前進的。攀附於「客觀求真」史學精神的驥尾,託身於「求全窮盡」治學態度的青雲,學者或打著「補充歷史」的旗幟,呼籲「將女人還給歷史,將歷史還給女人」,或坦言收集婦女相關史料,「是為歷史,而非為婦女」 。無論是策略性說辭,或是誠摯的初衷,婦女史在萌芽發枝的階段,都曾經以量變作論,略帶謙卑地側身史學之林:「我們只是來彌縫補缺!」不過,既然有可彌補之處,就表示原本的圖像並不完整,雖說僅僅是提供女性這邊的經驗,卻在增益歷史敘事的同時,暗示了改寫的必要,進行著改寫的動作 。質變在量變的過程中靜悄悄地發生,雖然未必高呼挑戰或批判,實作的結果卻持續攪擾著既定的歷史意識。本書的出現,便是上述史學發展的一項印證。
1970年代,當美國的婦女史學者以補充之名挑戰歷史學的論述與架構時,台灣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才剛起步。1975年,李又寧與張玉法兩位教授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抄錄珍稀文獻,出版《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兩冊,促成數本學位論文的誕生。1977年,鮑家麟教授自美歸來,在臺大歷史系首開「中國婦女史」課程,並於1979年出版《中國婦女史論集》,引發學生興趣,並介紹既有的成果 。1980年代,台灣的政運與社運皆風起雲湧,女性主義的衝擊,不論校內校外都可窺見。1982年,台灣第一個婦運雜誌《婦女新知》創社發刊;1985年,在亞洲協會的贊助下,學院中的第一個婦研單位「臺大婦女研究室」成立。不過,這些變化對歷史學界的影響並不明顯。由近百位老將新秀合作完成的《中國文化新論》,一套十三冊,匯集了當時文史哲學界的眾多寫手,綜論中國史各個領域的最新研究,1982年甫出版,即成為年輕學子入行必備叢書。然而,其中並無「婦女篇」,僅有的一篇專論:〈正位於內——傳統社會的婦女〉,是放在社會史的脈絡中,概述中國父系家族內各種女性的生活面貌;另一篇涉及女性處境比較多的,則是「宗教禮俗篇」中〈琴瑟和鳴——歷代的婚禮〉一文 。
透過父系家族的架構,以及維繫此架構的重要機制——婚姻——來了解婦女,可說是婦女史的入門課題,也一直吸引著學者的目光。不論是親屬結構、婚俗禮制、夫妻生活,或守節再嫁,都占據著婦女史出版的大宗。1980年代末期,台灣政壇發生重大變化,解嚴打開新局,帶來多元氣象,婦女史研究穩定成長,論文集陸續出版,但課題和取徑並未出現明顯轉折。除了家族與婚姻之外,婦女史相關文章仍多環繞著古代的才女名媛、太后女主和近代的女權運動作論 。中國婦女史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恐怕還是要到1990年代以後,而其欣欣向榮的發展,卻正挑戰著將「婦女」視為單一群體的心態,反思「婦女」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角度。
1990年代,台灣的思想更加解放,言行益發激昂,或為反抗性侵害,或為追求性自主,或為爭取工作權,或為保障財產權,街頭運動,此起彼落,眾聲喧嘩,訴求非一。各種訴求之間,策略未必相同,目標時而扞格,雖都掛著女權婦運之名,卻可能因階級或族群利益衝突,而分手出走、另起爐灶 。「婦女」不是一個內容同質、外觀一致的團體,在運動界的實務經驗中獲得痛苦的印證。就在此時,聯合國正式宣示了「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理念,主張評估包括立法、政策、方案等各種計畫性行動對男女的不同涵義。透過將雙方歧異的經驗和關懷作為設計、實施、監督和判斷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達成性別平等的最?目標 。台灣雖非聯合國的會員國,但亟思參與國際社會、與世界組織接軌,女性主義學者與社團遂將性別主流化的概念引入,一方面擴大婦運的架構與目標,另方面推動正式體制運作中的男女平權。十年之間,陸續通過了堪稱「性平三法」的性騷擾防治法(1995)、兩性工作平等法(2001),和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性、兩性和性別,揭示了台灣婦運行動焦點和思維模式的發展與演變。
1990年代,臺灣的學界也同樣生氣蓬勃。學者為了分享經驗、吸收新知、交流理念,乃至結盟發聲,除陸續在校園內成立女性研究單位之外,也跨校串聯,於1993年組織臺灣第一個女學會。而這些社團,不論在名稱或發行刊物的標題上,亦出現遣詞用字的斟酌與轉變。創立之初隸屬於臺大人口中心的婦女研究室,原本發行《婦女研究通訊》,提供學界交流平台,1994年改名為《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2001年改為《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又於2003年改為《婦研縱橫》。而不論中文刊名是兩性、性別或婦研,英文刊名皆冠以gender一字。1990年,婦女研究室發行亞洲第一份性別研究學術期刊《婦女與兩性學刊》,2002年則改名為《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一方面因婦女研究室的成績斐然,另方面亦因應學術風氣的轉變,1999年,臺大人口中心正式更名為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也更名為婦女與性別研究組。繼臺大之後,清華大學也在亞洲協會贊助下,於1989年成立兩性與社會研究室,而於2000年更名為性別與社會研究室。之後臺灣各大學陸續成立相關社團,通識與專業課程持續增加,2000年起更設立研究所層級的教研單位,但不論是社團、課程或研究所,大多冠以性別之名,少有單純稱以婦女者 。至於女學會,則在討論學會理念和行動目標之後,確認會名為臺灣女性學學會(Taiwanese Feminist Scholars Association),以喚醒女性意識、改善女性地位為主要目標,並在章程中說明將推動校園中的性別研究 。
從婦女到兩性再到性別,名稱的改變表現了對課題性質的反思。婦女史學者雖亦參與上述社團,但大多並未直接回應社運論題。婦女史研究的量變到質變,除了外在氛圍的薰染,亦有內在理路可循。1986年,美國歷史學者Joan Scott倡言以「性別」(gender)作為歷史分析的類別,拓展僅僅以婦女作為研究對象所帶來的局限,除了將兩性共同納入討論範疇外,也檢討以馬克思理論和心理分析理論解釋性別體制的不足之處,提倡以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解釋性別權力關係,強調語言文字的建構力量。由於性別差異不斷被利用來合理化其他無關男女的社會現象,因此Scott主張在沒有女性身影的歷史文獻和場域中,也可以分析性別權力關係 。1993年,臺灣第一份婦女史專門學術期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創刊,在「學術討論」專欄中,成令方介紹女性主義對英美歷史學界的啟發,便詳細說明了Scott的後結構主義論點及其對歷史研究的挑戰 。雖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大部分的論著仍多以婦女為研究對象,但在「學術討論」和「研究動態」兩個專欄中,卻經常出現以性別為題的文章,作為跨學科交流的焦點。1996年,廣受年輕學生歡迎的《新史學》雜誌,出版了「女/性史專號」,則嘗試以標題中的斜線,提醒讀者婦女、兩性與性別的複雜離合關係 。與此同時,各種「後學」(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亦相繼登台,頻頻向歷史學者招手。婦女史學者或迎或拒,卻不改「史無定法」的行規,鮮少在前言結語申述特定理論或主義(即使女性主義也很少)。然而,不論從標題、取徑、議論,或分析角度來看,婦女史研究都已發生變化,以性別為題的論文頻頻出現,漸漸取代了探求婦女經驗、補充歷史敘事的素樸期望。
儘管如此,中國史的學者使用性別一詞的方式並不一致。有時性別只是婦女的代名詞,說明研究課題與女性有關,有時則是為了凸顯探討的重點在於兩性關係或同性性關係,有時,則是以性別作為一種歷史分析的類別,企圖在各種專史領域中考掘語言文字表現權力運作的方式。各種用法並存,數量與時俱增,卻不見專文檢討、回顧或分殊。性別一詞,既沒有引起類似美國歷史學界般的爭議,也沒有經過如中國大陸婦女史學者的正式翻譯引介,就在單位、刊物和文章標題的異動中,悄然進入了台灣的史學界中 。
事實上,中國婦女史的研究素材,向來以男性書寫女性最為大量。家族與婚姻的研究,大多從男性對女性的規範與期望入手。深入家族倫理與婚姻生活之中,則不論是生育禮俗、親子關係、表揚節婦、緬懷亡妻,或是鬥毆相傷、財產分配,都涉及兩性互動。就算擴大史料範圍,走出正史的格局,不論是醫藥方書、墓誌碑銘、文人文集、律令檔案、筆記小說,乃至出土文書或圖像等物質文化的史料,亦鮮有不是男性記錄或創作而成。不論入仕、出家,或行醫、執法,留下文獻者,既然大多是男性,一旦言及女性,便不乏男性觀察、描寫、分析、褒貶,乃至裁判女性的痕跡。尤有甚者,女性的生命經驗被抽離出現實情境,凍結成特定的樣貌,作為教化的象徵,或理解世界的模型。女性身處其中,或參與建構陰陽大分的性別體制,或質疑挑戰父系倫理的重擔壓力。由女性書寫、創作或在無意間留存的史料,雖可藉以強調女性主體意識,卻也多包括書寫者對男性的情感與意見,並且是相對於原本男性為主的一種發聲。亦即,研究中國婦女史,很難不牽涉男性,過去單純以婦女為對象,忽略了男人在幕後那隻其實仔細看就看得見的手,恐怕未能得實。若真要發掘女性的處境與地位,不能不從「關係」的角度出發,探討兩性的互動及其影響,而這包括了追問女性文獻稀少甚至闕如的領域。換言之,「性別」既是傳統社會歸類人群的一種方式,也就成為現代學者考察權力意義的一個角度。而這,正是本書題為「性別史分冊」的緣故。
本書是為慶祝史語所創立八十周年而作,四年前籌備之初,即邀請不同斷代的學者,針對各個時代中涉及女性的特殊材料或重要議題,進行介紹與綜述,並且很榮幸地,獲得北京大學鄧小南教授的支持,參與寫作。其間,舉辦兩次工作坊,並經數十封電郵往返討論,最後確認本書性質,應兼顧概觀與深論,除階段性總結學界最新研究,提供年輕學子整體的圖像之外,亦指出可進一步鑽研的課題,期望引導未來方向。同時,為了展現新氣象,親近讀者,決定每一篇文章皆以一個故事起始。十位作者中,陳昭容、劉增貴、鄧小南、賴惠敏和游鑑明五位,分別介紹了各自專業斷代中性質特殊而重要的史料,包括商周青銅器與隨葬品、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唐宋墓室壁畫、誌銘和敦煌吐魯番文書、明清司法檔案,以及現代口述訪問紀錄等,說明它們如何可以作為婦女史的素材、看出哪些兩性互動的面向,以及截至目前在性別史研究上的意義。另外五位作者,劉靜貞、胡曉真、李玉珍、鄭雅如和李貞德,則就近年來較具突破性發展的領域,如歷史書寫、文學史、佛教史、家庭史,以及財產權等,申論婦女在其中的處境與地位,以及納入性別角度的分析後該領域的演變與特色。
雖然在標題上,或以史料為主軸、或以專題為範圍,但在行文中,介紹史料的作者亦針對各種專題舉例說明,綜論專題的文章則羅列新舊材料作為證據。新史料與新課題,都是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動力。最重要的是,十篇文章之中,七篇以性別為題,即使未標舉性別者,其討論實亦涉及父系家族內部,乃至脫離於其外的各種兩性關係。換言之,性別被視為一種人群的分類、象徵的符號,以及切入的視角,放在與階級、族群、輩份(年齡)等其他分類相互作用的脈絡中,成為更深入了解婦女議題的取徑。
例如,陳昭容利用商周青銅器與墓葬遺物探討財富與身分之間的關係,除了介紹墓葬中反映性別的物品(包括笄、玉蠶和紡輪)之外,亦分析影響陪葬品豐薄的因素(如女性墓主的妻妾身分、與丈夫下葬時間先後、與繼任者的關係,以及母家地位等),然後從女性接受與製作青銅器的角度,探討女性生前所具備的財力。全文藉由考古出土物勾勒商周性別關係,突破古代婦女文獻不足的限制。其中談到女性擁有具禮器性質的青銅器數量較少、等級較丈夫為低,卻擁有大量而精美非禮器的玉器時,最能彰顯性別與階級的交互作用,以及作者謹慎處理性別議題的態度。
經濟力影響女性獨立自主的機會,是20世紀以來婦女運動的說帖、女性主義的關懷,也是性別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宋代以降,史料豐富,不論女性在父家與夫家的財產權利,或參加勞動營生的各種經驗及其意義,國內外研究皆成績斐然。然而近世以前這方面的資訊非常缺乏,難以深入考察。陳昭容從器物表現女性財富的角度窺得古史之一隅,李貞德則透過近年出土秦漢簡牘、傳世文獻中之六朝故事,乃至政書禮律所錄田宅制度,說明漢唐之間女性對動產和不動產之取得、持有、使用與支配的情況,指出婚姻對女性財產權之決定性影響。雖然女性以嫁妝形式自父家取得貨財等動產的習俗變化不大,但從漢初單子繼承到唐代諸子均分的法律規範中,女性獲得不動產的機會與份量似乎益發不穩定。即使透過繼承取得田宅,基於婦人從夫的原則,也可能因出嫁而併入夫家。而在漢唐之間各種田宅制度的設計中,為人妻者皆無法獲得國家授予永久田產。除非離寡另立一戶或招贅主家,否則難以完整掌握個人的財產權。
然而,在沒有個人權利觀念、婦人以夫家為主要生活場域的傳統社會中,離寡招贅並非什麼令人欣羨的身分。鄧小南整理敦煌吐魯番出土之戶籍、賦役和契約文書,描繪其中女性參與農務、商販、手工業與宗教等各種生活的面向,顯示在法律名義上,寡婦或獨身當戶的女性固然可以獲得國家授田,但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卻可能捉襟見肘,慘澹經營。鄧小南此文,大量羅列「邊緣材料」,除出土文書外,也包括唐宋墓葬壁畫與誌銘,期望突破「經典論述」的成規,直指女性生活的實況。然而,從其歸納墓誌銘的特色,乃至壁畫人物的分布格局,普遍具有「男詳女略」、「重男輕女」和「男外女內」、「男前女後」的模式化現象,則似乎不論天上人間,凡人手所為,皆難逃經典論述的影響。
不過,這種情況,在儒家倫理尚未取得全面支配性力量的漢代,可能有些不同。也是處理墓葬及其中圖像的劉增貴,從陰陽之位、男女分職,和列女群像等三個角度整理漢代畫像,得出了一些與傳統印象不同的結論。例如,一般以為漢代男陽女陰,男尊女卑,男左女右,男耕女織,男外女內,男強女弱……,但從畫像所呈現的男女角色看,西王母的地位遠高於東王公,女性從事許多過去以為只有男性才從事的農業生產或商業活動,而男性也從事過去設想只有女性從事的庖廚炊煮。女性欣賞歌舞,參加宴飲,有自己的社交空間,甚至操兵器、行復仇,並不單純「以弱為美」。換言之,畫像中呈現的性別角色,並不如經典中絕對。雖然畫像摻雜理想,不見得都是實態的折射,但這樣的結論頗可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漢代社會。
過去認為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儒家倫理具有強烈的延續性與一統性,對其中的性別體制影響深刻,直到20世紀才經歷重大變革。此一說法,近年來已被眾多細緻的研究所挑戰乃至推翻。針對個別斷代不同專題的深入分析,清楚顯示父系家族倫理並非一直被視為天經地義,而朝廷與士大夫所代表的統治階層,也未必總是全心全意、毫無保留地推動並執行 。即使是向來吸引學者關注,成果輩出的家庭史研究,在經過重新檢視之後,也呈現出「活潑的彈性」 。鄭雅如以母子關係為例,從性別角度回顧中國中古的家庭史研究,著重母子名分的界定、母職內涵的建構,以及母子關係與家庭衝突三方面。她廣採正史、禮律、政書等建構和規範家庭倫理的傳統典籍,並在介紹最近研究成果時,旁及墓誌碑銘、敦煌文書、醫藥方書,乃至佛典造像等新出材料。這篇總結性的論文,分析禮法、人情、制度與信仰等各個層面的影響,描繪了家庭中複雜多變、不斷挑戰父系權威的人際關係。
人倫關係的實態較之禮法的規範微妙許多,在胡曉真討論明清婦女文學的篇章中更是昭然若揭。女作家群像以強烈的創作自覺、驚人的產出能量,以及積極參與編輯、批評與出版的行動為輪廓,和傳統的賢妻良母典型幾不相涉。她們或效法男性文人宴遊唱和,或將自己化身在姐妹情誼的小說中,或以創作為逃避家庭壓力的方式,乃至因女兒能分攤家事而兒子打擾創作便疼愛前者多於後者。尤有甚者,女作家筆下的暴力書寫,不論是霸道父親作態治死脫軌的女兒,或是同女互以割肉飲血表達強烈慾戀,都遠遠超過經典論述中的女性形象。作者回顧20世紀以來婦女文學史的發展,指出明清女性詩人和彈詞小說家的作品與人生,近年來在學者的爬梳之下一一浮現,幾已改寫中國文學史。
胡曉真在篇首提問:「婦女文學作品適合做婦女史的史料嗎?」在文中則羅列近年來學者探索明清才女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的成果以為範例與證明。其實,書寫與敘述都是再現的活動,並不限於女作家的自傳或小說。本書中劉靜貞、賴惠敏和游鑑明三位的研究都提醒著讀者,歷史資料,不論是抒情伸志的經傳、史傳與文集,或是作為尋求真相以為裁判依據的司法檔案,乃至貌似現場直播的口述訪問紀錄,都具有建構的性質,難免虛構的況味。
賴惠敏利用《順天府檔案》和「刑科題本」等資料探討清代婦女法律地位。她以王龐氏之死一案,討論夫殺妻的處罪論據與刑責,以及清代殺人案件的處理通則。又以春阿氏殺夫案為例,說明清末辦報風氣與司法改革背景之下,妻殺夫案件的可能發展方向。從地方到中央層層上報的審判紀錄看來,不論殺夫之妻或被殺之婦,都逐漸遭到妖魔化的描寫,以至於最終顯得罪有應得。婦女的法律地位問題,可以從律令典章和民刑案件等各種角度切入,本文採用夫妻相殺為例,具體呈現夫妻在家族中的尊卑影響其在法律上的地位,而清代執法人員的心態,以及在故誤、緩決和舉證等各種訴訟程序上的演變,皆左右婦女在司法程序中的形象。這篇文章,一方面讓讀者得以藉由刑案這類非常狀況窺見日常生活中婦女遭受的待遇,帶有傳統婦女史探求女性經驗的樸質,另方面也透過分析各個層級的檔案資料,呈現文獻疊壓的建構過程,流露了後結構主義性別史的趣味。
不僅一向被視為最能忠實反映真相的檔案不免虛實交錯,即使我手寫我耳的口述訪問紀錄也未必沒有想像的成分。游鑑明藉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將近70冊的口述史資料,分析20世紀中葉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變動中,菁英階層對親情與愛情的看法,包括對男女長輩的評價、對配偶的期待,以及與子女互動的情形。她的研究發現:男性受訪人較之女性,好用符合傳統價值的陳辭套語來形容配偶(如賢慧),但也有人嘗試突破成說,重新建構性別倫理,並且透過褒貶他人展現自己的行誼風範。作者指出口述歷史具有當下性,是主訪人與受訪人在特定時空情境下共同建構的產物,因而呈現出特定時空下的性別意識。一方面提醒著讀者口訪紀錄的虛構性,另方面則努力推敲、去蕪糾謬,嘗試追求字裡行間的真相。不過,以宋代文本與之遙相呼應的劉靜貞,對於真相的興趣卻有些不同。
劉靜貞承認:「沒有資料就沒有歷史。」卻也斬釘截鐵地表示:「即使有資料,也不見得就會講出一樣的歷史。」她以中國史學中的「列女傳」傳統、歐陽修的詩文,以及宋人對王昭君的描寫等三方面為例,說明運用歷史文獻探求古代女性生活經驗的限制,對於史料與詮釋、社會現實與歷史書寫之間詭譎多變的關係,顯示出高度的警覺。她主張與其追問歷史書寫中的個人反映了多少當時代的實況,不如探索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和思想體系要求並支持特定的歷史書寫模式。當我們意識到:女性的行止不再散見於全書,而是以某種樣貌被歸納入獨立的「列女」篇章、歐陽修透過墓誌銘中的「虛寫」與「實錄」提倡特定的女性道德,而宋代知識分子藉由重新評價古代女性、甚至改寫歷史來符合陽尊陰卑、華夷之辨等天下大義,這時,研究的重點已經不在於探討宋代婦女生活,而在於透過宋人對當代及古代女性的歷史書寫,來了解宋代的社會、思想與文化。如此一來,「性別」所指涉的,已不僅是男女存在、兩性關係,或者同性情慾,而是古人理解周遭世界的模型,今人認識古人的鑰匙。
胡、賴、游、劉四位的文章都和語言文字有關,包括男性書寫女性,男女互相述說,女性自我表達。但不論是針對特定種類的文獻進行介紹與剖析,或窮盡搜羅之功以呈現專題研究成果,以上九篇多環繞家族內的性別關係,其規範、運作與象徵意義作論。除了鄭雅如和鄧小南因介紹中古情況而涉及佛教之外,大多未涉及溢出父系家族體系的宗教女性。李玉珍的文章補足了這部分,為近年來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多元性提供實例。作者期待一本佛教婦女通史,認為應環繞比丘尼僧伽的建立與發展、她們的修行典範、觀音信仰的影響,以及佛教婦女的宗教經驗等四個主題,依時代順序,說明佛教自傳入中國,吸引女性信眾開始、歷經中古的鼎盛與普及、明代的禁戒、清代的復興,以及戰後臺灣比丘尼國際化的情形。將近年來汗牛充棟的作品納入她的架構之後,李玉珍質疑:「為什麼婦女與佛教的研究已經這麼發達,成果豐碩,卻沒有一部婦女佛教通史?」她將矛頭指向傳統宗族研究,認為學者在提問時已畫地自限,將古代社會中的女性全納入宗族脈絡中思考,視野難以突破,容易忽略女性的宗教生活與經驗。
李玉珍的說法,提醒了學者應當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正因為宗教信仰確實是傳統社會婦女的重要生命經驗,今日的研究,不論是探求古代女性的生活實態,或分析性別作為一種權力關係在各領域的影響,都不應忽略宗教的面向 。不過,缺乏通史著作的,並不限於中國婦女與佛教此一課題。自陳東原1926年出版《中國婦女生活史》以來,婦女史的著作源源不絕,各個斷代的專書、論文,乃至輯本輩出,卻沒有一本新的中國婦女通史,可以取代八十年前令人激賞而今已顯不足的舊作,為什麼?其實,李玉珍的提問與試答,正點出了「婦女」不是性質單一的群體、未必有一致認同的事實。然而,這個現象並不限於在家與出家之別,即使全為俗世女子,大多嫁為人妻,也會因階級與族群差異而有不同的生命情境與生活經驗。差異中的差異,使每一個個案或課題各自具有學術合理性,卻難以統整提升,與其他面向的歷史研究對話,並挑戰歷史學原即存在的既定思考模式與研究軌範 。
此時,性別取徑的提出,便成為整合新興研究成果,重新理解歷史的一項利器。正因為男女有別、女女也有別(當然男男亦如此),過去以留下最大量記錄的漢人男性知識菁英代表全體傳統中國人生命經驗的做法,不得不受到檢驗。而因社會包括各種階層與族群的男男女女,他們的互動與分工、規訓與挑戰,都不限於家庭與婚姻之中,故而性別成為重新理解經濟史、法律史、文學史、史學史、宗教史,乃至醫療史的視角 。不但將原本被忽略的女性行跡挖掘出來,也追問何以有些領域女性比較多,而有些則幾乎不見。不再以「沒有資料就沒有歷史」的訓練為滿足,而是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沒有?本書,便是基於以上對歷史的理解所進行的打破沙鍋、追根究柢的嘗試,雖然距離通史專書的理想仍然遙遠,但作為對史語所八十周年的獻禮,庶幾不辱前輩「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
說到碧落與黃泉,不免使我再度想起那成人之美的人魚!自從聽到美人魚的故事之後,有一陣子,我不論在授課、演講、與同行座談,或和親友聊天,總愛拿出來分享。1999年的夏天,我出國訪問,剛好有機會和一些臺灣留學生聚會。席間,男同學引經據典、高談闊論,在座唯一的女生,可能年紀較輕,狀似怯弱,插不上話,頗為沉默。為了鼓勵她,我說:「來講個笑話吧!」
從前有三個男人到海邊釣魚,釣到一條美人魚……第一個男人儼然成了科學家……第二個男人搖身一變成了人文大師……第三個男人不聽美人魚的建議,堅持要自己的智力變成四倍……
結果,他變成了女人!
話一說完,全桌男生拍案叫絕、哈哈大笑,只見那女學生面色凝重,沒有反應,大約過了十秒鐘,終於開口,悠悠地說:「誰叫他要求這麼多呢!」
是男尊女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活潑的彈性」仍待開發?是女人並非性質單一的群體?或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答案啊答案,與其說在茫茫的風裡,不如說在轉念之間。
李貞德
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