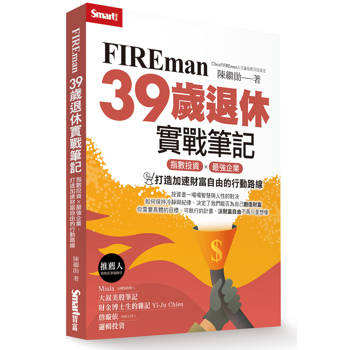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增訂版﹞-現代主義文學論叢6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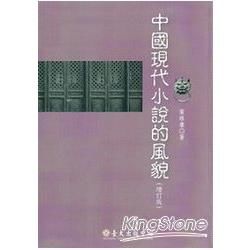 |
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增訂版﹞-現代主義文學論叢6 作者:葉維廉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0-03-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37 |
散文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教育學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增訂版﹞-現代主義文學論叢6
在這本被稱為「小說與詩的美學匯通」之書中,葉維廉如庖丁解牛般熟練透澈的觀點,以感性的心思體會輔以冷靜理性的思考剖析,借文字寫景深、運鏡,引領讀者體會詩與小說互動之美。 運用唐宋詩句之美,引入生命經驗深度,再峰迴路轉,解析王文興、白先勇、王敬羲、於梨華、聶華苓等名家的當代小說,從主題結構,到現象、經驗、表現,分析入。並分析作者鋪排、暗示、逆轉、對比、呼應等,為讀者開啟深刻的分析視界,達到詩與小說「美的匯通」。 經過二十多年的淬練與沉澱,作者以更深、更廣的角度,加入〈陳若曦的旅程〉與二○○八年十一月於加拿大學術研討會中論〈王文興:Lyric(抒情式)雕刻的小說家〉之篇幅,值得詳加閱讀與研究。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葉維廉
- 出版社: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0-03-01 ISBN/ISSN:986021274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軟精裝 頁數:245頁
- 商品尺寸:寬:148mm \ 高:210mm
- 類別: 中文書> 政府考用> 政府出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