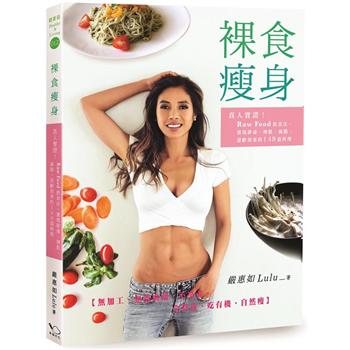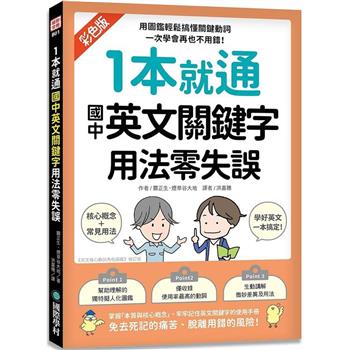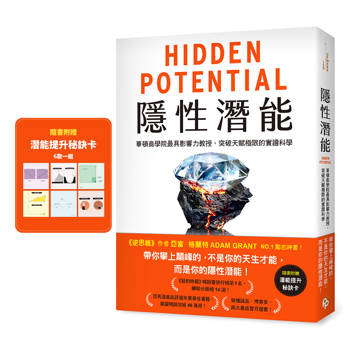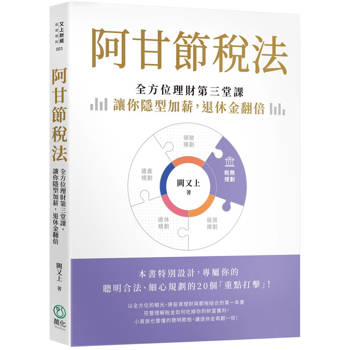序
《殺母的文化---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
1. 成書的背景
我在1983年出版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後,進一步批判中國人的「母胎化」,涉獵了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人研究「中國人性格」的資料,其中有「中國男孩身上母親的影響過重」的論斷,這批資料我如今把它們整理在本書附錄一裡頭。我在同時期的美國小說和電影中,亦留意到大量的「殺母」故事。這兩者難道是偶然的平行?
待到在一九九O年代寫作《未斷奶的民族》時,我試圖把中國人的母親崇拜與美國人的「殺母」合論,對兩者都作出批判,結果是內容超載,思路旋繞,題材陌生,並不理想。我當時的構想是,將來如有機會改寫這部著作,會只留下探討中國人的部分,關於美國人部分則另獨立成冊。
我在2002年發表了中國國民性的論述史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把美國人這部分當作第六章,但重點仍然是美國人如何在談中國人,美國方面的文化背景仍有待深入。2005年遷台後,拿到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補助,得以全面展開以美國為主的「殺母」主題研究,在此對國科會特致銘謝。
2. 「殺母」是美國的國民特徵?
「殺母」這個題材大逆不道,難於被人接受,尤其是東亞讀者。當今可以有同志和變性人的研究,並且組成團隊、形成網絡,但「殺母」研究將是獨步天下,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它在世俗陋見無視的、蒙眼的、否認的、噤聲的、鎮壓掉的一些角落裡建構了一整個透視美國文化的角度,其重要性不亞於從基督教角度去理解美國—事實上與該角度同等重要。本書把美國的殺母文化追溯至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世紀末文化」,它是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而且專挖掘人性的陰暗面與非理性成分,並已成為今日大眾文化的主要內容。
美國的殺母文化的源頭固不限於「世紀末」思潮,也包括與它共時的達爾文進化論,甚至長期內含於基督教文明的「夏娃論」,透露文化詮釋的多元性質,但「殺母」是否即呈現美國的國民特性?固態與原質的(hypostatic)「國民性」是一個陳腐的觀念。我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已避免用這個二十世紀早期的陳跡,但不少讀者仍挾此固態立場去理解我的「深層結構」。思想沒受過訓練的人,傾向將一組用詞指謂的對象當作該對象的本質,並視其能涵蓋該文化整體,或至少是它的「劣根性」大全。他們不會考慮是從哪一個角度看?相對什麼來說?為何而發?
但是,自詡為思想受過訓練者又如何?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ter)視《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為眼中釘。在他心目中,連「中國人」這個名詞都是不合法的:你如果只研究了兩百份材料,就只能談這兩百份材料裡的「對象」!在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下,他最明目張膽的「西方中心論」就紛紛出籠:中國人搞種族主義、尤其針對白種人;中國人缺乏個體化的情慾,後者只用來替傳宗接代服務;中國人的世界觀是整體主義的,非但模糊了個人與社會的界線、不信任多元民主,而且與現代科學相左;中國文化又是家長式的,允許國家權力對個人進行道德改造;甚至連清朝不成功的禁止鴉片煙之舉,都是干涉個人的權利,等等。馮客可以心安理得說:我並沒有涉及全體中國人,只在談有限材料給予的對象而已。白馬非馬,局部非整體,他絲毫沒有涉及「中國人」!
馮客這種文字遊戲騙得了誰?他僅僅抓住語言只是符號這點,認為符號背後沒有固定的「本質」,就將「中國人」這個意符整個地架空。孰不知先設定有些意符所指對象必須是空的,即涵示另一些意符所指是實有的,這樣的設定其實是將「空」「有」都予以本質化。這好比學佛學了半調子的人,只知道說「一切皆空」,卻被中觀學說糾正:執著於「空」與執著於「有」是同等的執著,執著於「非空」與「非有」也是執著:「有法不應生,無亦不應生,有無亦不生。」中觀論相當符合今日的解構論,因為設定有「自我」,並從自我的立場設定「他者」,才有了我與他,兩者皆有,也可以是皆無:「若無有自性,云何有他性,離自性他性,何名為如來?」馮客在論說一批材料時建立了自己這個主體—沒人說這就是馮客該人的「本質」,只是由兩百多份材料的客體構成的那個「馮客」,被他構成的「中國人」,固然如他所說並非全體「中國人」,卻畢竟是在他的話語底下被「他者化」的「中國人」。
「殺母的文化」是否呈現美國的國民特性?答案是:它不是實證主義意義裡的客體、供在那裡讓我們去發現的對象,而是我從美國人批判中國人母親崇拜引申出來的一個題目,它與中國人母親崇拜呈對角線狀的對立。這個現象既然是非中國的,自然成為了「美國的」,事實上乃是美國人與中國人相互把對方「他者化」的產品,是在同一個話語裡打轉。後結構主義心理學家夏克.拉岡(Jacques Lacan)即說:「言語總是主觀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
3. 章節內容的歷程:從迎合女性主義路線開始
一開頭,美國的殺母幻想似乎與「男性理想」絲絲相扣,到後來卻發現並非那麼簡單,但追蹤這條線索仍得從該理想開始,指出「殺母幻想」乃其很重要的一環。本書的第一章把追蹤的起步點設定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該時代透露出強烈的男性焦慮,表現為對「原野」的嚮往和對「神經衰弱」的防禦,前者為對「雄健性」的追求,後者乃對「女性化」的恐懼。由於時代的限制,該時對「雄健性」和「女性化」的思考仍以國家與族群為單元。但從第二章中已清晰看見:原野的理想落實到男童的性格培養,背後透露的焦慮具有當時流行的達爾文思想的背景。
交代了世紀之交的背景,即兵分兩路,追蹤兩條線索,一條是「雄健性」、「女性化」一類話語從族群化朝個體化方向之演變,由談種戰與國家決鬥轉向談人格,其具體表現為美國「性別研究」的成形,它組成第四章的內容。從一開頭,已可看出男女的兩極分化被當作常軌、同性戀成為最大偏差。這種靜態的分類至戰後演變成心理動力學模式,亦即:視男性的形成為從與媽媽不分化的階段到全面對立階段,該過程同樣是一個理想,也在前提上預設了對不完整的過渡階段衍生焦慮。「心理動力學」基本上打上佛洛伊德性慾化的人格成長論之烙印。與此同時,佛洛伊德亦被美國化,新佛洛伊德派把祖師的人格內發階段論修正了,改成對「母子關係」的強調,並視男子與母親認同為精神分裂之導因,同時把精神分裂等同於同性戀。
因為線索的紛繁,本書在第三章開始追蹤另一條線索:尼采一脈的「仇母論」,其背景是世紀末思潮的文明沒落、人種退化、陽剛隳沉氛圍。尼采將「文明再生」的希望寄託在「超人」身上,同類思想家包括奧國的懷寧格、英國的勞倫斯、美國的曼契金與菲利普.懷理。後者以發明「大媽咪主義」一詞著名,也替好萊塢寫劇本,直接與美國大眾文化連線。三、四兩章的提供的線索至二十世紀中期匯聚成為一股巨流,引發了世紀中期性別危機與它的伴隨現象:憂慮父親做主的傳統家庭之動搖以及對「陽具型女人」的恐懼,並把女性被當作黑暗勢力的代表。這些題材在第五、六章中獲得發揮。
第七章聚焦於一九六○年代美國電影的「殺母幻想」高峰期,也是該母題的經典著作時代。當時,美國進入性解放的革命,「媽媽的乖男孩」不能適應新式的自由性愛方式,譴責母親造成兒子的性無能,幾呈歇斯底里狀態。其時,戰後的嬰兒潮一代也長大成人,變成叛逆的一代,也是「殺父殺母」最起勁的一代。「殺父」並非本書的研究重點,因此被收入附錄中。更關鍵的是:父親的權威在當時已被視作蕩然無存了,它其實與陽剛隳沉、母親霸權(大媽咪主義)的悲鳴前呼後應。而且,打倒父權是美國男性的「成人儀」,是人格成長的制度化,也沒有湧現特別的高峰期或經典著作時代。相形之下,美國「殺母幻想」的材料就廣泛得多。
我的「殺父殺母最起勁的一代」歸根到底仍以「殺母」為主的洞察是精準的,事實上,緊接著一九六○年代男性「殺母」的高峰期是女性在一九七○年代的東施效顰。戰後女權的第一炮也從「殺母」開始:要「殺掉」由母親這個模範輸送的「賢妻良母」角色。女性真正出現「殺父」高峰期是一九九○年代,主要表現為與女性「殺夫」相互呼應的殺父幻想,乃女性對男性進行的「文革」—這是本書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要處理的題材。在本書的第八章裡,我們止於女性「殺母」的高峰期:一九七○年代。
4. 章節內容的歷程:超越女性主義的角度
到目前為止,我的分析架構不離美國女性主義立場,但再探討下去,該框架即遇到了極限。戰後女權運動復甦,走出的第一步也是「殺母」還情有可原,說是受了男性意識的洗腦。它很快就促使女性主義跨出第二步:擺脫與男性中心觀點任何沾邊,強調母女的延續性與傳承。第九章〈女性主義如何重建「母親」〉追蹤了這個發展。男女分道揚鑣逐漸湧聚成一九九○年代的「殺父」與「殺夫」高潮,出現兩性形同敵國的局勢。這一路的發展仍然具一致性,如果把女性主義革命堅持到底,一九九○年代的極左思潮乃其邏輯的歸宿。
然而,女權分子提出的「母女親和論」不論與美國社會或大眾文化都不符。沒人注意到美國人的母女關係特別親和、會超出母子關係,大眾文化裡女性的「殺母」仍照行不誤。性別觀點終於觸礁,因為它忽略了其他角度,例如:代間。美國文化的「殺父殺母」不可能只是性別政治問題,它更多地反映了代間衝突,男孩反母親、女孩一樣反母親。此現象在第十章〈言不由衷的母女親和論〉中深入分析。
自此,「性別對立論」就讓「代間斷裂論」占了上風。這個轉折令我挖掘到美國文化更深層的原則:分離與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既然下一代必須與上一代徹底斷裂,方能成形,個體之間自然也力圖避免人我界線不明朗的狀態,否則自我疆界就無法維持、個體性(individuality)遭到威脅。這可以解釋美國式個體為何亟亟於擺脫人生早期狀態,把母子關係設想成最大的陷阱!這原本是男性的成長觀,視「人我界線不明朗」為來自母親的威脅,並把這個威脅氾化成婦女這一整個性別的屬性。女性主義者為了對抗母子對立的命題,轉而強調母女的延續性與傳承,行得通嗎?
母女親和論終於證明是曇花一現,成為女權運動史上被遺忘的一章。進入一九八○、一九九○年代,美國的女權思潮走上另一條與男性分途之路:楚河漢界、形同敵國、兵戎相見。性別的兩極化不再是「男性追求分離與個體化、女性搞人我界線不明朗」,而是索性成為各自分離的單元,「分離與個體化」脫離男性的專利,終於成為全民理想。在「反思鄉、反懷舊」的文化總氛圍中,也只得如此。
兩性形同敵國將成為本書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之內容,本書剩下的部分是它的前奏。第十一章〈殺父殺母的心理倒影:殺子〉繼續追蹤代間矛盾這條線索,用美國人的「殺子幻想」來反證「殺母幻想」的代間斷裂性質。「殺子」雖然仍屬代間斷裂,但已與反權威、反宰制無關,更不能用性別矛盾去解釋,只能理解為純粹「斷裂」。第十三章則討論一個更令人意外的現象:殺狂慕者,狂慕者俗稱「粉絲」。從這個奇特的幻想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國人對「人我界線不明朗」的恐懼,它幾近被害妄想,其保衛「自我疆界」則呈歇斯底里狀態。殺狂慕者的幻想其實有殺母幻想的迴響:母親與狂慕者都是沒有「自我」而黏上別人者,都是用投射自己的願望限制被投射對象的自主權,甚至用取消被投射對象的存在來實現自己,因此,到後來演變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第十二章〈失去的地平線〉是全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它探索了另一脈美國思想,亦即是把「母子不分離」當作是最完美的、渴望重溫的終極性愛境界。前面各章都謂「母子不分離」導致人格困陷於人生早期,在美國遭大力聲討,如今又如何解釋這個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呢?在某一個意義上,它是自我疆界絕對化、人與我界線勢同涇渭的人格對「失去的樂園」之緬懷,卻暗示了母親唯有在「愛慾化」的情景中才能被接受。
這是什麼心態?佛洛伊德早已從嬰兒身上發現了性慾,這個見解且成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共識,雖然在連成人都有點非性化的東亞,它並不構成什麼「現代」意識。縱使佛洛伊德十分有創見,嬰兒身上的性也不過處於萌芽階段,因此,所謂「愛慾化的人生早期」並非兒童的思考,正是成人的幻想。在性成長與性別認同的意義上,「愛慾化的人生早期」乃由父權代表的文明還沒對人的原慾摧殘前的理想狀態,在這個階段上,原慾還未被強迫納入異性戀的渠道,它容許「多樣相的變態」。
因此,在殺母文化中出現這個環節,非但沒有否定殺母文化,而是替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同性戀、雙性戀的主流化找理論根據。它基本上製造了更多的新認同、更另類的分離主義、更多途的分道揚鑣,更多面的勢同水火,也與女權左翼的「異性戀是父權社會底下男人剝削女人的制度」命題互為犄角。
5. 未完成的交響曲
說到這裡,《殺母的文化》就不得不與它的續篇《男性的邪惡王國》切割。原本計畫是一氣呵成:我追蹤男性「殺母」與「殺父」這類線索,蜿蜒至一九九○年代女性「殺夫」與「殺父」的高峰期,發現基本上用的是同一個模式,亦即是主體受到宰制,必須打倒或消滅主宰的他者,個體從被動的「受害者」(victim)反客為主,變成「能動的主體」(active agent),否則「分離與個體化」就沒有完成。這種自我的徹底完成(coming into one's own)在心理上不會為他人留下空間。代間否,定還牽涉到權力移交問題,在這一點上,美國男性成人儀的「殺父」替一九九○年代的女性「殺夫」提供了一個典範。
在病態學方面,一九九○年代女性的「殺父」與一九六○年代成形的男性「殺母」經典範式則在大同底下出現小異。男性的角色模範原本是父親,殺父是儲君繼承王位,由兒童變成像父親一樣的男人;男兒受到母親宰制卻是變態,是性別角色錯亂,造成心理畸形和性無能。女性受爸爸殘害的方式則是童年受到性侵犯,造成花痴(nymphomania)或多重人格分裂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子女受到心理摧殘皆同,差異在於:母親的加害方式是「閹割」,父親的加害方式則是「強姦」。一者是被剝奪性能力,一者是被性強加於身。它是一種什麼邏輯?顯然,主動地獲得「性」乃能動的主體之健康指標,但「性」之為物又是顛覆自我疆域的。這也算是美國文化的一個死結吧!
本來認為必須要說到這裡,「美國的殺母文化」才算交代完畢。但這將使內容超載,重演《未斷奶的民族》一書的錯誤。而且,書寫得太慢了,已挨過一九九○年代女性「殺夫」與「殺父」的高峰期。進入新千年後,出現新的發展,亦即引起了反彈,促成小布希年代的美國大眾文化大力宣揚父子感情。把這個新發展與一九九○年代的美國「文革」合論似乎更為恰當,它證明歷史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它還在發生中,本書只能築一條人工的堤,把歷史河流隔斷於某處。
推薦序
十年磨一劍
這本《殺母的文化》是作者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之後的第三本鉅構。孫隆基教授在撰寫這一系列著作的時候,心中關注的焦點其實是「中國人的性格」。然而,任何人想要描述「自我」的性格,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個跟自己明顯不同的「他者」,作對照性的描述。所以孫教授在寫完前兩本有關中國人性格的著作之後,就再接再厲,花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完成這本鉅構。這種作法跟許烺光寫《中國人和美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或我寫《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是十分類似的。
然而,每一個學者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都會因為自己所受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而有不同的視域,他們對於同一問題的詮釋方式也會有所不同。許烺光是人類學家,他用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收集各種文化材料,撰寫他的著作;我是社會心理學家,根據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建構理論,從事實徵研究。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孫隆基教授,他以心理分析學派的理論作為基礎,用歷史心理學的方法,從中、美兩國大眾文化的產品中找尋材料,來支持他的論點。
這本書有個副標題《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換言之,孫教授收集的材料,時間橫跨一百年,他研究美國許多著名電影和文學作品的情節,分析每一個故事中的親子關係,說明美國文化中個人的所謂「成長」,就是要從依附父母的狀態中獨立出來,完成「分離個體化」的歷程。相反的,在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之下,中國文化強調的是親子之間永遠不斷的照顧和回報,以及家人之間的相互扶持,這種講究關係主義的文化,孫教授稱之為《未斷奶的民族》,美國人的強調個人主義,他稱之為《殺母的文化》,其理論依據都是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如果要將本書易名為《殺父的文化》,其實亦無不可。
正因為這本書的內容主要取材自美國大眾文化中的故事情節,這本書的撰寫不僅有學術的嚴謹性,而且有文學的趣味性。作者對於書中所引的每一部文學作品和電影故事,觀察入微,描繪深刻,而且文筆流暢,可讀性極高,讀來讓人感到興味漾然。古人有云:「十年磨一劍」,看到寶劍的鋒利,就可以想像主人磨劍所下的功夫。讀完這本書,除了佩服作者分析事物的洞識之外,令人感佩的是他長年的投入和堅持:沒有數十年的「磨劍」功夫,怎麼可能寫成這樣的作品?
黃光國
國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