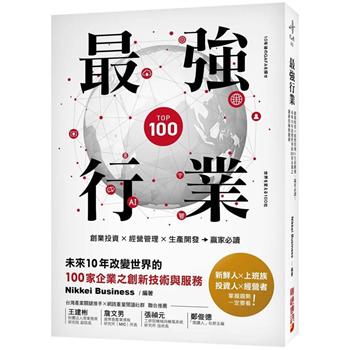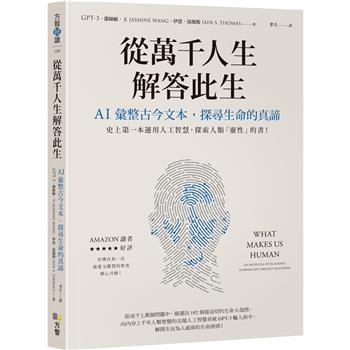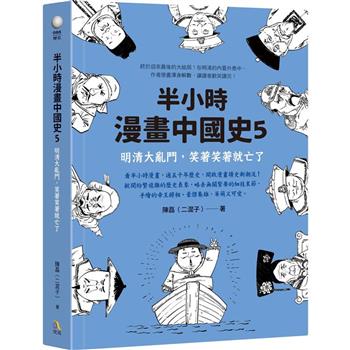當你用腳親炙我們的土地與風景,當你用心貼近台灣的文學與電影,仔細聆聽,台灣靈魂所發出的自然之聲,你將會發現:這塊土地充滿了愛、理想與淚光。
文學是透過文字的藝術,感應時代風潮,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思想和感情;電影則是以影像美學,極視聽之娛,呈顯各種交織的生命光影,揭露人們的慾望和想像。而文學與電影的夢幻結合,時而水乳交融,時而相互輝映。萌發於二○年代以後的台灣新文學與電影,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感應不同的時代變化,都曾經產生過不少成就斐然、令人繾綣難忘的傑作。
此次由行政院文建會策劃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發行,交由遠景出版公司所負責編輯製作的「文學‧電影‧地景」編篡出版計畫,經過多位電影人、文學人的討論與票決,揀選了三十部「文學電影」,延攬專人執筆,分別從小說至電影的轉化、題旨內涵、藝術特色,以及電影中地景之今昔對比等相關角度切入,撰文成書,希望能為台灣文學與電影一路走來艱辛的進程留下歷史的證言。這三十部「文學電影」,從1966年的《幾度夕陽紅》至2008年的《一八九五》,將近紀錄了半個世紀的歲月。
電影尚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像紀錄片一般,會為美好的風景定格,永恆保留台灣的地景實像。這三十部「文學電影」所呈現的地景,包括了台灣本島與離島,從北部港都基隆到南國港都高雄,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儼然展現了台灣海島地景的特色。為此,本書借重詩人路寒袖的攝影才華為台灣掌鏡,遠赴各地及澎湖離島,拍攝一系列現今的地景。
並且為求創新,本書打破以往搭配劇照的慣例,特別在內容上大量引用與電影地景相關的現今照片,並做了延伸的閱覽,在今昔的對照上,我們尤其強調「活在當下」、「突顯現狀」的意涵。相信透過電影中地景的今昔對照,當會加深我們對自己土地的認識與關愛,體悟台灣外在與內在真誠的素樸之美。
作者簡介:
李志薔
台大機械研究所畢業,為國內知名之小說家,並曾擔任多部影片及紀錄片導演、編劇、製片等職務。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國文藝協會青年文學首獎。第一部劇情長片《單車上路》,林正盛讚譽全片有種獨特散文詩的氣息,曼漢姆及福岡影展亦認為該片為亞洲電影開發了新的視野。2010年《秋宜的婚事》,甫入圍金鐘獎最佳電視電影、最佳編劇等三項。
林明昌
淡江大學中文博士。曾任林語堂故居執行長,現任教佛光大學文學系及外文系,並任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在學校教授現代詩及小說,也創作現代詩及小說;教授中國古典文學、華語教學、也解讀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及日本文學。喜歡素描、水彩和攝影,也是國術社指導老師,喜歡拉二胡及大提琴。遠離所有流行時尚。
亮軒
本名馬國光,著名散文家。畢業於國立藝專影劇科、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碩士。曾任國立藝專廣播電視科主任、中廣節目主持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副教授。亦為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若干雜誌專欄作家。曾獲中山文藝獎、中國時報吳魯芹散文推薦獎。出版散文集、時事評論集、小說集、文學研究文集二十餘種。
張昌彥
資深影評人,推動電影文化不遺餘力。曾任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國家電影資料館董事、影評人協會理事、金馬影展執委會執委等;也擔任過國內外多項電影競賽的評審,電影經歷十分豐富。
張恆豪
文學研究者。主要著作有《覺醒的島國──日治時代台灣文學論集》,主編有《台灣作家全集》(日治時代)賴和集、楊逵集、呂赫若集、龍瑛宗集、張文環集等十冊。
陳三資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畢業,美國北伊利諾大學戲劇碩士。曾任職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文化局以及所屬藝文館所。《插天山之歌》、紀錄片《鍾肇政文學路》執行製片。現為自由工作者。
陳儒修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電視學院電影理論博士,現任職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著有《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電影帝國》,譯有《電影理論解讀》、《第三世界電影與西方》、《電影之死》、《佛洛伊德看電影》,編著有”Cinema Taiwan: politics, popularity and state of the arts”等書。
黃玉珊
畢業於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後於美國愛荷華大學主修戲劇電影,之後又轉到紐約大學,1982年獲得電影藝術碩士學位。歸國後投入紀錄片工作,先後任教於世新、文化、台灣藝術大學、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等。主要研究領域是影視編導、獨立製片、女性電影、紀錄片以及電影評論。
黃建業
學者、影評人、舞台劇導演。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及電影創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曾任北藝大戲劇系主任及劇本創作研究所/劇場藝術研究所所長、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台北電影節總策劃等。著作包括《楊德昌電影研究》、《人文電影的追尋》、《潮流與光影》等,並主編《電影辭典》、《世紀回顧圖說華語電影史1896-1999》、《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等專書。
解昆樺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目前擔任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著有《轉譯現代性》、《詩史本事》、《青春構詩》等專著,並曾獲文建會台灣文學獎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等。在電影研究方面,主要著重在小說與電影劇本改編的課題,目前正展開侯孝賢、朱天文電影劇本之系列研究。
熊啟萍
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出版界短暫任職,隨後至加拿大留學多年,現為業餘文字工作者。作者對五、六○年代的電影極為熱愛及熟稔,自幼接觸當時的影與歌,早年曾為「今日世界」撰稿。基於對「古典美人」樂蒂的難以忘懷,因而寫下一本紀念她的書──《明月流霞》,也同時紀念一個輝煌的電影時代。
鄭順聰
1976年生,嘉義民雄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曾獲台北文學獎、雜誌編輯金鼎獎、行政院新聞局電影創意故事入選等。曾任《重現台灣史》雜誌主編、《聯合文學》雜誌主編。著有詩集《時刻表》。
應鳳凰
台北市人,師大英語系學士,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東亞系文學博士。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資料主編、成大台文所副教授,現任教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多年來致力於整理台灣文學史料,編有《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1980年文學書目》等工具書,著有《筆耕的人》、《台灣文學花園》《50年代台灣文學論集》等。
藍祖蔚
自由時報大生活群組執行長。看電影看了50年,寫電影寫了25年的超級影迷,持續每天以一篇文字,紀錄電影人生的心情。
章節試閱
【前言】
光影夢迴 照亮台灣──《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
文/張恆豪
文學與電影的夢幻組合
文學是透過文字的藝術,感應時代風潮,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思想和感情;電影則是以影像美學,極視聽之娛,呈顯各種交織的生命光影,揭露人們的慾望和想像。儘管它們藝術的媒介不同,但殊途同歸,其發掘探究人性的本質,豐富化並深刻化我們生命經驗的目的是一致的。
文學與電影的夢幻結合,有時是水乳交融,相互輝映,有時則是電影糟蹋了小說,也有不少是電影照亮了原著。
萌發於二○年代以後的台灣新文學與電影(皆同一年1922),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感應不同的時代變化,都曾經產生過不少成就斐然、令人繾綣難忘的傑作。
此次由行政院文建會策劃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發行,交由遠景出版公司所負責編輯製作的「文學‧電影‧地景」編篡出版計畫,經過多位電影人、文學人的討論與票決,從館方所交付的七十部片單中,揀選了三十部「文學電影」,延攬專人執筆,分別從小說至電影的轉化、題旨內涵、藝術特色,以及電影中地景之今昔對比等相關角度切入,撰文成書,希望能為台灣文學與電影一路走來艱辛的進程留下歷史的證言。
這三十部「文學電影」,從1966年的《幾度夕陽紅》至2008年的《一八九五》,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在時間縱軸上,經過國語片第一個綠意盎然的時期,以中影倡導的「健康寫實」為主潮,李翰祥率領團隊來台創立國聯,四大老牌導演李翰祥、胡金銓、李行、白景瑞的振翅昂揚,穿過七○年代的粉紅鬥豔時期,愛國軍教片、武俠功夫片、黑社會現實片盛行一時,也是二林二秦文藝片當紅的熱潮。再經八○年代的藍色翱翔時期,新電影的崛起,大量改編純文學的電影蔚為風潮;直到九○年代的「後新電影」,在躍動多變的年代,台灣電影卻進入黑色寒颯的冬天,窮極則變,冬盡春來,也可能是充滿無限契機的早春。
以下就讓我們擦拭歲月的痕跡,以尋溯和回顧的方式,將這些電影放置在歷史進程的脈絡,通過時代的觀照和前後的比較,管窺其中所蘊涵的意義和價值。
《沙鴦之鐘》──台灣「文學電影」的濫觴
若提及台灣文學改編成電影的第一部作品,要從日治時期說起,從當時所製作的十六部劇情片中,1943年由清水宏導演的《沙鴦之鐘》改編自小說家吳漫沙的同名小說,堪稱為台灣「文學電影」的濫觴。電影是以當時的新聞為骨幹──蘇澳原住民少女沙鴦,為了運送一位出征軍人的行李,在暴風雨中不慎跌落溪流溺斃的事件,台灣總督為了鼓吹台日親善乃將沙鴦神化為愛國之女廣為宣揚,可說是一部皇民化電影。《沙》片特別請來其時當紅的「滿映」女星李香蘭(山口淑子)主演,喧騰一時,至今其弦律優美的主題曲(即填成中文歌詞的《月光小夜曲》),猶傳誦不已。
五○年代末期,正是台語片當道的年代,1958年由辛奇執導的《恨命莫怨天》,改編自張文環小說〈閹雞〉;翌年,林搏秋執導的《嘆煙花》,再次將張文環〈藝妲之家〉搬上銀幕。這兩部影片都以黑白拍攝,台語(河洛語)發音,平實生動的描述了日治時期台灣人現實的生活經驗,一方面以寫實的手法刻劃荒謬的人性,一方面以悲憫的視角關懷庶民的悲苦。從1943年至五○年代末期,以「文學電影」言之,它是一個褐色時期,代表著開墾培土的階段。
綠色時期──蓬勃生機的年代
六○年代以後,台灣雖然陷於冷戰對立的內憂外患,但國內仍是一黨專政的威權時代,與五○或七○年代比較,相對上較為安定;中共則於1966年夏天爆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也進一步粉碎了在台外省人士還鄉的夢想。
文學或文化上,反共懷鄉文學漸漸退潮,取而代之的,現代主義在文學上、藝術上形成創作的主流,鄉土主義也逐漸在復甦。
以經濟層面言之,整個六○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之時,由農業轉型到工業,許多農村青年跑到都會或港都加工出口區,從事加工或勞力工作,造成農村人口漸漸外移,城市的經濟也慢慢小富起來。當時(1962年)雖開始有電視,但整個六○年代還是三台的時候,大家有閒情有餘錢都喜歡到電影院去消費娛樂。1963年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締造了驚人的賣座,造成台北變成「狂人城」,也對於國語片帶來了震撼性的影響。
1963年至1973年,正是台灣的國語片綠色萌芽的階段,充滿蓬勃的生機,代表生命的成長與希望。此時中影公司亟力倡導「健康寫實主義」;由於《梁》片創下瘋狂票房,導致李翰祥自邵氏出走,帶領大批香港表演和技術人才來台創辦國聯公司,1963年至1970年共攝製二十多部電影,最後因經濟與政治因素而停業,但對當時及往後的台灣電影工業,則具有前導性的影響。
在本書三十部「文學電影」中,首部《幾度夕陽紅》與《冬暖》就是國聯時期的傑出作品。《幾》片改編自瓊瑤的同名小說,堪稱是亂世的流離曲:國共內戰後,流離的外省族群,兩代人情愛的糾纏,精確的反映戰後來台外省人的生活實況。《冬暖》則改編自羅蘭的作品,透過五○年代兩個社會邊緣小人物的相濡以沫,進而表達了外省族群從過客逐漸想要落地生根的內心盼望。
這個時期,白景瑞自義大利電影實驗中心進修歸來,進入中影擔任編審。他於七○年代初期拍攝了《家在台北》與《再見阿郎》,前者改編自孟瑤〈飛燕去來〉,對於當時崇洋時尚與出國熱潮的反思,鼓舞各領域的青年回國返鄉投入十大建設,是中影典型的「健康寫實」作品,帶有宣揚國策的意味。本片眾星雲集,幾乎是中影演員大會串,加上義大利式的三段劇情集錦,使得本片在票房與獎項均雙雙告捷。《再見阿郎》則取材於陳映真的〈將軍族〉,在呈顯台灣女性/本省青年/外省老頭的三角曖昧戀情之餘,也和《家在台北》同樣在反映台灣社會的嬗替蛻變。白景瑞並創造阿郎此一鄉土小人物,描繪其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掙扎,最後只能憑著原始的勞力鋌而走險,亦注定成為時代巨輪下被淘汰的悲劇角色,此片可說是白氏寫實主義的代表作。
社會的蛻變必然帶來新舊思潮的衝突。六○至七○年代,也是台灣受外來新思潮與固有舊文化矛盾衝突與融和再生的劇烈階段,傳統的倫理觀和道德觀一再的受到衝擊和挑戰。
七○年代之初,宋存壽離開國聯後,自組香港八十年代電影公司。創業之作,即重拍瓊瑤的《窗外》,此片也是林青霞踏入影壇的處女座。在新舊思潮的矛盾衝突中,宋存壽藉著師生不倫之戀的禁忌,再次衝撞當時保守的道德觀。同年(1973)又開拍《母親三十歲》,透過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愛恨情結,大膽揭露女性情慾自主的可能;試圖顛覆農業社會以來對於女人、對母親刻板制式的觀點,慈母的另外一面也可能是慾女,這與《幾度夕陽紅》、《家在台北》的母親形象已是迥然不同。
粉紅時期──內憂外患下的逃避主義
1971年之秋,中共進入聯合國,台灣自此外交上節節失利,台日斷交,未久台美外交也正式斷絕,因應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中影主導的愛國軍教片趁勢而起,如《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等等。為了針對中共的文革和統戰,中影拍了《皇天后土》、《苦戀》。七○年代中葉之後,國內經歷了中壢事件、高雄美麗島事件,文化上的鄉土文學論戰也在此際如火如荼展開,中影為了抑止台獨意識的滋長,亦在這時拍了《香火》、《源》、《大湖英烈》等以中原意識為尋根題材的影片。
當時的台灣經濟,則是工商業突飛猛進,中產階級漸次成形,國民所得增加,經濟的富裕也帶動國語片的勃興和熱鬧。除了上述的愛國軍教片、反共片、尋根片之外,武俠片、功夫片、黑社會暴力片紛紛出籠,此時也正是二林二秦三廳式電影竄紅全盛的年代。在內憂外患的國難當頭,小市民在爭睹明星的丰采之餘,同時亦透過愛國的激情、浪漫的夢幻以及武打的宣洩,逃避現實的苦悶和蒼白。整個電影景況,就好像粉紅時期,繁花爭放,外觀嫣紅錦簇,實則脆弱不堪。集體的逃避主義,一窩蜂的粉飾太平,「政宣」或「夢幻」都離社會底層的聲音太遠,終竟難逃崩解凋零的命運。在此階段,李行的《原鄉人》於1980年適時出現,有幾點值得深思。
《原鄉人》以寫實手法追述鄉土文學作家鍾理和的同姓之戀,嘔心瀝血創作卻坎坷困頓一生的感人事蹟,但也隱約點出台灣人的原鄉認同,這應是編導的不言之喻。鄧麗君嘹亮動人的歌聲,秦漢與林鳳嬌有別於言情片的素樸裝飾和演技,都令人印象深刻。然仔細觀之,本片其實也是另一種逃避主義──雖然描摹了鍾理和的外在經歷,而對其最重要的內在思想卻毫無著墨。編導在那樣的年代,一廂情願地敘述鍾理和奔赴「原鄉」的情切,卻隱晦了後來鍾氏對於「原鄉」的失落之感、對於「祖國」徹底幻滅的事實,這些心理轉折在鍾理和的〈白薯的悲哀〉、〈祖國歸來〉均有悲痛的陳述,編導只顧外在的「健康寫實」,卻忽略了內在的「真摯寫實」,不可不說是種遺憾。
蔚藍時期──新電影的崛起
八○至九○年代,台灣的外交處境更形艱難,邦交國逐年減少,在國際間遭到中共嚴厲打壓;反觀國內,威權專政的國民黨政權屢屢遭到反對人士的抗議與挑戰,要求解嚴的呼聲,渴望民主與自由的聲浪愈來愈大,社會力在集結,本土意識正急速在萌發。
八○年代前後,中影所拍的反共片、「傷痕文學」電影、愛國大戲也出現瓶頸,缺乏創意,政宣意味又過濃,讓觀眾倒盡胃口;打鬥片在打打殺殺之餘,拳腳功夫千篇一律,早已令人看膩;而瓊瑤的言情電影又因缺乏新的元素,與現實全然脫節,使觀者漸漸失去興致。一時之間,國語片電影由紅轉紫,陷入低迷的陰霾。
解嚴之前,台灣整個大環境充滿山雨欲來的焦躁不安,社會底層力圖變革求新的氛圍也愈來愈強烈。八○年代晚期解嚴之後,言論尺度更為大鳴大放,堪稱史上空前,台獨、左翼、同志、女性、環保、原住民……,種種議題更堂而皇之躍上檯面,使得戒嚴期間單一的意識形態,逐漸轉向開放又多元的民主格局。
國語片在低迷中,中影花費鉅資推出的《辛亥雙十》,票房口碑皆告挫敗,在揹負沉重的債務壓力之下,中影當局自不得不企圖改弦易轍,改變製作方向。終因受到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刺激,讓危機終於出現轉機──中影總經理明驥大膽採用文學人小野、吳念真的建議,啟用新銳導演拍攝《光陰的故事》,在輿論和票房都叫好之下,為國語片帶來了希望的曙光。
接下來,《小畢的故事》大獲成功,同時間更啟用侯孝賢、曾壯祥、萬仁三人拍攝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在修剪始能上映的情況下,與老牌導演拍攝的《大輪迴》對壘角力的結果,新電影廣獲觀眾與輿論的支持,可說開啟了國片嶄新的紀元。接連著《看海的日子》、《海灘的一天》、《油蔴菜籽》、《我這樣過了一生》……,在評價與賣座上,均廣受迴響,亦屢在國際影展連連得獎。1982年至1989年,在台灣影史上正是新電影發光發熱、獨領風騷的重要年代。
電影向文學乞靈,文學與電影結合,一時成為國片電影的枯木逢春。解嚴前後,政治教條漸漸鬆綁,創作空間也增大,此際,有如蔚藍的天空,既開放又多元。大致言之,新電影有下列一些特質:
一、新電影大都改編自台灣作家優異的寫實小說,編劇群有不少是知名小說家參與其中,有些電影甚至由原作家本人自己改編(如黃春明、王禎和、朱天文)。
二、在題材上,以貼近庶民生活的本土經驗為主,表現手法上,則嘗試以新的美學形式、新的電影語言來敘述,力求敘事的客觀性與開放性。
三、由於解嚴之故,在創作心態上逐漸擺脫政治與情慾的諸多禁忌,有思想的導演自會在主題內涵上,呈現出有別於俗眾的異質性或顛覆性觀點。
四、落實於寫實精神,為求忠實於小說劇情,符合人物的語言,打破以往獨尊北京語的局面,而呈現各個族群使用自己母語的自主精神。
五、電影的製作,以小成本、低風險為策略,大量啟用非職業性或硬裏子演員擔綱演出,打破了以往的明星制度。
在本書所精選的三十部「文學電影」中,便有十七部出現於這一藍色時期,足見其份量。侯孝賢、陳坤厚、王童、萬仁、曾壯祥、楊立國……等新銳導演輩出,才情煥發,態度誠懇,運鏡上也極盡個人風格的敘事手法,深獲得影壇矚目。這十七部電影依其主題內涵,約可分為以下幾類:
反映台灣農業社會轉型工商社會的變遷與進步(如《油蔴菜籽》、《我這樣過了一生》);傳統母親的受苦、勤勞、宿命(如《金水嬸》、《我這樣過了一生》、《小畢的故事》);保守農村婦女以肉體換取溫飽的荒謬和受辱(如《嫁粧一牛車》、《殺夫》);被凌辱女性的反抗、殺夫或自我犧牲(如《殺夫》、《結婚》)。
呈顯傳統與現代的糾葛與對抗(婚姻理念之對抗,如《結婚》;教育理念之對抗,如《魯冰花》;新舊女性理念之對抗,如《油蔴菜籽》);女性一生情愛之糾纏、滄桑、追求情慾自主或生活歸宿(如《桂花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本省女子與外省男人婚姻的悲劇(如《小畢的故事》、《孽子》)。
描繪青少年的啟蒙、成長,或叛逆出走,或天才早夭(如《冬冬的假期》、《小畢的故事》、《在室男》、《春秋茶室》、《孽子》、《魯冰花》),乃至隱晦低調的點出同志的議題(如《孽子》)。
揭露弱勢的邊緣人物在社會轉型中生存的艱辛、堅忍或無奈(如《兒子的大玩偶》、《金水嬸》、《嫁粧一牛車》);底層小人物面對外來強勢科技文明的隔閡(如《小琪的那一頂帽子》)、對政經大國的卑屈(如《蘋果的滋味》);對於資本主義下世俗拜金媚外心態的嘲諷(如《玫瑰玫瑰我愛你》、《嫁粧一牛車》)。
對照鄉村自然文明與都會文明,以及個人的選擇與回歸(如《冬冬的假期》、《看海的日子》)。
這些文學,這些電影,無論是延續六○年代以來舊的議題,或開拓新的觀點,都扣緊台灣的歷史和現實,確實反映了戰後的本土經驗和族群記憶,表現出他們內心的掙扎和希望,吐露了小人物卑微的心聲,也描繪出新時代的願景,故頗能受到影評界的青睞。
但台灣無三日好光景,可惜後來一窩蜂的搶拍,假借「電影文學」之名,漸漸淪為媚俗與煽情,失去了早先的理想和誠摯,創意闕如,內涵不足,一味討好觀眾,缺乏文化的自覺,再加上新電影揚棄明星的魅力,後來有些又過於自溺,手法也很疏離,造成曲高和寡,新電影乃漸漸退潮。
黑色時期──國片的寒冬或是早春?
九○年代迄今,在政治上,中國憑著經濟的躍進快速崛起,三通成了海峽兩岸不可抵擋的態勢;文化上,則有「後殖民」、「後現代」思潮在解嚴後衝擊文藝創作;在電影發展上,為了走出困境,政府因應的方法之一,在1989年開始實施國片輔導金政策,雖鼓舞不少有潛力的新秀踴躍下海,但以績效而言,大多是零星浪花,並未掀起波瀾,大環境和結構性的問題依然沒有改變。
一般論者提及九○年代後的台灣電影,皆稱它是「後新電影」或「新新浪潮」。除了李安異軍突起,電影叫好又叫座,滿足了中產階級的中庸敦厚、溫情甜美的口味,連連踏上國際舞台獲獎,造成「李安現象」之外,整個電影氣候卻有如黑濛濛的冬夜,無論是在拍片的數量、市場的反應、影評輿論,或在國際影展評價上(李安、蔡明亮少數例外),都遭到嚴重的挫敗。
有感國片的衰微,即有不少片商將資金投入港片或中國電影,亦造成中港台三地合作交流的現象。此一低迷,直到2008年借助一千萬輔導金拍攝的《海角七號》(實際的資金當然不只此數目),大放異采,再次掀起票房的熱潮,也給台灣電影打了一劑強心針,似乎又給國片帶來一絲新的希望。
本書的三十部「文學電影」,其中有六部正是屬於九○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紀的產物。
《沙河悲歌》,係以靜觀內斂的運鏡,逝水悠悠的舒緩節奏,敘述醉心吹奏藝術的男子,卻難以見容於戰後初期的保守社會,竟致咳血以終。時代的今昔對照,兼及男女、父子、兄弟的感情點染,並側寫歌仔戲、那卡西的流浪生涯,瀰漫著懷舊與鄉愁,沒有《原鄉人》尋根的虛矯,卻另有一股平淡中的雋永。
《月光下我記得》,編導則是將政治的傷痕與女性的情慾做了有機性的連結。《沙河悲歌》有個專制父親,無法包容兒子的夢想;《月光下我記得》也有個權威的母親,難以容忍女兒的情愛。其實,父親與母親的背後,都有其難言的歷史傷口。月娘浮光,情慾流動,母親原想阻撓女兒與外省男子情愛,孰料反而竟衍生出自我壓抑的情慾潰堤;在此隱然可見「後殖民」所熱衷挖掘的「白色恐怖」歷史記憶,以及「後現代」所興味揭露的「女性情慾」,此皆為台灣經驗的深層部分,過往在電影中未敢觸及,大概是解嚴之後才敢正視的禁忌吧?
《徵婚啟事》以劇中人的徵婚管道,讓觀眾恣意地偷窺到時下社會各種人性百態、男女情慾及光怪陸離的私密告白,充滿了「後現代」的多元異質、身分流動、懷疑論、雜燴、拼貼……之種種特質與機趣。《向左走向右走》也是以「後現代」的思維,藉著偶然相遇卻暗中互相愛慕的男女,企圖探究緣份的偶然和必然,思索生命的絕望與希望,最後出現大地震屋牆碎裂的誇張表現手法,迥異於早先李行、白景瑞、瓊瑤的文藝愛情片,見證了「後現代」與世紀末的另一種超現實的風情。
《插天山之歌》與《一八九五》,分別改編自鍾肇政與李喬的小說,時代背景均設定在日治的殖民時期。前者試圖以小成本書寫大歷史,憑著獨立製片挑戰商業體制,可見其企圖與勇氣;影片描述客籍青年在日本讀書,因反日遭到通緝,返台時遇到船難後逃入山區,在漫長的逃亡旅程中,一方面受到鄉親保護,體認到母親大地的溫暖,一方面透過實踐學會農事技能,更堅定了自我的獨立想法。全片以客語、河洛語、日語發音,洋溢著台灣純樸的農村景緻與客家人的家居生活,突顯出台灣(客家人)自主的精神,也正面揭示了原住民的形象。而《一八九五》則以客籍秀才吳湯興等人自組義勇軍的抗日壯舉為主軸,不同於一般抗日片,並不刻意醜化日人,而是讓殖民者──文學家也是儒醫的森鷗外觀點,與被殖民者──客家母親的觀點,流漾其間,並置對照,骨子裡卻是站定台灣人的立場,高舉客家女性的形象。這兩部電影具有台灣意識的內涵,均帶有八○年代以來「後殖民」創作的意味,從台灣中心的歷史觀出發,試圖挖掘原住民、客家人、河洛人的歷史記憶,探討台灣抗日的心靈創傷,此與早先中影所強調的中華意識已顯然不同,也是只有在解嚴之後逐漸走向民主化才可能出現的現象。
告別舊時代 進入新世紀
有人說,電影是個工業,是商品;也有人說,電影是藝術,是文化產物;對大多數的市民而言,電影則是娛樂,是家族的回憶;而對於我們,寧可視之為台灣共有的文化資產,也是大家繾綣夢迴的美好回憶,在曩昔的歲月,它伴隨著許多人成長、流淚、歡笑,也帶給不少人啟發、警惕和深思。
這三十部「文學電影」的作家,都是戰後台灣作家的翹楚,他們嘔心瀝血的小說無疑都是文學殿堂難得的極品,整體觀之有如一座繁華盛開的花園,細品它又像走入一部精采的文學史,這些作品誠值得有識之士再三溫故知新。而電影的編導與演員,也幾乎涵蓋了台灣三個世代優異的電影精銳,他們的摸索、努力和成就,正顯示出台灣半世紀以來電影的榮景與風華,頗值得大家再次品味觀賞。
近來,終於見到楊德昌的《恐怖份子》、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陳玉勳的《熱帶魚》三部電影的「數位修復典藏版」在坊間出現,其實這項數位修復的工作早就應該積極進行。觀諸歐美日本重視電影工業的國家,不僅早就從事電影大師及經典電影數位處理的工程,還不斷增添新加的收錄內容,不定期推出新的典藏版,舉凡費里尼、雷奈、柏格曼、塔可夫斯基、布紐爾、楊秋、巴索里尼、小津、溝口健二……的電影,皆可輕易購得其數位化修復版的全集,可見他們對電影經典的重視。在此,我們一方面期盼修復的工作能再接再厲,讓這些文化資產有較理想的畫質、有豐富的收錄,也希望有心的電影朋友能給予熱情的回饋。
電影尚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像是紀錄片一般,會為美好的風景定格,永恆保留台灣的地景實像。這三十部「文學電影」所呈現的地景,包括了台灣本島與離島,從北部港都基隆到南國港都高雄,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儼然展現了台灣海島地景的特色。為此遠景出版社還特別借重詩人路寒袖的攝影才華,聘其為台灣掌鏡,不辭辛勞遠赴各地及澎湖離島,拍攝一系列現今的地景,相信透過電影中地景的今昔對照,當會加深我們對自己土地的認識與關愛,體悟台灣外在與內在真誠的素樸之美。
這些文學,這些電影,容或在藝術形式上有優點也有缺憾,但都包含了各種身分人物曾所發生過的故事,反映出各個族群、各個階層,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角落,共同成長、互相依存的記憶,都是令人可以歌泣、足以深思、彌足珍貴的台灣經驗。相信這些族群記憶的再現、爭辯及交流,將有助於我們命運共同體的了解、包容與尊重,除了能凝聚內部的向心力、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之外,這些族群共生共榮、患難相助的經驗,應該也是我們告別舊時代、進入新世紀主要的動力吧!
在台灣和世界與時俱進的關鍵時刻,舉國沸騰,全民激情,老是圍繞著政治與經濟的議題而爭論不休,有何新意呢?或許,換個角度、換個心情,就可發現福爾摩沙好旅行;多用您的腳親炙這片土地和風景,多用您的心貼近台灣的文學與電影,細聽台灣內在靈魂自然發出的聲音,您當會發現它們可愛多了,也寧靜多了,充滿了智慧與生機。面對國際的風雲變幻,凝視世局的詭譎多變,似乎也在指引著台灣的現在和未來。
2010年,台北,深秋
【前言】
光影夢迴 照亮台灣──《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
文/張恆豪
文學與電影的夢幻組合
文學是透過文字的藝術,感應時代風潮,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思想和感情;電影則是以影像美學,極視聽之娛,呈顯各種交織的生命光影,揭露人們的慾望和想像。儘管它們藝術的媒介不同,但殊途同歸,其發掘探究人性的本質,豐富化並深刻化我們生命經驗的目的是一致的。
文學與電影的夢幻結合,有時是水乳交融,相互輝映,有時則是電影糟蹋了小說,也有不少是電影照亮了原著。
萌發於二○年代以後的台灣新文學與電...
目錄
下冊
導言 光影夢迴 照亮台灣 張恆豪
輯四
1984 風塵中的純純愛:從《在室男》看蛻變的高雄 鄭順聰
1985 火焚的女神:從《結婚》看現代與傳統的角力 張恆豪
1985 吧女速成班,在花蓮:談王禎和的小說及電影《玫瑰玫瑰我愛你》 林明昌
1985 桂美一生的腳步:電影《我這樣過了一生》所見證的台灣經濟地景 陳儒修
1986 同志電影的先河:論電影版《孽子》 李志薔
1987 台灣的母親金水嬸:從《金水嬸》看台灣的社會經濟與底層庶民 陳儒修
1987 桂花巷裡春光老:電影《桂花巷》中女人的一生 熊啟萍
1988 從前從前有座春秋茶室:從《春秋茶室》看內灣山村的今與昔 鄭順聰
1989 閃閃的淚光《魯冰花》:電影《魯冰花》的童稚與現實 陳儒修
輯五
1998 最終,敗犬嫁給了城市:《徵婚啟事》中的台北地景 鄭順聰
2000 明亮的理想,黯淡的哀鳴:電影《沙河悲歌》中李文龍的音景與情景 解昆樺
2003 繪本、漫畫與電影的三角習題:看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亮軒
2004 風吹雲散,月娘浮光:論《月光下我記得》中的女性情慾 李志薔
2007 亂世中的插天山之歌:談《插天山之歌》的文學、電影、地景 陳三資
2008 而今客家作主人:李喬《情歸大地》與電影《一八九五》 林明昌
下冊
導言 光影夢迴 照亮台灣 張恆豪
輯四
1984 風塵中的純純愛:從《在室男》看蛻變的高雄 鄭順聰
1985 火焚的女神:從《結婚》看現代與傳統的角力 張恆豪
1985 吧女速成班,在花蓮:談王禎和的小說及電影《玫瑰玫瑰我愛你》 林明昌
1985 桂美一生的腳步:電影《我這樣過了一生》所見證的台灣經濟地景 陳儒修
1986 同志電影的先河:論電影版《孽子》 李志薔
1987 台灣的母親金水嬸:從《金水嬸》看台灣的社會經濟與底層庶民 陳儒修
1987 桂花巷裡春光老:電影《桂花巷》中女人的一生 熊啟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