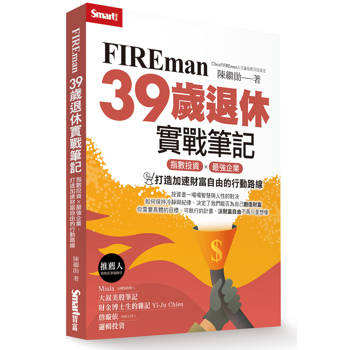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的圖書 |
 |
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 作者:朱漢民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1-07-01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40 |
哲學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中國哲學 |
$ 387 |
中國/東方哲學 |
$ 387 |
社會人文 |
$ 38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n 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上影響巨大的兩大思潮,二者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本書主要採用「內在理路」的解釋方法,著重探討玄學與理學的學術脈絡與思想理路,探討在中國的社會歷史「外緣條件」下演變、發展的「內在理路」。
\n\n 中國思想傳統本來就體現了中國人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獨立思考,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和視角,產生了一套獨有的問題意識和概念體系,譬如人性與天道、陰陽與五行、名教與自然、有為與無為、知與行等等,從而建構了一套既高深又實用的中國式學術傳統和思想體系。學術界對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但是對於玄學與理學內在理路的研究,學術界還較少涉及。本書希望在玄學與理學的不同學術形態中尋找其內在關聯。
\n\n 關於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研究,其實是要思考與解決這些重要的問題:玄學為什麼會轉型為理學?理學是如何既汲收玄學又取代玄學成為主流學術思想?玄學、理學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對先秦儒、道兩家學說的會通,從而體現了秦漢以後中國學術思想走向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但是,玄學是以道家為主體而相容儒家,被當代學者稱為「新道家」;理學則是以儒家為主體而相容道家(也包括佛學),被當代學者稱為「新儒家」。
\n 本書的基本結構是「生活世界→思想觀念→經典學術」。作者首先討論玄學家、理學家在生活世界、人格理想的思想理路;繼而探討他們生活世界之後的思想基礎,即思考玄學、理學的身心之學、性理之學的思想理路;最後則研究了他們思想觀念的經典依據,挖掘了玄學、理學關於《論語》、《周易》詮釋的內在理路。
\n 宋儒在整合傳統資源時,對玄學的繼承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魏晉玄學在個體安頓、哲學思辯、身心修養三個方面是先秦、漢唐時期儒學所不及的,玄學作為一種能夠用來對抗外來佛學的重要傳統資源,正好能夠為儒學重建作出有價值的重要貢獻。但是,學術界對玄學與理學的這種內在關聯一直重視不夠,形成的學術成果較少。本書的研究探索,可以明瞭宋儒是如何利用傳統資源回應佛教,實現中國思想文化的時代更新、理論重建的問題。對當代中國如何充分利用傳統資源,以解決回應西方文化、實現傳統儒學、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重建提供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