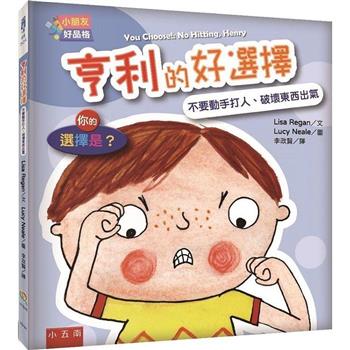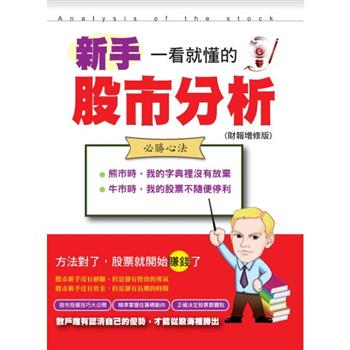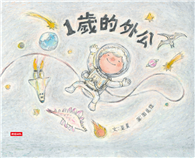序
任劍濤教授在2010年10月至12月來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在訪問期間與本院研究東亞儒學的同仁時相過從,切磋學問,並撰寫《複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乙書。現在書稿終於殺青,並經本院送兩位學者匿名審查後,再經作者修正通過。在付梓之際,承劍濤好意,要我寫一篇序言,我樂於從命,略申我拜讀此書的一些心得與淺見,以就教於本書的讀友。
儒學是東亞文明的主流思想,中日韓各國學者關於儒學的研究論著之出版如雨後春筍,指不勝屈。劍濤這部《複調儒學》在近年中日韓文的同類著作中,最大的貢獻在於指出並分析儒學傳統的「複調」性。所謂「複調」一詞,是劍濤取自巴赫金(1895-1975)論杜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小說的特質的名詞。劍濤以「複調儒學」一詞呈現數千年來儒學傳統的複雜面向,因此,在這部書中所探索的儒學思想是宋人楊萬里(1127-1206)的詩所謂「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場景。在這種多樣的儒學發展潮流中,並不存在「正統」與「異端」的區別,任劍濤教授在本書〈導論〉開宗明義中說:
歷朝歷代的儒家思想家,都是因應於它們各自時代,既承接孔子的基本原則,又努力適應時代所需,因此獨立地承接並開創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儒學的思想主體。在「儒學」的總名之下,從來不存在哪個單一的學派被公認為「正宗的」儒學,而其他儒學流派的創制就是「偽託的」儒學的情形。只要是站在儒家基本價值立場上的理念演繹、制度構思和生活籌畫,都是儒學中具有獨立價值的組成部分,具有其不可忽略的存在理由。
劍濤以上述態度研治「複調儒學」,可以說做到了荀子(約公元前298-238)所揭示的「以學心聽,以公心辯」的治學原則。
傳統的「正統」與「異端」之辨,固然可能是建立在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的基礎上的偏見,但是,正如劍濤所說,「複調儒學」的發展,仍是經由人心秩序與政治秩序二大主軸的淘說與篩選,因此,「複調儒學」呈現某些基本結構,劍濤把這種結構區分為三類,他說:
所謂複調儒學之「複調」,至少有三個含義,一是儒學本身處理的主題是複調的。從一部儒學史來看,它對於政治和倫理的雙向同化,自始至終懷抱濃厚興趣;二是儒學在中國社會流變中逐漸吸收了不同思想流派的精華,因此在顯得愈來愈蕪雜的同時,也愈來愈增強了與各派思想相容的能力;三是儒學與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緊密互動,政治生活與思想學術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各個不同時代的社會倫理生活狀態與政治生活氣氛,構成儒學自身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
劍濤從思想主題、思想內涵與社會政治背景,歸納儒學的「複調」,這是符合中國儒學史幾千年的發展事實的。
但是,我想進一步補充的是:在21世紀亞洲發展與全球化的新時代裡,我們的儒學研究事業如果能夠宏觀儒學傳統在東亞各地如朝鮮、日本、臺灣、越南等地的發展,我們對儒學的「複調」性就更能獲得新解,我們對於儒學之作為東亞文明公分母的內涵,以及儒學在東亞各地發展的異趣,就更能心領神會。舉例言之,朝鮮時代儒者對孟子(約公元前371-289)所說的「四端」與源出於《禮記.禮運》的「七情」之說,就展開兩場激烈的往返論辯,雖然朝鮮儒者均籠罩在朱子的義理架構之下,但是卻又於朱子當有所歧出。李明輝教授在《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一書中有精彩的分析。中國儒學經典東傳朝鮮與扶桑之後,均獲得異域知音,展開經典的新生命。我過去曾經在《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出版,2008再版,韓文本在2011年在成均館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就《論語》中最具關鍵性的「學而時習之」、「吾道一以貫之」以及「五十而知天命」等三項命題在日韓儒者手中,所獲得的新解釋有所探討。在異域儒學的「萬山不許一溪奔」的思想場景中,時而石破天驚,聲析江河,時而管絃嘔啞,低訴衷曲,在同一個儒學主調中展開多音的詮釋。日韓地區的歷代儒者在研讀中國儒學經典時,常飽受儒學普世價值與各國地域特性之間的拉扯,各國儒者也常輾轉呻吟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張力。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日韓儒學常能「六經責我開生面」(王夫之詩),提出具有時間性特質(time-specific)與空間性特質(site-specific)的新詮釋,使「複調儒學」的「複調性」更加豐富。簡言之,如果我們要欣賞「複調儒學」的豐富內容,那麼,「東亞儒學」這塊學術園地確實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是我們值得努力以赴的新領域。
但是,我必須強調的是:作為「複調儒學」的東亞儒學,並不是中、日、韓、越各國儒學的機械性組合。相反地,所謂「東亞儒學」的「複調」性之所以獲得彰顯,關鍵正是在於將各國儒學置於「東亞」的時間性(temporality)與空間性(spatiality)交織而成的架構中加以衡量,其地域特性與思想特質才能豁朗。也只有在「東亞」的框架之中,我們才能掌握中國儒學經典如何經歷日韓儒學加以「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並賦予新解而「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於各自國家的文化思想風土之中,由此而完成由中國儒學在異域的「脈絡性轉換」(“contextual turn”)。而且,經過「脈絡性轉換」的新詮釋之後的中國儒學經典,也經歷「從此奇男已丈夫」的生命轉化,在異域的文化風土中「橘逾淮為枳」,取得新的生命力。只有在「東亞儒學」研究的廣袤視野之中,我們才更能欣賞「複調儒學」在空間的視域中所揭露的鳥語花香的思想世界。
除了以上所說的開啟儒學的「複調」性這一點之外,劍濤這部新書的另一項貢獻在於對現代性儒學建構的進路問題的探索。正如劍濤所宣稱,他在這本書中所關心的是「力圖展現儒學從它的古典新解釋演進到現代性條件下如何重建」的問題。劍濤不僅著眼於儒學經典的學問的梳理,而是關心儒學的當下處境、現實作用及其未來展望。劍濤特別強調他這本書「不是一本基於辯護或批判的儒學研究著作,而是一本力求陳述儒學發展的現代方向的作品」,正如本書作者的特質與風格一樣,這本書所關懷的是儒學作為指引21世紀人類的明燈的作用,劍濤筆下所論述的不是護教的(apologetic)儒學,而是具有普世意義的所謂「現代性儒學」。
事實上,劍濤所關心的問題,正是最近數十年來國內外許多儒學研究工作者殫精以思的課題。上個世紀港臺新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徐復觀(1904-1982)、牟宗三(1909-1995)都曾思考如何從儒家傳統開出民本政治的問題。唐君毅寄望於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牟宗三訴諸於道德主體之「良知的坎陷」,而徐復觀則希望以儒家的性善論賦予現代民主政治以道德的基礎,並經由自耕農階級的復興,而創造「儒家民主政治」,我在拙著《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一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中,對上述問題也有初步討論。最近有許多學者撰文探討儒學的民主觀、資本主義觀以及法治觀,對「儒學」與「現代」的接筍問題有所思考(參考:Daniel A. Bell and Hahm Chaibong eds.,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劍濤在本書第10章主張:重建儒家「覆蓋律的普遍主義」立場,將儒家推進到與現代自由民主政體相得益彰的思想世界,是今天面對現代性儒學建構任務的儒家中人必須正視的要務。他關心的是「儒學如何開展其現代內涵」這個問題。20世紀港臺當代新儒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都聚焦在儒學的根本精神:「道德主體性的建立」這個問題,但是在21世紀的今日,儒學面臨的挑戰也許是:「道德主體性的客觀化如何可能」這個問題。用20世紀自由主義大師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話來說,就是:傳統儒家思想家很重視以「自作主宰」(self-mastery)為核心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但卻忽視保障「積極自由」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換言之,傳統儒家重視「freedom of …」 而較為忽略「freedom from …」。我們在21世紀思考所謂「儒家民主」、「儒家憲政主義」或「儒家資本主義」等可能性的時候,恐怕也不能完全跳過其下層結構的基礎如「儒家民主」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等。劍濤正在構思「普世儒學」作為他下一部著作的主題,我相信儒學研究同道以及廣大的讀者都期待劍濤在下一部新著中,對上述問題提出他獨到的見解。我相信現在《複調儒學》這部書的出版,將為儒學研究開啟一個新視窗,並引領儒學與21世紀進行更深刻而具有創造性的對話。
黃俊傑
序於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1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