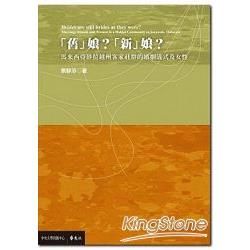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舊」娘?「新」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10 |
社會科學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性別研究 |
$ 270 |
社會人文 |
$ 270 |
教育學習 |
$ 285 |
大學出版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舊」娘?「新」娘?
婚姻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婚姻將女兒從原生家庭的暫時身分轉為另一個家庭的成員,因而給她一個永久的安身之處。她組成自己的子宮家庭,同時也成了婆婆的子宮家庭之一員。透過結婚「儀式」從而轉變的「身份」,得以觀察女性對自身的角色變化與社區家庭的貢獻認同,以及外地工作的年輕一輩是否會帶回一套影響婚姻儀式進行的新想法和思維。
本書透過研究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客家社群的一個村落——大富,探討客家女性議題,觀察記錄客家族群這個聚落的聚集與誕生。希望了解華人女性人生中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婚姻」的變遷,以及女性與婚姻儀式的關係。
作者簡介
蔡靜芬
出生在古晉,於聖德麗莎小學及中學接受小學及初中的正規教育,之後到聖若瑟中學完成其高中教育,其後她榮獲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負笈日本深造七年;期間獲得日本國際語言和文化促進組織的兩年獎助金。她先取得日本東京一橋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後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及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完成其博士學位。
任教於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社會科學院人類學暨社會學系,並擔任課程主管之職位。於此同時,也執行由國內外所資助的砂拉越華人廟宇調查、砂拉越客家人與比達友婦女通婚,以及華人習俗與婚喪跟中元節儀式之研究計畫。她亦活躍於砂拉越客家公會,並擔任義務的馬來語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