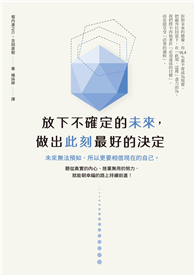英國文化研究和戲劇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於《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一書,提出他對西方悲劇發展的獨特見解。他認為「悲劇」這術語從古希臘流傳至廿世紀,沒變的是術語本身,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已隨著年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一般人只注重一個戲劇傳統的延續,卻往往忽略了斷裂的層面。從他的視野來看,所謂「悲劇已死」其實是無稽之談,它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罷了。
這個概念的延伸即是:審視悲劇傳統的工程不一定意味我們要研究一堆劇作或想法,或只是在被公認的整體(assumed totality)裡找出不符合那整體的例子(例外的徵兆或跡象)。這項工程的意義在於,以批評和歷史的視角,審視那些作品和思潮。最重要的是,除了找出歷史傳承的軌跡外,更要以當時的脈絡(immediate contexts)來檢視作品與思潮的位置與功能,從而發現它們和其他作品與思潮的關係,以及它們和活生生經驗的關係。簡言之,我們不能在真空狀態下研究一個概念。(威廉斯 6-36)
威廉斯指出,希臘悲劇之後,西方於文藝復興時期發展出人文主義悲劇(humanist tragedy):文藝復興時期悲劇的主要來源之一就是有名望人士的隕落(falls of famous men)。但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此時的悲劇有了新的連結。舊的故事被重新改寫,而因為這些故事和整體人類有些關連,作者企圖在著名人士的隕落和一般人的經驗找到了連結。人文主義悲劇強調人的重要性,強調個人主義,它擅於描寫個案,關於一個特定人士的故事。這個人通常在結尾時發現到他的極限(有時是死亡),但他是在意欲衝破極限的行動中才發現了自身的侷限。悲劇英雄的探索朝兩方向行進:一是外在的極限,例如《馬克白》(Macbeth);另一是內在的極限,例如《哈姆雷特》(Hamlet)。在希臘悲劇,悲劇英雄的身分(世襲的位階、榮耀、責任)蓋過個人色彩(那個人的個性已被涵括在身分裡面);但是文藝復興的悲劇裡,個人色彩超越了他的社會位階──有時候這種身分與個性不合之處正是戲劇衝突的地方,例如《奧賽羅》(Othello):張力來自個人和他的社會角色。(6-36)
到了十九世紀末,也就是現代戲劇的開端,悲劇又有新的發展,從人文主義悲劇演變為自由主義悲劇(liberal tragedy);後者的獨特情境是:「人既處在自己能力的顛峰,也面臨自己力量的極限。他的理想遠大,卻遭到挫折。他釋放很多能量,卻被自己的能量所摧毀。這一結構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因為它強調不斷超越的個人;這一結構也是悲劇性的,因為它最終認識到失敗或勝利的侷限」(79)。如果說人文主義悲劇的英雄意欲超越的是不可捉摸的神秘宇宙和命運,自由主義悲劇英雄的死敵大都是社會體制(婚姻、宗教、父權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因此,後者往往以解放者或烈士的形象現身─易卜生(Henrik Ibsen)之《娃娃之家》(A Doll's House)和《人民公敵》(Enemy of the People)就是兩個明顯的例子:
我們一次又一次在易卜生的作品中看到,主人公面對的世界充滿謊言、妥協和僵硬的觀念;當他奮起抗爭的時候,主人公發現作為人的他也屬於這個世界,而且繼承了它的毀滅傾向。(91)
於是,英雄逐漸自我懷疑。對威廉斯而言:
這正是自由主義悲劇的關鍵。究其原因,我們已經從反抗社會並渴望自由的個體解放者的英雄立場,轉向反抗自我的悲劇性立場。換句話說,就像理想被認為是個人內心的東西,罪惡也被內在化和個人化了。到最後,個人內心的事實成了唯一普遍的事實。英雄階段的自由主義開始走向它在廿世紀的瓦解:它走進了那個自我封閉、充滿內疚,並且與人隔絕的世界。在這個時代,人成為自己的受害者。(94)
我們在易卜生的劇作裡看到如上的發展,而到了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作裡,個體已淪落為全然的受害者。
然而,威廉斯進一步指出,除了自由主義悲劇外,廿世紀的西方還發展出其他形式的悲劇。例如,以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歐尼爾(Eugene O'Neill)、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為代表的「私人悲劇」──在其中,「悲劇是與生俱來的。這不僅因為人的最深層的原始欲望被他人和社會挫敗,而且因為這些欲望本身包含著破壞和自我破壞。所謂的死亡意向被賦予了普遍本能的地位,由它派生出來的破壞性和傾略性也被認為基本上是正常的」(100)。或如,同樣描寫悲劇性的困境與僵局的契呵夫(Anton Chekhov)、皮藍德羅(Luigi Pirandello)、伊爾涅斯柯(Eug?ne Ionesco)、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劇作家──「在困境中,人雖然還在努力奮鬥,但他沒有勝利的可能。這位生活鬥士竭盡全力而死去。在僵局中,不存在任何行動的可能性,甚至連行動的企圖也沒有;每一項主觀行動都會自我抵銷」(139)。
以上是威廉斯對於西方現代悲劇發展,從易卜生以降到1960 年代的分析。1970 年代之後呢?「悲劇」是否仍然存在?依照威廉斯的觀點,悲劇當然存在,只不過它的面貌勢必不同。以本書論及的品特(Harold Pinter)和馬梅特(David Mamet)為例,之前的「悲劇英雄」或「悲劇性受害者」似乎都無法解釋兩位劇作家的人物。品特的劇作裡,我們看到傳統戲劇的人物(character)的死亡:他的人物的內在無法捉摸,甚至一片漆黑,而人物的行動往往源自於當下的、本能的欲望。馬梅特的戲劇裡,我們見識到人之為主體的死亡,他的人物幾乎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充其量只是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傀儡。除了自身眼前的障礙外,兩位劇作家筆下的人物大半對於超乎個人的困境與僵局毫無察覺。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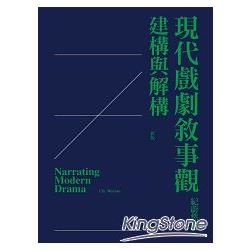 |
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 作者:紀蔚然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0-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5 |
藝術設計 |
$ 308 |
藝術設計 |
$ 315 |
高等教育 |
$ 315 |
高等教育 |
$ 315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
在後現代主義劇場當道的年代,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劇作家對於刻畫存在處境的執著反而留下值得反覆思辨的軌跡。他們回應身處的時代情境和物質條件,發展出新穎的敘事策略、對白風格、語言觀,進而突破傳統情節論,書寫現代人繁複的心理結構。本書通過後結構主義敘事理論為文本分析提出新的蹊徑,更立體地論述易卜生、史特林堡、梅特林克、契訶夫、皮蘭德羅、貝克特、伊爾涅斯科、品特、馬梅特、謝伯德等劇作家的敘事策略和存在情境之間的辯證互動。
作者簡介:
紀蔚然
第17屆國家文藝獎得主;美國愛荷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臺灣大學戲劇系專任教授。專長領域為當代戲劇、劇本創作,亦是國內知名劇作家。
章節試閱
英國文化研究和戲劇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於《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一書,提出他對西方悲劇發展的獨特見解。他認為「悲劇」這術語從古希臘流傳至廿世紀,沒變的是術語本身,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已隨著年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一般人只注重一個戲劇傳統的延續,卻往往忽略了斷裂的層面。從他的視野來看,所謂「悲劇已死」其實是無稽之談,它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罷了。
這個概念的延伸即是:審視悲劇傳統的工程不一定意味我們要研究一堆劇作或想法,或只是在被公認的整體(assumed totality)裡找出不符合那整體...
這個概念的延伸即是:審視悲劇傳統的工程不一定意味我們要研究一堆劇作或想法,或只是在被公認的整體(assumed totality)裡找出不符合那整體...
»看全部
作者序
現代戲劇與悲劇的傳統
──代新版序
英國文化研究和戲劇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於《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一書,提出他對西方悲劇發展的獨特見解。他認為「悲劇」這術語從古希臘流傳至廿世紀,沒變的是術語本身,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已隨著年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一般人只注重一個戲劇傳統的延續,卻往往忽略了斷裂的層面。從他的視野來看,所謂「悲劇已死」其實是無稽之談,它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罷了。
這個概念的延伸即是:審視悲劇傳統的工程不一定意味我們要研究一堆劇作或想法,或只是在被公認的整...
──代新版序
英國文化研究和戲劇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於《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一書,提出他對西方悲劇發展的獨特見解。他認為「悲劇」這術語從古希臘流傳至廿世紀,沒變的是術語本身,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已隨著年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一般人只注重一個戲劇傳統的延續,卻往往忽略了斷裂的層面。從他的視野來看,所謂「悲劇已死」其實是無稽之談,它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罷了。
這個概念的延伸即是:審視悲劇傳統的工程不一定意味我們要研究一堆劇作或想法,或只是在被公認的整...
»看全部
目錄
現代戲劇與悲劇的傳統──代新版序
原序
導 論 故事該怎麼說?──重返三個犯罪現場
一、重返第一犯罪現場
二、故事是這樣說的
三、故事是這樣說的?
第一章 敘述之驅魔儀式?──《娃娃之家》的形構過程
一、《娃娃之家》的開頭
二、敘述的挑逗/挑逗的敘述
三、驅魔之後的餘毒
第二章 單音與複調──另類疏離的《櫻桃園》
一、集中或打散
二、單音VS.複調
三、腹語術
第三章 述說真理──《鬼魅奏鳴曲》及現代戲劇的弔詭
一、事物的核心
二、執著與迷失
三、弔詭重重
第四章 語言觀──從寫實到荒謬
一、深信不...
原序
導 論 故事該怎麼說?──重返三個犯罪現場
一、重返第一犯罪現場
二、故事是這樣說的
三、故事是這樣說的?
第一章 敘述之驅魔儀式?──《娃娃之家》的形構過程
一、《娃娃之家》的開頭
二、敘述的挑逗/挑逗的敘述
三、驅魔之後的餘毒
第二章 單音與複調──另類疏離的《櫻桃園》
一、集中或打散
二、單音VS.複調
三、腹語術
第三章 述說真理──《鬼魅奏鳴曲》及現代戲劇的弔詭
一、事物的核心
二、執著與迷失
三、弔詭重重
第四章 語言觀──從寫實到荒謬
一、深信不...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紀蔚然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0-08 ISBN/ISSN:978986041954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正18開
- 類別: 中文書> 教育> 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