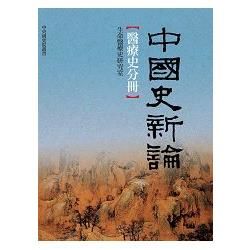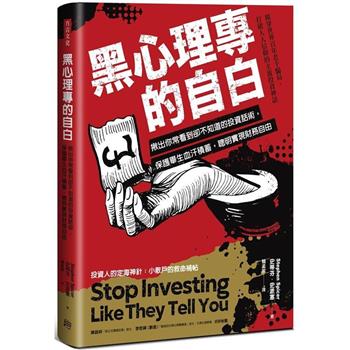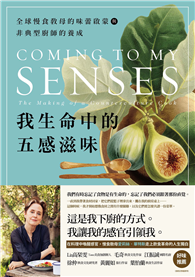《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強調:
一、中國人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
二、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醫與巫、道、儒的關係)
三、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
四、從醫學看文化交流的問題
五、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等
醫療史在中國史研究中,一向被視為專技的偏門,長期為具有中醫背景者所主導。199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杜正勝先生主導下組成「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小組,以史學為主體的研究取向,定期舉行月會討論醫療史課題,嗣後更在1997年正式創設「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並積極與國際學界交流、多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走出一條「另類醫療史研究」的大道,因此2001年成立的亞洲醫學史學會選擇將秘書處設置於史語所。
這個聚焦於社會史視野的中國醫療史有五個重要研究課題:「一、中國人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二、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醫與巫、道、儒的關係);三、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四、從醫學看文化交流的問題;五、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等。」用意在發掘歷史上中國人的生活、心態與文化深層,在政治、經濟與制度的骨幹上,賦予中國史研究血肉。
相較於醫家所寫的正統醫學史或是歐美的醫學史研究傳統,臺灣的醫學社會史還很年輕。這本論文集除了呈現臺灣近20年來中國醫學史研究的部分成果與特色,也試圖勾勒出它的未盡之處與未來的發展可能。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10 |
二手中文書 |
$ 593 |
總論 |
$ 593 |
醫學總論 |
$ 593 |
中國歷史 |
$ 638 |
健康醫療 |
$ 660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成立於1997年7月,成立宗旨是結合不同學科、不同單位的學者,以「生命與醫療」為核心課題,共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以增進學界對於各個歷史時期和各個人類社會的整體認識。此外,並擬藉著各種形式的研討會、出版品,以及長期不斷的搜集研究資料,使該研究室成為「生命醫療史」主要的研究中心。
為了墾拓中國史(和臺灣史)研究的新領域,也為了使中國和臺灣的歷史經驗成為人類整體歷史的一部分,史語所若干同仁於1992年夏天(7月)共同籌組了「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每一年都舉行10次左右的討論月會,並邀約所內外同道參與活動,至1995年夏天,共舉行30次的討論月會。
1995年,「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的成員,與該所人類學組另一群以宗教、禮俗研究為重心的學者結合,成立了「生活禮俗史研究室」,「生活禮俗史研究室」由「疾病、醫療與文化」與「宗教史研究」兩個小組所組成。除了繼續舉辦持續了三年之久的討論月會、進行資料整理之外,在1997年6月26日至28日,更召開了「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除了使國際學術界知道這個研究小組的存在與具體成就之外,也提出我們所關心的若干課題,和國內外的學者一起探索。
1997年7月,「生活禮俗史研究室」一分為二,分別成立「禮俗宗教史研究室」和「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承接「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原有之工作,並規畫各項主題研究。
1998年起,該研究室共舉行八次專題討論會,出版專書《從醫療看中國史》(李建民主編,2008)、《帝國與現代醫學》(李尚仁主編,2008)、《性別‧身體與醫療》(李貞德主編,2008)、《疾病的歷史》(林富士主編,2011)、《宗教與醫療》(林富士主編,2011)五冊(均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目前正推動「醫療的物質文化」先期計畫。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成立於1997年7月,成立宗旨是結合不同學科、不同單位的學者,以「生命與醫療」為核心課題,共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以增進學界對於各個歷史時期和各個人類社會的整體認識。此外,並擬藉著各種形式的研討會、出版品,以及長期不斷的搜集研究資料,使該研究室成為「生命醫療史」主要的研究中心。
為了墾拓中國史(和臺灣史)研究的新領域,也為了使中國和臺灣的歷史經驗成為人類整體歷史的一部分,史語所若干同仁於1992年夏天(7月)共同籌組了「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每一年都舉行10次左右的討論月會,並邀約所內外同道參與活動,至1995年夏天,共舉行30次的討論月會。
1995年,「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的成員,與該所人類學組另一群以宗教、禮俗研究為重心的學者結合,成立了「生活禮俗史研究室」,「生活禮俗史研究室」由「疾病、醫療與文化」與「宗教史研究」兩個小組所組成。除了繼續舉辦持續了三年之久的討論月會、進行資料整理之外,在1997年6月26日至28日,更召開了「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除了使國際學術界知道這個研究小組的存在與具體成就之外,也提出我們所關心的若干課題,和國內外的學者一起探索。
1997年7月,「生活禮俗史研究室」一分為二,分別成立「禮俗宗教史研究室」和「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承接「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原有之工作,並規畫各項主題研究。
1998年起,該研究室共舉行八次專題討論會,出版專書《從醫療看中國史》(李建民主編,2008)、《帝國與現代醫學》(李尚仁主編,2008)、《性別‧身體與醫療》(李貞德主編,2008)、《疾病的歷史》(林富士主編,2011)、《宗教與醫療》(林富士主編,2011)五冊(均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目前正推動「醫療的物質文化」先期計畫。
目錄
《中國史新論》總序╱王汎森
導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杜正勝
一、史家與醫家有交集嗎?
二、臺灣一個史學新領域的誕生:另類醫療史
三、看得見的成長:從茅廬到華廈
四、新腳成軍,十年斐然
五、另類醫療史的再思
附錄一 「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歷年活動
附錄二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歷屆研討會
中國的「巫醫」傳統╱林富士
一、引言:「獵巫」的醫學史?
二、巫為醫先
三、「巫醫」考釋
四、巫醫同職共事
五、病人巫醫兼致
六、信巫不信醫
七、不用巫醫與巫醫無用
八、結語:在批判與禁斷之下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醫學╱范家偉
一、引言
二、魏晉南北朝隋唐醫學發展的特點
三、世家大族與醫學傳承
四、隋唐時代官方醫療機構
五、士人知醫
六、醫學經典的重整——以《新修本草》為中心
七、方書與醫學知識的整合——以孔穴知識為例
八、佛道與醫療
九、總結
性別、醫療與中國中古史╱李貞德
一、前言:從一組生產造像談起
二、女性作為被照顧者
三、女性醫療照顧者
四、結論:複數的醫療史和多元的中國中古史
宋代儒醫╱陳元朋
一、引言
二、宋代士人尚醫風氣的形成背景
三、尚醫士人的醫學知識掌握深度
四、從「尚醫」到「醫者身分結構」的轉變
五、「儒醫」稱謂的出現及其延續
六、結論
附錄 兩宋官方醫籍編校暨刊印簡表
明清社會中的醫學發展╱梁其姿
一、醫者與醫學知識的傳播
二、有形與無形的制度
三、觀念的變化
四、結論
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邱仲麟
一、前言
二、惠民藥局未能惠民
三、醫者出診與交通工具
四、病家延醫的其他支出
五、生熟藥材與藥錢負擔
六、負擔能力的兩極化
七、社會認知與儒醫的醫道
八、結語
疫病、文本與社會:清代痧症的建構╱祝平一
一、引言
二、文本及其指稱功能
三、痧之為疾:指稱與實體
四、痧為疾乎?
五、結語
清代檢驗典範的轉型——人身骨節論辨所反映的清代知識地圖╱張哲嘉
一、前言
二、清代醫學所認識的人身骨節
三、清代檢驗知識之加速進展
四、乾隆、道光間對檢骨〈圖〉、〈格〉的商榷
五、許槤對檢骨〈圖〉、〈格〉的全面檢證
六、結論
清代外感熱病史——從寒溫論爭再談中醫疾病史的詮釋問題╱皮國立
一、前言
二、學說創新之外——復古尊經思想的影響
三、檢討溫病學與古典傷寒的關係——地域與方劑論述
四、外感熱病學門的問題——定義疾病之分歧
五、結論
晚清來華的西醫╱李尚仁
一、中國環境與歐洲人健康
二、治療中國病人
三、西方醫學遭遇的反挫
四、研究中國醫學
五、傳播西方醫學
六、結語
英文目次
導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杜正勝
一、史家與醫家有交集嗎?
二、臺灣一個史學新領域的誕生:另類醫療史
三、看得見的成長:從茅廬到華廈
四、新腳成軍,十年斐然
五、另類醫療史的再思
附錄一 「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歷年活動
附錄二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歷屆研討會
中國的「巫醫」傳統╱林富士
一、引言:「獵巫」的醫學史?
二、巫為醫先
三、「巫醫」考釋
四、巫醫同職共事
五、病人巫醫兼致
六、信巫不信醫
七、不用巫醫與巫醫無用
八、結語:在批判與禁斷之下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醫學╱范家偉
一、引言
二、魏晉南北朝隋唐醫學發展的特點
三、世家大族與醫學傳承
四、隋唐時代官方醫療機構
五、士人知醫
六、醫學經典的重整——以《新修本草》為中心
七、方書與醫學知識的整合——以孔穴知識為例
八、佛道與醫療
九、總結
性別、醫療與中國中古史╱李貞德
一、前言:從一組生產造像談起
二、女性作為被照顧者
三、女性醫療照顧者
四、結論:複數的醫療史和多元的中國中古史
宋代儒醫╱陳元朋
一、引言
二、宋代士人尚醫風氣的形成背景
三、尚醫士人的醫學知識掌握深度
四、從「尚醫」到「醫者身分結構」的轉變
五、「儒醫」稱謂的出現及其延續
六、結論
附錄 兩宋官方醫籍編校暨刊印簡表
明清社會中的醫學發展╱梁其姿
一、醫者與醫學知識的傳播
二、有形與無形的制度
三、觀念的變化
四、結論
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邱仲麟
一、前言
二、惠民藥局未能惠民
三、醫者出診與交通工具
四、病家延醫的其他支出
五、生熟藥材與藥錢負擔
六、負擔能力的兩極化
七、社會認知與儒醫的醫道
八、結語
疫病、文本與社會:清代痧症的建構╱祝平一
一、引言
二、文本及其指稱功能
三、痧之為疾:指稱與實體
四、痧為疾乎?
五、結語
清代檢驗典範的轉型——人身骨節論辨所反映的清代知識地圖╱張哲嘉
一、前言
二、清代醫學所認識的人身骨節
三、清代檢驗知識之加速進展
四、乾隆、道光間對檢骨〈圖〉、〈格〉的商榷
五、許槤對檢骨〈圖〉、〈格〉的全面檢證
六、結論
清代外感熱病史——從寒溫論爭再談中醫疾病史的詮釋問題╱皮國立
一、前言
二、學說創新之外——復古尊經思想的影響
三、檢討溫病學與古典傷寒的關係——地域與方劑論述
四、外感熱病學門的問題——定義疾病之分歧
五、結論
晚清來華的西醫╱李尚仁
一、中國環境與歐洲人健康
二、治療中國病人
三、西方醫學遭遇的反挫
四、研究中國醫學
五、傳播西方醫學
六、結語
英文目次
序
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導言
醫療史在浩瀚的中國史研究中,一向被視為專技的偏門,長期為具有中醫背景者所主導。在臺灣這種情況要等到杜正勝先生於1992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設「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小組,定期舉行月會討論醫療史課題,隨後並陸續發表〈什麼是新社會史〉、〈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等綱領性的論文,倡議研究生命醫療史之後,才有明顯的改變。杜正勝指出,「中國醫療史的研究向來著重於醫理、症候、方藥、醫案、醫說和醫家等方面」,相對的他從社會史的視野提出中國醫療史五個重要研究課題:「一、中國人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二、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醫與巫、道、儒的關係);三、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四、從醫學看文化交流的問題;五、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等。」相較於過去由中醫主導的醫史研究,杜正勝謙稱其所提倡的是「另類醫療史研究」,用意在發掘歷史上中國人的生活、心態與文化深層,政治、經濟與制度的骨幹上,賦予中國史研究血肉。
杜正勝的醫學史史學主張主要來自他研究中國史的心得,但他視醫學史為社會史的重要一部分,主張以研究社會文化的方法來研究傳統醫學,卻也和近年西方醫學社會史研究方法不謀而合。此外,此一研究綱領的立意,也迥異於中國醫史主流建構傳統、支持現今中醫正當性的研究旨趣,而成為臺灣中國醫學史研究在華文學界之特色。這種以(社會文化史)史學(而非醫學)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有助於和國際學術界溝通交流、密切合作。此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97年正式成立「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並積極與國際學界交流、多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乃至2001年成立的亞洲醫學史學會選擇將秘書處設置於史語所,可見一斑。為此,本集重刊杜正勝近年回顧臺灣醫史研究的重要論文〈另類醫療史研究二十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以助讀者瞭解臺灣醫學史的學術發展史與研究特色。
除了杜正勝的史學回顧外,本書所收其餘十篇論文大多和「新社會史」的研究旨趣與課題有關。例如林富士的〈中國的「巫醫」傳統〉透過分析大量的文獻,探討巫在中國歷史上擔任的醫療角色,以及巫與醫之間的身分區別與互動關係,同時也討論了庶民的心態與身體觀;陳元朋的〈宋代儒醫〉一文則對儒醫身分的興起作了詳盡深入的探討,堪稱對中國醫學史這段重要發展的最佳導論之一;范家偉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醫學〉則是中國中古醫學史宏觀的綜述,在探討中古醫療各個重要趨勢時,特別強調道教的影響以及家族的重要;梁其姿的〈明清社會中的醫學發展〉也以精要方式概論明清醫學,以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其重要特徵;李尚仁的〈晚清來華的西醫〉則討論中西不同的身體觀、醫療概念與中國大眾的信仰與心態,如何影響現代西方醫學的傳播與中西醫學交流。
近年中國醫學史研究不斷尋找新的主題、開拓新的領域,因此本論文集部分文章探索的觸角已經超出當初「新社會史」所標舉的主題。例如本集所收錄李貞德〈性別、醫療與中國中古史〉,除了探討女性醫療照護者的角色、生育問題及相關大眾心態之外,也觸及到受照護者的研究課題;邱仲麟〈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同樣觸及到「病人史」這個重要的面向,該文透過比較物價、工資與醫者收費來探討醫療史的經濟面,更是中國醫史研究值得深化開展的研究方向;祝平一的〈疫病、文本與社會:清代痧症的建構〉和本書收錄的數篇文章同樣處理到各類醫者的身分與其醫療實作的關係,但他還進一步引用美國醫學史大家查爾士.盧森堡(Charles Rosenberg)近年對西方醫療文化史研究影響極大的「框構疾病」(framing disease)的概念,深入探討中國疾病史,分疏醫者身份、文本與疫病等多重因素的互動,如何塑造疾病範疇與治療方法。
皮國立〈清代外感熱病史——從寒溫論爭再談中醫疾病史的詮釋問題〉也是疾病史的研究,卻以文化史的方法重新回頭探討過去傳統醫學史所關注的「 醫理、症候、方藥、醫案、醫說和醫家等方面」。就這點而言,這篇文章間接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研究方向:該如何以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回頭探討傳統「內史」的重要課題;張哲嘉〈清代檢驗典範的轉型:人身骨節論辨所反映的清代知識地圖〉則指出,相對於西方法醫學與醫學的密切關係,中國的檢驗學與醫學是分立而少有聯繫的兩個領域,清代檢驗學新典範的興起,並不是中國解剖學的開端,而是官僚文化與考據學學風等社會文化力量激盪下出現的檢驗學轉型。此文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文本、身體觀與醫學知識之間在中國歷史上的複雜關係,也間接解構了「中國醫學沒有解剖學究竟有何意義與影響?」這個在現代西方醫學衝擊下才會出現的假歷史問題。
論文集的編輯限於人事時機,總會挂一漏萬。這本論文集雖然盡力呈現近年臺灣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潮流與特色,但也無法周全。例如,近年對中國古代醫學史研究的成果頗為可觀,在多篇論文之外更有重要的專著陸續出版。然而這本文集除了林富士的文章觸及到古代醫學之外,卻未能收錄更多此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宗教與醫療的關係一直是臺灣醫史學界研究的重點,但佛教與醫療這個重要主題,這次卻無法涵蓋在內。這些遺憾必須在此序言中說明,以免造成讀者對醫療史的史學研究狀況有了偏頗的印象。
任何學術研究主題都難有窮盡的一天,即便中國醫療史研究目前在臺灣仍氣象蓬勃,但有待努力的地方與需要探索的方向仍多。梁其姿在〈明清社會中的醫學發展〉的結論提到,即便是目前相當蓬勃的明清醫療史,相較於歐美學界對於同一時期西方醫學的研究,「研究成果實在很少、深度上亦仍待加強」。這個斷語或許自謙太甚,但在繽紛大量的明清醫史論文之中,確實還沒有出現宏觀的綜述、新的史學命題和研究架構。 就中國醫療史整體而言,也很缺乏整合近年研究成果,同時為學界、學生乃至有興趣的讀者所寫的編年敘述體通史。這些都是中國醫史研究者未來可以進一步努力的地方。相較於醫家所寫的正統醫學史(杜正勝用語)或是歐美的醫學史研究傳統,臺灣的醫學社會史還很年輕,編輯這本文集的用心不只在呈現它的成果與特色,也試圖勾勒出它的未盡之處與未來的發展可能。
本書編輯出版因為種種因素,延宕已久,最後由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同仁組成編輯小組,並請余玟欣小姐擔任執行編輯,協力完成。本書最後能夠出版,終賴余玟欣小姐以及負責聯絡協調出版事宜的林明雪小姐,在此特致謝忱。最後,也要向貢獻大作並且願意耐心等待漫長編輯過程的所有作者致謝與致歉。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導言
醫療史在浩瀚的中國史研究中,一向被視為專技的偏門,長期為具有中醫背景者所主導。在臺灣這種情況要等到杜正勝先生於1992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設「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小組,定期舉行月會討論醫療史課題,隨後並陸續發表〈什麼是新社會史〉、〈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等綱領性的論文,倡議研究生命醫療史之後,才有明顯的改變。杜正勝指出,「中國醫療史的研究向來著重於醫理、症候、方藥、醫案、醫說和醫家等方面」,相對的他從社會史的視野提出中國醫療史五個重要研究課題:「一、中國人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二、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醫與巫、道、儒的關係);三、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四、從醫學看文化交流的問題;五、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等。」相較於過去由中醫主導的醫史研究,杜正勝謙稱其所提倡的是「另類醫療史研究」,用意在發掘歷史上中國人的生活、心態與文化深層,政治、經濟與制度的骨幹上,賦予中國史研究血肉。
杜正勝的醫學史史學主張主要來自他研究中國史的心得,但他視醫學史為社會史的重要一部分,主張以研究社會文化的方法來研究傳統醫學,卻也和近年西方醫學社會史研究方法不謀而合。此外,此一研究綱領的立意,也迥異於中國醫史主流建構傳統、支持現今中醫正當性的研究旨趣,而成為臺灣中國醫學史研究在華文學界之特色。這種以(社會文化史)史學(而非醫學)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有助於和國際學術界溝通交流、密切合作。此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97年正式成立「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並積極與國際學界交流、多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乃至2001年成立的亞洲醫學史學會選擇將秘書處設置於史語所,可見一斑。為此,本集重刊杜正勝近年回顧臺灣醫史研究的重要論文〈另類醫療史研究二十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以助讀者瞭解臺灣醫學史的學術發展史與研究特色。
除了杜正勝的史學回顧外,本書所收其餘十篇論文大多和「新社會史」的研究旨趣與課題有關。例如林富士的〈中國的「巫醫」傳統〉透過分析大量的文獻,探討巫在中國歷史上擔任的醫療角色,以及巫與醫之間的身分區別與互動關係,同時也討論了庶民的心態與身體觀;陳元朋的〈宋代儒醫〉一文則對儒醫身分的興起作了詳盡深入的探討,堪稱對中國醫學史這段重要發展的最佳導論之一;范家偉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醫學〉則是中國中古醫學史宏觀的綜述,在探討中古醫療各個重要趨勢時,特別強調道教的影響以及家族的重要;梁其姿的〈明清社會中的醫學發展〉也以精要方式概論明清醫學,以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其重要特徵;李尚仁的〈晚清來華的西醫〉則討論中西不同的身體觀、醫療概念與中國大眾的信仰與心態,如何影響現代西方醫學的傳播與中西醫學交流。
近年中國醫學史研究不斷尋找新的主題、開拓新的領域,因此本論文集部分文章探索的觸角已經超出當初「新社會史」所標舉的主題。例如本集所收錄李貞德〈性別、醫療與中國中古史〉,除了探討女性醫療照護者的角色、生育問題及相關大眾心態之外,也觸及到受照護者的研究課題;邱仲麟〈醫資與藥錢:明代的看診文化與民眾的治病負擔〉同樣觸及到「病人史」這個重要的面向,該文透過比較物價、工資與醫者收費來探討醫療史的經濟面,更是中國醫史研究值得深化開展的研究方向;祝平一的〈疫病、文本與社會:清代痧症的建構〉和本書收錄的數篇文章同樣處理到各類醫者的身分與其醫療實作的關係,但他還進一步引用美國醫學史大家查爾士.盧森堡(Charles Rosenberg)近年對西方醫療文化史研究影響極大的「框構疾病」(framing disease)的概念,深入探討中國疾病史,分疏醫者身份、文本與疫病等多重因素的互動,如何塑造疾病範疇與治療方法。
皮國立〈清代外感熱病史——從寒溫論爭再談中醫疾病史的詮釋問題〉也是疾病史的研究,卻以文化史的方法重新回頭探討過去傳統醫學史所關注的「 醫理、症候、方藥、醫案、醫說和醫家等方面」。就這點而言,這篇文章間接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研究方向:該如何以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與成果,回頭探討傳統「內史」的重要課題;張哲嘉〈清代檢驗典範的轉型:人身骨節論辨所反映的清代知識地圖〉則指出,相對於西方法醫學與醫學的密切關係,中國的檢驗學與醫學是分立而少有聯繫的兩個領域,清代檢驗學新典範的興起,並不是中國解剖學的開端,而是官僚文化與考據學學風等社會文化力量激盪下出現的檢驗學轉型。此文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文本、身體觀與醫學知識之間在中國歷史上的複雜關係,也間接解構了「中國醫學沒有解剖學究竟有何意義與影響?」這個在現代西方醫學衝擊下才會出現的假歷史問題。
論文集的編輯限於人事時機,總會挂一漏萬。這本論文集雖然盡力呈現近年臺灣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潮流與特色,但也無法周全。例如,近年對中國古代醫學史研究的成果頗為可觀,在多篇論文之外更有重要的專著陸續出版。然而這本文集除了林富士的文章觸及到古代醫學之外,卻未能收錄更多此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宗教與醫療的關係一直是臺灣醫史學界研究的重點,但佛教與醫療這個重要主題,這次卻無法涵蓋在內。這些遺憾必須在此序言中說明,以免造成讀者對醫療史的史學研究狀況有了偏頗的印象。
任何學術研究主題都難有窮盡的一天,即便中國醫療史研究目前在臺灣仍氣象蓬勃,但有待努力的地方與需要探索的方向仍多。梁其姿在〈明清社會中的醫學發展〉的結論提到,即便是目前相當蓬勃的明清醫療史,相較於歐美學界對於同一時期西方醫學的研究,「研究成果實在很少、深度上亦仍待加強」。這個斷語或許自謙太甚,但在繽紛大量的明清醫史論文之中,確實還沒有出現宏觀的綜述、新的史學命題和研究架構。 就中國醫療史整體而言,也很缺乏整合近年研究成果,同時為學界、學生乃至有興趣的讀者所寫的編年敘述體通史。這些都是中國醫史研究者未來可以進一步努力的地方。相較於醫家所寫的正統醫學史(杜正勝用語)或是歐美的醫學史研究傳統,臺灣的醫學社會史還很年輕,編輯這本文集的用心不只在呈現它的成果與特色,也試圖勾勒出它的未盡之處與未來的發展可能。
本書編輯出版因為種種因素,延宕已久,最後由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同仁組成編輯小組,並請余玟欣小姐擔任執行編輯,協力完成。本書最後能夠出版,終賴余玟欣小姐以及負責聯絡協調出版事宜的林明雪小姐,在此特致謝忱。最後,也要向貢獻大作並且願意耐心等待漫長編輯過程的所有作者致謝與致歉。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