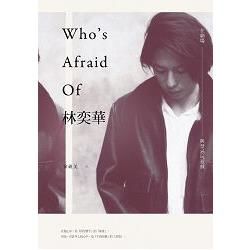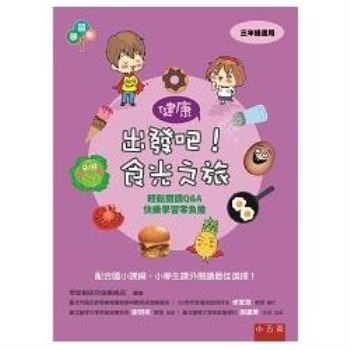序
我,再想想
「我能不能寫一本書去讓更多人知道林奕華這個人,或者是他的戲?」這個問題,是在收到邀請時,第一個在我腦中盤旋的念頭。
我總覺得,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在真正認識林奕華,與他一起工作以前,我就跟所有觀眾一樣,只是見戲,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見他的戲,跟見他的人,是一樣的。
第一次看他的戲,是二○○七年在臺北信義誠品展演廳上演的《包法利夫人們》。看戲的前一個月,他因為宣傳,來到大學的課堂當中演講,轉眼間,那已經是八年以前的事了。但,我還記得他在那場演講中的每一個問題。
那是一堂選修課,小小的教室,不到三十位學生,一開始,他放了一段關於「非常林奕華」的劇作回顧影片,然後,他問了一句:「你們覺得我的戲和你們看過的其他戲,有什麼不一樣?」
「我看到吳彥祖!」一個女學生興奮地說。他指的是二○○三年的《快樂王子》。
而林奕華很快地回問:「你很喜歡他?」女學生點頭如搗蒜。
「那你為什麼喜歡他?」林奕華再問。
「帥呀!」沒有任何意外的,女學生直率地回答,然後補了一句:「喔!我也好喜歡劉若英。」
他們開始閒聊(林奕華是一個常在演講過程中跟聽眾閒聊的人),過程中,他不外乎是分享一些他跟這些「明星」合作的經驗。
「我覺得你在設計演員肢體時,和我看過的戲不太一樣。」這是那時候的我問的問題。它很成功地吸引了林奕華的注意。
他回過頭來問:「怎麼不一樣?」
我呆住了,我知道不一樣,但就是找不到任何詞彙去回答,只好很直覺地說:「我不知道。」然後低下頭,想迴避這段對話。
「你不要這麼快說『不知道』,你一定是知道才說,只是你還沒『想』。」林奕華看著我說。
我繼續語塞,而他又連問了兩個問題。
「你在剛剛的影片中看到什麼?」
「你在過去的戲中看到什麼?」
「我再想想……」我說。
他笑了,而且說了一句:「你想想,我們等一下還要再聊。」
順著我們的對話,他又問了一個問題:「你們覺得明星拍照跟你們拍照有什麼不一樣。」
有人回答「眼神」,有人回答「姿勢」,有人回答「氣勢」。林奕華再問:「都對,可是這些到底在釋放出什麼樣的訊息?」有人說「買我」,有人說「自信」,有人說「神祕感」。
我心裡逐漸有一個字浮上來──性。
「幹我。」
林奕華在一陣吵雜聲之中突然說了這句話,所有的人安靜下來,因為,對於一群十八、九歲,二十歲不到的大學生而言,這個答案太禁忌了。我說太禁忌,並非大家不懂,只是,不可言說。
「難道不是嗎? 你們試試看把『FUCK ME!』放在那些雜誌、廣告的封面上,當作照片中人的『潛臺詞』,是不是很合呢?」他用英文再說了一次「幹我!」我發現沒人再注意他在解釋什麼了,大家開始陷入面面相覷,偶爾有人掩嘴訕笑,但不再有人接話。
在空氣中,彷彿可以聽見「哪有,才不要這樣說我的偶像!」或者是「又不是拍色情雜誌,怎麼可能所有的雜誌跟廣告都是這樣?」總之,那一段安靜的時間,我彷彿聽見比剛剛回答更大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而且持續發酵。但是,看起來都跟剛剛的議題有關,其實,這個議題早已被眾人的「想像」拉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去,人們在質疑,在提問,可是,始終沒有再討論下去。
從這裡,林奕華才開始談到關於《包法利夫人們》這齣戲的內容,概述了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談到他們怎麼樣讓十幾個北藝大的學生在香港花一個月的時間「讀」這本書。只是,真的是從這裡才開始談嗎?
在我看完戲走出劇場的那刻,我才發現,那天的演講,短短不到一百分鐘,林奕華看似只聊了二十分鐘的戲,然而,整齣《包法利夫人們》所要說的,早在「閒聊」的八十分鐘中說了。
所以,文章一開始我說:「我覺得他自己就可以完成這本書,去介紹他的人和他的戲。」的這件事,原因就是他的人,和他的戲,是密不可分、如出一轍的。他自己,就是一本叫做「林奕華」的書,裡面紀錄的,就是「非常」。
什麼是「非常林奕華」的「非常」?
我為什麼要詳實地記錄我和他初次見面的那一堂課? 為什麼那一堂課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因為,那一堂課中,蘊藏著太多「非常」和「如常」了。
八年了,至今仍有許多人在說:「林奕華是不是有明星焦慮?」說他的戲,非明星不用(在此明星的定義可以擴及劇場界的明星演員);也有人在問:「為什麼林奕華的戲,老是在談『性』與『慾望』?」甚至也有人在問:「林奕華的戲為什麼這麼難『懂』?」
那年的女學生一眼看見了吳彥祖和劉若英,之後可能有人一眼看見了張艾嘉、林依晨、何韻詩,甚至,現在有人一眼看見了朱宏章、時一修、謝盈萱、莫子儀、周姮吟。但,卻鮮少有人回答他的問題:「你為什麼喜歡他?」或者是說:「你能問問自己為什麼『第一眼』看到的就只是『明星』?」
那年的我看見了不一樣,卻在第一時間找不到詞彙回答,我很快地說:「我不知道。」而他一再地追問,只是想聽見我說:「我再想想。」至今,在我與他合作的過程中,他仍舊在等我思考,總是想辦法在議題中不斷地用問句「拓寬」討論的範疇,而非用答案終結一個議題。
「如果你被困在一個密室之中,問題是門? 還是答案是門?」這是他在一場宣傳《梁祝的繼承者們》的演講中,提給學生的問題。而到現在,許多學生還是回答:「答案是門」。把答案當作門的人,究竟有多麼恐懼與「問題」共處一室呢? 當問題來了,焦慮就發生,焦慮發生,就急切地希望有人能給予一個答案,而不是透過另一個問題,來探尋眼前問題為何而生。
這是我認為每一個創作者都需要面對到的「現實」,究竟,我們要消弭人的焦慮? 還是要透過作品,來啟發他們探尋焦慮的來源為何?
至今,仍有許多的觀眾,企盼坐在劇場的觀眾席裡,享受在黑暗中隱身的安全感,在光亮舞臺上尋找到自己想要看見的「答案」得到認同感,卻發現在林奕華的戲中,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冷不防地往內心去,一時之間找不著詞彙回應時,也是說著那句:「我不知道。」而在林奕華的心中,帶領他從困境中離開的,一直是「問題」。他一直在等,有人能夠說「我再想想」。
那年,那句「幹我!」換來的一點點的笑聲和一長段的沉默,至今,還是一樣。不是將林奕華所談的「性」當作一種點綴式的玩笑;就是將這樣的「性」視為一種禁忌,看到時仍舊是說:「才不是這樣的!」或者說:「『我』才不是這樣的!」而鮮少有人再問下去,為什麼「性」可以歷久不衰地成為戲劇的主題? 為何「性」在我們的文化中不是被看作「玩笑」,就是「禁忌」?
就在那堂課的六年之後,我成為一個文字工作者,自由撰稿人,這六年間,我和林奕華一直維繫著諸多奇妙的緣分。包括二○○七年《西遊記》在臺灣演出時,偌大的國家戲劇院,他就坐在我的旁邊。二○一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寫完了《三國》的觀後感放到網上,不到一小時,我收到了他的答謝。自此,我們常常聊天,網上聊,見面聊,工作時聊,吃飯時也聊。
一直到,聊到要寫這本書。之所以會答應,最主要是我想試著履行七年前在課堂上答應他的那句:「我再想想。」
現在,當我和他一起合作了四大名著系列的最後一部──《紅樓夢》,再回首這些年所看過他的作品,才發現,那些戲,談的是我還有好多好多人的,人生。
所以,如若再問我什麼是「非常林奕華」的「非常」?
在許多人心中,林奕華的如常,是非常的。他那麼愛問問題,問的問題又都是那樣地難以回答,他關懷的議題與平常的議題不同,當記者訪問他有關政治或是時下一些正炒得也吵得火熱的問題時,他的回答總是像一盆冷水,往那些熱切又充滿預設的「眼睛」與「耳朵」澆去,可是,他不關心嗎? 他怎會不關心? 一個不關心的人,哪需要問這麼多的問題呢? 在合作的過程中,我漸漸瞭解,他關心的不是「現象」,而是引起現象的「現代」,他不是追著「現象」被一個又一個的「話題」左右,而是將引起現象的「文化」,一層一層地剖析,帶出一個又一個「議題」。這如常嗎? 在他心中,是「為什麼不」的「如常」,但是,在許多人的心中,是「不為什麼」的「非常」。
何其有幸,能有機會將我對林奕華「習以為常」的非常這一點心得寫成一部作品與大眾分享。我想我與林奕華都是這樣地期望,透過這本書,在我們所看的戲中,在我們的人生中,能夠多那麼幾次「我再想想」的機會。
徐硯美 2015.04.17 23:39 寫於 臺北汀州路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