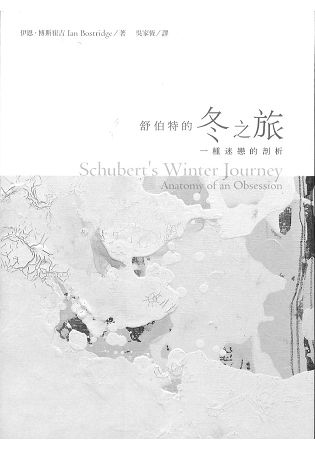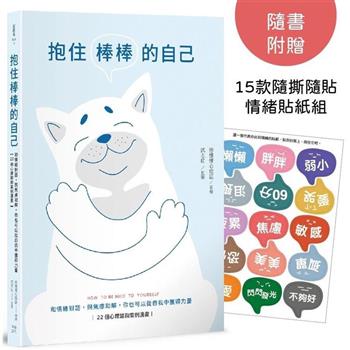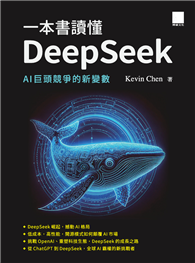《經濟學人雜誌》選為2015年度好書!
舒伯特在病痛折磨下,以德國詩人穆勒24首詩為本譜作了冬之旅聯篇歌曲,詩作描寫失戀的種種心情與情境,加上舒伯特的譜曲,而成為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也成就令世人魂牽夢縈的經典之作。
當時舒伯特是在什麼經歷之下,完成這一連串作品? 或許由近30年來詮釋冬之旅的最佳男高音暨牛津大學歷史博士——伊恩.博斯崔吉能帶來最佳的解答!
博斯崔吉以演唱者與歷史學者的雙重身分,對冬之旅做多層面、多角度的細緻解析:對音樂本身的分析,也分享演唱詮釋的竅門,更從歷史、文學、文化研究、哲學各種角度,探索音樂與詩文背後的意涵。
冬之旅本身是一趟旅程,而博斯崔吉長達三十年的探索,也是一趟旅程。這本書說明了何以博斯崔吉演唱的冬之旅如此豐富,也會讓讀者——包括音樂愛好者與歷史文化感興趣的人——對冬之旅產生全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