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稍微早一點、稍微晚一點的人,大概都多多少少受到五四運動及五四運動以後,三〇年代以及抗戰現實的影響。苦難的現實使人無法逃避,所以從我們讀書的時候開始,從小學開始,都有一個精神在後面鼓動我們,那個精神是什麼呢?就是一種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在二十世紀的五〇年代,仍然成為臺灣知識分子鼓動生命的源泉。───尉天驄
《在徬徨的年代:〈筆匯〉與五○年代》收錄「2015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活動紀錄,以《筆匯》、《文學季刊》、《文學雙月刊》、《文季》為主軸,探討「戰後人文思潮與臺灣文學的轉折」,由劉大任先生與張錯教授回顧戰後初期亞洲文化的變遷,以及陳芳明教授與楊澤先生細數1949年以來的臺灣文學發展,最後由尉天驄教授總結。本書並收錄相關學術論文及尉天驄教授的訪談記錄,讓我們能對這一段人文思潮與臺灣文學轉折有更深刻的瞭解與認識。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在徬徨的年代:《筆匯》與五○年代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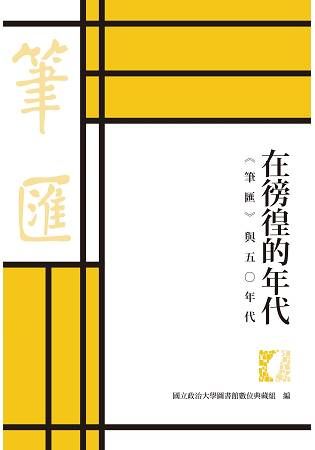 |
在徬徨的年代:《筆匯》與五〇年代 作者: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編 出版社:政大圖書館數位典藏組 出版日期:2017-01-1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華文文學研究 |
$ 315 |
文學作品 |
$ 315 |
小說/文學 |
$ 326 |
文學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在徬徨的年代:《筆匯》與五○年代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政大圖書館數位典藏組
近年來致力於史料數位保存,及促進數位人文學術發展,搭建史料與學術研究結合之平台為期許。「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即是落實此目標之具體行動,每年定期舉行,提供研究者利用圖書館所建置之數位典藏之史料,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與意見交流之平台。為讓更多關心者能參與,特將論壇之文集集結成冊出版系列專書,協助推動史料研究之創新學術發展。
政大圖書館數位典藏組
近年來致力於史料數位保存,及促進數位人文學術發展,搭建史料與學術研究結合之平台為期許。「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即是落實此目標之具體行動,每年定期舉行,提供研究者利用圖書館所建置之數位典藏之史料,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與意見交流之平台。為讓更多關心者能參與,特將論壇之文集集結成冊出版系列專書,協助推動史料研究之創新學術發展。
目錄
序
●館長序
引言
對談
●戰後初期亞洲文化變遷 陳芳明╲主持 劉大任、張錯╲對談
●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文學 林載爵╲主持 陳芳明、楊澤╲對談
結語
論文
●文化政策下的「五四」詮釋──戰後初期至五○年代的臺灣文學轉折
●一九六〇年代文學與藝術交織的光芒──以《筆匯》革新號與五月畫會為例
●「官方論述」與「文學自主」的消長──論《筆匯》革新號與《革命文藝》的文學創作觀
●從「寫實」到「現實」──論《文學季刊》、《文季》與臺灣文學思潮的「左轉」
●存在主義與左翼傳統的交會──重探「文季社群」六、七○年代的發展軌跡
口述歷史
●也可算是一次自我文化的摸索和啟蒙 尉天驄
文獻選輯
●在那樣的日子,大家不斷地追尋!懷念《筆匯》歲月 尉天驄
●館長序
引言
對談
●戰後初期亞洲文化變遷 陳芳明╲主持 劉大任、張錯╲對談
●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文學 林載爵╲主持 陳芳明、楊澤╲對談
結語
論文
●文化政策下的「五四」詮釋──戰後初期至五○年代的臺灣文學轉折
●一九六〇年代文學與藝術交織的光芒──以《筆匯》革新號與五月畫會為例
●「官方論述」與「文學自主」的消長──論《筆匯》革新號與《革命文藝》的文學創作觀
●從「寫實」到「現實」──論《文學季刊》、《文季》與臺灣文學思潮的「左轉」
●存在主義與左翼傳統的交會──重探「文季社群」六、七○年代的發展軌跡
口述歷史
●也可算是一次自我文化的摸索和啟蒙 尉天驄
文獻選輯
●在那樣的日子,大家不斷地追尋!懷念《筆匯》歲月 尉天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