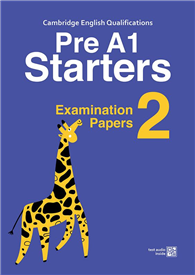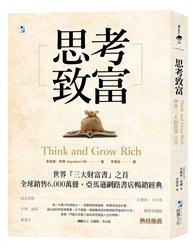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公民參與的框架與擴散:法、德、英的參與式預算的圖書 |
 |
公民參與的框架與擴散:法、德、英的參與式預算 作者:安雅•羅可 / 譯者:白舜羽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1-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財經/企管/經濟 |
$ 260 |
中文書 |
$ 260 |
高等教育 |
$ 266 |
社會與心理學群 |
$ 266 |
財經企管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公民參與的框架與擴散:法、德、英的參與式預算
內容簡介
起源於巴西愉港的參與式預算儘管被譽為民主創新的成果,在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時仍成效不一。本書藉由深度的經驗與理論分析,詳細解釋參與式預算在法、德、英三國的擴散動態,和框架與調整適用的過程。探討的問題包括參與式預算的國家特徵、及其促使社會更加民主的潛能。據此,本書針對三個歐洲國家的參與式預算倡議,進行理論上創新、經驗上紮實的綜觀,並對其提供批判性評估。本書的雙重焦點為個別案例的擴散及施行中的框架,並對其成果進行系統性評估。透過本書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參與式預算及其他公民參與制度流程的「成功因素」與成果。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安雅‧羅可( Anja Röcke)
現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她研究參與式民主及民主創新,近期也涉獵教育社會學。她研究過不同的參與式流程,從柏林的公民陪審團到歐洲的參與式預算,並在這些議題上有許多相關著作。
譯者簡介
白舜羽
臺大工商管理學系、哲學系雙學士,挪威科技大學應用倫理碩士,英國雷丁大學商學院博士候選人。
譯有《有毒污泥愛你好》、《輕輕鬆鬆實踐綠設計》、《父親的罪》,合著作品《倫敦腔: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
安雅‧羅可( Anja Röcke)
現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她研究參與式民主及民主創新,近期也涉獵教育社會學。她研究過不同的參與式流程,從柏林的公民陪審團到歐洲的參與式預算,並在這些議題上有許多相關著作。
譯者簡介
白舜羽
臺大工商管理學系、哲學系雙學士,挪威科技大學應用倫理碩士,英國雷丁大學商學院博士候選人。
譯有《有毒污泥愛你好》、《輕輕鬆鬆實踐綠設計》、《父親的罪》,合著作品《倫敦腔: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
目錄
謝 辭
引 言
第一部分 分析架構:框架、擴散與民主創新
第一章 框架與擴散
第二章 公民參與及民主創新
第三章 一項民主創新:愉港的參與式預算
第二部分 參與式預算國家模式的發明?
第四章 法國:「近鄰」民主與參與式民主
第五章 德國:諮詢、現代化與「公民城鎮」
第六章 英國:社群培力的國家策略
第二部分 小 結
第三部分 從框架到民主創新?三個參與式預算的在地案例
第七章 學校裡的參與式民主?法國波圖-夏洪大區的案例
第八章 參與式預算作為「公民城鎮」?德國柏林利希騰貝格的案例
第九章 一種由上而下的社群培力流程?英格蘭索爾福的案例(英國)
第三部分 小 結
結 論
註 解
參考書目
索 引
引 言
第一部分 分析架構:框架、擴散與民主創新
第一章 框架與擴散
第二章 公民參與及民主創新
第三章 一項民主創新:愉港的參與式預算
第二部分 參與式預算國家模式的發明?
第四章 法國:「近鄰」民主與參與式民主
第五章 德國:諮詢、現代化與「公民城鎮」
第六章 英國:社群培力的國家策略
第二部分 小 結
第三部分 從框架到民主創新?三個參與式預算的在地案例
第七章 學校裡的參與式民主?法國波圖-夏洪大區的案例
第八章 參與式預算作為「公民城鎮」?德國柏林利希騰貝格的案例
第九章 一種由上而下的社群培力流程?英格蘭索爾福的案例(英國)
第三部分 小 結
結 論
註 解
參考書目
索 引
序
謝辭
圖1.1「全球參與式預算概況(2013)」已於Sintomer, Y., Herzberg, C.與G. Allegretti(由A. Röcke協力研究)(2010)《向南方學習:世界各地的參與式預算:全球合作的邀約》(Learning from the Sout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orldwide – An Invitation to Global Cooperation)(Bonn: InWent gGmbH,Service Agency Communities in One World)一書中出版,p. 10。圖2.1「歐洲的參與式預算案例數目與參與人數」已於Sintomer, Y., Traub-Merz, R.與J. Zhang (eds)(2013)所編輯之《亞洲與歐洲的參與式預算:參與的關鍵挑戰》(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Asia and Europe, Key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ion)(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一書中出版,p. 10。感謝出版商允許重製。
此外,我也要感謝這些年來所有接受訪談的第一線人士,包括政治運動者、行政官員與政治人物。他們解答我參與式預算的理由與方式,以及提供對於公民參與更廣泛的規範性觀點,同時也用自己的問題挑戰這個研究。同樣地,感激我學術上的老師,伴隨我完成計畫並提供無比珍貴的協助。他們是Donatella della Porta、Yves Sintomer與Hans-Peter Müller。我還要謝謝其他研究者與同僚,他們在這個計畫的不同時刻給予我珍貴建議,尤其是Marie-Hélène Bacqué、Loïc Blondiaux、Carsten Herzberg、Joan Font、David McCourt、Alice Mazeaud、Stefania Milan、Lea Sgier、Graham Smith、Julien Talpin與Peter Wagner。
最後,我要對家人表達謝意,特別是我的父母Marja-Leena與Werner,以及我的手足Timo與他的家人,他們總是以各種方式支持我,沒有他們,這個研究不可能問世。另外我要大大擁抱Elena,和Fabian在愛與智性上的支持,讓這個研究能走到最後。
引言
「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參與式民主必須做到真正的權力分工﹝⋯⋯﹞要不然你只是應對公民諮詢、傾聽他們的聲音、接近他們⋯⋯儘管這些都很重要。但真正的參與必須要能作成決策,或至少可以影響決策。」這段話語出法國波圖-夏洪大區主席塞格琳‧賀雅爾(Ségolène Royal)的前任顧問,賀雅爾是主導地方高中參與式預算(PB)流程實踐的擘畫者。在此案例中,參與式民主成為新參與流程的主要參考架構,此流程讓一般人民即使未經選任,也可參與公共預算的分配。參與式預算在1980年代後期首創於巴西愉港,現已成為民主創新的「經典」案例,與英屬哥倫比亞公民議會(Lang, 2007)或芝加哥社區警務(Fung and Wright, 2003c)等量齊觀。在呼應這種新參與式體制的潮流下,「參與式民主」的理想應運而生(Genro, 1998, 2001; de Souza, 1998)。參與式預算在2000年代間以強而有力的新型態擴散全球,重啟這個來自1960年代的主要訴求(Wainwright, 2009: 22),並成為世界各地左翼與另類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參照之一。
本書所處理的理念是關於公民參與及其在參與式預算倡議中的角色,理念在此被視為「框架」(frame),即相對融貫但有彈性的「概念包裹」(ideational packages)(Polletta and Kai Ho, 2006: 191)。行動者不管有意無意,為求更有效地「理解」世界與/或公開發表訴求時,都會運用到這些概念包裹。這項研究計畫的開端,是觀察到2005年前後,法國、德國與英國投入參與式預算的人士,在爭論參與式倡議的目標與意義時,經常援引不同的概念。在德國,提倡普及參與式預算的人士,通常會提到公民城鎮(Bürgerkommune),內容包括增進公民參與,但通常排除參與式民主概念中的權力分工;然而參與式民主在法國的公共論述中,幾乎與公民參與畫上等號;在英國,參與式預算則往往連結到社群培力及社區發展的理念。此外,這些國家實行參與式預算時的程序型態,似乎也見證了特定的國族特徵。這些觀察引發了兩個主要問題:(1)就英、法、德參與式預算倡議中的擴散、實踐與成果而言,理念作為框架扮演了何種角色?(2)這些國家中參與式預算的具體成效為何?換言之,若民主創新的定義是為了改善民主制度運作所著意建立的新穎流程,可否視參與式預算為民主創新?亦實際達成了此目標?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亦有必要針對參與式預算的擴散動態以及調適參與式預算時,這三個歐洲民族國家框架的角色,進行更精確的理解。本章將提供這個主題的概覽、使用文獻與方法論架構。
圖1.1「全球參與式預算概況(2013)」已於Sintomer, Y., Herzberg, C.與G. Allegretti(由A. Röcke協力研究)(2010)《向南方學習:世界各地的參與式預算:全球合作的邀約》(Learning from the South: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orldwide – An Invitation to Global Cooperation)(Bonn: InWent gGmbH,Service Agency Communities in One World)一書中出版,p. 10。圖2.1「歐洲的參與式預算案例數目與參與人數」已於Sintomer, Y., Traub-Merz, R.與J. Zhang (eds)(2013)所編輯之《亞洲與歐洲的參與式預算:參與的關鍵挑戰》(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Asia and Europe, Key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ion)(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一書中出版,p. 10。感謝出版商允許重製。
此外,我也要感謝這些年來所有接受訪談的第一線人士,包括政治運動者、行政官員與政治人物。他們解答我參與式預算的理由與方式,以及提供對於公民參與更廣泛的規範性觀點,同時也用自己的問題挑戰這個研究。同樣地,感激我學術上的老師,伴隨我完成計畫並提供無比珍貴的協助。他們是Donatella della Porta、Yves Sintomer與Hans-Peter Müller。我還要謝謝其他研究者與同僚,他們在這個計畫的不同時刻給予我珍貴建議,尤其是Marie-Hélène Bacqué、Loïc Blondiaux、Carsten Herzberg、Joan Font、David McCourt、Alice Mazeaud、Stefania Milan、Lea Sgier、Graham Smith、Julien Talpin與Peter Wagner。
最後,我要對家人表達謝意,特別是我的父母Marja-Leena與Werner,以及我的手足Timo與他的家人,他們總是以各種方式支持我,沒有他們,這個研究不可能問世。另外我要大大擁抱Elena,和Fabian在愛與智性上的支持,讓這個研究能走到最後。
引言
「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參與式民主必須做到真正的權力分工﹝⋯⋯﹞要不然你只是應對公民諮詢、傾聽他們的聲音、接近他們⋯⋯儘管這些都很重要。但真正的參與必須要能作成決策,或至少可以影響決策。」這段話語出法國波圖-夏洪大區主席塞格琳‧賀雅爾(Ségolène Royal)的前任顧問,賀雅爾是主導地方高中參與式預算(PB)流程實踐的擘畫者。在此案例中,參與式民主成為新參與流程的主要參考架構,此流程讓一般人民即使未經選任,也可參與公共預算的分配。參與式預算在1980年代後期首創於巴西愉港,現已成為民主創新的「經典」案例,與英屬哥倫比亞公民議會(Lang, 2007)或芝加哥社區警務(Fung and Wright, 2003c)等量齊觀。在呼應這種新參與式體制的潮流下,「參與式民主」的理想應運而生(Genro, 1998, 2001; de Souza, 1998)。參與式預算在2000年代間以強而有力的新型態擴散全球,重啟這個來自1960年代的主要訴求(Wainwright, 2009: 22),並成為世界各地左翼與另類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參照之一。
本書所處理的理念是關於公民參與及其在參與式預算倡議中的角色,理念在此被視為「框架」(frame),即相對融貫但有彈性的「概念包裹」(ideational packages)(Polletta and Kai Ho, 2006: 191)。行動者不管有意無意,為求更有效地「理解」世界與/或公開發表訴求時,都會運用到這些概念包裹。這項研究計畫的開端,是觀察到2005年前後,法國、德國與英國投入參與式預算的人士,在爭論參與式倡議的目標與意義時,經常援引不同的概念。在德國,提倡普及參與式預算的人士,通常會提到公民城鎮(Bürgerkommune),內容包括增進公民參與,但通常排除參與式民主概念中的權力分工;然而參與式民主在法國的公共論述中,幾乎與公民參與畫上等號;在英國,參與式預算則往往連結到社群培力及社區發展的理念。此外,這些國家實行參與式預算時的程序型態,似乎也見證了特定的國族特徵。這些觀察引發了兩個主要問題:(1)就英、法、德參與式預算倡議中的擴散、實踐與成果而言,理念作為框架扮演了何種角色?(2)這些國家中參與式預算的具體成效為何?換言之,若民主創新的定義是為了改善民主制度運作所著意建立的新穎流程,可否視參與式預算為民主創新?亦實際達成了此目標?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亦有必要針對參與式預算的擴散動態以及調適參與式預算時,這三個歐洲民族國家框架的角色,進行更精確的理解。本章將提供這個主題的概覽、使用文獻與方法論架構。
自由選擇背後的行為賽局:讀哪間學校、跟誰結婚、是否生小孩、想與誰為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你繞開從眾偏誤,在人生關鍵時刻做出最佳決定
社畜有點BLUE
花得清楚,活得自由:一套沒有公式的庶民經濟學,用選擇改寫你的人生價值排序
被財神爺喜歡到怕的方法:淨化金毒、史上最簡單的開運增財術
2024年臺灣IT Spending 調查:批發零售業
散戶交易天才15萬滾10億的最強短線操作攻略
你漏財了!用錢致富的底層邏輯:漏財≠很會花。從消費到投資,有錢人想的、做的跟你哪裡不一樣!
一人公司的第零年教科書:不想只領死薪水!經營副業、全職接案、自行創業的致勝祕笈。任何時間(第零年)都可開始。
破框投資,照著做就能富:八大破框武器,不論是低薪、小資或準退休族,都能靠台股、美股、ETF,翻轉人生。
順勢傾聽:職場向上、抓住人心的深度溝通力
社畜有點BLUE
花得清楚,活得自由:一套沒有公式的庶民經濟學,用選擇改寫你的人生價值排序
被財神爺喜歡到怕的方法:淨化金毒、史上最簡單的開運增財術
2024年臺灣IT Spending 調查:批發零售業
散戶交易天才15萬滾10億的最強短線操作攻略
你漏財了!用錢致富的底層邏輯:漏財≠很會花。從消費到投資,有錢人想的、做的跟你哪裡不一樣!
一人公司的第零年教科書:不想只領死薪水!經營副業、全職接案、自行創業的致勝祕笈。任何時間(第零年)都可開始。
破框投資,照著做就能富:八大破框武器,不論是低薪、小資或準退休族,都能靠台股、美股、ETF,翻轉人生。
順勢傾聽:職場向上、抓住人心的深度溝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