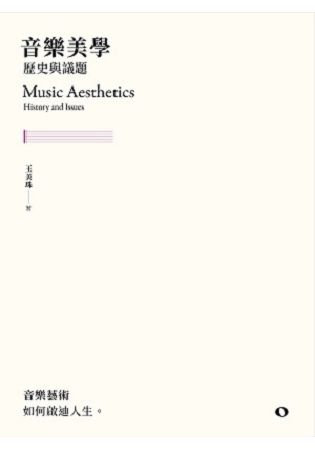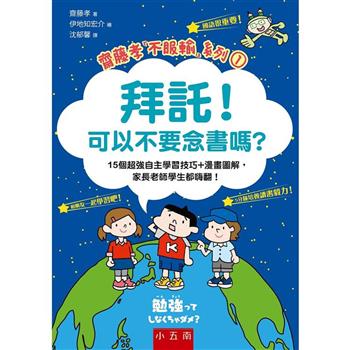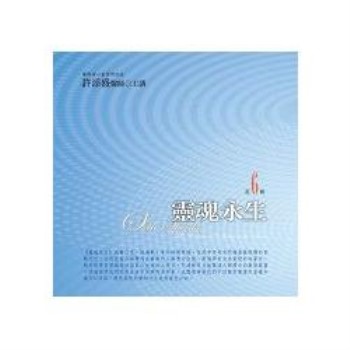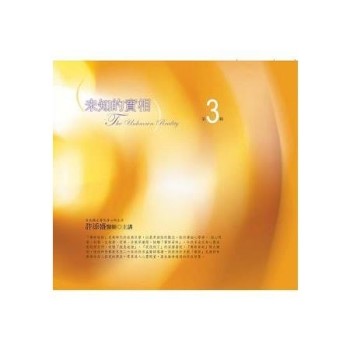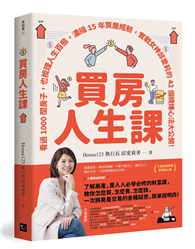音樂藝術如何啟迪人生與它在提升人類文化層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相關研究,一直是作者思考的出發點與企圖闡明的議題。
Homo sum, 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
作為一個人,我思考理解人類的一切。
( Terenz, Heautontimorumenos 77, in : Antike Komödien, Band III, in
der Übersetzung von J. J. C. Donner,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964 )
Vita brevis, ars longa.
生命短暫,藝術常存
( Seneca, De Brevitate Vitae 1, 1, nach Hippokrates, Aphorismoi 1, 1, in: Veni,
vidi, vici: geflügelte Worte aus dem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 ausgew.
und erl. von Klaus Bartels. - 9. Aufl. – Darmstadt: Wiss. Buchges., 1992 )
「音樂美學」 是「系統音樂學」跨學科研究領域中關於美學層面上的思考面向。它以音樂為藝術的一個特殊類型,把音樂做為一個整體,對音樂本質、內在規律性、意義與評價進行研究與闡述;這正是本書思考的出發點與立論根據。書中以歐洲音樂歷史發展為主軸,並以代表性思想家與音樂理論家的相關論述為議題,嘗試鋪陳歐洲「音樂美學」思想。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音樂美學:歷史與議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5 |
音樂 |
$ 315 |
音樂總論 |
$ 315 |
藝術設計 |
$ 315 |
音樂 |
$ 325 |
中文書 |
$ 326 |
音樂 |
$ 333 |
音樂 |
$ 333 |
音樂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音樂美學:歷史與議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美珠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德國漢堡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系統音樂學哲學博士;主修系統音樂學,副修歷史音樂學與哲學。1984 年10 月至1989 年7 月於漢堡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兼任教職。1989 年9 月回國後,先後兼任於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改制後今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東吳大學音樂系、國立藝術學院(改制後今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實踐大學音樂系與國立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2 年8 月至1997 年7 月專任於東吳大學音樂系,1997 年8 月至今專任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所專任期間曾兼任該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2002-2006)與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所長(2003-2009)。
研究主軸為音樂的跨域研究,如音樂美學、音樂心理學、音樂社會學、音樂語義學、音樂與符號、音樂與視覺藝術、音樂與文學等。主要著作:專書有《音樂.跨域.文集》,臺北:美樂出版社,2012 年11 月初版;《音樂.文化.人生》系統音樂學的跨學科研究議題與論文,臺北:美樂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2012年10月修訂版初版;《西洋音樂理論與美學對中國音律、數字與思想體系的接受與詮釋》(Die Rezeption des chinesischen Ton-, Zahlund Denksystems in der westlichen Musiktheorie und Asthetik, Frankfurt am Main/Bern/New York, 1985)等;近年來發表的期刊文章與研討會論文如〈音樂與符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評論》第23 期/2012 年7 月;《Musi? — 多面向音樂概念的闡釋與思考》,2007 臺灣音樂學論壇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等。
王美珠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德國漢堡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系統音樂學哲學博士;主修系統音樂學,副修歷史音樂學與哲學。1984 年10 月至1989 年7 月於漢堡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兼任教職。1989 年9 月回國後,先後兼任於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改制後今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東吳大學音樂系、國立藝術學院(改制後今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實踐大學音樂系與國立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2 年8 月至1997 年7 月專任於東吳大學音樂系,1997 年8 月至今專任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所專任期間曾兼任該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2002-2006)與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所長(2003-2009)。
研究主軸為音樂的跨域研究,如音樂美學、音樂心理學、音樂社會學、音樂語義學、音樂與符號、音樂與視覺藝術、音樂與文學等。主要著作:專書有《音樂.跨域.文集》,臺北:美樂出版社,2012 年11 月初版;《音樂.文化.人生》系統音樂學的跨學科研究議題與論文,臺北:美樂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2012年10月修訂版初版;《西洋音樂理論與美學對中國音律、數字與思想體系的接受與詮釋》(Die Rezeption des chinesischen Ton-, Zahlund Denksystems in der westlichen Musiktheorie und Asthetik, Frankfurt am Main/Bern/New York, 1985)等;近年來發表的期刊文章與研討會論文如〈音樂與符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評論》第23 期/2012 年7 月;《Musi? — 多面向音樂概念的闡釋與思考》,2007 臺灣音樂學論壇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際會議廳等。
目錄
序
第一章 定位
第一節 哲學 - 美學 - 音樂美學
第二節 音樂 - 音樂學 - 音樂美學
第二章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音樂思想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音樂的本質
第三節 音樂的功能
第四節 音樂的理解
第三章 歐洲中世紀音樂思想與代表人物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音樂理論家波埃提烏斯(Anicius Manlius Torquatus Severinus Boëthius)
第三節 女性作曲家賓根聖女希兒德佳特(Heilige Hildegard von Bingen)
第四章 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期音樂思想與代表人物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音樂理論家札利諾(Gioseffo Zarlino)
第三節 音樂理論家嘎利略(Vincenzo Galilei)
第五章 歐洲巴洛克(Barock)時期音樂思想與代表人物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情緒論(Affektenlehre) ─ 巴洛克時期音樂的主導思想
第三節 布爾邁斯特(Joachim Burmeister)的音樂修辭理論
第四節 音樂理論家馬泰松(Johann Mattheson)
第六章 法國百科全書(L' Encyclopédie)與百科全書派 (L' Encyclopédistes)
第一節 形成背景
第二節 代表人物與音樂思想
第三節 百科全書派與喜歌劇論戰(La querelle des Bouffons)
第七章 古典與浪漫時期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音樂形上學
第三節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與音樂
第四節 漢斯利克(Eduard Hanslick)與《論音樂美》
第八章 二十世紀以來
第一節 音樂哲學或音樂美學
第二節 多元化的二十世紀音樂
第三節 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
名詞索引
參考資料
第一章 定位
第一節 哲學 - 美學 - 音樂美學
第二節 音樂 - 音樂學 - 音樂美學
第二章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音樂思想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音樂的本質
第三節 音樂的功能
第四節 音樂的理解
第三章 歐洲中世紀音樂思想與代表人物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音樂理論家波埃提烏斯(Anicius Manlius Torquatus Severinus Boëthius)
第三節 女性作曲家賓根聖女希兒德佳特(Heilige Hildegard von Bingen)
第四章 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期音樂思想與代表人物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音樂理論家札利諾(Gioseffo Zarlino)
第三節 音樂理論家嘎利略(Vincenzo Galilei)
第五章 歐洲巴洛克(Barock)時期音樂思想與代表人物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情緒論(Affektenlehre) ─ 巴洛克時期音樂的主導思想
第三節 布爾邁斯特(Joachim Burmeister)的音樂修辭理論
第四節 音樂理論家馬泰松(Johann Mattheson)
第六章 法國百科全書(L' Encyclopédie)與百科全書派 (L' Encyclopédistes)
第一節 形成背景
第二節 代表人物與音樂思想
第三節 百科全書派與喜歌劇論戰(La querelle des Bouffons)
第七章 古典與浪漫時期
第一節 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
第二節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音樂形上學
第三節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與音樂
第四節 漢斯利克(Eduard Hanslick)與《論音樂美》
第八章 二十世紀以來
第一節 音樂哲學或音樂美學
第二節 多元化的二十世紀音樂
第三節 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
名詞索引
參考資料
序
作者序
王美珠
很高興2017年底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音樂美學:歷史與議題》有機會進行增補出版,使得作者當時因為時間關係只能點到為止的著作第八章第三節,關於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音樂的跨學科研究議題部分,得以進行可能性研究主題與思考議題的補充探討,讓本文更具完整性與實用性。
1885年,《音樂學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的首度發行,標示著「音樂學」(Musikwissenschaft)學門的確立。而古伊多•阿德勒(Guido Adler)在《音樂學季刊》創刊號中發表《音樂學的範圍、方法與目的》(Umfang, Methode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一文,提出依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上的差異,將音樂學分為「歷史的」與「系統的」音樂學二分法的主張,開啟了百餘年來「音樂學」學門的發展。
雖然如此,一直到二十世紀中期,音樂學還是等於音樂的歷史研究。1948年,奧籍音樂學者威雷克(Albert Wellek)在《音樂研究》(Die Musikforschung) 雜誌發表〈系統音樂學的觀念、結構與重要性〉(Begriff, Aufbau und Bedeutung einer Systematischen Musikwissenschaft)一文,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系統音樂學」的發展,除了建立系統音樂學的三個主要研究領域:音樂心理學、音樂社會學與音樂美學,還提出了與實踐有密切關係的音樂教育學。
本文以系統音樂學核心領域之一的「音樂美學」為研究內容,從「原則上涉及重複性的、有規則出現性的」(nomothetisch)學術研究觀點與方法出發,以音樂為藝術的一個特殊類型,將音樂做為一個整體,對音樂本質、內在規律性、意義與評價進行研究與闡述。文中不只提出系統研究的歷史觀點,也藉由系統思考洞察歷史,企圖闡明音樂藝術如何啟迪人生與它在提升人類文化層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著作首先言簡意賅與簡明扼要從「哲學」與「音樂」領域定位「音樂美學」。之後,以歐洲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經過啟蒙時期、古典與浪漫時期,到現代的歐洲音樂歷史發展為主軸,藉由呈現各時期的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再以幾位代表性思想家與音樂理論家相關論述的系統研究為議題內容,進行歐洲「音樂美學」的鋪陳。
除了思考二十世紀以來「音樂美學」或「音樂哲學」、多元化的二十世紀音樂等相關問題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基於人文科學的精神所在,也因不滿足傳統方式的音樂理解,音樂學者從不同角度觀察與剖析音樂,進而認識音樂的各種研究嘗試,同樣是本文關注的議題;著作第八章第三節「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內容的增補就提供重要實例。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中音樂的跨學科研究議題,如文中關於音樂與視覺藝術、音樂與文學、以及受到語言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啟發,以符號作為理解音樂本質基本概念的「音樂符號學」與「音樂語義學」等研究領域的勾勒與探討,不只掌握國際研究趨勢,有助於音樂藝術愛好者審美經驗與審美態度的培養與建構,對於音樂藝術與相關哲學思考有興趣者更值得一讀。
最後要感謝自1989年9月回國任教以來,曾經提供給作者機會與場域開設「音樂美學」課程,並得以累積教學經驗的學校與修習的學生,其中包括兼任的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改制後今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與實踐大學音樂系,尤其是專任教職的東吳大學音樂系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所。而本著作的發行更要感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支持與兩位校外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
王美珠
很高興2017年底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 —《音樂美學:歷史與議題》有機會進行增補出版,使得作者當時因為時間關係只能點到為止的著作第八章第三節,關於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音樂的跨學科研究議題部分,得以進行可能性研究主題與思考議題的補充探討,讓本文更具完整性與實用性。
1885年,《音樂學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的首度發行,標示著「音樂學」(Musikwissenschaft)學門的確立。而古伊多•阿德勒(Guido Adler)在《音樂學季刊》創刊號中發表《音樂學的範圍、方法與目的》(Umfang, Methode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一文,提出依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上的差異,將音樂學分為「歷史的」與「系統的」音樂學二分法的主張,開啟了百餘年來「音樂學」學門的發展。
雖然如此,一直到二十世紀中期,音樂學還是等於音樂的歷史研究。1948年,奧籍音樂學者威雷克(Albert Wellek)在《音樂研究》(Die Musikforschung) 雜誌發表〈系統音樂學的觀念、結構與重要性〉(Begriff, Aufbau und Bedeutung einer Systematischen Musikwissenschaft)一文,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系統音樂學」的發展,除了建立系統音樂學的三個主要研究領域:音樂心理學、音樂社會學與音樂美學,還提出了與實踐有密切關係的音樂教育學。
本文以系統音樂學核心領域之一的「音樂美學」為研究內容,從「原則上涉及重複性的、有規則出現性的」(nomothetisch)學術研究觀點與方法出發,以音樂為藝術的一個特殊類型,將音樂做為一個整體,對音樂本質、內在規律性、意義與評價進行研究與闡述。文中不只提出系統研究的歷史觀點,也藉由系統思考洞察歷史,企圖闡明音樂藝術如何啟迪人生與它在提升人類文化層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著作首先言簡意賅與簡明扼要從「哲學」與「音樂」領域定位「音樂美學」。之後,以歐洲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經過啟蒙時期、古典與浪漫時期,到現代的歐洲音樂歷史發展為主軸,藉由呈現各時期的音樂文化與主導思想,再以幾位代表性思想家與音樂理論家相關論述的系統研究為議題內容,進行歐洲「音樂美學」的鋪陳。
除了思考二十世紀以來「音樂美學」或「音樂哲學」、多元化的二十世紀音樂等相關問題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基於人文科學的精神所在,也因不滿足傳統方式的音樂理解,音樂學者從不同角度觀察與剖析音樂,進而認識音樂的各種研究嘗試,同樣是本文關注的議題;著作第八章第三節「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內容的增補就提供重要實例。二十一世紀音樂美學新趨勢中音樂的跨學科研究議題,如文中關於音樂與視覺藝術、音樂與文學、以及受到語言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啟發,以符號作為理解音樂本質基本概念的「音樂符號學」與「音樂語義學」等研究領域的勾勒與探討,不只掌握國際研究趨勢,有助於音樂藝術愛好者審美經驗與審美態度的培養與建構,對於音樂藝術與相關哲學思考有興趣者更值得一讀。
最後要感謝自1989年9月回國任教以來,曾經提供給作者機會與場域開設「音樂美學」課程,並得以累積教學經驗的學校與修習的學生,其中包括兼任的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改制後今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與實踐大學音樂系,尤其是專任教職的東吳大學音樂系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所。而本著作的發行更要感謝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支持與兩位校外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