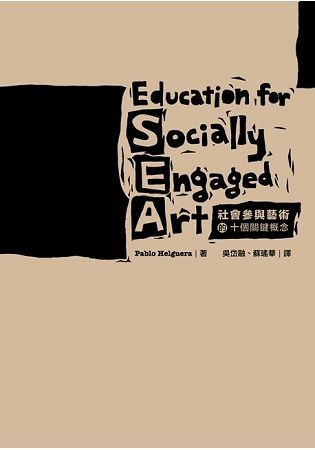長期以來,社會實踐被市場取向的當代藝術視為不堪一擊的對手:彷彿只是一個由社區/群中『自我感覺良好』的實踐者們所書寫構築的世界,卻無視於其類行動主義、反形式主義的立場,其實承襲了長久以來的藝術傳統,並可透過視覺藝術與劇場的歷史方法批判分析。埃爾格拉這本挑戰性十足的社會參與藝術入門書,肯定為仍在廣闊社會領域中的漂流者,提供了一個必不可少的羅盤。-克萊兒.畢莎普 (Claire Bishop)紐約市立大學當代藝術與展覽歷史教授
這是一本即時且極富思想性的參考著作。從實證、大量經驗與研究抽絲剝繭而生,這本書為探究社會參與藝術的複雜性,提供了課程與框架。埃爾格拉從行為藝術、教育學、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社區/群與公共實踐的歷史,為這本書在不同領域間劃定了方法學的座標。與其是提出一個系統,他更像揭露如何讓情境作用與合理的能與不能。這本工具書讓我們得以思考進行社會參與藝術的困境,從而尋找適切的語言得以再現或討論其影響。-莎莉.邰蘭蒂(Sally Tallant)利物浦雙年展藝術總監
埃爾格拉這本具高度可讀性的書,絕對是任何有意教授或學習社會參與藝術的人的必備讀物。-湯姆.費克博爾 (Tom Finkelpearl)前紐約皇后美術館館長/現任紐約市文化局局長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6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藝術設計 |
$ 252 |
藝術設計 |
$ 266 |
教育學習 |
$ 266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保羅‧埃爾格拉(Pablo Helguera)
出生於墨西哥的保羅‧埃爾格拉(Pablo Helguera),目前是一位活躍於美國紐約的視覺與行為藝術家,並擔任紐約市現代美術館教育部門「成人與學術計畫」的主任。他的創作類型涵蓋了裝置、雕塑、攝影、繪畫、行為、與社會參與藝術,題材則廣泛地涉及歷史、教育學、社會、語言學、民族學、記憶與怪誕,並結合演說、博物館展示策略、音樂劇表演與虛構小說等形式。
埃爾格拉另一個身分是教育工作者,這使他對詮釋、對話、以及當代文化在全球實境中的角色等議題格外關注。在2006年的力作《動盪的汎美學校(The School of Panamerican Unrest)》,即為他結合多重視角、身分的代表作,不但被認為是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公共藝術計畫,也為社會參與藝術開拓了另一個新的類型。
譯者簡介
吳岱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當代藝術教育理論、女性主義教學法與博物館學等。近年研究議題專注藝術創作與身體知識、社會參與藝術教育,並透過「教學即為創作實踐」,強調教師與藝術家兩者身分的共棲與疊合,從藝術學院脈絡建立藝術教育的當代論述。
蘇瑤華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文化規劃與城市再生、社會策展、博物館與可持續發展等。曾任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草創總監,臺北市URS華山大草原「臺北那條通」城市後巷生活展、日本瀨戶內藝術祭「種子船」策展人,為社會參與藝術的實踐者和教育者。
保羅‧埃爾格拉(Pablo Helguera)
出生於墨西哥的保羅‧埃爾格拉(Pablo Helguera),目前是一位活躍於美國紐約的視覺與行為藝術家,並擔任紐約市現代美術館教育部門「成人與學術計畫」的主任。他的創作類型涵蓋了裝置、雕塑、攝影、繪畫、行為、與社會參與藝術,題材則廣泛地涉及歷史、教育學、社會、語言學、民族學、記憶與怪誕,並結合演說、博物館展示策略、音樂劇表演與虛構小說等形式。
埃爾格拉另一個身分是教育工作者,這使他對詮釋、對話、以及當代文化在全球實境中的角色等議題格外關注。在2006年的力作《動盪的汎美學校(The School of Panamerican Unrest)》,即為他結合多重視角、身分的代表作,不但被認為是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公共藝術計畫,也為社會參與藝術開拓了另一個新的類型。
譯者簡介
吳岱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當代藝術教育理論、女性主義教學法與博物館學等。近年研究議題專注藝術創作與身體知識、社會參與藝術教育,並透過「教學即為創作實踐」,強調教師與藝術家兩者身分的共棲與疊合,從藝術學院脈絡建立藝術教育的當代論述。
蘇瑤華
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涵蓋文化規劃與城市再生、社會策展、博物館與可持續發展等。曾任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草創總監,臺北市URS華山大草原「臺北那條通」城市後巷生活展、日本瀨戶內藝術祭「種子船」策展人,為社會參與藝術的實踐者和教育者。
序
中文序
當我在七年多前著手撰寫這本書時,可以說是社會參與藝術的黃金時代。當代藝術在八至九年代初期歷經了後現代許多藝術家對於機構的批判,以及九年代關係美學的洗禮,社會參與藝術在當時看來,充其量不過是藝術家試圖將社會與政治批判結合在其作品中的一種作法。但就我的觀察,在911 和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社會實踐在美國的發展倏地成形,「社會互動」從此不再只是名義上的,而必須真實包含觀眾有意義的參與。
廿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藝術家們所進行的各式實驗與途徑,也許在日後回顧時,會是社會參與藝術不斷從實踐的錯誤中修正與摸索的關鍵期。
而在歷經這段關鍵期之後,幾位在美國不同藝術校院任教的藝術家們,也開始著手在學院課程中,教授社會參與藝術的可能性。這些藝術家包括了在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創設美國第一所社會參與藝術系所的泰德‧ 普維斯(Ted Purves),在奧勒岡州立大學(Oregoniv 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State University)任教的哈洛‧ 佛烈契(Harrell Fletcher),以及在奧蒂斯藝術設計學院(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任教的蘇珊‧ 雷西(Suzanne Lacy)等;這些相關系所與課程的建立,加速了社會參與藝術的課程化發展,我也因此穿梭在這些藝術系所之間,試著貢獻一己之力,將實踐經驗轉化為課堂素材,而這本書就是在奧勒岡州立大學,進行社會參與藝術的短期授課時所完成的。
觀察社會實踐在這幾年的迅速演進,是一件極為有趣的事。近年來,社會參與藝術向社會正義與行動主義靠攏,對於將藝術視為一種政治工具的藝術家們,特別具有吸引力。但這本書並不特別關注社會參與藝術在這個面向上的進展,因為在書寫的當下,這樣的思維仍在醞釀當中;然姑且不論社會參與藝術在這幾年的轉向,我相信以章名貫穿全書的十個關鍵概念,或在其之下所探討的對話、合作與評量原則等,即使參照社會參與藝術的現今發展進程,依然十分受用。此外,我有意識地不針對社會實踐的類型或方法,進行框限或評論,無論其本意是政治的、個人的、或是詩意的。是而,這本書的定位,是成為一本探究社會參與藝術「媒材」與「技法」的操作手冊,期望能描繪某些特定社會歷程的特質與結構,以及如何應用其建構特定的社會經驗,提供具體建議。
最後,在本書中文版發行的前夕,我仍舊在思索一個重要問題,即:這本書當中所談論的觀念和歷程,究竟對其他國家和不同的社會脈絡有否助益?過去幾年,我陸陸續續聽到日本、挪威、愛爾蘭、澳大利亞和瓜地馬拉等國家的藝術家與教授,在他/她們的教學現場中成功應用了這本書,這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回應了我的問題。因此,即使每個社會和文化的脈絡不盡相同,我相信這本書中所提及的若干基礎概念,應能適應殊異情境,協助讀者們找到可行的實踐路徑。
保羅.埃爾格拉
紐約,2017 年6 月
譯序
朝向一個更真實的實踐
閱讀埃爾格拉,實在是一個極具互動性的過程。身兼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工作者的他,遣詞用字不見艱澀卻極具批判力道;曾為文坦然面對自身在「動盪的汎美學校(The School of Panamerican Unrest)」藝術計畫中挫敗與教訓的他,在每一個關鍵概念下信手捻來的案例,無不讓讀者會心。加上他對於社會參與藝術脈絡的綜整,竟回應了我當年在賓州州立大學修習查爾斯.葛羅安(Charles Garoian)課程時的未竟之問(當時的我還無法理解為什麼我的老師要透過行為藝術,進行藝術教育)。每一次的閱讀,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思想鬆綁,彷彿埃爾格拉坐在眼前,真切地與讀者對話。
研究生們對於埃爾格拉的喜愛亦不在話下。年輕敏銳的他/她們,對於藝術圈的現象觀察,也需要相關理論撐持,這也促使我在擔任出版組組長期間,決心簽下本書中文版版權,讓埃爾格拉說起中文,使我們對於當代藝術家的教育性計畫,或如何透過參與式藝術與社群共學,能有更深切的認識與掌握。不過,翻譯之於我,從來就不是機械性的語言切換,它更像是譯者的詮釋與再造;為了避免失準,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合作對象,就是我心目中對於社會參與藝術,最具實踐與論述能力的瑤華。
在我們倆都有教學、研究、服務以及母職的多重壓力下,翻譯緩如牛步,但也因為這樣的低效作業,我們對於每一章節的推敲,得以反覆論辯。在此,我想針對幾個作為章名的關鍵概念進一步說明。首先是第二章「社群」(community)一詞,我們譯作「社群」而非「社區」,主要是其指涉對象不全然是地域上的社區,而是一群可能有共同地域或價值的人,是以「社群」名之;然而在正文當中,我們也以「社區/群」做為權衡譯法。其次則是「行為」(performance)一詞,我們回到社會參與藝術的發展脈絡,追溯其與行為藝術之間的關係,選擇以「行為」而非「表演」,作為第七章章名。第八章章名「文件」(documentation),則從「文件展」(documenta)演繹而來,除了以「文件」說明紀錄(在社會參與藝術中)的重要性與多樣性,也以文件展中,去中心化的、回顧性質的、教導啟發的特質,回應社會參與藝術。而第九章章名「跨教育學」(transpedagogy),則是我們感到最為棘手,卻不得不然的命名。埃爾格拉在本章當中,提出「跨教育學」一詞,說明社會參與藝術的展演性、知識性與轉化性,需透過融貫藝術與教育領域達成,但埃爾格拉語境中的trans,實在很難在中文裡找到精準的對位,是以「跨」名之,保留我們對此一教育學的想像空間。
吳岱融
關渡,2018 年1 月
譯序
參與的現場,微光
在抵達「社會參與藝術」這個命名之前,臺灣經歷過「戶外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公共藝術(民眾參與)」、「藝術介入」、「社區/社群藝術」等各種具「參與」性質的藝術實踐;戶外裝置藝術湧現於政治解嚴後,挑戰空間運用的方式、尺度,及藝術家對抗政治權威的批判;倡議民眾參與的公共藝術、社區藝術和藝術介入,則與民主價值和公民意識發展,息息相關。這些藝術的在地實踐各有其脈絡,但並不見得全部屬於本書範圍,埃爾格拉《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提供了描繪社會參與藝術的關鍵在於「社會實踐」。
「社會實踐一詞模糊了社會參與藝術所屬的『藝術』領域」。──埃爾格拉
藝術家的角色在社會參與藝術計畫中被削弱,帶來藝術家自身角色認定的危機,「是不是應該放棄藝術而成為專業的社區組織者、行動主義者、政治份子、民族誌工作者或社會學,才更能有所貢獻。」但也為其他領域提供了跨入藝術領域的路徑,「藝術工作者」成為描繪社會參與藝術推動者較貼切的稱謂,但這並不意味藝術家的稱謂或角色須被取代,只是多重角色的肯認,創造出更加細緻入微(而且誠實)、攜手合作的創作者和觀眾此消彼長的關係。也就如羅蘭‧ 巴特所說:創作者是多樣性的,而且不斷地受惠於他人。
社會參與藝術既以啟動創作者以外其他人的涉入參與為定義,辯論藝術家種菜究竟是不是藝術,其實就不是本書意圖為藝術家提出辯護或為觀眾進行藝術教育的首要目的。我在寶藏巖推動國際藝術村籌備工作時,以公共藝術作為一種啟動文化治理的方法,曾經邀請藝術家周靈芝與回住的社區居民一同整地種菜,藝術家放掉「既有」、「擅長」的藝術技能與知識,向社區居民學習種菜的方法,向生態工作者討教堆肥製作的技術,「生態農園」創作計畫過程的描述曾經被我以文字「紀錄」,翻譯埃爾格拉「定義」、「合作」、「文件」、「去技能化」等篇章時,記憶如跑馬燈般回想起諸種執行的情景,試想,如果當時有埃爾格拉這本書,作為實踐現場參照對話的對象,或許扭轉晦暗碰壁的作法會早些浮現!《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是一本以實踐者為對象的基礎入門書,書中所列一到十章並不意味著「操作流程」、或順序,每個章節都可各自獨立存在,回應實踐者現場的躊躇,所以建議讀者可以依照自身面對的情境,困擾你/妳的問題,以任何一章為起始,挑選閱讀。
對觀眾的思考與探討,幾乎是企業、行銷、管理、治理等全領域的議題,談社會參與藝術的「參與者」,埃爾格拉以「多層次的參與結構」拉出一個極富啟發性、寬闊的討論基礎,而「先創造,而後再考慮觀眾」,不只是藝術家這類創作者的想法,這樣的做法也存在於許多創新導向的工作者中,關心觀眾研究、社群建構的讀者可以仔細閱讀「社群」一章,將驚艷於作者的辯證分析:「觀眾……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他/她們在我們的作品中辨識出自己……」但自我辨識的發展非靜止、停滯,只提供觀眾固定的服務,未與建造它們的社群持續演化,反倒會帶來社群的蛀蝕或解散。社會參與藝術計畫雖在理論上是對廣大公眾開放,但實際上所服務的仍是非常特定的觀眾群。埃爾格拉務實的指認所謂追求肯認的核心迴圈為:(一)直接相關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二)藝術圈、(三)整體社會,例如政府組織、媒體等其他可能含納吸收此一計畫理念或面向的組織系統。
我從藝術行政現場轉入教育現場,觀察到改變對世界的理解與改變世界結構有著相近的效用,埃爾格拉在「跨教育學」一章對基進教育的提示,讓我相信,這本工具書提供的「微光」,即便現場不同因而對應的策略自有殊異,然而人們可以通過自我解放來改變權力關係,從而實現改變整體社會的目的,也就是個體應改變慣常思維和行為方式,在積極富有創造性和想像性的實踐中創造自己的「處境」。
當我在七年多前著手撰寫這本書時,可以說是社會參與藝術的黃金時代。當代藝術在八至九年代初期歷經了後現代許多藝術家對於機構的批判,以及九年代關係美學的洗禮,社會參與藝術在當時看來,充其量不過是藝術家試圖將社會與政治批判結合在其作品中的一種作法。但就我的觀察,在911 和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社會實踐在美國的發展倏地成形,「社會互動」從此不再只是名義上的,而必須真實包含觀眾有意義的參與。
廿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藝術家們所進行的各式實驗與途徑,也許在日後回顧時,會是社會參與藝術不斷從實踐的錯誤中修正與摸索的關鍵期。
而在歷經這段關鍵期之後,幾位在美國不同藝術校院任教的藝術家們,也開始著手在學院課程中,教授社會參與藝術的可能性。這些藝術家包括了在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創設美國第一所社會參與藝術系所的泰德‧ 普維斯(Ted Purves),在奧勒岡州立大學(Oregoniv 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State University)任教的哈洛‧ 佛烈契(Harrell Fletcher),以及在奧蒂斯藝術設計學院(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任教的蘇珊‧ 雷西(Suzanne Lacy)等;這些相關系所與課程的建立,加速了社會參與藝術的課程化發展,我也因此穿梭在這些藝術系所之間,試著貢獻一己之力,將實踐經驗轉化為課堂素材,而這本書就是在奧勒岡州立大學,進行社會參與藝術的短期授課時所完成的。
觀察社會實踐在這幾年的迅速演進,是一件極為有趣的事。近年來,社會參與藝術向社會正義與行動主義靠攏,對於將藝術視為一種政治工具的藝術家們,特別具有吸引力。但這本書並不特別關注社會參與藝術在這個面向上的進展,因為在書寫的當下,這樣的思維仍在醞釀當中;然姑且不論社會參與藝術在這幾年的轉向,我相信以章名貫穿全書的十個關鍵概念,或在其之下所探討的對話、合作與評量原則等,即使參照社會參與藝術的現今發展進程,依然十分受用。此外,我有意識地不針對社會實踐的類型或方法,進行框限或評論,無論其本意是政治的、個人的、或是詩意的。是而,這本書的定位,是成為一本探究社會參與藝術「媒材」與「技法」的操作手冊,期望能描繪某些特定社會歷程的特質與結構,以及如何應用其建構特定的社會經驗,提供具體建議。
最後,在本書中文版發行的前夕,我仍舊在思索一個重要問題,即:這本書當中所談論的觀念和歷程,究竟對其他國家和不同的社會脈絡有否助益?過去幾年,我陸陸續續聽到日本、挪威、愛爾蘭、澳大利亞和瓜地馬拉等國家的藝術家與教授,在他/她們的教學現場中成功應用了這本書,這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回應了我的問題。因此,即使每個社會和文化的脈絡不盡相同,我相信這本書中所提及的若干基礎概念,應能適應殊異情境,協助讀者們找到可行的實踐路徑。
保羅.埃爾格拉
紐約,2017 年6 月
譯序
朝向一個更真實的實踐
閱讀埃爾格拉,實在是一個極具互動性的過程。身兼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工作者的他,遣詞用字不見艱澀卻極具批判力道;曾為文坦然面對自身在「動盪的汎美學校(The School of Panamerican Unrest)」藝術計畫中挫敗與教訓的他,在每一個關鍵概念下信手捻來的案例,無不讓讀者會心。加上他對於社會參與藝術脈絡的綜整,竟回應了我當年在賓州州立大學修習查爾斯.葛羅安(Charles Garoian)課程時的未竟之問(當時的我還無法理解為什麼我的老師要透過行為藝術,進行藝術教育)。每一次的閱讀,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思想鬆綁,彷彿埃爾格拉坐在眼前,真切地與讀者對話。
研究生們對於埃爾格拉的喜愛亦不在話下。年輕敏銳的他/她們,對於藝術圈的現象觀察,也需要相關理論撐持,這也促使我在擔任出版組組長期間,決心簽下本書中文版版權,讓埃爾格拉說起中文,使我們對於當代藝術家的教育性計畫,或如何透過參與式藝術與社群共學,能有更深切的認識與掌握。不過,翻譯之於我,從來就不是機械性的語言切換,它更像是譯者的詮釋與再造;為了避免失準,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合作對象,就是我心目中對於社會參與藝術,最具實踐與論述能力的瑤華。
在我們倆都有教學、研究、服務以及母職的多重壓力下,翻譯緩如牛步,但也因為這樣的低效作業,我們對於每一章節的推敲,得以反覆論辯。在此,我想針對幾個作為章名的關鍵概念進一步說明。首先是第二章「社群」(community)一詞,我們譯作「社群」而非「社區」,主要是其指涉對象不全然是地域上的社區,而是一群可能有共同地域或價值的人,是以「社群」名之;然而在正文當中,我們也以「社區/群」做為權衡譯法。其次則是「行為」(performance)一詞,我們回到社會參與藝術的發展脈絡,追溯其與行為藝術之間的關係,選擇以「行為」而非「表演」,作為第七章章名。第八章章名「文件」(documentation),則從「文件展」(documenta)演繹而來,除了以「文件」說明紀錄(在社會參與藝術中)的重要性與多樣性,也以文件展中,去中心化的、回顧性質的、教導啟發的特質,回應社會參與藝術。而第九章章名「跨教育學」(transpedagogy),則是我們感到最為棘手,卻不得不然的命名。埃爾格拉在本章當中,提出「跨教育學」一詞,說明社會參與藝術的展演性、知識性與轉化性,需透過融貫藝術與教育領域達成,但埃爾格拉語境中的trans,實在很難在中文裡找到精準的對位,是以「跨」名之,保留我們對此一教育學的想像空間。
吳岱融
關渡,2018 年1 月
譯序
參與的現場,微光
在抵達「社會參與藝術」這個命名之前,臺灣經歷過「戶外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公共藝術(民眾參與)」、「藝術介入」、「社區/社群藝術」等各種具「參與」性質的藝術實踐;戶外裝置藝術湧現於政治解嚴後,挑戰空間運用的方式、尺度,及藝術家對抗政治權威的批判;倡議民眾參與的公共藝術、社區藝術和藝術介入,則與民主價值和公民意識發展,息息相關。這些藝術的在地實踐各有其脈絡,但並不見得全部屬於本書範圍,埃爾格拉《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提供了描繪社會參與藝術的關鍵在於「社會實踐」。
「社會實踐一詞模糊了社會參與藝術所屬的『藝術』領域」。──埃爾格拉
藝術家的角色在社會參與藝術計畫中被削弱,帶來藝術家自身角色認定的危機,「是不是應該放棄藝術而成為專業的社區組織者、行動主義者、政治份子、民族誌工作者或社會學,才更能有所貢獻。」但也為其他領域提供了跨入藝術領域的路徑,「藝術工作者」成為描繪社會參與藝術推動者較貼切的稱謂,但這並不意味藝術家的稱謂或角色須被取代,只是多重角色的肯認,創造出更加細緻入微(而且誠實)、攜手合作的創作者和觀眾此消彼長的關係。也就如羅蘭‧ 巴特所說:創作者是多樣性的,而且不斷地受惠於他人。
社會參與藝術既以啟動創作者以外其他人的涉入參與為定義,辯論藝術家種菜究竟是不是藝術,其實就不是本書意圖為藝術家提出辯護或為觀眾進行藝術教育的首要目的。我在寶藏巖推動國際藝術村籌備工作時,以公共藝術作為一種啟動文化治理的方法,曾經邀請藝術家周靈芝與回住的社區居民一同整地種菜,藝術家放掉「既有」、「擅長」的藝術技能與知識,向社區居民學習種菜的方法,向生態工作者討教堆肥製作的技術,「生態農園」創作計畫過程的描述曾經被我以文字「紀錄」,翻譯埃爾格拉「定義」、「合作」、「文件」、「去技能化」等篇章時,記憶如跑馬燈般回想起諸種執行的情景,試想,如果當時有埃爾格拉這本書,作為實踐現場參照對話的對象,或許扭轉晦暗碰壁的作法會早些浮現!《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是一本以實踐者為對象的基礎入門書,書中所列一到十章並不意味著「操作流程」、或順序,每個章節都可各自獨立存在,回應實踐者現場的躊躇,所以建議讀者可以依照自身面對的情境,困擾你/妳的問題,以任何一章為起始,挑選閱讀。
對觀眾的思考與探討,幾乎是企業、行銷、管理、治理等全領域的議題,談社會參與藝術的「參與者」,埃爾格拉以「多層次的參與結構」拉出一個極富啟發性、寬闊的討論基礎,而「先創造,而後再考慮觀眾」,不只是藝術家這類創作者的想法,這樣的做法也存在於許多創新導向的工作者中,關心觀眾研究、社群建構的讀者可以仔細閱讀「社群」一章,將驚艷於作者的辯證分析:「觀眾……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他/她們在我們的作品中辨識出自己……」但自我辨識的發展非靜止、停滯,只提供觀眾固定的服務,未與建造它們的社群持續演化,反倒會帶來社群的蛀蝕或解散。社會參與藝術計畫雖在理論上是對廣大公眾開放,但實際上所服務的仍是非常特定的觀眾群。埃爾格拉務實的指認所謂追求肯認的核心迴圈為:(一)直接相關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二)藝術圈、(三)整體社會,例如政府組織、媒體等其他可能含納吸收此一計畫理念或面向的組織系統。
我從藝術行政現場轉入教育現場,觀察到改變對世界的理解與改變世界結構有著相近的效用,埃爾格拉在「跨教育學」一章對基進教育的提示,讓我相信,這本工具書提供的「微光」,即便現場不同因而對應的策略自有殊異,然而人們可以通過自我解放來改變權力關係,從而實現改變整體社會的目的,也就是個體應改變慣常思維和行為方式,在積極富有創造性和想像性的實踐中創造自己的「處境」。
蘇瑤華
新莊,2018 年1 月
新莊,2018 年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