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裕醫師【廢人心理學三部曲】:
◆第一部 廢人與荒涼 / 生命荒涼所在,還有什麼? (2020年3月1日出版)
◆第二部 廢人與曖昧 / 不是想死,只是不知道怎麼活下去(2020年9月1日出版)
◆第三部 廢人與迷惘 /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2021年3月1日出版)
【廢人心理學第三部】廢人與迷惘 /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
「你說,都是記憶出現在你前面,你只是追著記憶跑。
你突然靈光一閃說,你的記憶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它們都是被派出來應付你的好奇,難怪你老是覺得不對勁。
有時,你不由自主地這麼想:難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嗎?
不然何以會出現那些記憶,來阻擋自己的迷惘呢?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記憶,
你就會完全迷失了,像是個徹底失落的人。
難道一直緊抓著這些記憶,
就只是為了不讓自己被這種失落感淹沒嗎?」
從實況來看,有些地方,你細緻刻劃了自己沒有察覺的苦,
那些苦後來都四散,在無家可歸的經驗裡遊走。
你建造了美麗的城牆來安置那些遊魂暗鬼,
只因它們被拋棄了,也失去了起源於何處的記憶,
變成沒有名字的苦痛。
不再和原始起因相連結的苦和痛並不會暗暗消失,
反而四處尋找依附的對象,
於是生活到處都是苦、心裡充滿各種痛,
你淡漠那些苦痛,只覺得無以名之的迷惘......
今夜,又是哪個晚上呢?
◎蔡醫師這本書的重點之一在於闡明理論與實作永遠有一道鴻溝,百年來臨床實務技術的修正,解決了某些問題,但也看到了其他問題......
越來越多個案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邊緣型人格、是躁鬱症,自己會解離、有多重人格、有伊底帕斯情結,很容易產生移情等等,這或許意味個案對於自己的症狀有一定的認知,當然,也或許有更多的錯誤認知。透過網路媒介,有情緒困擾的個案自助管道越來越多樣化,這個趨勢對於心理治療工作者來說不見得是好事,假設診斷與症狀是一種防衛,一種阻抗,蔡醫師形容個案「只是說著一句死掉的語言」,然後安枕無憂、好整以暇地躲在一處庇護所或是蔡醫師形容的「古堡」中,也就是說,個案進入診療室前已經重度(再度)武裝(防衛)自己了。現今心理治療工作者面臨的現實挑戰是個案屬性從過去的neurotic與non-neurotic世代進入borderline與non-borderline世代,亦即個案的問題涉及更早期更深層的失落與創傷,人格碎裂的程度更嚴重,更缺乏彈性,治療難度更高。(李俊毅醫師)
◎在蔡醫師的大作【廢人心理學三部曲】第三部「廢人與迷惘」中,延續著廢人與憂鬱的核心主軸,這次所談的是千古不散的迷惘。好似說書人翻開了書,隨著聲音一落下,手杖一揮點,眼前就突然現出了婆娑幻化的潛意識,載浮載沉的看起來不太真實,但裡面會不會有著別有洞天的境地,或鬱鬱蔥蔥的桃花林呢?就這麼勾引人從幻境般的入口走探進來,讓人邊看邊猜想著「薩所羅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藏在古老村落裡到底有著什麼?為何會是心理治療師與病人交會的戰場?既可繁複遞變如萬花筒世界,又是每個人所建造出來的內在景象或用以保護自身的城牆?甚至「薩所羅蘭」它就自己活了起來,走到你的面前?!在【小小說】段落裡,從治療師第一人稱細膩的心思,看似具像化了潛意識幻想與心理治療中的潛意識交流(或交手),與艱緩的行走步調(或稱作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技藝吧!)但其實卻更突顯出「迷惘」的本質是多麼地空洞,令人困惑與捉摸不定啊!(李芝綺心理師)
◎蔡醫師以拼接方式將不同形式卻觸及迷惘的生命故事和探究串接著,一篇小說、一份邀請、一場聚會討論、一個回應、一齣舞台劇,有如運用蒙太奇的處理方式,讓不同距離和角度的拍攝鏡頭重組,構成獨特的影片邏輯。這些被提取、看似無秩序的章節,以阿莎布魯的獨角戲在更高一層的觀點上進行串聯和編輯工作,讓現實的洶湧波瀾景象與無法言說之境,被聚合在一個層次中,產生強烈的對比與想像空間。每個迷惘的結尾,悲傷的阿莎布魯現身都讓我感到好奇,這個常被用來描述亂七八糟,行為不合理的用語,在賦予具生命的角色之後,既在暗喻這樣的生命本身便充滿了迷惑和茫然,也讓古老的故事有了新意,緊扣著「廢人與迷惘」《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的核心佈展。(劉玉文心理師)
作者簡介:
蔡榮裕
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成員
精神科專科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無境⽂化【思想起】潛意識叢書策劃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委員會副主委
《薩所羅蘭》分析顧問公司顧問
章節試閱
【內文試閱一】
【小小說】
你來了,
來到古老村落薩所羅蘭
1.
你來了這裡,是我的薩所羅蘭,也是你的迷惘,是你帶我來的地方。
2.
你來了,你是來了。你竟說,你的精神史跑來找你,讓你不知道怎麼應付它們?我聽了也嚇一跳,倒不是不舒服的嚇一跳,而是有一股奇怪的暖流感受。我覺得你這麼說實在太誘人了,讓我被你這句話吸引住,「我的精神史跑來找我」實在是太生動的說法!
雖然這個生動的說法到後來,仍只是失落的空洞裡張貼的一句美麗的話語。不過,可以想到這些,是以後以後的事了。後來的知道,無法彌補先前的興奮所帶來的失落。
你說,都是記憶跑在你前面,你只是追著記憶跑。你突然靈光一現,覺得你的記憶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它們都是被派出來應付你自己的好奇,難怪你老是覺得不可思議。你是不由自主地這麼想:難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嗎?不然何以它派出那些記憶,來阻擋自己的迷惘呢?結局卻是讓你更迷惘。
但是,如果你現在沒有這些記憶,你就會完全迷失了,就像個徹底失落的人。難道一直緊抓著這些記憶,就只是為了不讓自己被這種失落感淹沒嗎?你是不相信的,你覺得自己看透了一些人生,怎麼可能會甘願被這樣的記憶所欺瞞呢?也許說欺瞞是有些過頭,不過,這也只是你這麼想時的必然反應吧?
3.
你來了,你是來了。你說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你我的交會,在山中古老村落,薩所羅蘭。
其實這個描述是我的想法,你說你以為自己還在沙漠,頂著陽光,尋找綠洲。你堅持你獲得太多的陽光了,幾乎把你心中很多想法和記憶都曬死,害得你要不停地藉者片片斷斷的想法,想像以前到底是什麼?
這是有些可怕的感覺呢!你說,有電影導演曾說,內心的變化才是豐富的紀錄片。你來這裡就是為了替自己拍攝這部紀錄片。
我一時之間還不是很了解,你這麼說是什麼意
思?不過把紀錄片和內心變化連在一起,的確是有趣的想法。你把紀錄片也連結到你來這裡,你的說法影響我,你想像成來到了古老村落薩所羅蘭。是啊,你就這樣帶著我,來到了薩所羅蘭。
你我的交會是起源於,你深深地相信,自己的困局是來自於母親。我知道這種結論,因為很多人都這麼說過。但我還是得從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想起,這是在薩所羅蘭的生活方式,一切嘗試都從不了解開始。我們可以了解的,都已經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和困局,而在這裡,需要從不了解開始。
這的確是個難題,你我怎麼可能不了解什麼呢,尤其是你和自己相處這麼久了,怎麼可能會不了解自己呢?你來找我,就是覺得自己知道自己有些迷惘,想要改變,只是這種想改變的前提,對你來說,常是居於你已經了解自己了,你要的只是「改變」。在這種情況,你設定給我的難題是,你只要我告訴你如何做可以改變,而不是要如何知道和認識你。
還有不認識的自己嗎?這很容易被說得很玄,雖然在我的工作取向和經驗裡,這是一點也不玄,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改變,也許不是被告知要怎麼做,而是找機會再了解自己——是否還有不認識的自己?如何再認識它們,聽聽它們想要表達什麼?不過,這可是會變成你我之間的戰爭。很奇怪的一場戰爭,唯有你來了,在薩所羅蘭才會出現的戰爭。雖然,你我並不會真的動手,我們只是依著感受來說說心中的想法。我說的是「自由聯想」,卻是困難重重的「自由」。
誰知道這樣的相遇,會有什麼結果呢?可能在還沒有結果前,就先遭遇了錯綜複雜的情緒糾葛,好像有什麼不知名的東西糾纏住的感覺。你說真的好奇怪,怎麼來了薩所羅蘭才有這些呢?我說是的,這是薩所羅蘭特有的心中風景,你我一時之間,很難看清
楚的風景,真的是奇怪的景緻啊!
4.
你來了,我還在想著不久前發生的一些事。我要盡快回到你帶來的心中風景。是你在重遊,你希望我也可以在場的重遊,這是薩所羅蘭獨特的景緻。
你我一起重遊你記憶中的從前。你說爸爸離家的時候,你毫無記憶,你覺得父親一定是受不了母親才會離開的。也許父親離開前,有跟你說些什麼話,只是當時你年紀太小,記不得了。聽母親說,父親在幾年前就死了。你說,你不知道母親是如何知道的?
至今你還不知道如何說這件事,只好把母親的說法原封不動地包裝起來,放心中。你知道你心中所困惑的,「父親離開前,說了什麼話?」這件事已經不可能有答案了。你說你不敢問母親這件事,怕母親因為恨意,故意說些話來挑撥你和父親的關係。
雖然你根本不知道,你跟父親是什麼關係?但是你覺得很親密就是了。我是不了解也無法馬上區別你說的親密,和一般人所說的親密,是否是相同的東西?或者有你個人獨特的定義?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定義,而且根深蒂固。
父親是男性,你是女性,你先前就聲明自己喜歡女人。也許這是表明你對母親有著恨意的意味?很強烈的意思吧?這也是佛洛伊德宣稱性學的基礎,我不是憑空想像,而是有你在我眼前呈現的你自己,讓我更知道佛洛伊德的想法是有它的臨床意涵。
至於現今如何看待精神分析的性學,這是另一個學問了。但是光想著你說的,父親早就離開你,卻是你最親密的人,而母親曾一度離開你,後來接你一起住,卻變成你恨意和歸罪的主要對象;好像人性裡所有的恨意,都有機會走上迷惘,在你和母親的關係平台上露露臉,說說各種不同的恨意之間是如何交纏。
這一切都會轉移到我的身上嗎?我跟你母親同性別,也會是你恨意的對象嗎?
5.
你來了,我的疑問可能來得太早了,我太受以前
的經驗和專業職人理論的影響,卻很難察覺你流露的恨意。你對我有恨意嗎?我要如何對待這個存在我心中的假設呢?或許它早就不再只是假設——在我的工作取向裡,百年來,這已成為我的常識了。
我的常識,畢竟仍是局外人的常識,雖然也有移情的假設:你會搬來早年的經驗。但這仍是謎團,是需要一直在其中摸索的情境,並不是如我們期待的那般,以為「移情」這個語詞,就足以說明一切——如果這麼想,我覺得是對人的心智的蔑視吧?這樣只會讓心智等待時機反撲,讓我們覺得怎麼如此莫名其妙?
是的,通常是以「莫名其妙」來開展出人性迷惘的奧秘吧?我只能說,因為理論和經驗,使我等著你對我的恨意。因為你對母親恨意的唯一出路,是在我這裡。坦白說,要你先接受自己這個狀態,就是一種莫名其妙。
是誰把我推到這種處境呢?你怪母親害你一輩子,而我和你在薩所羅蘭,我需要責怪什麼嗎?我不是說我一定不會怪罪什麼,而是「怪罪什麼」本身就是值得再細思的事件,不是只依著那怪罪的內容,來決定如何回應。
你在薩所羅蘭,你和我需要不同的想法,但是這種不同不會自然出現,而是要緩慢的交談。這種場景可以讓薩所羅蘭的描繪,成為繁雜如萬花筒的世界,也許不是那麼美,並且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說得出,「哇,你的辛苦讓你成為一道美麗的傷口」。如果說太快,會讓這句話的美意成為某種諷刺。我需要諷刺你嗎?我真的不知道呢!
6.
你來了,是薩所羅蘭走到你面前。雖然我也常說,是你來到了薩所羅蘭,那裡跟溫尼科特說的「過渡空間」有什麼關係嗎?我不是很清楚,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是在往清楚的路上走,因為我還卡在先前的諷刺說法裡。
我腦海裡的直覺想法:「你那些過往創傷能活到現在,呈現萬花茼般的美麗。」這句話好像是在支持你,但你需要這種支持嗎?理論上,我深知支持的必要,尤其你一再地說著,父親是如此遙遠。儘管父親的遠或近,在你的心中是不定的,也許是這種不定,帶來的失落,它的影響比完全消失還要更大。
不過,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此刻在我心頭上綻開的是你美麗的傷口。我無法在這時候說出我的想法。如果我的專業是直接的溝通,何以我覺得不能在這個時候說這些話呢?或者,我有必要思考的不是「說不說」,而是要把「如何說」想得更仔細。把想說的想得更細緻是必要的事,這是來薩所羅蘭需要的質地。
你大概只感受到我的緩慢,但是我無法完全猜到你是如何看待我的緩慢。你說你的母親在父親離開她後,是如何地對你感到不耐煩。雖然你早就覺得,根本就是母親的問題!你很快補充說,你已經記不起來,多小的時候,就這麼覺得了。你說,你不知道「母親」是什麼?我想著,是父親的離家或者是母親的在家卻不如你預期,所帶來的困擾,分別地影響著你?到底是母親的因素影響你,或者是父親的不在更影響你?這些影響很難完全了解,不是如一般想像的迷惘。如果我說「都會影響」,那等於什麼都沒有說。
如何了解你當年的經驗,也是一大難題!並不 是你說出來的,就是當年的情況,你現在所說出來的,是長年一再磨練後的結果,要從這個結果去回推當年,的確是項重大的挑戰。不過既然來了薩所羅蘭,就需要一步一步地讓這些猜測有發揮的餘地。
你對母親有著多年恨意所搭建起來的城牆,雖然在城牆上畫著一幅接著一幅精美的圖畫,以此表明你是想用良善的方式躲開生命的苦痛,讓自己不必在每個時刻都經驗著生命的苦。我的專業行話是說,你運用著各種方式來避免自己承受那些苦,而那些潛在的運作方式,叫做「經濟原則」。以一般話來說,可能是接近以「便宜行事」的經濟學來達成讓受苦,失落的苦,被隔離起來。只因是便宜行事,那些城牆呈現出來的是美麗的模樣。這是我在聽你述說時,心中重複浮現的景象。
7.
你來了,薩所羅蘭在你的心中,是你建構出來的樂園。後來,它就自己活了起來,在那裡,所有的美麗和創造背後,都是苦和痛。
你說父親消失不見前,是相當愛你的,你後來停了一會兒,沈思地說,你不知道那是不是愛?你很快再修正你的疑問,說「那是愛」,沒有錯!看來你是不希望你對那段感情有疑惑,而且你要在你的薩所羅蘭裡確立,那是毫無疑問的愛。雖然你也說父親不是一個有出息的人,但你仍拒絕說出,沒出息是指什麼?雖然你在其它時候早就說過,父親整天游手好閒。我不知這是不是你說的,沒出息?
這讓你辛苦建造的薩所羅蘭的美好,常常有風雨的緣故吧?只要有生活和工作上的不順利,就會動搖你的薩所羅蘭,你就需要加強修繕它,增強它的美好,也就是讓離家的父親更加美好——這使你動員了大部分的能量和注意力,回想著當年父親的一舉一動,甚至懷念著你還不會說話時,躺著他懷抱裡的情景。
如果我說,那是你後來建構起來的場景,既不是回憶也不是記憶,那麼我就變成了你的薩所羅蘭的破壞者,無情的闖入後,對你指指點點。這到底是不是我專業的工作呢?如果我只是被我的專業告知,有些事要忍受挫折,那麼這是忍受挫折嗎?或者只是一再的錯失良機呢?我錯失了什麼呢?走進你的薩所羅蘭,替你命名每個事件的名稱、每道防衛的名字,你需要知道這些嗎?雖然我也很難完全相信,一定不能這麼做。你早有自己的命名,而我的命名只是一種交換意見;對相同的現象和場景,有不同的命名,也許就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這些景象的豐饒。
我走進薩所羅蘭,在你的城牆貼上我的說帖,這是我的工作嗎?雖然我的工作就是說話,嘗試說出內心裡最難被說出的那些話。當我一心一意想著如何張貼我的說帖時,你也一心一意簡單地說著迷惘:母親不當的待你,讓你一生就這樣毀在她手中。
8.
你來了,我說「簡單」,並不是你把故事說得很簡單,相反地,你是說的很複雜,你也舉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例來佐證自己的說詞。我覺得「簡單」,是你說的「你的一生就毀在你母親的手裡」。
不能說這是錯的,但是否全對呢?如果是全對,接下來能做什麼?何況走到這個地步,你親手建構的薩所羅蘭,也影響著現在和未來的重要風情呢!不過,如果把這些歸結到某個單一因子,就是我說的「簡單」,卻是便宜行事的簡單。就像把很多事歸結於男性沙文主義一樣,變成了不用思考的答案,是對,也不全對,偏偏在對和不全對之間,可能容納一個風情萬種的村落。
如何讓簡單的,卻不是便宜行事的便宜,而有細緻的品質?當你一再歸罪母親時,我心中也是重複地想著:在你如此便宜的歸因裡,我只能等待。雖然我也重複問著自己,在你的薩所羅蘭,我能說些什麼,讓事情不再只是如此便宜行事?
我是奉行簡單原則的人,但是,簡單看來卻是不簡單,還需要更多的細緻化。值得想像的是,同樣以簡單原則,卻有便宜行事的簡單和謹慎細緻的簡單之別。我相信你在建構薩所羅蘭時,不必然知覺到這種分野。
從實況來看,有些地方你確實很細緻地刻劃了自己沒察覺的苦。那些苦,後來都四散,像個無家可歸的迷惘經驗。你建造了美麗的城牆來安置那些苦和痛,它們卻好像被拒絕停駐,而失落地四處流浪。
9.
你來了,你的薩所羅蘭,原本是要安置或管理那些讓你受苦的痛,但雖有傷口裡美麗的城垣,卻無法將所有的苦和痛都關在裡頭,它們隨處流浪。我使用「流浪」,不是要呈現它們的浪漫,而是一種不著邊際、難以觸及的苦和痛。因為它們是被拋棄了,也失去了原來的起源,變成沒有名字的苦和痛。那些不再和原始起因相聯結的苦痛,並不會因此消失,反而四處尋找依附的對象,因此生活變得到處都受苦,時時充滿痛,但是你不再說那裡有苦有痛,而是覺得有某種無以名之的迷惘。
我還需要更多的觀察和推想,來回答你給自己的問題,雖然你是對我說的話。你說,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爸爸當年會離開?這句話只是輕輕滑過嘴邊,像閃電後的悶雷聲。我覺得雨天要來了,但你馬上大笑說,唉,哪裡有人會一直想著這種無聊的問題!這個問題又無法解決!反正我早就知道,爸爸不是因我而離開家,都是母親的無能,才會使父親離開。
在薩所羅蘭的午後,你的悶雷聲依然震撼著我。這樣的說法並不稀有,但這個時候,你以這種方式說話時,像是在空洞裡拍了一記掌聲,不斷地迴響,雖然是迴響,我卻感受到空洞。到底這些失落帶來的苦和痛,有多重要呢?這些苦和痛在空洞般的感受裡,不斷地迴響著......
10.
你來了,我想著山谷裡的聲音迴響,和你的空洞裡悶雷般的迴響,兩者的差異是什麼?也許這個差異的不同描繪,有助於我了解你可能是怎麼回事。
在山谷和在空洞裡的感受是很主觀的,對任何人來說,這些主觀的感受常是暗地裡,在實質上左右著自己的心情,以及和他人的關係。這個比喻只是個開始,這是我了解你的方式之一。也許不能說是「了解」,而是嘗試「推論」你內在世界的可能狀況,這是比較精準的說法。
我大膽地想著,是否你提過的種種不安和焦慮,以及你喜歡的對象所遭遇的性課題,可能都是在這個空洞裡的迷惘,所產生的各種迴音?它們都需要說出自己的想法,但是背景是,你從小以來的失落和創傷所呈現的那種空洞感,你拒絕再讓自己有這種感受,於是生活充斥著各種聲音的喧嘩,變成好像生活不再空洞,如前所述,你的薩所羅蘭就這樣建造出各種迷人也迷惑自己的城牆。只是在有些時候,自己會突然蹦出奇怪的想法,讓自己迷失在某個地方。
這種迷失的感覺,並不是讓你可以把視野打開的地方,而是讓你喘不了氣的所在,這是我的推論,你身在這種處境裡,是在空洞裡有迴聲,不是山谷間的那種迴響。也許有人在山谷裡反而會很恐慌,如果是這樣子,那麼我這個比喻對你就不是有效的比喻了。
11.
你來了,當薩所羅蘭走到你面前時,已經在過去史的表面,再鋪上厚厚一層新來的滄桑。新來的滄桑,這種說法是有些奇怪,「滄桑」都是老掉牙的故事,怎麼會是新的?它是從什麼地方來呢?你說著往事,是想要走回以前,但是薩所羅蘭卻自己跑來找你,它有很長的時間都不說話。它帶著委屈吧?至少你看得出來的地方,都是這樣子。
委屈,是常常出現在你說話的背景裡,雖然你幾乎不曾直接提到這兩個字。甚至你常常覺得你不是委屈也不是恨意,而是你被不公平的對待,包括被不公平地生下來。母親不曾問你意見,就生你下來,這表示你想要再回到母親的子宮嗎?顯然這是一個更可怕的問題,因為後來你發現母親根本不在意你,你說你
甚至沒有後退的路了。
你是指,連回到子宮的想法,都是不被你接受的了。你只有薩所羅蘭可以回去,全然屬於你自己的迷惘,你相信那不會被母親搶走,你可以慢慢等待父親,你相信父親會來找你,他會知道,你打造的薩所羅蘭就是為了等他。
你曾說,你真的不知道父親到底怎麼啦?你想要從他的嘴巴再度聽到,他當年離開前站在門口對你說的話。你竟然記不起來當時他對你說了什麼話,但是你相信,他一定對你說了什麼話,他不會就這樣離開家,你說,他不會走得無聲無息。你說無聲無息時,我卻聽到你發出很大的聲音。
我先前還在想著空洞或山谷間的迴響;是否你後來所造出來的各種問題,都是一再地出現,重複迴響般影響著你的生活?或者說,在你的薩所羅蘭裡,你過的日子就是迴響的日子,你的日子一直在那種迴響裡打轉?迴響的聲音變成你真正的日子,你有時候想著,自己真正的聲音是什麼?這是你一直在尋找的,自己是什麼?
背景是,你從小以來的失落和創傷所呈現的那種空洞感,你拒絕再讓自己有這種感受,於是生活充斥著各種聲音的喧嘩,變成好像生活不再空洞,如前所述,你的薩所羅蘭就這樣建造出各種迷人也迷惑自己的城牆。只是在有些時候,自己會突然蹦出奇怪的想法,讓自己迷失在某個地方。
這種迷失的感覺,並不是讓你可以把視野打開的地方,而是讓你喘不了氣的所在,這是我的推論,你身在這種處境裡,是在空洞裡有迴聲,不是山谷間的那種迴響。也許有人在山谷裡反而會很恐慌,如果是這樣子,那麼我這個比喻對你就不是有效的比喻了。
12.
你來了,連薩所羅蘭都忍不住變老了,帶著委屈,一步一步走向衰老。對你,這幾乎是一場災難,明知會發生,卻不想要它真的發生,這反而帶來災難!也許「災難」只是一個走過頭的形容詞,在風中,拎著過時卻不想回頭看自己一眼的一句老話:其實你早就等不到,父親親口說出他當年的想法。
父親在你來這裡前,就已經不在人世了。你很小心地用詞,你頓了一下,不知道要如何形容父親的不在人世。為了避免直接用你說的話語,呈現在這裡的是我的語詞:「他不在人世」。雖然這樣子會損減別人更貼近想像你說的話,但是我寧願拉開一些距離,讓想像力再豐富些。
這只是我的假設,我是覺得你的用詞在你說出來的氣氛裡,有著你仍是不相信的意味。父親是不在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你的薩所羅蘭,父親是在那裡,因為迷惘從來不曾消失過。
你剛來這裡時,我不曾察覺,你的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你流露的是,他一直都在,不曾真的消失。你此刻說,他的肉身已經不在人世了,流露的氣氛仍是,他存在,讓你想要知道當年他離家時,曾對你說了什麼話。你等著他回來找你?或者我帶你走到現在,其實你仍沒有放棄這個期待?這是個不合現實的期待?
但是,從你的反應卻讓我想著,現實是什麼?我提醒你這個現實,就是治療嗎?或者我不要陷在二分法的處境裡,這就變成要不要點出你父親的不在?那我如何告訴你,你想要知道的答案?當我想著,如果我只說出簡單的回答,可能會失去心理學深度的問題時,你說你的朋友和親戚都告訴過你,要面對現實,他們說你父親早就不在人世了,你怎麼這麼不切實際呢?你說你痛恨這種答案!你當然知道父親早就不在了,甚至他離開不久後,他在你心中早就死掉了!真正的死掉了!你根本不在意他在不在人世!
我驚訝你的說法!讓我驚訝的說法總是在提醒我,我的了解是有距離的,或者表示我根本是不了解。
13.
你來了,嗯,看來我是要再回到不了解的立場。先前的氣氛,我在心中的想法是站在,你的父親在你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你和母親,但他一直還活著,你是在等他回來,你想問他當年的一些事。跟你工作到現在,對於薩所羅蘭的景象,透過我的驚訝,我想我是需要再回到不了解你的立場。這讓我有些迷惘和困窘,好像這麼多個月的工作,是白白浪費了時間。但是在薩所羅蘭,有所謂「浪費時間」這種事嗎?
14.
你來了,我想著這是另一種了解吧?你的薩所羅蘭是這樣子展現你和父親的關係,內心深處你堅持他是不死的。如果他死了,是離開人世,不是離開你,你早就為他佈置的世界:薩所羅蘭,在這裡你讓他一直存在著,雖然是以疑問的方式——父親當時是否說了什麼重要的話?和你有關。
甚至你隱隱相信他說的話是類似,有一天,他會回來接你。何以你仍以疑問的方式呈現,而不是很確定他就是這麼說的呢?我也很好奇,何以你要一直處在這種懸浮的狀態裡,讓你的薩所羅蘭仍殘留一些瑕疵?父親的不在,就是一個很大的瑕疵,卻經由你的疑問,變成一個迷惘,這樣就不再是那麼大的瑕疵,是這樣子嗎?其實我並不清楚,我是充滿了好奇,我只能對自己的好奇,保持著某種距離。你仍有自己的長路要走,此刻,我擔心我的好奇,只是薩所羅蘭裡一種很會生長的奇怪雜草。我無意說,我所有的好奇都是一種雜草。
有人說佛洛伊德對精神官能症宣戰,比昂則是對記憶和欲望宣戰。說宣戰,也許有些誇張,但不可否認,從精神分析取向來說,這些帶來人和人之間想要達成理解的困局,的確像風雨中的戰爭。至少是一場接著另一場的風暴,掀起了人性裡無限的糾葛。
如果宣稱是戰爭,這卻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你的困局,好像是為了讓一切都失敗,來成功地打敗自己。這裡頭複雜的勝利結果,是帶來失敗,而失敗捲起風雲,再度集結潰散的力量,隨時準備再一次的成功。
世俗成功和失敗的說法,在這裡已經被混在一起,我不是故意說這些矛盾的話,來混淆你的了解。你是分得很清楚,但你的「清楚」,我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失敗是成功」的結果。你以疑問,作為中間的緩解,讓成功和失敗之間築起一道高牆。
這種結果,讓你失敗前的成功,難以被看見,它是多麼精緻地,讓你一路走著失敗的道路,而你的疑問,「父親是否說了那句要回來接你的話」,是你心裡成功的創意,卻被你以疑問,削減它的效力。我這麼說,並不是說你的父親真的曾經這麼做,我說的是,薩所羅蘭有一片你從小就建構出來的領域,你把它帶來我這裡,讓我在薩所羅蘭裡經歷著難言卻又不斷說出口的過程,交換著你的從前、現在和未來。
雖然在薩所羅蘭,這些從前、現在和未來都只以相同的時間方式交流著,也可以說,是不需要時間的。
15.
你來了,在薩所羅蘭,我還需要做這些文字的佈展,讓路過的你,能夠每天消化一些迷惘,這些被當作是常識的一部分,是精神分析對文明的重大貢獻。我想要展覽這些想法,等著你來,雖然這些佈展的文字,離要了解人性,和解決你的受苦,仍還有很長的路,至少有這些想法後,可以不再那麼孤寂吧。
【內文試閱二】
伊底帕斯情結與餓鬼道
精神分析與文學或宗教對話的後設想像
當佛洛伊德宣稱要走進潛意識的領域時,他的確需要找尋其它領域裡,有趣且切中他想像的象徵,來替潛意識裡的某些現象命名,以便後續者可以追隨並跟上他的步伐,讓他引介自己所發現的東西時,不會因為辭窮而陷在說不出話,或說些別人無法完全了解的內容,使自己陷在孤單的困境。
他在父親過世後,失落和哀傷,於是開始自我分析,透過世紀之作《夢的解析》,成功地打響了精神分析的名號。開展出第一大步後,即使是說著自己的夢話或實質和夢有關的記事,他都需要再從其它領域裡,引進某些象徵和故事來服務他的心思。他的心思想要讓世人說出大家還不知道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往事,而且是被打扮過的記憶;他需要尋找別人說過的故事,張貼在自己發現的故事上,但那只是文字或語言的象徵,不是原本的事物本身,這讓不斷地說話,成為精神分析取向的宿命。不過,不說話的時候,我們的心智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我要一直說,一直說,我要說到什麼時候,才說得完,才說得到自己想說的......?」
其實他這麼說時,我已經聽他說話一段時間了,他有悲慘的人生,父母離婚後,他在不同的親戚家裡輪流住,從一兩天到兩三個月。就這樣,他度過了三歲到六歲的時光,他說他完全沒有任何印象,後來母親才將他接去一起和姐姐同住(故事情節有修改)。他記得日子很悲慘,更悲慘的是,他只能重複使用「悲慘」兩字來形容那段日子。但是這兩個字卻使他更無助,他需要替那段日子想起什麼事,才會有助於他的探索嗎?
這是什麼樣的探索呢?他甚至說,他真的不知要說什麼。他覺得我不說話時,好像是在逼著他要一直說。我說,說話是很重要,現在很重要,以後也會很重要,但並不表示不能沈默想些事情,我的工作不是逼他說話,而是等他說話。
不過個案所說的,不知什麼時候才說得完,這個疑問不是容易回答的習題。在這時候更像是,他不知要說什麼或沒什麼要說。這個沒什麼,卻像是「陽具欽羡」的場景,等待著不曾擁有,卻期待是獨一無二的那根陽具。這跟等待「空無」是接近的,因為我們會習慣想像任何問題,都可能有著其它的內在動機或者內在困局,因此我們會再等待,再多聽一些訊息。
我們在等待的時候,除了我們的想像外,我們仍是期待著個案可以有話說,雖然我們會觀察和想像身體症狀和記憶課題。
他甚至表示,目前說的,不是自己想說的,但也不是這樣,只是覺得好像不是自己在說。他再更正,好像是自己的嘴巴在說,但不知是誰的心思?他再加問,還要一直說嗎?我回應,看來是說不完的,甚至會覺得一直說的不到位,不過在這裡是需要一直說。我突然想起,他在某次的會談時,坐下來的第一句是說,我的治療師告訴我,我的問題是伊底帕斯情結。當時,我應該是沒有理會他,因為根據經驗,伊底帕斯情結如果像他這樣子說出來,是意義不大的,因為他說這句話時,好像只是說著一句死掉的語言,是一片落葉掉在水面上,就要漂走了,那次之後他也未再多衍生他的體會。
回想當初,我大概是覺得不太愉快吧?想著他已經知道精神分析最核心的概念「伊底帕斯情結」,那何必再來這裡呢?不過,我的輕忽更像是,原本認為他和我工作許久後,會有不同的體會,但是他一見面就這麼說,我對著這句死掉般的結論,覺得他只是說著他還無法消化的話。畢竟,伊底帕斯情結是蘊涵著很有重量的悲劇,卻被他這麼輕鬆地說了出來,但他並沒有要從這個術語裡,得到什麼樣的簡單感受,好像他只是說了一句風涼話。也許這是指「伊底帕斯情結」已經是風涼話的句號,再怎麼說也只是這樣子,沒什麼新鮮的可以說了,甚至已經是日常化的語言;他困在一句話裡,讓這個術語,活生生的死在我們眼前。而他依然努力要活下去的模樣。
他曾這麼說,好累,嗯,他覺得說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不知說這些做什麼,說了也等於沒說。
但是有說還是可能會不同啊!他告訴我,已經說了那麼多了,他有什麼不同嗎?他覺得還是都一樣。
我想著他說的「都一樣」是什麼意思?是什麼跟什麼一樣呢?或者他是想要重複說著一樣的自己,這樣子他才能維持著自己的模樣;一樣的模樣,可能意味著他需要藉著相同的故事來綁住自己,讓自己一樣。這使得他說自己說了很多話了,但仍是一樣,不必然是在抱怨沒有改變,而是在確定自己仍是自己,並沒有被自己的恐怖故事給解體了。
值得我們再來想一想,當佛洛伊德引進希臘神話的故事,這是和文學有關的劇本,文學原本就有它能維持或擴展的功能,但是文學需要承擔這麼大的社會或個人的痊癒功能嗎?顯然佛洛伊德以降的精神分析,已存在一百年以上,以它特有的形式關係和說話方式,建構出人類文明裡特有的一個環節,讓我們對心理困局的想像和處理有了新的出路,這呈現在目前
的精神分析取向專業裡。
雖然還有其它聲音,例如以戲劇為主的治療模式,或者精神分析取向者也想要從已有的有限理論,嘗試回饋文學和戲劇,於是我們宣稱是「精神分析的運用」,不過,精神分析取向專業職人仍得站穩,回到特有的架構設置和談話的型式裡,慢慢審慎的伸展手腳,而不是過於急切,反而踢翻了遠比精神分析存在久遠的文字藝術,或接下來我將觸及的宗教課題。或許不能說是踢翻,而是不必要被當作是精神分析式的闖進,造成無法對話的處境;雖然精神分析取向者,一直是在面對個案的負面移情下,仍持續著意志,嘗試尋求對話的可能性。
不論如何,精神分析的發展,是要在心理學市場上和現有一般所說的,具有「療癒」感受的各式存在裡,走出自己的路;我們眼前的是,在文學和宗教持續存在下,還是有個案群願意走進來診療室找我們,想以心理學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困局、空洞感、失根感或迷惘。
在精神分析經驗的知識寶庫裡,對於「伊底帕斯情結」的概念,何以會出現在這位個案的說法裡?我只是萃取出不少個案的共同情況,來呈現「伊底帕斯情結」的概念,在成為知識日常化的了解後,實際上對某些人的幫助是很有限的。雖然我們可以繼續沿用精神分析前輩的觀察,認為這是大眾對於精神分析的阻抗,或者再次證明了,果然我們前輩說的沒錯,只知道精神分析的概念並不是有用的,
需要到診療室才能真的體會精神分析的奧義。
不過,我想的是,如何不違和這些實質經驗,但也有其它的想像空間?例如,是否我們對人性的理解仍有限,不要急著在有限經驗裡,做出恆久的結論。我個人相信精神分析的重要知識,是起源於診療室裡的經驗,要讓精神分析長長久久,是需要盡力維持著精神分析取向診療室裡的工作。如果只認同了前述「大眾阻抗精神分析」的說法裡,呈現無力感、無助感和無望感,那麼我們更需要再引進其它學門,利用它們在人類文明史裡的長久經驗,對於人和人性的描繪,作為思索和觀察的參考點。至於技術上,仍得在精神分析特有的診療室經驗裡,審慎地一步一步去想和去做。
我們繼續探問,何以「伊底帕斯情結」的概念,會在個案的心中死掉,徒留下這個語詞在某個地方?除了以古典概念的「阻抗」來說明外,其實從目前跟邊緣型或自戀型者一起工作的心得來看,另涉及的是生命早年的失落創傷後,有著如比昂(Bion)所說的碎片的存在,以及其中蔓延的「無可命名的畏懼」(nameless terror)。也就是,當年的經驗,除了佛洛伊德在《記憶、重複與修通》這篇有關技術的論文裡提到的,真正的早年記憶不在故事裡而是在於行動裡之外,結合佛洛伊德和比昂的概念來看,是在行動出現的,人和人之間的枝枝節節或片片斷斷裡。關於「人和人之間」,更精準的說法是,那些破碎的部分客體四處投射,而展現出來的行動裡,因為破碎而造成無法整合,各自為政,各自成長的破碎自己,帶來外顯行動上的阻抗現象。
所謂「部分客體」是指以人的某部分來代表人,例如乳房、陽具或其它的部分。在生命早年時,跟這些部分客體的互動,就是嬰孩的主要經驗,要經過一段成長,才得以讓這些破碎般的部分客體經驗,整合成「完整客體」。例如成人感覺到的一個人,如父親或母親等,這是伊底帕斯情結的經驗基礎,是有「完整客體」能力後的孩童經驗。
因此,在這些臨床經驗的基礎上,我們是不可能只想著,是否只要搬進來戲劇、文學和神話的技藝就可以,那是不足以幫得上忙,但這並非意味著,這些古老經驗是毫無作用,畢竟閱讀文學和欣賞戲劇的經驗,是人在有文字能力後的感受,這是有著高度智識化的經驗。但是前述的「部分客體」經驗,都是在語言發展能力還很薄弱的時候,也就是語言仍難以抵達碰觸的領域。
不過,戲劇和文學的存在久遠,它們的內涵和表現,對我們而言,是值得採用的描繪方式。這也是當初佛洛伊德引用這些古老經驗故事的緣由吧!至今這些採用和藉用仍是需要的,甚至是需要意識和積極的尋覓。目前也有A.Ferro等人發展的精神分析「舞台理論」(field theory),這裡的field從原本的「場域理論」,到現在看來是更貼近舞台理論。他的論文裡,引進電影和戲劇等藝術,不只是理論也有技術上的參與。這些對於精神分析多元發展的影響,後續仍值得再觀察。
幾次的會談後,個案說了句「我完了」,就大哭約有五分鐘,突然停下來又說「我完了」 ,愈說愈小聲的重複......我說,嗯,看來「我完了」這三個字有很豐富的內容,不是三個字可以說清楚。或者,他覺得這三個字就完全說清楚心思了?他說,嗯,這是結論,生活到現在的結論。我說,看來先下結論,再來慢慢說這個結論裡的眉眉角角。他沈默,後來說他不知道我的意思,但未再追究。再經過幾次會談後,他說他知道我的意思了。我問是什麼?他說我前幾次說的,先說了結論,再說眉眉角角。沈默後,他說,就是這樣空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再沈默。後來他開始談,他父親很早就過世了,他母親一直很憂鬱。我問是指什麼?他說不知啦,是精神科醫師說的,幾個月前,媽媽終於願意去看精神科門診,以前也不知是什麼診斷,反正就覺得媽媽像個遊魂。我說像空空蕩蕩的人?他哭泣,然後邊說,也不是空空蕩蕩,是像餓了很久的人,看到東西卻什麼都不要,他修正,是什麼都要,但都丟一旁,根本不知道媽媽要什麼?他說的是他和媽媽的關係,只覺得媽媽要從他這裡拿走很多。他說只是這種感覺,但不知是什麼,因為他只覺得自己無法做到讓媽媽可以滿意。
這種感受也出現在診療室裡——直到他如此描述媽媽時,我才驚覺,是啊,這也是我對他的感覺,只覺得他是一直要,一直要,但是不知他到底要什麼?只感受到他有著無止盡的失望,對診療室外的人事物,也包括對治療和我。但是他不斷的述說,讓治療得以持續下去,雖然我覺得幫不上忙,或者更像是幫不完的忙,不論是談論自己或他人,過去的故事或未來的心事。
佛洛伊德在《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裡所傳遞的「無止盡的心思」,可以說,就是請大家不斷地「說」,尤其是作為診療室裡的個案,而治療師也是以話語來回應。雖然我們也需要配備其它的能力,例如沈默的等待,或忍耐著無理無情的期待。也許這就是精神分析取向專業職人的宿命了。
當他談到媽媽難以滿意他的所有付出時,我想到的另一個象徵是佛教裡的「餓鬼道」。所謂「六道輪迴」,六道分別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阿修羅道、人道、天道,前三者稱「三惡道」,後三者稱「三善道」。我先來描述一下,它的形象之一是,這餓鬼肚子很大很大,需要吃很多東西才會飽足;它的脖子很細很長,嘴巴也有些大,但是嘴巴裡都是火,當東西放進嘴巴裡,幾乎都是被火燒光了。如果有未燒光的,也難以透過細長的脖子到肚子裡,因此它就是一直挨餓,一直處於需要很多東西,卻始終無法進到它所需要的地方。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意象是在貶抑當事者,帶有歧視的意味,不過我想說的是,這是佛教描述人如果不好好修行,有可能會在轉世時,墮進這「餓鬼道」。在這裡我不是強調轉世論,而是覺得這個意象,頗像個案的媽媽,或者說,這意象是貼近他感受裡媽媽的形象。雖然他不曾如此意識化、具象化他的媽媽,而是處於某種無法讓媽媽滿意的狀態。無論他做了什麼、給了什麼,好像都不是媽媽要的,或者是她要的,但是很快就變得毫無價值。他甚至一點點被感謝的機會都沒有,媽媽就馬上變得再需要其它的,他永遠無法弄清楚,媽媽要什麼?
我不是建議要以「餓鬼道」的形象,來詮釋他媽媽的舉止,或者詮釋他對治療者也是這般。我想說明,如果回到我們在地的了解,這是可以引用的譬喻,當然也可以從藉用其它國度的故事,不過佛教在台灣算是發展得不錯,因此佛教的某些意象和說詞已是我們的日常用語,例如「放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說法。在診療室,我相信一整天裡,勢必會聽到很多次,不同個案在面對難解的困局時,總是以要自己放下,作為表達自己無法做到的遺憾。
我引述「餓鬼道」這個比喻,是想要提議,我們是需要觀察自己是以什麼潛在方式,來理解個案所述說的故事。從督導經驗來說,我發現受督者都有以在地或生活上熟悉的象徵和故事,作為了解的方式,來讓自己比較容易記得個案所說的內容,也就是,我們會被我們自己熟悉的故事再翻譯過,作為了解這種現象的基礎,因為實情上,我們不可能只依著目前已有的精神分析外來語來了解個案,就算我們已經可以充份掌握那外來語的意思。
不論是否有說出來,我們理解個案所說的故事,都是經過我們內在裡的詮釋過程,除了詮釋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在診療室裡的大部分時間,當個案說著他們的心事和想法時,我們是在聆聽,但只是聆聽嗎?我們沈默地聽,和其他人的聆聽,有什麼差別?以前我們大都是談論,我們對個案的說話,叫做「詮釋」,那麼在沈默的時候,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的心智有什麼在運作,讓我們可以宣稱我們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或者,我們是在孕育著可以說話的詮釋?
這個孕育過程,有什麼心智和情感在運作呢?我們需要尋找更多的故事和象徵,來描繪這些沈默時的景色。畢竟我們大部分的時候,是處在沈默的狀態,不是要忽略詮釋和持續不斷述說的重要性,但如同葛林(A. Green)在《死亡母親》裡的案例表示,當個案對分析師的移情,是如同死亡的母親時,分析師這時對負面移情的詮釋,無法讓個案心理上有所成長,而是需要其它主動的,或者可以說是「同理」的處置。葛林未再說明細節,不過這是反映著,在說話時,除了要說什麼或不說什麼,還有說話之外的內容,也是治療過程所需要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當前述以「伊底帕斯情結」或「餓鬼道」作為象徵時,這並非Hanna Segal所說的「象徵等同」(symbolic equation),而只是一種比喻或翻譯。「象徵等同」是指把現在的某物比喻,等同於就是當年的某事物,而不是以象徵式的雷同方式來理解。因此使用「伊底帕斯情結」或「餓鬼道」來比喻個案潛在的某種心理現象,並不是就等同那個形象在原本故事脈絡裡的樣貌。
例如,常有人以「伊底帕斯情結」是要弒父戀母,因此如果要做自己、要獨立,就要做出「弒父」的舉動?這裡所說的「弒父」並不是身體上的殺害,而是象徵式的,不過這種說法就算是象徵式的舉動,在這個情結的意義上,仍是過於具象了。雖然是以伊底帕斯王的故事放進臨床現象,而有「伊底帕斯情結」的說法,但並不是把整個伊底帕斯王的故事都完全搬進來,只是擷取故事的片段做類比,來說明難以被理解的潛意識內容。當把「伊底帕斯情結」的說法,變成「象徵等同」式的運用,好像要依照這麼做才是「做自己」,這跟原本引用故事來描繪潛意識的景象,是不相干的作法。
引進戲劇伊底帕斯王的故事或佛教的餓鬼道的意象,並不是搬來整個戲碼或宗教的所有儀式和教理,這不合實際,也不可能,對精神分析來說,是藉用它們的故事,來看見我們想要看見的潛意識。但是,故事仍只是故事,不是潛意識裡的「本尊」。對精神分析來說,是仍要保有我們的說話特色,不是要把戲劇搬進診療室,即使有精神分析裡的「舞台理論」(field theory)者的說法,或戲劇治療的型式,我引來餓鬼道的意象,也不是要搬來佛教的修行方式。精神分析自然是在自己的模式裡精進。
至於後續是否要以戲劇手法來處理某些情結,也許會有戲劇治療和精神分析的對話,或者與宗教的後續對話,但不是要以文學、戲劇或宗教來取代精神分析的談話和聆聽,更不是要以精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待文學。雖然餓鬼道有道德或價值判斷,這是需要更多的論述,不是橫的移植,就像不是把古代戲劇裡,伊底帕斯王的故事和作法完全搬過來。
對於古典的論述,如果我們只是基於保護已有的,而無法在面對臨床的某些情境,以新的象徵來了解失落的空洞感,裡面有著難以言語的意涵,就會如同只是在空洞的牆上,添加一些古老精神分析的詩詞字畫,也許會有某些功能,如同戲劇的宣洩,但離精神分析取向診療室的痊癒,或分析的無止盡,可能仍有距離。我們早知精神分析的術語,可能進不了個案心思的大門,或者被當作只是貼在牆上的裝飾品,表示他曾到精神分析一遊而已。
此刻精神分析發展一百多年後,另有的宿命是,仍需要張開視野來尋找更多其它的象徵,來命名臨床的新發現,或者古老發現裡的細節脈絡。如同我們談論著一根大腿骨時,它的高低起伏、孔洞或某種凹痕,需要有個細緻名稱來標定它,讓我們更容易找到它,也知道環繞著它的血管或神經,在大腿上流浪時,仍有些規律可以被發現。
佛洛伊德的學生之一費倫齊(Ferenczi)提出「主動技術」,他看出佛洛伊德的不足,目前仍需要預設這種不足,才會讓我們不是滿足於目前已有的。但是如何不讓這種不滿足,變成是一種淹沒,或太急於成效而貿然引進其它不合宜的技術,這也是需要在意的。如果在態度上能夠有更廣闊的想法,這會更貼近分析的態度,並不是一直分析他人,就是分析的態度,而是包含了能夠慢下來、多想、交談,再多想、多談的過程。
就概念體系的建構,如同結構學派人類學家李維史陀,他建構的知識體系,運用了地層學、馬克思主義、佛洛伊德和索緒爾的語言學,雖然他的論述至今有些內容仍是如謎般,但是他影響了福柯、拉岡和羅蘭巴特,所造成的風雲仍是餘緒中,這是我想像的「回到佛洛伊德」的方式,需要再有意識地引進其它語詞,來描繪臨床所見裡,覺得了解或不了解的經驗。
【內文試閱一】
【小小說】
你來了,
來到古老村落薩所羅蘭
1.
你來了這裡,是我的薩所羅蘭,也是你的迷惘,是你帶我來的地方。
2.
你來了,你是來了。你竟說,你的精神史跑來找你,讓你不知道怎麼應付它們?我聽了也嚇一跳,倒不是不舒服的嚇一跳,而是有一股奇怪的暖流感受。我覺得你這麼說實在太誘人了,讓我被你這句話吸引住,「我的精神史跑來找我」實在是太生動的說法!
雖然這個生動的說法到後來,仍只是失落的空洞裡張貼的一句美麗的話語。不過,可以想到這些,是以後以後的事了。後來的知道,無法彌補先前的興奮所帶...
作者序
【推薦序】
|李俊毅
誰比自戀的敵人更自戀?
「X醫師,我來這裡之前有打電話給我媽媽,這樣我會覺得好一點。或是治療結束之後,回去馬上打電話給媽媽,我覺得這樣才公平。」個案來心理治療何必稟告媽媽呢?過世二十年的爸爸早早在外頭另組一個家庭,回家的時間很短,每次個案靠爸爸太近,媽媽就會生氣,連當年爸爸癌末住院時,個案在病榻照顧他,媽媽也吃醋。媽媽告訴個案,有她就好,不要依賴心理治療師。
這是一種「父系移情」(paternal transference),心理治療工作者應該不難懂,可以想像個案過去幾年掙扎在伊底帕斯情結困境中而進入治療室。如同蔡醫師所言,當年朵拉分析工作的失敗,是因為佛洛伊德忽略移情的分析,這是心理治療工作者耳熟能詳的一段歷史,即使佛洛伊德在半知半覺的狀態下,確立移情與移情詮釋的重要性,一百年後,我們在熟知理論與技術的情況下,處理這類問題並沒有比較輕鬆,這是怎麼一回事?
蔡醫師這本書的重點之一在於闡明理論與實作永遠有一道鴻溝,百年來臨床實務技術的修正,解決了某些問題,但也看到了其他問題。蔡醫師點出一個臨床工作者的普遍認知,那就是對負向移情詮釋的共識度比正向移情高出許多,因為前者對於治療架構有巨大的破壞性,必須儘早處理。對於正向移情的處理,蔡醫師是這麼說的:「正向移情只要觀察注意它就好,不要去詮釋它,因為那就見光死,讓原本是治療過程的重要推動力,因此而渙散。」這個原則算是圈內共識,然而,假如治療師被極度理想化呢?這顯然是個案內在客體經過「深度分化」(deep splitting)後,外化到治療師身上的結果。我記得蔡醫師在一次研討會中,強調克萊恩眼中這個客體是以「理想化客體」(idealized object)呈現出來的,這時治療師的處境無異於被綁架在診療椅上或說是釘在十字架上動彈不得,這種極度正向移情的處理並不比負向移情容易。
談到負向移情及其詮釋,我們總是會想到克萊因學派,尤其Rosenfeld強調的「破壞性自戀」,這源自於死亡本能、嫉妒等原始的毀滅力量。既然是「自戀」在運作,基本上處於無客體狀態或是與客體聯繫極少的狀態,如同蔡醫師所言:「這時透過移情裡所流露的生命早年的記憶,是行動式的記憶且更貼近生命早年的經驗,而不是語言式以故事記得的方式」,如同「佛洛伊德在《記憶、重複與修通》這篇有關技術的論文裡,提到的真正的早年記憶不在故事裡,而是在於行動裡」。因此,移情詮釋的效用此時大打折扣,所以呢?蔡醫師提到葛林(André Green)在《死亡母親》一文裡論述某些個案,在某些處境下,他們需要的不是詮釋,而是「同感」(empathy)。蔡醫師說得好:「我們的專業經過一百多年的臨床試煉,早就知道是『慢慢等』,但這種慢如果被個案當作如同死亡般,那麼這種慢就不再只是慢,而是死亡,勢必需要動一動的說些什麼,只是顯示我們還在,是否有時候這就是最必要的empathy?」這類困境其實也是臨床工作者經常遇到的難題,也是讓人挫折的情境。
越來越多個案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邊緣型人格、是躁鬱症,自己會解離、有多重人格、有伊底帕斯情結,很容易產生移情等等,這或許意味個案對於自己的症狀有一定的認知,當然,也或許有更多的錯誤認知。透過網路媒介,有情緒困擾的個案自助管道越來越多樣化,這個趨勢對於心理治療工作者來說不見得是好事,假設診斷與症狀是一種防衛,一種阻抗,蔡醫師形容個案「只是說著一句死掉的語言」,然後安枕無憂、好整以暇地躲在一處庇護所或是蔡醫師形容的「古堡」中,也就是說,個案進入診療室前已經重度(再度)武裝(防衛)自己了。現今心理治療工作者面臨的現實挑戰是個案屬性從過去的neurotic與non-neurotic世代進入borderline與non-borderline世代,亦即個案的問題涉及更早期
更深層的失落與創傷,人格碎裂的程度更嚴重,更缺乏彈性,治療難度更高。
人的思考路徑絕對不是循著線性邏輯,而是一種繁複的辯證過程,蔡醫師的劇本與診療室中的對話一向引人入勝,那是以一種自我對話式的型態呈現,基本上就是精神分析式的思路,是一種創作演繹過程,並非歸納性質,真實呈現也帶領讀者進入蔡醫師運作中的內在世界。讀者必須帶著耐性與專注力隨著蔡醫師的思緒起伏,進進出出,撥雲見日,終於得到甚至開展另一種見解,而不是所謂正確的答案。心理治療師在這聆聽過程並非僅僅沈默、被動的聆聽,而是保持一種所謂的「分析式聆聽」(analytic listening),但若碰到葛林在《死亡母親》中的案例,蔡醫師叮嚀則必須加上主動的同理,還有,保持Bion強調的「無憶無慾」(no memory, no desire)態度。
最後,蔡醫師提到的精神分析與文學或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他舉〈伊底帕斯王〉這部希臘悲劇為例:「對精神分析來說,是藉用它們的故事,來看見我們想要看見的潛意識。但是故事仍只是故事,不是潛意識裡的『本尊』。對精神分析來說,是仍保有我們的說話特色,不是要把戲劇搬進診療室。」【高雄精神分析讀書會】多年來維持「應用性精神分析」(applied psychoanalysis)性質,以電影、文學作品、藝術等等為媒介,嘗試與精神分析理論與臨床經驗結合,期待可以看到這些作品更深邃更廣泛的意涵,並非藉精神分析理論強行解讀作者創作動機。我一直覺得讓精神分析工作能夠持續下去的動力,有一部分來自於治療室外或說是躺椅外的應用性質活動,而非僅僅嚴肅的學術活動。
(李俊毅/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無境文化【生活】應用精神分析系列叢書策劃)
【推薦序】
|李俊毅
誰比自戀的敵人更自戀?
「X醫師,我來這裡之前有打電話給我媽媽,這樣我會覺得好一點。或是治療結束之後,回去馬上打電話給媽媽,我覺得這樣才公平。」個案來心理治療何必稟告媽媽呢?過世二十年的爸爸早早在外頭另組一個家庭,回家的時間很短,每次個案靠爸爸太近,媽媽就會生氣,連當年爸爸癌末住院時,個案在病榻照顧他,媽媽也吃醋。媽媽告訴個案,有她就好,不要依賴心理治療師。
這是一種「父系移情」(paternal transference),心理治療工作者應該不難懂,可以想像個案過去幾年掙扎在伊底帕斯情結困境中而...
目錄
目 錄
【 序 】
李俊毅 誰比自戀的敵人更自戀?
李芝綺 既是迷惘,要如何想得清楚又寫得出來呢?
劉玉文 那些值得迷惘,不得不迷茫的事
詹婉鈺 歡迎來到精神分析主題樂園
陳昌偉 沒有記憶、沒有慾望的薩所羅蘭
陳瑞慶 廢而不廢
【 小小說 】
你來了,來到古老村落薩所羅蘭
七彩虹光想念媽媽,想用一道白光看見真實母親
靠山:一通電話裡,empathy的心智地圖能吞下多少茫然?
伊底帕斯情結與餓鬼道
精神分析與文學或宗教對話的後設想像
如果阻抗、防衛和移情,是埋在地下古堡群的迷惘
兼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技術課題
【 劇本 】
想忘的,一定要記得......
三個人的孤寂和迷惘
目 錄
【 序 】
李俊毅 誰比自戀的敵人更自戀?
李芝綺 既是迷惘,要如何想得清楚又寫得出來呢?
劉玉文 那些值得迷惘,不得不迷茫的事
詹婉鈺 歡迎來到精神分析主題樂園
陳昌偉 沒有記憶、沒有慾望的薩所羅蘭
陳瑞慶 廢而不廢
【 小小說 】
你來了,來到古老村落薩所羅蘭
七彩虹光想念媽媽,想用一道白光看見真實母親
靠山:一通電話裡,empathy的心智地圖能吞下多少茫然?
伊底帕斯情結與餓鬼道
精神分析與文學或宗教對話的後設想像
如果阻抗、防衛和移情,是埋在地下古堡群的迷惘
兼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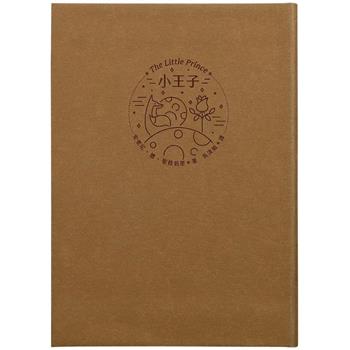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