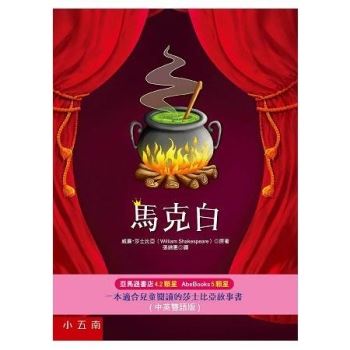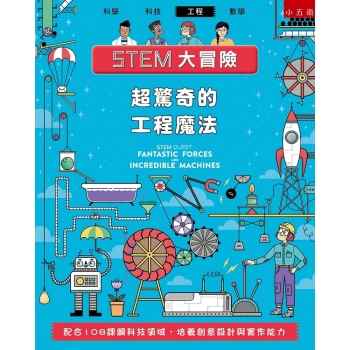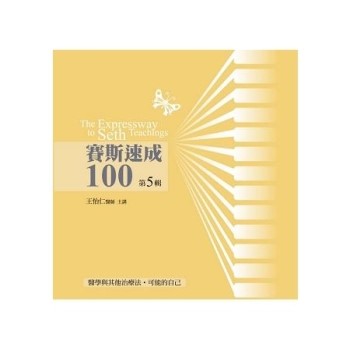CHAPTER 064 暖意
身體被蝕質包裹,漸漸暖和起來。疼痛與舒適的反差讓祝延辰有些眩暈,身上有什麼溫暖的東西蠕動、成形。
他睜大雙眼,卻被黏稠的黑暗蓋住眼球,看不真切。
難道是自己瀕死之際,出現了幻覺嗎?
他能聽到周遭的蝕質湧起落下,發出潮水般的拍打聲,彷彿某個巨物將要從漩渦中浮出。束鈞徹底與蝕質融合,若是他在精神折磨中放棄思考、喪失人性,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蝕沼將會誕生。
然而嘈雜聲逐漸平息,他周遭越來越暖,包裹他的不再是溫暖的蝕質,而是一個人類的擁抱。
果然是幻覺吧。
祝延辰心中嘆氣,他剛決定閉上眼,卻在黑暗中看到兩點銀白的光。它們越貼越近,隨後有什麼溫暖柔軟的東西覆上了嘴唇。
那是一個吻,淺嘗輒止,輕柔小心,純粹得不帶一絲情欲。彷彿稍微用力,自己便會碎掉一般。
束鈞確實吻得小心。
他不知道要怎麼處理內心噴薄而出的情感,過去的點點滴滴終於拼湊完整,他的心臟鼓脹,難以呼吸。腦中的理性與瘋狂通通退卻,他幾乎無法思考,只剩情不自禁。
祝延辰醒著,他知道。那雙深如古井的眸子半闔,目光穿過黑暗,安靜地停在自己身上。饒是情感奔湧如潮,束鈞仍放慢了動作,給對方留下了足夠的閃躲時間。
祝延辰卻沒動。
儘管自己治癒了對方的傷,祝元帥的嘴唇冰涼,仍帶著幾分血腥味。
先前,知道祝延辰在研究蝕沼上付出生命,束鈞只當他是個偏執的研究者。如今他才深切體會到,對方「從十六年前就開始研究蝕沼」到底意味著什麼。
有那麼一瞬,束鈞甚至希望「煙塵」只是個普通小孩。如果沒有生於權貴之家,按祝延辰的執念,他大可轟轟烈烈反對玩家系統,成立個像樣的反抗組織。
如此就算道路有限,他的朋友也能瀟瀟灑灑地拚個問心無愧。
可祝延辰終究選擇站在高位,力圖親自解決這個問題。
同為上位者,束鈞清楚這代表了什麼。祝延辰不能毫無理由地廢除玩家系統,若是他找不到合適的理由,必然會被虎視眈眈的競爭者們推翻。在維護合成人的同時,他還要肩負人類的安全。
當今時局下,這條路無異於飛蛾撲火。
就算知道救不了自己,就算知道改變一切只能滴水穿石,他這位曾經瑟縮的朋友,還是義無反顧地當了第一滴水。
「阿煙,我還以為你是穩重的人。」束鈞慢慢移開嘴唇,輕聲說道。「你怎麼這麼……」
他想說傻,想說瘋狂,想說偏執,但最終都嚥了下去。想到當初兩人相遇時,這人刻意擺出的疏離模樣,束鈞連氣都順不過來。
他心疼到想揍對方,卻連擁抱都不敢太用力。罷了,束鈞側過頭,又吻了吻祝延辰的嘴唇。
過去的時光無法追回,但從今以後,他至少可以確定,對方不需要再一個人前進。
去他的戰爭結束再追求,這個人是他的。
哪怕祝延辰對他沒有愛情方面的感覺,這個人也是他的友人與親人,這點絕不會改變。
那些灌頂的戾氣有了出口,它們被撫平了刺,盡數化為堅定與心酸。
束鈞試圖再次移開嘴唇,腦海中的黑暗漸漸散去,又變成「待會如何誠懇解釋這個吻」的腹稿。可他這腹稿還沒打完開頭,祝延辰便吻了回來。
如果說束鈞之前的吻小心翼翼、蜻蜓點水,是帶著憐惜和安撫的試探。這個回吻氣勢洶洶,帶著十足的渴求和絕望。
祝延辰按住束鈞的後腦,吻得極深。
束鈞愣了幾秒,半是純然的愣,半是摻了酸意的喜悅。他不甘示弱,攏住祝延辰的背,熾熱地回應。
彷彿缺失多年的拼圖終於完整,兩人的呼吸曖昧地交纏在一起。溫熱的吐息化為沸水,誰都不願意停下,任憑熱度上升,嘴唇與舌頭幾乎要融化。
最終,祝延辰的舌尖掃過束鈞犬齒的齒根,雙手稍稍用力,兩人終於分離。
「慶典會場的支援。」
各自喘息一陣後,兩人幾乎同時開口。
他們吻是吻得投入,分開後,奇妙的尷尬便湧了上來。
束鈞搜腸刮肚,再次開口。
「你的傷還好嗎?」
「你的身體怎樣了?」
兩人再次異口同聲。
長吻的熱氣散去,又一陣冷場。
「先去週一那裡吧。」許久,祝延辰說道,聲音裡有種怪異的飄忽感。「我們都需要光照和檢查。」
「嗯。」束鈞忙直起身,扶起虛弱的祝元帥。這人傷勢無礙,體力卻流失不少,一時半刻補不回來。
藤蔓蝕沼已經化為普通蝕沼,束鈞也沒吸收大量蝕質,來個大變形。眼下兩人腳下的蝕質深及膝蓋,相當不好走。
「週一在哪邊?」
「往那邊走個一千二百公尺。」兩人靠得很近,祝延辰索性抬起手來指。
「好。」束鈞手臂用力,攬起祝延辰的腰,將他抱在身前。可惜祝延辰塊頭較大,束鈞又不擅長這樣抱人,動作有少許彆扭。
束鈞原地思忖了片刻,蝕質隨著他的意念朝上方伸展,形成無數漆黑的枯手,小心地托起祝延辰,好讓他躺得更舒服點。
一個頗為駭人的公主抱,完成。
曖昧的氣氛無影無蹤,束鈞的表情太過大義凜然,祝延辰又把自己繃得近乎筆直,場景多了幾分莫名其妙的悲壯。
以至於週一剛發現他們,便扯著喉嚨哭喪。
「祝──死──啦──」
「閉嘴。」束鈞磨磨牙,把祝延辰放在一片乾淨的石板上。
觸到地面,方才繃成鐵棒的祝元帥放鬆了點,慢慢地坐起身來。
週一身上掛了不少東西,束鈞將它一拔,劍尖一挑,所有行李都到了祝延辰眼前。
祝元帥喝了整整一壺補充液,雖然他被汙水和血液搞得全身濕透,氣色卻好了不少。
束鈞則打開一旁的背包,生了火。緊接著他拿了條毯子,圍在祝延辰身上。
祝延辰漆黑的雙眸牢牢鎖著他。
束鈞的目光軟了下來,沒有開口解釋,只是捉住祝延辰的手,另一隻手伸出,兩人小指相勾。
祝延辰收回目光,閉上眼,隨後呼出長長的一口氣,像是要把十六年的壓抑全部呼出來。
兩人沉默相對。
這裡的環境比戰鬥前還混亂恐怖,束鈞卻覺得整個世界彷彿被洗涮一遍,柔和了許多。
「束鈞,幫我拿一下那邊的白色儀器……我得看看你血液的各項指標。」祝延辰恍惚了幾分鐘,再次開口,語調裡帶著前所未有的輕鬆。
束鈞不動。
「怎麼了?」
「你先休息一下,十分鐘後測。然後你再休息個二十分鐘,等你體力恢復,我們再去慶典會場。」束鈞掏出錶,像模像樣地計時起來。
隨即束鈞打了個響指,幾團蝕質捲成球,把自己在火邊烤暖,再爬向祝延辰。
後者狐疑地看向那些怪球。
「你這樣容易感冒。」束鈞指揮著球狀物前進,「而且你一向愛乾淨,身上沾著這麼多髒東西,肯定受不了。我只是讓它們清除把水和汙垢,不會傷到你。趁這段時間,我們正好談談……談談……」
他想說「談談剛才那個吻」,卻怎麼都說不出口。
束鈞挖空心思打著腹稿,幾個溫暖的蝕質球已然湊近祝元帥。它們輕柔地滾過祝延辰的皮膚,掠走水分,血跡和泥漬盡數分解,一點衣服纖維都不敢吃。軟球們爬過剛癒合的傷口,觸感如同指尖輕拂,祝延辰皺起眉,輕輕哼了聲。
這下束鈞的腹稿徹底散架,滿腦子只有「自掘墳墓」四個大字。
「我……我沒有別的意思。」束鈞不自在地交叉雙手,爪尖差點劃傷自己。「剛才我也……不、不是,剛才我──」
祝延辰安靜地看著他。
束鈞深呼吸幾次,眼一閉,話調裡又有了戰士的氣勢,「算了,總卡著也沒意義。阿煙,待會處理完會場那邊的問題,我們兩個得好好談談。」
他乾脆地走近,揪起一個扭動的蝕質球。蝕質球在他手中扭了扭,開始乖乖裝死。
「我弄這東西,沒有別的心思。」束鈞板著臉,語調無比嚴肅。「但剛才我親你,確實有別的意思。本來我想等戰爭結束再說,可剛才想起了所有事,我一時沒控制好情緒……
「我承認,我很清醒地在親你。」他又湊近了些,獸瞳收成細細一條縫。「不過你剛才很恍惚,這事還是說清楚比較好。」
「你未必清醒。」祝延辰低聲道,「你被負面情緒干擾太久,回憶又剛恢復。衝擊之下,你可能對我產生本能的依賴。」
他謹慎地頓了片刻,臉上看不出情緒。
「我同意,我們是該把這些說清楚。畢竟現在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比如慶典那邊的戰況,以及你的身體……」
他還沒說完,便被迫將後半句嚥了下去。
束鈞一手一個綿軟的蝕質球,從祝元帥腦袋兩邊糊上,把他的臉夾在中間,那張英俊的臉被擠得微微皺起。
「我好不容易才想好的說法。」束鈞指甲尖銳,不敢直接上手,只得揉著蝕質球,間接擠祝延辰的臉。「你這樣有意思嗎,阿煙?嗯?要不是我心疼得慌,我真的很想敲你腦袋,還負面情緒擾亂呢,我他媽……」
束鈞咬咬牙,吞下了後面的一串髒話。
阿煙從小就是個死腦筋,又孤身一人這麼多年,對情感遲鈍也在所難免。如今時間有限,這場「究竟誰占了誰便宜」的辯論大會很難得出結果。
「你這消極念頭倒是一點都沒變。好,等會場那邊搞定,我們關上門,好好談。」
束鈞露出牙尖,一字一頓,最後擠出咬牙切齒的微笑。
他們是合作者、是戰爭搭檔,反正跑不了,這下連來日方長都不需要考慮了。是傾心已久還是一時衝動,他絕對要按住這個肚子裡七彎八拐的悶葫蘆,好好把話說清楚!
想到這裡,束鈞惡狠狠地哼了聲。他鬆開祝延辰的臉,順手用蝕質球擦乾淨對方的頭髮。
束鈞光顧著生悶氣,漏過了祝延辰的眼神。
祝元帥專注地盯著面前的人,目光猶如撲食前的野獸,寫滿志在必得。
火焰抖動,照亮了那雙深不見底的眸子。祝延辰伸出手,下意識猶豫了片刻,隨後他勾起嘴角,果斷握住束鈞的手腕。
「時間到了,該驗血了。」他說,「你說得對,我們得盡快解決會場的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禁止存檔(3)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華文 |
$ 298 |
科幻/奇幻小說 |
$ 315 |
中文書 |
$ 35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禁止存檔(3)
謊言構築的虛幻世界中,
你,是我唯一的真實──
--
──進入 侵蝕──
伺服器連接中……
正在讀取遊戲存檔……
存檔錯誤……
從夢中醒來的瘋狂靈魂,一步步將現實化為噩夢,
被迫捲入其中的束鈞,終於將破碎的過去拼湊完整──
與祝延辰的初識、兩人絕望的臨別約定,
一旦意識到這些年來對方為守住承諾付出了些什麼,
憐惜與愧疚就讓心隱隱作痛。
面對這份羈絆,事到如今,束鈞絕不可能放手。
此刻,「玩家系統」的漏洞浮出水面,
蝕沼變異的真相再也無法掩蓋。
束鈞與祝延辰聯合雙方勢力,
在仇恨與生存之間搭起最後一道防線。
然而,當情勢脫離控制,合成人動亂一觸即發,
兩人之間的信任,是否足以託付一切?
商品特色
◆ 知名耽美作者「年終」末日廢土科幻力作
◆ 禁欲系元帥美攻╳狂野系戰士強受
◆ 作者全新修訂並收錄加筆番外〈尾巴〉
◆禁止存檔03精美人物書衣
◆首刷限定
◆韓國知名繪者 코바 繪製
作者簡介:
年終
一隻普通白熊。
最喜歡暖光燈和怪東西,希望新的一年抓到更多靈感海豹。
繪者簡介
코바
그림그리고 게임하고 수다떠는게 좋은 일러스트레이터
一個喜歡畫畫、玩遊戲、聊天的繪師。
章節試閱
CHAPTER 064 暖意
身體被蝕質包裹,漸漸暖和起來。疼痛與舒適的反差讓祝延辰有些眩暈,身上有什麼溫暖的東西蠕動、成形。
他睜大雙眼,卻被黏稠的黑暗蓋住眼球,看不真切。
難道是自己瀕死之際,出現了幻覺嗎?
他能聽到周遭的蝕質湧起落下,發出潮水般的拍打聲,彷彿某個巨物將要從漩渦中浮出。束鈞徹底與蝕質融合,若是他在精神折磨中放棄思考、喪失人性,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蝕沼將會誕生。
然而嘈雜聲逐漸平息,他周遭越來越暖,包裹他的不再是溫暖的蝕質,而是一個人類的擁抱。
果然是幻覺吧。
祝延辰心中嘆氣,他剛決定閉上...
身體被蝕質包裹,漸漸暖和起來。疼痛與舒適的反差讓祝延辰有些眩暈,身上有什麼溫暖的東西蠕動、成形。
他睜大雙眼,卻被黏稠的黑暗蓋住眼球,看不真切。
難道是自己瀕死之際,出現了幻覺嗎?
他能聽到周遭的蝕質湧起落下,發出潮水般的拍打聲,彷彿某個巨物將要從漩渦中浮出。束鈞徹底與蝕質融合,若是他在精神折磨中放棄思考、喪失人性,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大蝕沼將會誕生。
然而嘈雜聲逐漸平息,他周遭越來越暖,包裹他的不再是溫暖的蝕質,而是一個人類的擁抱。
果然是幻覺吧。
祝延辰心中嘆氣,他剛決定閉上...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CHAPTER 064 暖意
CHAPTER 065 歸隊
CHAPTER 066 夜晚
CHAPTER 067 一觸即發
CHAPTER 068 會議
CHAPTER 069 祝盛
CHAPTER 070 衝突
CHAPTER 071 爭吵
CHAPTER 072 動搖
CHAPTER 073 行動變更
CHAPTER 074 黑霧之中
CHAPTER 075 怪物
CHAPTER 076 誘餌
CHAPTER 077 殘響
CHAPTER 078 金屋藏嬌
CHAPTER 079 錯誤認知
CHAPTER 080 封城
CHAPTER 081 二十一人
CHAPTER 082 刺殺
CHAPTER 083 海邊
CHAPTER 084 圖窮匕見
CHAPTER 085 步步緊逼
CHAPTER 086 混亂之始
CHAPTER 087 屠殺宣告
CHAP...
CHAPTER 065 歸隊
CHAPTER 066 夜晚
CHAPTER 067 一觸即發
CHAPTER 068 會議
CHAPTER 069 祝盛
CHAPTER 070 衝突
CHAPTER 071 爭吵
CHAPTER 072 動搖
CHAPTER 073 行動變更
CHAPTER 074 黑霧之中
CHAPTER 075 怪物
CHAPTER 076 誘餌
CHAPTER 077 殘響
CHAPTER 078 金屋藏嬌
CHAPTER 079 錯誤認知
CHAPTER 080 封城
CHAPTER 081 二十一人
CHAPTER 082 刺殺
CHAPTER 083 海邊
CHAPTER 084 圖窮匕見
CHAPTER 085 步步緊逼
CHAPTER 086 混亂之始
CHAPTER 087 屠殺宣告
CHAP...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