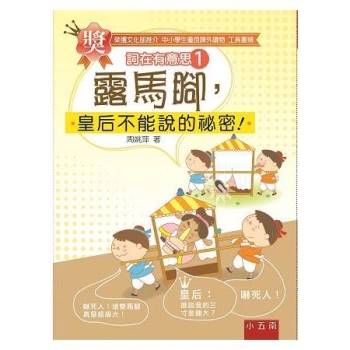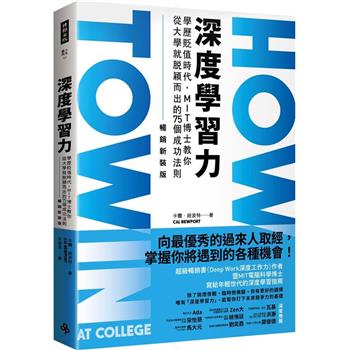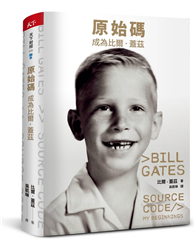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 古風耽美作者 刑上香 經典之作
◆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 特邀古風水彩繪師 慕容緋潔 繪製絕美封面
◆ 特別收錄全新番外〈姬回〉
病弱偏執皇帝╳市井騙子國師
與君再別,
只願從此以往江湖相忘……
姬雲羲輕輕地哼笑一聲,
殘存無幾的理智似乎湮滅在他的雙眼中,只剩一片冰冷和絕望。
「我想相信你的……」姬雲羲將額頭抵在宋玄的額頭上,「可我沒有耐心了,宋玄……」
宋玄本只想著護送姬雲羲平安回到盛京,
而後便獨自遠走江湖。
未料姬雲羲日益深重的執著,
竟是要將他囚困於這一方宮城,
讓他再難逃開他的占有。
對姬雲羲來說,
宋玄是他晦暗生命中僅有的溫暖,
是他朝思暮想、求而不得的妄念;
可對宋玄而言,
兩人之間卻好似隔著無法逾越的高牆,
一個是高高在上的尊貴皇子,
另一個卻是混跡市井的江湖騙子,
除卻陌路,便再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