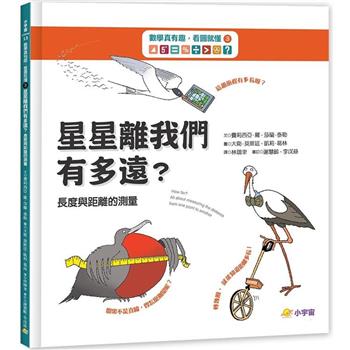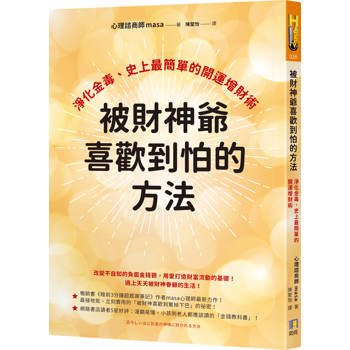國家人權博物館X春山 合作出版
胡淑雯.童偉格 主編
歷史是一個人性劇場繼《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之後,春山出版與國家人權館再度合作白色恐怖散文選,散文選涵蓋散文、回憶錄、傳記與口述,同樣由小說家胡淑雯、童偉格主編,在超過兩百本書籍中,精選四十七篇作品,四十三位作者,近九十萬字的規模。散文選以截然不同的視角切入白色恐怖歷史的肌理,區分為繫獄作家、青春、地下黨、女人、身體、特務、島等七大主題,並由研究者逐篇注釋,增強背景理解。
在這個選集中,我們將首次將這些受挫、受辱或者心靈扭曲的主體放置一處,甚至涵蓋特務、線民等加害者與協力者,也注重多元族群包括外省、原住民與離島馬祖、外國人的經驗,使他們共同發聲,像是一個巨大的人性劇場。我們在這些活生生的記憶中,找到一條通往人間之路,看到無辜受難者、革命者、人生遭到毀棄的家屬,也有判決了兩百多位共產黨卻遭內鬥誣陷的調查局處長。這些故事或者令人驚怖、畏懼、迴避,但同時是這塊土地上曾經擁有的真實人性,在這個人性劇場中,觀者將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啟示,同時也找到與這些歷史的聯繫,以人性的方式。
■卷二地下燃燒 The Underground
藍博洲白色恐怖的掘墓人
林書揚曾文溪畔的鬥魂──莊孟侯與莊孟倫
黃素貞我和老蕭的抗戰和地下黨歲月
陳明忠口述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節選]
吳聲潤二二八之後祖國在哪裡?[節選]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節選]
林易澄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
葉怡君白堊記憶:一群五○年代「老同學」戰鬥的故事
本卷以藍博洲撰寫的曾梅蘭一九九三年尋得其兄徐慶蘭之墓開啟地下黨的湮沒歷史,並一路或跟隨莊孟侯、莊孟倫與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黃素貞,理解日治時期反日與農工運動的脈絡,或重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現場,明白這個關鍵事件如何讓許多年輕人,成為一九五○年代受左翼思想燃燒的名字,於是銀行員在銀行被捕(陳英泰)、教師、國小校長在學校被捕(陳明忠、郭慶),以及機械廠的工人開始製作手榴彈(吳聲潤),最後則以五○年代倖存者看到刑場馬場町成為紀念公園以及政府開始進行補償作業為詰問:歷史該如何補償?
■本書特色
1將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至今,陸續出版的龐大的白色恐怖書寫,節選出層次分明的主題,並藉此更新對白色恐怖理解的視野。
2兼具文學與歷史性。選集中你將認識到相對陌生的當事者,他們可能不是文學家,但你將驚訝於他們的文學豐富性,如本卷的林書揚,他筆下在曾文溪畔長大的莊孟侯、莊孟倫兄弟,如一則俠客傳奇。本次選集將以主題的方式,逐步引介讀者認識過去的重大白色恐怖案件,如臺大與師範學院的四六事件、形同滅村的鹿窟案、共產黨支部在臺灣各地的發展與瓦解、牽連一百多名師生的澎湖煙臺聯中案、綠島再叛亂案、柏楊案、臺獨案、民主臺灣聯盟案、海軍白恐案與美麗島事件等。透過選集閱讀,建立認識的基本框架。
3製作大事記,透過作品寫作、首次發表與出版時間,對照作者經歷以及政治、文化的發展,能對白色恐怖的歷史作用力有全貌理解。
作者簡介:
藍博洲(一九六○~)
一九八三年開始小說創作,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臺灣思想起》製作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代表作小說有《藤纏樹》、《臺北戀人》等,報導文學有《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等,歷史報導有《紅色客家庄》、《麥浪歌詠隊》、《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臺共黨人的悲歌》等。
林書揚(一九二六~二○一二)
臺南麻豆人,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畢業,一九五○年五月底因省工委麻豆支部案被捕,判處無期徒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假釋,繫獄長達三十四年七個月,是臺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之一。出獄後一九八六年發起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並陸續參與創建工黨、勞動黨,著有《林書揚文集》四冊。
黃素貞(一九一七~二○○五)
本名黃怡珍,臺灣汐止人。因養父在福州做生意,在福州受完高中教育。盧溝橋事件後,全家返回臺灣,以教授北京語為生,認識許多有愛國情懷且反日的知識分子,包括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蕭道應。與蕭道應結婚後,兩人與鍾浩東、蔣碧玉及鍾浩東表弟李南鋒五人計劃潛赴中國大陸參加抗戰,其後加入丘念台的東區服務隊,黃素貞為丘念台改的化名。二戰後,一九四六年黃素貞與蕭道應先後返臺,蕭道應加入共產黨,《光明報》事件後,兩人陸續逃亡鶯歌、苗栗與屏東佳冬,一九五二年四月於三義被捕,並於同年自新。
陳明忠(一九二九~二○一九)
高雄岡山人。就讀臺中省立農學院期間,遇到二二八事件,並在埔里加入二七部隊的敢死隊,遭通緝,因農學院院長周進三營救取消通緝。後至岡山農校任教,一九五○年七月遭捕,判刑十年。出獄後至藥廠工作,一九七六年遭控陰謀叛亂二度入獄,經過海外學人與國際組織援救,判刑十五年,一九八七年三月以保外就醫名義出獄,之後組織成立夏潮聯誼會和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以及中國統一聯盟和勞動黨。
吳聲潤(一九二四~)
高雄六龜人。十六歲赴日就讀機械專業,芝浦工業學校畢業,戰後一九四六年二月回到臺灣,二二八事件後,於第六機械廠工作時,與好友傅慶華加入地下組織。一九四九年底接到解放通知,暗地製作手榴彈,後被通知毀棄。一九五○年十月開始逃亡,年底被捕,判刑十二年。為第一批送往綠島的政治犯。出獄後開設鐵工廠,轉為東陽精機,一九九○年代與難友投入歷史平反運動,歷任「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臺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老人關懷會」會長。
陳英泰(一九二八~二○一○)
臺北木柵人。曾就讀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戰爭時考上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因被日方徵為學徒兵休學,戰後復學,臺北經專後併入臺大法學院。畢業後至臺灣銀行。因已有初步接觸左傾思想,在臺北二中同學兼同事林從周的介紹下加入省工委組織。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銀行被捕,送至軍法處審判,判刑十二年,中間兩度被送至綠島服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獲釋。出獄後開設大剛貿易公司,並開始逐步記憶寫作白色恐怖回憶,曾任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常務理事,臺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著有《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下冊、《再說白色恐怖》、《回憶2:由小牢改坐大牢》、《回憶3:開啟白色恐怖平反之門》、《回憶4:到達不了的平反之路》六冊。
林易澄(一九八三~)
臺灣嘉義人,臺大歷史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合著有《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葉怡君(一九七二~)
臺灣臺南人,政治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新聞所畢業,亦有筆名葉淳之。曾任公共電視環境專題記者及製作人、臺灣電視製作人、地方及中央機構公務員、統一集團行銷企畫。曾獲時報文學獎、臺灣文學獎、臺北文學獎等。著作有《島嶼軌跡》、《冥核》等。
國家人權博物館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總統府公布《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歷經多年籌備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於二○一八年正式成立,除持續推動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文物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工作外,亦擴大支持各種人權議題及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的組織發展,展現臺灣追求落實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決心。二○一九年,人權館成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Asia-Pacific),與國際人權思潮接軌,促進民主與人權理念的推廣及深化。
主編
胡淑雯
一九七○年生,臺北人。著有長篇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短篇小說《字母會:A~Z》(合著)、《哀豔是童年》;歷史書寫《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主編、合著)。
童偉格
一九七七年生,萬里人。著有長篇小說《西北雨》、《無傷時代》;短篇小說《字母會:A~Z》(合著)、《王考》;散文《童話故事》;舞臺劇本《小事》。
章節試閱
白色恐怖的掘墓人藍博洲
◎收錄於二○○四年十二月《紅色客家庄》,印刻出版。
曾梅蘭,苗栗銅鑼人,一九五二年與二哥徐慶蘭先後被捕,處刑十年。徐慶蘭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槍決,屍骨無蹤。曾梅蘭出獄後輾轉尋找數十年,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終於在臺北六張犁公墓的亂草堆下,找到了二哥的墓塚;同時挖掘到總數二百六十四個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石。
客家佃丁
一九三○年五月十九日,我在苗栗銅鑼三座屋(今竹森村)的屋家出生。
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甚至懷疑,為什麼我姓曾,而我哥徐慶蘭卻姓徐呢?其實,那是因為我爸徐阿享當初跟我媽曾草妹結婚時是被招贅的。
我爸原來住在銅鑼七十分。三歲時,他爸就過世了,他媽改嫁後就失去聯絡。他就跟著叔叔和祖母過日子。後來就一直在叔叔家幫忙種田。
我媽曾草妹是我阿公的獨生女。我阿公叫曾阿統,祖籍是廣東梅縣合浦,從大陸移民過來臺灣的時候,最早是在通霄楓樹窩落腳,後來才漸漸移到三座屋。我阿公是佃農,自己耕三甲多的田,四十幾歲的時候,眼睛痛壞掉而瞎了。他就給我媽招親,條件除了入贅之外,還要能耕田、做工,而且多少識一些漢字。
我爸就這樣入贅到曾家。
當時,我阿公和我爸事先有約定,男的頭胎要從女方姓。我爸和我媽一共生了四個兒子。我排行老四,和大哥春蘭姓曾。而二哥慶蘭和三哥貴蘭則跟父親姓徐。
除了四兄弟,我還有兩個阿姊。她們很早就嫁人了。所以,我家基本上是六口人在生活。
我讀的書不多,銅鑼富士國民學校(原稱公學校,到我五、六年級時改稱國民學校)畢業後,一方面是自己認為考不上高等科,一方面家裡的經濟能力也供不起我念,所以就沒再繼續升學。白天,幫忙家裡做田事,晚上就到銅鑼街上,跟一個叫作羅吉仁的先生讀漢文。
羅先生一共收了二、三十個學生。在當時,漢文是被日本政府禁止的。所以,羅先生只能偷偷地教,我們也是偷偷地學。每次,只要他一發現有日本警察遠遠地走過來時,立刻緊張地叫我們安靜,不要出聲。否則,要是被發現的話,他就會被叫到派出所問話,而且被打,有時甚至被關起來。
我跟羅吉仁先生讀「漢文」,前後大概有兩年吧。就在我十五歲、十六歲(虛歲)那兩年。
到我十七歲那年,臺灣就光復了。
二哥徐慶蘭
我二哥徐慶蘭是一九二四年出生的,比我足足大了六歲。我還記得,我上公學校一年級的時候,他還沒畢業。因為家裡窮,我媽每天就裝了一個大大的便當,讓我們兩兄弟帶到學校去吃。到了學校,中午休息時,他總是先吃,然後就留比較多的菜給我吃。
講到我這個阿哥,我實在是很尊敬、欽佩他。他也非常疼我,從來不曾用巴掌打我一下耳光。他一直鼓勵我要用功讀書,而他也會教我做功課。他從來不會對自己的兄弟刻薄。所以,講起我這個阿哥,我的眼淚就會流出來。
我爸從日本時代一直到光復後,都靠著種田,農閒時就做泥水工,來養活我們。他繼承我阿公的分,總共耕有三甲多的田。地主鍾阿有,是崁下鍾屋人。
後來,國民政府準備要施行「三七五減租」的土改計畫。我們這些種田的鄉下人卻呆呆的,根本不知道有什麼「三七五減租」這種東西。相反的,我們家的地主卻已經知道這個情報了。
結果,當我們頭一冬的稻子割完,繳了租穀以後,他就跟我爸說,那三甲多的田,他要拿回去,自己耕。果然,第二年,也就是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四月,陳誠就開始施行「三七五減租」的政策。
我那個二哥徐慶蘭,個性非常硬。當地主要把田地收回去的時候,我記得,他跟我爸說過這樣的話:「怕什麼?那麼多人沒田可耕都不會餓死,我們怎麼會餓死?」
我爸聽他這樣說,就把三甲多的田還給地主。
當時,石炭非常缺乏,一般瓦窯燒瓦都用菅草做燃料。因為沒田可耕了,又找不到什麼工作,我和大哥和三哥,三個兄弟就去山上打瓦草,賣給瓦窯。而我那個第二的徐慶蘭,自己就另外去給人打油車。當時的油車是舊式的,完全要用人力去榨油,不像現在都用電。當時打的主要是花生油。
油行主持人羅乾,是慶蘭同學羅坤春[注1]的阿叔。我想,他會去那裡,可能和羅坤春有連帶的關係。雖然油行離我家很近,他卻很少回來。我也不容易有機會看到他。
跪別父母
後來,大概是一九五○年吧。幾月,我已經記不得了。銅鑼派出所叫一個給事(小弟)來家裡,要我二哥徐慶蘭到派出所走一趟。那個給事來喊了兩次。我哥都不在家。
我爸看那情形,似乎不去走一趟不行的樣子,於是就親身去油車行,叫二哥回家。回到家,他就跟我哥說:「派出所派人來找你,已經來過兩次了。不知什麼事情?」
然而,當派出所第三次來叫我哥時,就不再是那個給事來傳話了,而是兩、三個刑警親自到家裡來。當時,我想我哥本身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可是我爸我媽並不知道。
他究竟有參加還是沒有參加什麼「地下組織」,或者是牽連到其他什麼事情?他根本就沒讓我們兄弟知道。而我父母當然更不清楚。
所以,我爸我媽就跟他說:
「既然派出所喊你去,一下子就轉,你就去吧。」
我哥徐慶蘭因為我爸我媽這樣吩咐,只好去了。可他一走出大門,在門前的大禾埕上,突然就雙膝落地,跪了下來;跪我爸、我媽三次;每次跪下去就拜三下。我當時就站在旁邊親眼看到這個場面。
我哥向我爸我媽跪拜以後,就跟他們說:「阿爸、阿媽!我現在一去就轉不得了呀!以後可能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我哥他就只講了這幾句話而已,然後就跟著警察走。我則偷偷地跟在他們後頭,想要知道他們要把我哥帶到哪裡。走了約有四、五十米那麼遠的時候,我就看到他們用手銬把我哥的手銬了起來。我想,剛出門的時候,他們恐怕我爸我媽會有什麼不可預料的反應,所以不敢給他銬。一直要到離我家有四、五十米那麼遠的時候,他們馬上就把我哥銬起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事實。我一直跟到大路上,然後看著他們的身影漸漸地走遠。
後來,他們就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是否有什麼刑求、拷打的情形,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家屬也沒人可去會面。
我記得,他們離開我家的時候,大概是下午三、四點鐘左右。到了臨暗頭(傍晚),差不多五、六點鐘的時候,銅鑼分駐所的兩個刑事和一個不知什麼級位的警官卻急急忙忙地跑來我家,問我爸:
「你兒子有回來嗎?」
「我兒子?」我爸覺得奇怪就回他們說:「我兒子我已經讓你們派出所的兩、三個刑警帶去了,你們怎麼顛倒來問我呢?你們到底把他帶到哪裡去了?」
我爸這樣應下去後,他們就沒話好說了。我爸看他們說不出話來就追問:
「你們究竟把我兒子帶到哪裡去了?」
他們不得已只好告訴我爸:「我們要把他帶到苗栗去時,他跳火車跑了。」
那時候,火車燒的是石炭,走沒那麼快。從銅鑼到苗栗,離銅鑼車站大概四、五百米遠的地方,剛好又是爬坡路段,速度又更慢了。據他們說,我哥就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帶著手銬,從車門跳下去,然後逃走了。
第二天,我就親自到我哥跳火車的地方看看。我注意到那附近剛好有一條小土溝。我想,也許他跳車以後就是順著那條山溝逃走的吧。至於他是否有受傷或是沒受傷?這我就不知道了。
從此以後,家裡就一直沒有我哥的消息。跟他走得近的羅坤春也早就跑路了。連他家裡的人也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究竟我這個阿哥徐慶蘭跑到哪裡去了?實在也沒有人知道。要問也不知要去哪問。
一直要到一九五二年,過完農曆年後,我哥從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寫信回家。我們才知道他被捕了[注2],人在軍法處。收到信後,我還帶了些水果啦、雞肉等吃的東西,上臺北,要去看他。但是上來兩次都沒有被准許會面。
我後來才知道,大概是「兩條一項」[注3]的人都不能被接見。(全文未完)
注釋(本篇注釋為原注)
1羅坤春,苗栗銅鑼人,徐慶蘭公學校的同班同學;二二八事變後,因參與苗栗治安隊而被捕,在大直訓導營囚禁半年;返鄉後不久,經同學曾永賢吸收,加入蔡孝乾領導的地下黨,推動地方的農民運。
2據安全局機密資料,徐慶蘭大約是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間,與黃逢開同時被捕。
3兩條一項,意指《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凡是「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白色恐怖的掘墓人藍博洲
◎收錄於二○○四年十二月《紅色客家庄》,印刻出版。
曾梅蘭,苗栗銅鑼人,一九五二年與二哥徐慶蘭先後被捕,處刑十年。徐慶蘭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槍決,屍骨無蹤。曾梅蘭出獄後輾轉尋找數十年,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終於在臺北六張犁公墓的亂草堆下,找到了二哥的墓塚;同時挖掘到總數二百六十四個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石。
客家佃丁
一九三○年五月十九日,我在苗栗銅鑼三座屋(今竹森村)的屋家出生。
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甚至懷疑,為什麼我姓曾,而我哥徐慶蘭卻姓徐呢?其實,那是因為...
推薦序
地下燃燒[導讀]童偉格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一個掘墓人: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十三歲的曾梅蘭。為尋找二哥徐慶蘭屍塚,曾梅蘭長居六張犁山下,工作之餘,就去巡山。知道六張犁有什麼的人不少,但他們不說。沒關係,曾梅蘭等到自己夢見一叢竹頭,等到結識一位也姓徐、有點眼花的撿骨師;等到某日,撿骨師想上山採點「拐鬚」來炒田螺時,一個臺灣白色恐怖死難者的地下社會,就以徐慶蘭墓碑為原點,被他掘獲了。
另一個掘墓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生下的,「自身的掘墓人」。「消滅私有制」——多年以前,所有肩扛理想、披瀝而行的地下黨人可能都明瞭:在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現場,權威詮釋者用一句話,總括這個貴重理想的全部訴求,也宣告此外言詮,可能盡是誤解。詮釋者既斷言誤解論述的反動或空想,也判定一切企圖圍剿「共產主義的幽靈」之舊體制的必然失敗。他們不僅判定掌權的資產階級必敗,也同等嚴峻地,預言成功奪權後,無產階級之統治權力的必將自動瓦解。由此,這個理想昭然破土,為除此以外,別無憑恃的同行者,近指一個人人自由的新世界。
近指願景的理想,不時卻也高遠難及,只因也許,如《宣言》所示:當它陳明先有物質生產的自由,方有精神生產之自由時,它也以更火燙的詞,催促黨人一本精神,即刻解放物質的禁錮。當它嚮導立即行動,它卻也以更大維度的觀瞻,認定人類歷史事實上,從未真正邁開過一步:必須絕對堅硬卻炙烈,像是地核裡的鐵與鎳,才能焚盡層層次次階級鬥爭史;才能自那鐵鎳亦化的灰燼底,鍊出一個真正起點,給所有人。而「我們」,顯然都還太過軟弱與自憐。
這關於集體「真正歷史」的熱望,將怯懦有時,虛無有時的私我生命,穿蝕為恍若無明的史前逆旅。於是成為「我們」,意謂不斷自我否證,也意謂在那「固定的都煙消雲散」、「神聖的都被褻瀆」的龐然渾沌裡,尋索不滅的定向。一部實蹈夜暗的黨人史,因此總是一部精神潛行史。
多年以後,林書揚以〈曾文溪的鬥魂〉(一九九四),考察左翼精神系譜,連貫日治與戰後的步履實跡。「我」的講述,徐展大圳新行的嘉南故土,一個殖民規限下,「米糖相剋」的競作場,而複現兩代人,於同一潛抑失根苦痛的原鄉裡。舊人如父親:「終其一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也「幾乎不會走在街上鬧區」。父親以對眼下新景的刻意漠視,默記民族往歷:它嚴正的儒教理序;它溫煦的淑世舉措。新人如大表哥莊孟侯,「有機會接受現代化教育」,實踐遠更激越的抵抗行動。莊孟侯跨海返鄉,祖國同行:一個資產階級新民國,與另個新我更想望的未來國。莊孟侯銜前者之名,行後者之義,直至病逝鄉里,無緣見證身後一月,新祖國肇創於對岸。
莊孟侯末弟孟倫返鄉奔喪,跨海,更嚴密偽裝的義理同行。「雙面諜」莊孟倫,隱身保密局系統,暗助工農與學運,冒險掩護同志,直至一九五一年蒙難。多年後「我」的追探,代替只錄大名的革命史,寄存兩孟俠者,在他者記憶裡的星芒。莊孟倫陪伴同志搭船脫島,獨留荒僻海岸的送別身姿,明喻「鬥魂」原地的自持。
當祖國原地險阻,跨海,「我們」奔赴她的苦難。黃素貞〈我和老蕭的抗戰和地下黨歲月〉(二○○四),重述「好男好女」對國族之愛的真摯學習:從語言,到身赴戰場;從重重隔礙,到往復轉進;從死難同志如鍾浩東,如高草,也從倖存者同赴一九五二年「自新」現場的行蹤。整部自述,留白眾人加入地下黨的細節,而以更多細節,具現必要潛入地底的實然情感,與地下生活的艱鉅景況。地下生活,仰賴無名群眾的惜憫與護持,如鶯歌黃屋,如屏東與魚藤坪等處鄉親。他們生活的拮据,與奉獻的慷慨,黃素貞皆細細寫存,留存「歲月」裡,同難的日常。整部自述因此,亦是對光輝理想的邊廓影描:我們讀到一位妻母,在險境中猶然不息地生養,包容許多,捨離不少,卻仍譴責自己,對同志的拖累。
當莊孟倫在險境中發展組織,一九五○年夏,更年輕的「鬥魂」陳明忠被捕。陳明忠口述回憶錄《無悔》(二○一四),栩栩直陳兩度刑獄的身心實歷:以為將死的緊張中,發覺原來「人的頂門,天靈蓋上還有動脈」,會突突跳動;移監時,忘取自己留食的十顆花生米,多年後仍深以為憾,「現在還會想起這件事」;遭灌飲汽油後,晚上睡覺不可自抑地放屁,「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這些細節,反寫一位臨刑不屈的反抗者,對個人信念的堅守。陳明忠也以同樣逼真描述,重置耳聞為見歷,勾連整部《無悔》,為元氣淋漓的現場史:一個不論聖者、瘋子,叛徒或病人,盡皆同囚的無級別人間。而也許,這部見歷最寶重的,是赴難同志的體溫。如馮錦煇:將被槍決,與「我」握手道別,「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全文未完)
地下燃燒[導讀]童偉格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
目錄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 寫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出版前
童偉格.胡淑雯 編序 靈魂與灰燼
童偉格導讀地下燃燒
藍博洲 白色恐怖的掘墓人
林書揚曾文溪畔的鬥魂──莊孟侯與莊孟倫
黃素貞我和老蕭的抗戰和地下黨歲月
陳明忠口述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節選]
吳聲潤二二八之後祖國在哪裡?[節選]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節選]
林易澄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
葉怡君白堊記憶:一群五○年代「老同學」戰鬥的故事
編輯說明與誌謝
作品清單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大事記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 寫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出版前
童偉格.胡淑雯 編序 靈魂與灰燼
童偉格導讀地下燃燒
藍博洲 白色恐怖的掘墓人
林書揚曾文溪畔的鬥魂──莊孟侯與莊孟倫
黃素貞我和老蕭的抗戰和地下黨歲月
陳明忠口述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節選]
吳聲潤二二八之後祖國在哪裡?[節選]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節選]
林易澄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
葉怡君白堊記憶:一群五○年代「老同學」戰鬥的故事
編輯說明與誌謝
作品清單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大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