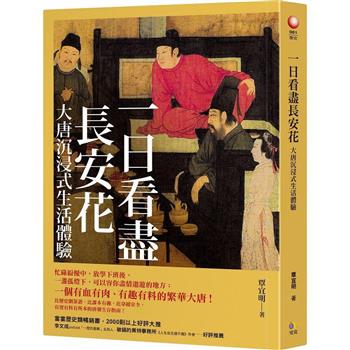原著序
生活在流行病蔓延的世界裡
─致華文讀者
原著/磯前順一
本書的日文版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世界的前一年所寫,書中內容預示了當今疫情社會狀態的到來。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在全球各國傳播,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社會結構。但本書的立場是在指出社會結構變化之上,挖掘潛藏的社會認識。
那麼,這種社會結構的特點是什麼?管見有三:一是經濟對人類生活的決定力。眾所周知,這就是卡爾‧馬克思所揭示的經濟基礎。但是,沒有什麼比這次疫情更能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經濟的自主運行力。
無法預見未來的生活使我們開始節約,並儘量不外出以避免感染。兩者都使我們的生活在經濟上變得拘謹。但實際上,我們被責令繼續促進經濟發展,以免經濟崩潰。以日本為例,儘管有感染的危險,但我們仍被鼓勵去旅行花錢,雖然收入減少了,但卻被鼓勵增加消費。每個人都清楚,這是當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矛盾。
但是,經濟活動中不會出現零增長,更不可能有負增長。我們都極度擔心經濟活動會停止。我們本來應該在學術上分析經濟自主運行的原理,但實際上由於擔心經濟垮塌而急於給經濟注入活力。
第二,以不可避免被傳染的視角來看待人類。目前,我們為了保護自己,在工作和進餐時與周圍的人儘量保持一定距離。這與原來在親密的距離內進行活動的傳統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如果回顧人類悠久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從遠古時代開始,人類的生活方式就一直是高密度人群模式,感染是無法避免的。
人體本來就存在病毒和由此產生的抗體,並且還存在一種通過在相互感染的同時產生抗體來挽救生命的系統。它揭示了人類在彼此感染的情況下只能與其他人一起生活的規律。這樣的話,當前彼此保持距離的生活方式對於以集體生活為核心的人類來說可能是致命的。
這一點引出了第三個特徵-網路對虛擬空間的擴展。人們已經看到,隨著電腦技術在社會生活中的全方位滲透,直接性的感覺開始減弱,使人們保持社會性距離的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這導致我們的社會越來越依賴電腦,削弱了以直接性感覺為基礎的群體活動。
然而,與新型新冠病毒一樣,人類通過感染而獲得抗體是作為生命體人類生活的基本原則,那麼只能通過規避手段來維持秩序的這種理想應對措施,還可能是對人類生存的致命打擊。
從此以後,經濟活動的中心將取決於電腦上虛擬實境的發展。在那裡,盡可能避免了自古以來一直作為人類社會活動基本原則的「接觸」行為。在沒有身體接觸和缺乏具體性的情況下參與到虛構的世界。在那裡甚至連性行為可能被限制,而這是人類與他人互動的根源性活動。
因為它是與他人互動的一種形式,具有較高的感染風險。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假想的現實為滿足性欲的網路消費可能會增加。向活生生的人敞開思想和身體,把委身於對方,這是一種對人類來說是最不可替代的,同時又容易導致相互受到傷害的本質關係。它可能會陷入自我幻想中。
這種生活方式的質變極大地腐蝕了人類。但是我不將此稱之為疫情後人類社會的狀態。因為這種質變正是宣告人類這一存在的滅亡。已經不會有疫情後的人類社會了。
不管人類走多遠,都會將動物性的接觸行為放在關係的主軸上。回避此行為時人類就會否認自己的身體動物性,只剩下「觀念」在電子產品上獨行。這個世界裡沒有被暴打所產生的痛苦,也沒有因「接觸」所產生的喜悅。誰期待這樣的世界呢?在這種世界中,將動物性本性作為生存核心的人能否繼續生存下去呢?人類被自己創造出來的虛擬實境之幻想所吞噬而滅亡。
曾經,法國哲學家蜜雪兒‧福柯(Michel Foucault)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佛洛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學和尼采(Nietzsche)的系譜學來提倡具有現代啟蒙主義意義的人之死問題。現代啟蒙主義的人類觀以自我意識為根據來宣導如法國哲學家笛卡爾(Descartes)所說「我思故我在」一樣的人類合理性。無意識、經濟和意識形態所規定的人類理性之脆弱性在此暴露無餘。
在這次疫情中,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變得越來越不受人類控制而失控,使在人類理性思想下無法理解的無意識幻想無限膨脹。最終否認了自己的身體狀況以及由此為起點的「接觸」社會關係。它預示著所謂「動物性的社會人之死」的到來。
最後,我想闡述一下上述世界性疫情問題與本書中討論的日本社會之間的聯繫。書中探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社會如何面對自我歷史的問題。這本書的結論之一是日本社會只關注與美國關係中的受害者身份,而從未正視在戰爭中對於亞洲自己也是加害者。
這源於在冷戰時期所建立的、巨大的國際政治陰謀。但是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不能否認這種認識使戰後日本社會對於歷史現實視而不見;也不能否認此種事實,它孕育了這種由於受害者認識而放棄戰爭的幻想。
日本社會否認現實並沉浸在自我幻想中,現在看來這種社會狀態預示了當前遭全球疫情流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除戰敗以外,還有本書所強調的兩個案例-1995年的歐姆真理教事件和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都加快了這一趨勢-沉溺自我幻想的膨脹和對現實的否認。
膨脹的日本民族主義也是表現這種自我幻想的標識之一。尤其是智慧手機的一代年輕人將自己埋沒在手機螢幕映現的虛擬實境中,以免面對國家或自己所處的艱難歷史。他們沒有實感到「自己就是自己」之痛楚,而是放棄自我,尋求一種將自己納入某物之中的舒適感。
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我們人類從中能得到哪些教訓?筆者相信,這本書值得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社會上進行翻譯和閱讀。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昭和‧平成精神史:「未結束的戰後」和「幸福的日本人」的圖書 |
| |
昭和‧平成精神史:「未結束的戰後」和「幸福的日本人」 出版日期:2021-06-07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6 |
Social Sciences |
$ 328 |
Social Sciences |
$ 360 |
歷史 |
$ 380 |
亞洲史 |
$ 380 |
中文書 |
$ 380 |
社會人文 |
$ 380 |
世界國別史 |
$ 380 |
Books |
$ 400 |
日本觀察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昭和‧平成精神史:「未結束的戰後」和「幸福的日本人」
二戰,都過了七十餘年,但日本人仍生活在「戰後」裡。「戰後」這個生活便利、物質豐富的社會,同時充滿著災難和痛苦-太宰治的絕望、哥斯拉的恐怖、力道山的矛盾、奧姆真理教的破產,以及迄今仍無法治癒的東日本大地震陰影。
面對這樣的災難和痛苦,只有側耳傾聽他者的「無言之聲」,勇於正視戰後日本社會自身的病症,才能看到那一絲絲的希望和幸福。
磯前順一教授第一部中文譯本,這是一曲與「戰後」訣別,獻給昭和、平成兩個時代的鎮魂之歌。
作者簡介:
原著
磯前順一
.1961年生於日本茨城縣。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宗教學批評理論。
.曾訪學(客座研究員)於倫敦大學、哈佛大學等,曾任波鴻魯爾大學等歐美知名大學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近代日本の宗教言説とその系譜》(岩波書店)、《喪失とノスタルジア》(みすず書房)、《ザ・タイガース》(集英社)、《死者のざわめき》(河出書房新社)等十餘部,其中多部著作譯成英文、韓文。
翻譯
馬冰
.1990年生於吉林省吉林市。
•本科與碩士就讀於吉林大學日語系,2018年取得大阪大學博士學位。
•現為北華大學東亞歷史與文獻研中心講師,碩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文化史、文化表像論。
推薦序
原著序
生活在流行病蔓延的世界裡
─致華文讀者
原著/磯前順一
本書的日文版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世界的前一年所寫,書中內容預示了當今疫情社會狀態的到來。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在全球各國傳播,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社會結構。但本書的立場是在指出社會結構變化之上,挖掘潛藏的社會認識。
那麼,這種社會結構的特點是什麼?管見有三:一是經濟對人類生活的決定力。眾所周知,這就是卡爾‧馬克思所揭示的經濟基礎。但是,沒有什麼比這次疫情更能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經濟的自主運行力。
無法預見未來的生活使我們開始節約,並儘量...
生活在流行病蔓延的世界裡
─致華文讀者
原著/磯前順一
本書的日文版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世界的前一年所寫,書中內容預示了當今疫情社會狀態的到來。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在全球各國傳播,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社會結構。但本書的立場是在指出社會結構變化之上,挖掘潛藏的社會認識。
那麼,這種社會結構的特點是什麼?管見有三:一是經濟對人類生活的決定力。眾所周知,這就是卡爾‧馬克思所揭示的經濟基礎。但是,沒有什麼比這次疫情更能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經濟的自主運行力。
無法預見未來的生活使我們開始節約,並儘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原著序:生活在流行病蔓延的世界裡─致華文讀者/磯前順一
序章:人生用來游泳,既不安全也不合適。
戰後日本社會的歸結
人生用來游泳,既不安全也不合適
本書討論什麼?
第一章 潘朵拉魔盒之「戰後」─太宰治的提問
長崎、原子彈爆炸
絕望深處有希望
信賴之賭注
叮叮噹噹
何為「戰後」
後殖民地狀態
美國的殖民地
手機地獄
《赤腳阿元》
面向戰後民主主義的叮叮噹噹
第二章 失去的語言─東日本大地震與「否認」的共同體
被海嘯吞噬
人間失格
蔓延的受災地之暗
「共...
序章:人生用來游泳,既不安全也不合適。
戰後日本社會的歸結
人生用來游泳,既不安全也不合適
本書討論什麼?
第一章 潘朵拉魔盒之「戰後」─太宰治的提問
長崎、原子彈爆炸
絕望深處有希望
信賴之賭注
叮叮噹噹
何為「戰後」
後殖民地狀態
美國的殖民地
手機地獄
《赤腳阿元》
面向戰後民主主義的叮叮噹噹
第二章 失去的語言─東日本大地震與「否認」的共同體
被海嘯吞噬
人間失格
蔓延的受災地之暗
「共...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