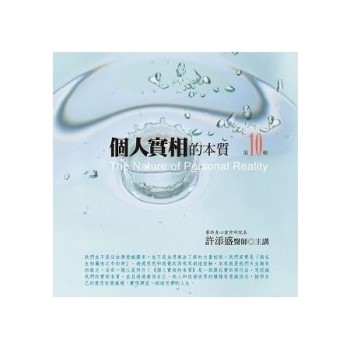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 寫對生命的照顧,即使有種種艱難
儲蓄陽光
我總是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中午十二時之前,如果沒有約定的工作,我總是在花很多時間在照顧各種生命,順序是:照顧白果貓、照顧植物、照顧房子,最後是照顧自己。早上八時或之前起來,給貓預備早餐換水清理貓砂;為植物澆水,細看它們的狀況;然後,拖地拭抹灰塵整理床鋪和房子,洗衣服晾衣服和疊摺衣服。最後,打坐和做瑜珈。11時半左右,才吃當天的第一餐。早餐後,才開始當天的寫作和各種工作。
曾經試過不同的時間表。例如,村上春樹式的凌晨四時起來,以清晨的時間為一天寫作時間表的重心,但我發現,晚睡的我,必須有充足的睡眠,早起後還有太多掛心的事。中午是一天最溫暖的時間,太陽在天空的中心點,朝東的房子會被陽光包覆著,這時份,我的精神最佳,最適合寫作。忙碌的早上,也是把自己投入一天的預備工作。如果那天要上早課,或早上有約定的工作或會面,照顧工作被迫暫停,長久下來,我便會疲累不堪或情緒不穩。有時,我會質疑自己,花一個早上照顧貓咪植物房子和自己,會否太奢侈,但我又確實知道,如果省略了每天早上的照顧日程,沉睡在身體內部的獸便會醒來,變得焦躁巨大充滿攻擊力。我本來就是個容易焦慮、緊張、擔憂和憂鬱的人,晨起至中午的流程,就像緩慢地梳毛,為貓梳毛,為植物梳毛,為房子梳毛,為自己和獸梳毛,讓自己和四周慢慢平靜下來。
平常的日子,每天都有一餐在外面吃,以免為了照顧身體而把自己弄得太累。可是,瘟疫限制了出門的次數。這幾天都自己做早餐。因為前天晚上,向友人的南涌的農莊,買了本地栽種的有機意大利生菜、車厘茄和蕃茄,於是一連兩天吃了沙律。不喜歡買現成的沙律醬汁。把蔬菜洗淨,切了,拌進橄欖油、岩鹽、黑胡椒、梅子醋,就非常鮮甜可口了。再煮一顆溏心蛋,放在上面。配一片藜麥米包。
今天是「八三一」的半週年了。外面的殘忍,並沒有因為疫情而停止,濫捕、警隊加薪又增加部門開支,屍體繼續浮在海面,被捕的人因為法庭停擺而遲遲無法審訊。因為世界沒有多餘的憐憫,才需要從內在釋出更多善意。正如,土地和陽光也沒有因為任何事的發生而停止過,蔬菜仍然能種出來,農夫也沒有因為四周黑暗而停止耕種,所以本地菜仍然持續供應。
白果從漫長的午睡中醒來時總是會跟我交流照顧身體的經驗(貓是這方面的高手)。種植善意,從照顧自己的身心開始,因為過於陰冷的體質,無法承受陽光和溫暖。
◆◆寫對香港這座城市當下的觀察
沉默的H城
有人說,H城一直都是個喧鬧,甚至粗鄙的城巿,往往以一種聲音掩蓋另一種聲音,再在這些聲音之上堆疊更多的聲音;以一種人造香精的氣味,企圖覆蓋空氣污染所帶來的混濁氣息,再在這些令人難以忍受的窒息感之上,鋪上一層聲稱以有機天然萃取精油製成的香薰噴霧;在一幢大型樓宇前,再建另一幢大型建築物,然後在大廈的外牆掛上巨大的熒幕,播放無人細看的影像,面對著一條被車輛和行人爭相使用的馬路。
不過,也有人認為,H城一直都是個沉默的城巿。作為一個從來無法自主的城巿,最初,人們有著的是一種找不到言語和表達慾望的沉默,不久後,當人們嚐到一點真正的壓迫和威嚇,城巿裡被一種逆來順受的沉默籠罩。多年後,曾經有人爭相尖叫、怒吼、辯論和呼喊,不過,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被捕,帶到法庭上,被控以失去理性、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煽動他人情緒,危害城巿安全,入獄的人多不勝數。監獄有堅實的牆壁,無論裡面發出如何凌厲的求救或哭叫,外面的人都有各種理由,聽而不聞,何況,其實所有被囚禁者,早已在進入監倉之前,把屬於他們的語言和聲音,連同所有私人物品,交給了獄吏。
我並沒有被捕,卻漸漸被一種近乎死亡的沉默,或比沉默更可怕的言不由衷所拘禁,這禁制如此幽微,任何人都可以不承認它的存在,但每個人都會感到。有時候,我渴望刺傷自己以達到痛苦,因為,皮膚和沉默相似,都有三層。表皮,真皮,皮下組織;真相,失語,謊言。我頻密地需要痛苦。安逸是沉淪。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痛苦是嗎啡,它令人得到昇華的幻覺。
◆◆◆寫自己在生活中尋根安頓的經歷
根
我會注視別人的手。如果眼睛泄露了一個人的心性,手掌的形狀則透露了一個人另一面的個性。我喜歡肥厚多肉的土形手掌。白果的手掌是一個白饅頭,我的手很小,似乎在十二歲之後,手就忘了長大,以致,我常常懷疑是手掌欠缺支撐的力量,以致無法做到瑜珈式子烏鴉式,只能更頻繁地練習樹式,通過腳掌和土地的接觸尋找植根的感覺。
別人是如何讓自己落地生根?有些人和別人組織家庭,有些人買下一所房子,有些人全副心神投注在工作賺取很多金錢。我卻常常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那天,他問我:為何要搬到粉嶺,是工作嗎?我只能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何在短短幾年之間堆積了那麼多的書和雜物,以致打包離開時,頭暈腰痠。到了搬家那天,欠缺了和白果搏鬥的力量,只是不斷敦促他自己進籠,可是他無論如何也不願進去。我只能改變方向,打算讓搬運先生先把家具和雜物搬到新居,讓白果留在舊居,我再回來接他。搬運先生們來到舊居時,白果如常嚇得躲在床底。我太疲累,忘記了一扇打門的大門是危險的。終於,搬運先生包裹家具需時,白果大概過於驚嚇,在某個瞬間從床底跑出來,衝出門口,撲向鄰居關上的閘門,我尖叫奔向他,大聲叫他不可以離家出走,但,我抓不住他,他力氣大動作快,幸好瘋子仍存留三分理性,他從我的雙手逃出來,又奔回家裡,直衝書房,我跟在他身後,立刻關上書房門。
嚇呆了的搬運先生這時才說:「幸好他跑回家,否則,這樣跑掉了很難找回來。」我點了點頭,沒有說出,我已失去過他一次。
書房門一直關著,直至搬運先生帶著我的所有行裝離開。幫忙看顧白果的朋友抵達舊居時,我對她說:「白果不去新居也不要緊,不要丟失就好。」
搬運先生開車前問我:「你不帶貓離開嗎?」我說:「會帶啊,待會再回來帶他。」他大概以為我要棄貓,問我:「不再試一次嗎?」我心裡在說:「在我所有的東西之中,貓最重要,但,現在再勉強我就會失去他。」我只是告訴他:「我待會再回去。」
那時我並不知道,當我在新居告訴搬運先生家具的擺放位置時,在朋友斬釘截鐵的吩咐和沒有迴轉餘地的催促下,白果已一邊說著各式貓粗口,一邊自行走進貓籠。然後,朋友就用我不知為何會留下的一件衣裙和一個白色宜家儲物袋,包裡籠子,帶著貓乘的士送到我的新居。我一直在想,為何這世上沒有搬貓公司,但,原來朋友就是一家只對內開放的搬貓公司。
我覺得異常感激,不知如何言說的感激,有時不順利比順利更難得,因為那突顯了,身邊所有的一切,都是僥倖而難得的存在。
然後,我去買了一個濾水器,但,回到家裡,濾水器開關的位置滲水,我想把它開啟再關上,但,已無法扭動,它自行栓塞了。絕望之下,問了幾位朋友,用了他們所說的方法,也無法扭開濾水器。只能繼續收拾,平伏自己的心情。幾天後,一位朋友,在網上找了許多資料,又買了一個傳說中的開罐器(媽咪王國有苦主表示可以打開這款常常扭不開的濾水器),從巿中心遠赴偏遠地區,汗流浹背地在我的廚房,耗了半小時,用盡各種方法,終於,把濾水器扭開,而且成功安裝,運作良好。我驚訝得說不出話。
「為何你可以堅持扭開它?」我問。在所有客觀條件之下,濾水器是打不開的。
「我沒有想過放棄,只是覺得反正都來了,就打開它。」朋友說。
開瓶,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我來說,堅持開啟一個打不開的容器,比持續寫作二十年更難。
搬貓公司朋友,和開瓶的朋友,大概都有一雙厚實的手,或許,他們都可以成功地完成烏鴉式,用雙手把整個自己舉起。
我常常都覺得自己的根無法抓住什麼,可是,每次眼看自己的船快要觸礁,都總是有人前來帶著我的船駛往另一個安全的方向。
◆◆◆◆寫發生在新聞裡的事
無愛鏈
每個人來到這世上,跟離去時一樣,都是赤條條地,一無所有地來,離去時什麼也帶不走。但,她的情況有點不同。當她被發現泡在海水中時,不但已失去生命跡象,也失去所有蔽體的衣服,那個只有十五歲,仍在急促地成長的幼嫰的身體,祼䄇、發黑和腫脹,內裡所有細胞都已枯萎。這樣的死亡,帶著太多難以言喻的訊息。
經過了大半年,死因聆訊結束之後,被裁定「死因存疑」後,女孩的母親說,希望事情盡快過去,可以恢復上班和正常的生活。在新聞中讀到這句話,忽然感到澈骨的孤寂。那不止是已逝女孩生前所感受到的孤獨,而是整個家族,從一代傳遞到另一代的深沉的孤單。一個真正無情的人,只要有著正常的社交能力,就能輕易地戴上各種情感面具,即使內心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也能隨時七情上面。許多看來冷漠無情的人,卻是因為難以處理心裡千絲萬縷的情感枝節,只能把心完全關閉起來,只要不顯露出脆弱,就不會有難過,生命似乎因而可以順遂。
有些人說,女孩的母親似乎過於冷酷,可是,為什麼人們要假設,母愛是與生俱來的本能,而不願承認,那更多是一種社會為女性設定的身份價值?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感受過足夠的愛護和安全感,也難以讓另一個人(即使那是自己的骨肉)得到深刻的溫暖和愛。
一條無愛的傳染鏈,在一個家族內蔓延,慢慢擴散到整個社會,以至城巿。
◆◆◆◆◆寫面對自我內在深處的內疚感,與目睹城市在分崩離析中的新生
中陰生活
瘟疫蔓延至不可收拾,足不出戶的時候,台灣好友S寄來了一個箱子,內裡有各式用品──不同顏色的口罩、潤手霜、海邊走走蛋捲、果醬、書和一封信。數月後,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我再次收到S的箱子,那是生日禮物,箱子裡全是我渴望但沒有宣之於口的東西。他都知道。我把箱子裡的物事一件一件地取出來,忽然,一種深深的內疚和自我厭惡感從身體深處湧出來。
把音樂盒開啟的人已離我很遠,像死去很久的蟬,只餘下半透明的蟬蛻。原來,對我懷著最深恨意和惡意的人,不是他者,而是我自己。他把音樂盒翻出來,成了我必須通過的隧道,讓我到達心裡更深的部份。
我讀到命運的脈絡,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有原因,一環緊扣著另一環。
在病毒來襲之前,城巿的空氣已瀰漫著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殘餘物,還有歪理和謊言,人們的身心便因而被鍛練得強壯了一點。苦難成了一種鋪墊。有些人把自己隔離在家裡,有些人被關進牢房裡,有些人被迫出走。但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感到,和城巿裡無數陌生人如此緊密地連繫著。
城巿在分崩離析的時候, 長出了粗壯的枝椏,這是一株特異的植物。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半蝕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半蝕
當時代是深淵,
她凝視深淵,與深淵對話
言叔夏:「『我城』自西西以來的定義被改寫。」
★ 2021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黑日》作者韓麗珠最新力作
二〇二〇年,疫情與政治改變了香港,也改變了世界。許多地方日常中斷,進入一種「半蝕」的狀態。外在的世界變得不安全——或因為病毒,或因為政治。人們發現,原本以為如陽光普照、無處不在的安全和自由,現在突然蝕去。人類正在進入一種新的生存狀態。
不是全蝕,也不是全明。
不是生來就被剝奪,而是曾經擁有,卻正在失去。
不是沒有家,而是持續不斷地失去家,失去安定感。
就像生活在地面的自己,逐漸被天文現象的暗影所籠罩。
倘若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存在狀態,人要如何在這死去中生?
韓麗珠以她敏於內省,富同理心的思索,諦觀這半蝕的宇宙。她從反觀自我寫起,也見證城市改變。當世界處在半蝕或明或暗的變動之中,她既向內也向外探測,感知個體與共同體的邊界,看見善與惡、生與死,彼此交織的羅網,城市的毀滅其實也是重生。《半蝕》從香港這個現場出發,實際上是一本寫給全世界、給經歷當下流轉變幻之人的書。
正如言叔夏說的:「《半蝕》的不易在於:在『暴政』面前,先低頭反身凝視的,先是『自己』,然後才能是『他人』。」這本書中沒有任何關於香港命運的大聲疾呼。它極度安靜,但這安靜卻使我們感到:文字內蘊的訊息進入了每一個細胞,意義被重新整理,糾結被梳開。或許,將這本書讀到最後時,會感到細胞中微微有光。外在的世界暗蝕,內在的光亮起。
★專文導讀
言叔夏|作家,東海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劉滄龍|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哲學博士,師大國文系教授)
「《黑日》與《半蝕》,以一種接近日記的體例,看似直面『現場』,真正要叩問的卻其實是人與時間、人與歷史、人與他所在的『此刻』之間的千種綰結。」——言叔夏 (散文家,東海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以日記體裁為形式的文學作品通常是私密情感的自我揭露,然而《黑日》當中的個人感受不僅具有公共的意義,而且飽含描述的力量。」——劉滄龍 (德國洪堡大學哲學博士,師大國文系教授)
★共同推薦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房慧真|作家
馬世芳|廣播人,作家
孫梓評|作家
黃宗儀|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黃崇凱|作家
董啟章|作家
廖偉棠|作家
顧玉玲|北藝大文學跨域所助理教授
作者簡介:
韓麗珠
香港當代重要小說家。2018年香港藝術發展局頒「2018藝術家年獎」得主。她的小說帶有超現實主義色彩,行文往往安靜透徹,以文學凝視超越表象的真實,在華文世界擁有跨越區域疆界的讀者。
已出版的作品有:中短篇小說集《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風箏家族》、《雙城辭典》(與謝曉虹合著)、《失去洞穴》,長篇小說《灰花》、《縫身》、《離心帶》、《空臉》,與散文集《回家》、《黑日》。
其中,《灰花》獲2009年《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獎、第三屆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風箏家族》獲台灣2008年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獎、2008年《亞洲週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獎,《寧靜的獸》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黑日》獲2021年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首獎。
章節試閱
◆ 寫對生命的照顧,即使有種種艱難
儲蓄陽光
我總是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中午十二時之前,如果沒有約定的工作,我總是在花很多時間在照顧各種生命,順序是:照顧白果貓、照顧植物、照顧房子,最後是照顧自己。早上八時或之前起來,給貓預備早餐換水清理貓砂;為植物澆水,細看它們的狀況;然後,拖地拭抹灰塵整理床鋪和房子,洗衣服晾衣服和疊摺衣服。最後,打坐和做瑜珈。11時半左右,才吃當天的第一餐。早餐後,才開始當天的寫作和各種工作。
曾經試過不同的時間表。例如,村上春樹式的凌晨四時起來,以清晨的時間為一天寫...
儲蓄陽光
我總是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中午十二時之前,如果沒有約定的工作,我總是在花很多時間在照顧各種生命,順序是:照顧白果貓、照顧植物、照顧房子,最後是照顧自己。早上八時或之前起來,給貓預備早餐換水清理貓砂;為植物澆水,細看它們的狀況;然後,拖地拭抹灰塵整理床鋪和房子,洗衣服晾衣服和疊摺衣服。最後,打坐和做瑜珈。11時半左右,才吃當天的第一餐。早餐後,才開始當天的寫作和各種工作。
曾經試過不同的時間表。例如,村上春樹式的凌晨四時起來,以清晨的時間為一天寫...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