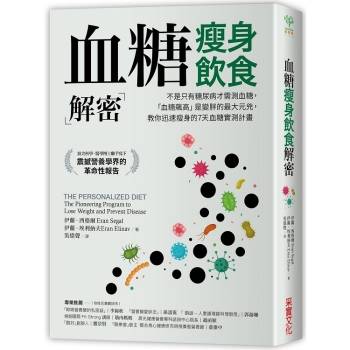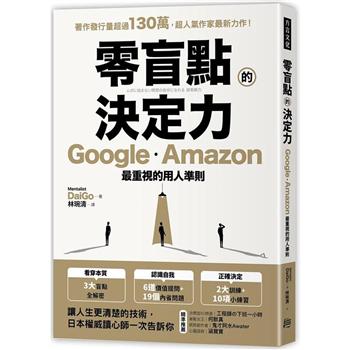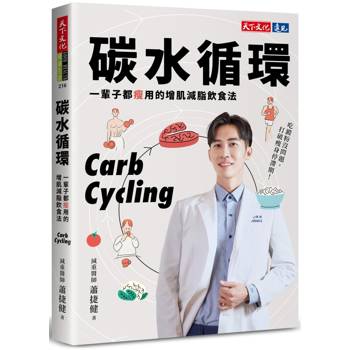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黃錦樹 / 緒論——冷戰、馬來亞化與現代主義
《蕉風》對馬華文學的重要性至少持續了三十多年,九○年代後方漸趨黯淡,面貌模糊。它創刊於馬來亞建國前,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不過六年,鐵幕拉下不過十年、冷戰正火熱。流亡的反共知識菁英嘗試在域外重建文化基地,民國殘骸落腳的臺灣之外,英殖民地香港、及有大量華人定居的英屬馬來半島,也是重要選項。
彼時,正積極朝向建國之路的馬來亞,國家意識在凝聚中,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化卻正面臨愈來愈嚴酷的考驗。雖然如此,三○年代以來華人社會內部隱然形成的「國共之爭」即便在中共建國之後,也還在殖民地星馬延續著,激烈的爭奪著文化主導權。《蕉風》創辦之年,因韓戰而甫站穩陣腳的民國臺灣,也在不久前方重啟僑教政策,吸引南洋華裔青年到臺灣,以免被中共吸引而左傾。那當然不乏文化冷戰的戰略意味,但也因此開啟了馬華文學的另類可能。遠離當地熱熾的左翼紅潮,但也難免可能受一種返祖誘惑的風險。《蕉風》的創辦則等同直接進駐到文化鋒火的前線,企圖火中取栗。它和它的對手,都是冷戰的產物;倘要談政治,沒有哪一方更高尚些。如果沒有《蕉風》和相關文化代理人的努力,很難想像,那二十多年(直到文革結束),除了濃郁的政治硝煙味,紅潮下的馬華文壇還會給我們留下甚麼。
戰後的馬華文學,不論有無國籍,都不能不考量冷戰下的地緣政治,也不能對民族國家形成後的文化政治避而不談。《蕉風》正處身在這複雜權力場中,馬、中、臺、港的華文文學(及翻譯的世界文學)在那裏交織,因此透過它,或許可以寫一部視角獨特、異於左翼史觀的馬華文學史。
處於那樣的交錯的位置,讓它在數十年的歲月裏,不得不時時嘗試回應時代的需求和挑戰。整體來看,圍繞《蕉風》的重大主題大概可以概括為幾個關鍵詞:馬來亞化(本土化)、現代性(現代主義)、文學的自主性、大眾化。重中之重的,是馬來亞化及現代(主義)。這兩者都關涉《蕉風》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前者回應的是馬來(西)亞的建國,文學的認同政治,寫作者及其作品的政治歸屬。從馬來亞化到「馬華文學的國籍」或籠統的「本土化」甚至「終結離散」,異名而同實。後者則是文學存在的理由,究竟是為了它自身(美學上的完成),還是當下(掏錢購買雜誌)的讀者。
收入本論文集的文章分別從不同的立場,時而交錯於共同或相似的議題;提供了不同的觀察視角。
《蕉風》創刊之初就直面了「馬來亞化」這「一個大問題」,林春美的〈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處理了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間,「從《蕉風》的編輯主張與輿論、編輯理念之實踐,及創作文本此三方面,探討編者作者們,對即將誕生的新興國族的集體召喚與想像」,她注意到編者大量刊用本地風光的寫作或譯作,彼時對即將到來的共同體的召喚是樂觀的;賀淑芳〈方天與《蕉風》的寫實主義書寫〉處理了《蕉風》創刊人方天本身在小說寫作上的「純馬來亞化」實踐。在短短的兩年間,方天以一個外來者身份,下鄉考察星馬各行業,以寫實的手法、適量的方言土語,生活化的對白,寫了十一篇小說,發表在自己主編的《蕉風》上,爾後結集為馬華文學史上的小經典《爛泥河的嗚咽》。這不只是和其時甚為喧囂的馬華現實主義者爭奪話語權,而毋寧是企圖在實踐上和他們徒手對決──作品才是真正的戰場。方天也由此無意中開創了一個傳統──《蕉風》的編者常同時是創作者,甚至是不凡的寫作者(白垚和牧羚奴[陳瑞獻]是兩個最出色的例子)。他們不只是有理念、鑑賞力,同時能以實作應證其理念。對讀者而言,那讓他們的主張顯得更具說服力。
關於馬來亞化,黃國華的〈蕉風、采風、食風: 論馬來亞獨立前夕物體系與國家認同的重構〉從物的再現的角度具體的考察了獨立前《蕉風》上「純馬來亞化」的具體化。南來文人的熱帶體驗,從奇花異果到異民族的風俗、飲食,也一向是竹枝詞抒寫、采風的對象。《蕉風》早期這些密集的風土書寫,南來文人身體五官感知上的初體驗,「吃風」的紀錄,和「蕉風椰雨」一樣,都是最表層最直接的「馬來亞化」。同樣的「馬來亞化」問題,鄧觀傑的論文則以編輯時間最長的黃崖為個案,一直追溯到他被令人沮喪的偏狹的國籍論擊垮為止。
「馬來亞化」問題,當然也和冷戰戰略有關。
長期致力於東亞文化冷戰研究的王梅香教授,從文化社會學和史學的角度(〈香港友聯與馬華文化生產:以《蕉風》與《學生周報》為例(1954-1969)〉),詳細疏理了《蕉風》與《學生周報》的美援背景。以那樣的背景為參照,「馬來亞化」可以說是相當精細的文化戰略,對應的是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後,南洋華人面臨的、在即將成立的新興民族國家中國籍身份的選擇。那也可說是為了對抗自有馬華文藝以來普遍存在的「雙重任務說」,也就是(如鐵抗指出的)因為華僑的中國身份,馬華文藝應同時屬於馬來亞和中國,是一種邊疆文學、地方文學,具備雙重任務。 朝向建國之路的「馬來亞化」戰略,或許即蘊含著對華人政治上的中國認同的抑制。
另一方面,因為冷戰年代的華語也因冷戰被劃分為兩個世界,「自由世界」港臺星馬是聯通的,構成一個共通的「文學世界」。在中共出版品在「自由世界」被嚴格管控後,港臺的文學資源常在《蕉風》流通,其中最重要的或許當屬現代主義,及非左翼的「世界文學」。
同樣著眼於冷戰,莊華興〈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別出心裁的把一九四九以後南下星馬的非左翼文人的文化建構統統視為「民國遺址」,流亡民國知識人的價值理念的投射,一種右翼的、流亡文化建構。這種觀點延續且深化了星馬左翼對《蕉風》和《學生周報》的長期政治批判, 那種嚴分敵我(國/共,美/中)的政治批判無疑讓冷戰在馬華文學場域內部化更形顯豁了。對左翼而言,文學不過是宣傳的工具(向大眾傳達「正確的思想信念」),「文學自身」(尤其是箇中的審美特性)不過是右派的、個人化的小資品味,是頹廢、不屑一顧的、沒有價值的,當然不值得費心經營、勞神閱讀。
然而《蕉風》一貫的立場,那被左翼激烈否定的,卻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基本條件,也是馬華文學現代性的必要條件。現代主義的引介推動正是《蕉風》最主要的貢獻之一。因此本《論文集》所收這方面的論文偏尤多。
然而,文學的「馬來亞化」和它的現代感性是相衝突的嗎?郭馨蔚認為,「純馬來亞化」退燒和臺版現代主義的引進之間不純是時間上的更迭選,而是有著因果關係,二者是不相容的(〈臺灣、馬華現代主義思潮的交流:《蕉風》的第一波現代主義〉)。該文著重談論《蕉風》中的現代主義推動、《蕉風》對港臺現代主義文學引介,從白垚的「新詩再革命」到余光中的登場。
黃琦旺的〈反叛文學運動誰反叛?談戰後馬來亞的新寫實及獨立前後《蕉風》的「現代」〉間接反駁了馬來亞化和現代(主義)的不相容,她直探馬華文學現代感性的起源,指出五、六○年代與左翼現實主義對抗中的另類「寫實」、浪漫調子所營造的馬華文學現代性,和《蕉風》創刊十年間逐步營構的「反叛文學」的現代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不難合流。馬華有自己的「本土現代主義」的可能性。
另外,幾個現代主義的重要推手都有專論。白垚,陳瑞獻(牧羚奴)、黃崖之外,被天狼星詩社奉為神祇的余光中也各有專論。 林春美的〈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和張錦忠的〈想像一個前衛的共同體:陳瑞獻與馬華現代文學運動2.0〉仔細討論了兩個最富聲名的《蕉風》編輯和作者,前者集中考察的是白垚的創作成就;後者勾勒了有多方位創作能力的陳瑞獻、憑其外語能力開啟了迥異於港臺的華文現代主義路徑。從這兩個個案不難窺見,《蕉風》長期標榜的個人主義、尊重個性、獨異的個人,方可能容許獨創性的創造。反之,左翼的集體主義、教條主義並沒有給行動者留下那樣的空間。
張錦忠和林春美也曾是《蕉風》編輯,也是出色的寫作者;或許緣於對《蕉風》的深情,讓他們對《蕉風》研究投入的心力,也比一般馬華文學研究者多得多。
相較於白垚、牧羚奴的高度現代主義路徑(菁英、小眾、不考慮讀者),鄧觀傑的黃崖論勾勒了個不同的路徑(〈大眾化、反共、馬來亞化:黃崖與六○年代《蕉風》現代主義〉),因黃氏本身的不同選擇,而顯得或許比白、牧個案更為曖昧複雜。因為這個案必須在現代性/馬來亞化之外加上另一個向度:大眾化——考量作品能不能為大眾接受。大眾化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意涵,左翼的大眾化是大眾啟蒙,為的是「覺民」,讓他們認清自身所處的被剝削、被壓迫狀態,以期被動員反抗。黃崖的大眾化是朝向另一個方向,左翼所不齒的方向——通俗化,商品化,因而向類型小說、資本主義邪惡的商品機制靠攏。觀傑同時追蹤黃崖這位「《蕉風》友聯時間在任最久的編輯」的編輯與寫作,仔細探究他對現代主義的迎拒、片面接受心理描寫卻捨棄語言與文體的實驗,以致其馬來亞化和現代主義的綜合實踐終究不免流於浮淺,而為「大眾化」所馭。這個案也可以看做是:在馬、用華文寫作而努力迎合讀者的,一個悲傷的寓言,那很容易就走上港臺、甚至民初上海通俗文學的老路,普遍流俗而淺薄。而拒絕大眾化,單純焊接現代主義和馬來亞化,一樣處境困難。菊凡、溫祥英、宋子衡這三位年輕時頗被期待的《蕉風》現代主義作者,中年後陷入的長期寫作困境充份揭示了這一點。
李樹枝的〈升起現代文藝的大纛:《蕉風》、余光中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則梳理那位對馬華文學影響最大的民國─臺灣作家長達三十年的馬華投影,這是獨一無二的,這多少也反映了華社本身文化體質的脆弱。余光中開啟的路徑既現代而中國,既中國而現代,那中國是文化中國,是江湖,當然無關乎蕉風椰雨。對開端的「馬來亞化」意圖而言,那無疑是一大反諷。在冷戰的年代,藉由臺灣海峽旁「不沉的航空母艦」,祖國幽靈還是登堂入室的回來了。那也因為,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種族主義之牆的高和厚遠超乎當年南來文人的想像,甚至危及了中文寫作的正當性。
張光達的〈當代詩作的變異及其限度〉討論的是後期《蕉風》上發表的若干詩作,它們和早已更其小眾化、邊緣化、南方化的《蕉風》本身的關係其實不那麼大。此時的《蕉風》或許就只不過是個文藝平台而已。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7 |
小說/文學 |
$ 313 |
中文書 |
$ 314 |
文化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
《蕉風》作為馬來西亞最具地位及影響力的純文藝雜誌,出版迄今六十七年,將其作為馬華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重心可說是極其適合。而本論文集即以《蕉風》研究為主軸,共收錄十二篇研究論文,分別以「冷戰與國族想像」、「編者的身影」和「交流、反叛與變異」三大主題切入,探討《蕉風》所反映出的種種議題──那些關於時空脈絡的、文藝思潮的和國族建構的。
作者簡介:
張錦忠
生於馬來西亞彭亨州,一九八○年代初來臺。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壁虎》、詩集《像河那樣他是自己的靜默》、隨筆集《時光如此遙遠》與《查爾斯河畔的雁聲》。
黃錦樹
馬來西亞華裔,一九六七年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著有論述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論嘗試文》、《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時差的贈禮》等。另著有小說與散文集多種。
李樹枝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畢業,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由島至島:余光中對馬華作家的影響研究》、《花開成塔:馬華文學論述》;編有論文集《時代、典律、本土性:馬華現代詩論述》(與辛金順合編)。
作者序
◆黃錦樹 / 緒論——冷戰、馬來亞化與現代主義
《蕉風》對馬華文學的重要性至少持續了三十多年,九○年代後方漸趨黯淡,面貌模糊。它創刊於馬來亞建國前,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不過六年,鐵幕拉下不過十年、冷戰正火熱。流亡的反共知識菁英嘗試在域外重建文化基地,民國殘骸落腳的臺灣之外,英殖民地香港、及有大量華人定居的英屬馬來半島,也是重要選項。
彼時,正積極朝向建國之路的馬來亞,國家意識在凝聚中,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化卻正面臨愈來愈嚴酷的考驗。雖然如此,三○年代以來華人社會內部隱然形成的「國共之爭」即便在中共建...
《蕉風》對馬華文學的重要性至少持續了三十多年,九○年代後方漸趨黯淡,面貌模糊。它創刊於馬來亞建國前,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不過六年,鐵幕拉下不過十年、冷戰正火熱。流亡的反共知識菁英嘗試在域外重建文化基地,民國殘骸落腳的臺灣之外,英殖民地香港、及有大量華人定居的英屬馬來半島,也是重要選項。
彼時,正積極朝向建國之路的馬來亞,國家意識在凝聚中,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化卻正面臨愈來愈嚴酷的考驗。雖然如此,三○年代以來華人社會內部隱然形成的「國共之爭」即便在中共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v ︱李樹枝 _ 前言
001︱黃錦樹 _ 緒論——冷戰、馬來亞化與現代主義
卷壹◎ 冷戰與國族想像
009︱王梅香 _ 香港友聯與馬華文化生產:以《蕉風》與《學生周報》為例(1955-1969)
035︱莊華興 _ 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
057︱林春美 _ 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
071︱黃國華 _ 蕉風、采風、食風:論馬來亞獨立前夕物體系與國家認同的重構
卷貳◎ 編者的身影:從寫實到現代
099︱賀淑芳 _ 方天與《蕉風》的寫實主義書寫
137︱林春美 _ 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
155︱鄧觀傑 _ 大眾化、反共、馬來亞...
001︱黃錦樹 _ 緒論——冷戰、馬來亞化與現代主義
卷壹◎ 冷戰與國族想像
009︱王梅香 _ 香港友聯與馬華文化生產:以《蕉風》與《學生周報》為例(1955-1969)
035︱莊華興 _ 戰後馬華(民國)文學遺址:文學史再勘察
057︱林春美 _ 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
071︱黃國華 _ 蕉風、采風、食風:論馬來亞獨立前夕物體系與國家認同的重構
卷貳◎ 編者的身影:從寫實到現代
099︱賀淑芳 _ 方天與《蕉風》的寫實主義書寫
137︱林春美 _ 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
155︱鄧觀傑 _ 大眾化、反共、馬來亞...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