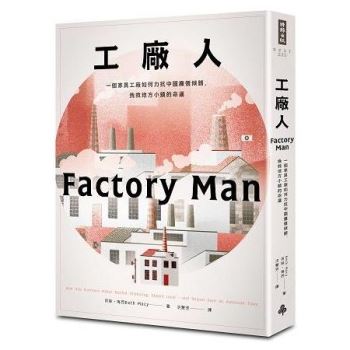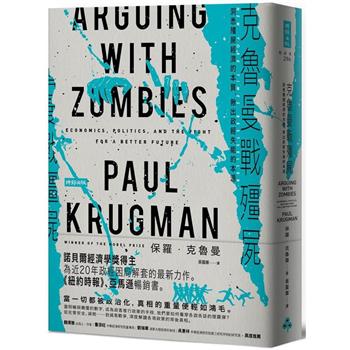即使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這一頁,仍無法翻過去。
歷史的缺頁。
這本書講的不僅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幕幕;它也是今天這個鬱悶的、壓抑的中國的寫照。——張彥(Ian Johnson)∕作家、普立茲獎得主
當代見證文學的必讀書。——Sabine Pamperrien∕作家、《柏林日報》主編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已有德法英日西等15種譯本,世界風行,是當代最重要的六四屠殺紀實文學作品。新編版除增補更多參與者的故事,力存歷史真貌,還原人的故事,更收錄藝術家劉毅「坦克人」系列作品,以撼動人心的油彩,直面歷史,值得藏讀。
本書近距離採訪了那場革命中抗爭過的人士、曾經被判入獄的人士—他們從監獄出來後,進入了一個突然疏遠了政治、左擁消費社會的醉生夢死、右抱民族主義的廉價激情的國家。正因如此,這本書講的不僅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幕幕;它也是今天這個鬱悶的、壓抑的中國的寫照。作者廖亦武,是從本土浮現出來的記錄現實中國的最出色的作家。他有點像中國的斯塔茲‧特克爾,為自己國家的歷史關鍵轉捩點編寫著口述史,但又帶著偉大的波蘭戰地記者理夏德‧卡普欽斯基的那種狷狂、無畏。廖亦武風趣、自嘲,近乎冷血地剖白自己的挫敗,這使他成了這些故事的悲憫而又可信的敘述者。
——張彥(Ian Johnson)∕作家、普立茲獎得主
廖亦武鍥而不捨地履行了他的作家職責,真實地寫作,真實地生活,他替中國民眾打破了沉默,替我們打破了中共的和平假象,因此,我很榮幸地授予他應得的、以瓦茨拉夫‧哈維爾命名的這個「打破沉默」獎。
——卡爾‧格什曼(Carl Gershman)∕美國民主基金會主席
作者簡介:
廖亦武,1958年8月生於四川鹽亭,天安門大屠殺主要見證人之一,政治犯群體中最為突出的詩人、作家、音樂家,也是西方公認的中國監獄文學開拓者。
因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與加拿大漢學家 Michael Martin Day 一起創作並製作《大屠殺》錄音磁帶,並傳播到二十多個城市,以及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而被捕,判刑四年,受盡折磨,曾在獄中自殺兩次。出獄後長期從事底層故事採集和地下文學創作,並通過「二渠道」出版了被中宣部和公安部聯合查禁的《沉淪的聖殿》、《中國底層訪談錄》。
2007年,紐約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在《巴黎評論》看到黃文翻譯的《底層》片段,立即取得全球版權。經數家出版社競爭,2008年5月該書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由蘭登書店出版,令廖亦武在西方一夜成名。彼得•伯恩斯坦評價道:「廖亦武不僅是中國當代作家中最優秀、最具挑戰性和創新的一位,更是一位勇敢大膽的有著獨立意志的人,任何時候都會捍衛自己自由言論和自由思考的權利(Liao is not only a fine writer but a courageous and brave and individual willing to stand up at every turn for his right to speak and think freely.)。」
可在中國,他始終被嚴密監控,被警察多次抄家並監禁,被搜繳手稿達幾百萬字,僅《六四•我的證詞》便重寫了三次。也曾十七次被阻止出國。2011年7月,在德國外交部長韋斯特維勒的親自幫助下,買通黑社會,走過中越邊境,從河內輾轉飛抵柏林。稍後獲得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2012年獎學金。2018年6月,德國主流媒體評選1949至2018間的傑出移民,每年一位,廖亦武被推選為2011年度移民代表。
廖亦武也是營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夫婦的主要活動家,曾利用自己的人脈和影響,不斷敦促西方各界向中國政府施壓,雖然劉曉波最終慘死獄中,但其遺孀2018年7月得以離開中國。此外,他也曾多次為李必豐、王怡、伊力哈木、王藏等獄中作家游說,呼籲,爭取國際聲援。
他的主要著作有中英對照詩集《屠城》;獄中詩集《古拉格情歌》;音樂專輯《河流或時間》;紀實文學《六四•我的證詞》、《吆屍人》、《上帝是紅色的》、《子彈鴉片》、《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地震瘋人院》等;長篇小說《輪迴的螞蟻》、《毛時代的愛情》、《鄧時代的地下詩人》、《當武漢病毒來臨》等。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近三十種外語,佳評如潮,並多次改編成話劇和音樂劇慘死獄中的諾獎得主劉曉波在2003至2007年出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期間,曾兩次應邀提名他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另一諾獎得主赫塔•穆勒也對他有同樣的提名。2019年歲末,《子彈鴉片》英文版入選全球十大人權書籍,名列第四。
廖亦武主要獲獎記錄:
Hellman-Hammett Grant獎(1995/2003)
自由寫作獎(獨立中文筆會,2007)
最佳圖書奬(美國《當代基督教》月刊,2011)
紹爾兄妹獎 (2011)
德國最佳廣播劇獎(2011)
德國書業和平獎(法蘭克福書展,2012)
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2012)
法蘭西文學和藝術軍官勛章(2013)
阿夏芬堡公民勇氣奬(2013)
抵抗詩人奬(法國Mouans-Sartoux書展,2015)
霍恩舍恩豪森獎(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博物館,2016)
瓦茨拉夫•哈維爾圖書基金會奬(紐約,2018)
章節試閱
北京
坦克人︱王維林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政權調集二十多萬解放軍,挺進並合圍首都北京,製造了讓全世界為之震驚的特大慘案。可死亡人數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以至眾說紛紜。官方發言人袁木在6月6日宣稱:經「初步統計」,死亡不超過300人。而中國紅十字會及學運組織對當時北京一百多所醫院的調查結果,計有2,600-3,000人遇難;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10,454人遇難,40,000人受傷;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至少10,000名平民遇難。
幾十個城市、幾千萬民眾捲入的幾百次街頭示威轉眼作鳥獸散。通緝令鋪天蓋地,數萬「政治罪犯」被投進監獄,還有數十萬「政治難民」逃亡到海外—這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緊接著柏林牆倒塌,東西德國合併,紅色蘇聯帝國轟然崩潰,東西方冷戰結束,人類歷史翻開新的一頁。
而在1989年6月5日上午,北京城依舊風聲鶴唳,他卻孤身一人阻擋坦克—這個渺小人類站在寬闊的長安街心與18輛以上的59式坦克對峙著。領頭的坦克試圖繞過去,可他左右跳躍攔截;坦克長隊終於剎車停頓,他乘機爬上炮塔,與露面的駕駛兵交涉片刻,然後退卻—當坦克長隊再次前進,他再次阻擋。正僵持不下,三個不明身分的人出場,清除路障一般,將他帶走。
被《戒嚴令》封鎖在北京飯店的多名西方記者,通過800米外的遠鏡頭,在樓內偷拍了這一過程。可主角下落不明。「WangWeilin」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的《星期日快報》,這是一份本土小型報,沒任何派駐北京的記者,可「坦克人王維林」這一發明創造,卻被全世界媒體廣泛借用。
十多億中國人也借用。於是「坦克人王維林」成為全國數百萬六四抗暴者的劃時代標誌。而那個真實的他姓甚名誰?從哪兒來的?到哪兒去了?這與天安門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一樣,乃至今無法破解的謎。
多數民眾認為他被秘密處決,那三個帶走他的人顯然是經過專業訓練的特務,可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多次斷然否認。另一名中共官員也表示:「我們無法找到他。我們從記者那兒取得他的名字,但用電腦檢查過後,無論是已逝世者、或遭到監禁者裡,都沒有辦法找到他。」
剩下的只能是猜測,只能是各種浪漫的想像。有人說在臺灣遇見偷渡過海的王維林,已經變成了考古學家,當談論坦克人那段歷史,如同談論沉寂的化石;有人說已經找到王維林的父母,但不願透露四處藏匿的兒子的下落。以此為素材的小說、詩歌、搖滾、藝術產品甚至廣告也源源不斷,晚近的一篇小說裡,王維林在另一星球率領老百姓起義。難怪2011年阿拉伯之春時,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在鎮壓反對派示威後,還在電視演講中引證道:「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站在坦克前面的所有人,都輾得粉碎。中國的完整和統一,高於天安門廣場那些人。」
王維林就這樣超越了時空。也許再過千百年,人類歷經一次次劫後餘生,又兜圈兒回到《山海經》時期。那時候,王維林如同挑戰極權帝國的刑天,雖被砍掉頭顱,失去了本來面目,卻仍然當街屹立,把胸膛當眼睛,把肚臍當嘴巴,張開雙臂,永遠抗爭。所以,晉代隱士陶淵明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六四畫家︱武文建
採訪緣起
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經藝術家高氏兄弟牽線,我在位於北京大山子的七九八藝術廠區內訪問了出身工人階級的畫家武文建。
天氣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紅襯衫,顯得神采飛揚。寒暄畢,高氏兄弟請吃東北菜。不用我誘導,武某就在嘈雜的飯桌邊打開話匣子,似乎早已埋下腹稿。
餐畢,覓一偏僻所在,讓武某繼續過嘴巴癮—1989年6月4日前夕,他才19歲,血氣方剛,酷愛藝術,懵懂捲入愛國風潮,卻在北京街頭目睹了一幕幕血腥,自己也差點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後,國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卻沒住嘴,所以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學生也不是精英,他就只能與動亂暴徒關一塊。「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過的底層人物一樣,沒歷史,沒社會面貌,不知該怎樣定位。」他歎息道,「16年了,沒人站出來為他們吆喝一聲,罪都白受了。」
我說:「那麻煩你牽個線,弄兩個暴徒來接觸一下?」
他說:「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關成老鼠了,認命囉。
我啞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相機,拍下武某悲憤的面孔。說實話,連我都幾乎忘記作為六四主體的成千上萬的「暴徒」們,更別提如何為他們重新定位了—文章由風雲人物來做,我每年都在海外網站上讀到不少。
直到午夜12點已過,武某才不得不安靜下來。我們在街口道別,我的懷裡揣了一沓血洗天安門的油畫圖片。武某每年都塗抹這些噩夢,卻一張也沒拿出去賣。他說:「等吧。16年都等了。」
「等吧?」我愣住了。計程車發動了,曾經作為歷史舞臺的街景紛紛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師私下說過的一段話,大意是,真到了六四平反昭雪的那一天,北京城的地縫將會突然湧出無數「英雄」。那時,我們倘若活著,就去遠方隱居,把腳下的名利場讓出來—因為死孩子的靈魂需要真正的安息。
※※※
老威:昨天見著老高,他告訴我,有個很有意思的畫家,六四栽進去,被當作暴徒關了幾年,出獄後,專畫大屠殺的題材,與這個健忘的時代搞不好關係。
武文建:我的飯碗是畫廣告,技術化的沒腦子的活兒;但我的激情還停在那兒,時光流逝了,它卻凝固成燙手的石頭,擱在16年前。我老是畫坦克壓人,血把天安門淹沒,民主女神像……畫框內的每一筆,都哇哇啦啦地喊著。這是永遠的題材,或許我畫得不好,或許應該反思反思再畫,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夢,我的手腳。這些畫,我不會賣;將來六四翻過來,我也不想賣—但願那時能建一個種族恥辱的博物館,我就把它們捐出去。
老 威:這個想法不錯,不過眼下,我們還是從頭說起吧。
武文建:從六四說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職業?
武文建:我出生於「根正苗紅」的產業工人家庭。北京地區有兩大國企,一是首鋼,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屬中國石油,地點在北京房山區,有幾十萬職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爺爺畢業於林彪任校長的抗日軍政大學,1941年就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了;我姥爺也是四幾年火線入的黨;另外,我爸,我叔,我兩個舅舅,全都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從小就受革命傳統教育:艱苦樸素,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解放全人類,軍民魚水情之類。
老威:窮棒子翻身鬧革命麼?
武文建:我家也不窮,我爺爺在舊社會上中專時,就秘密入黨。據我姥爺講,他哭著喊著,死活要上抗大,具體怎樣犧牲的,連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爺幹地下黨,被日本鬼子抓過,嚴刑拷打,背上還烙了一大塊印。由於姥爺口緊沒招,日本人也沒拿到實在把柄,所以村裡鄉親就湊了兩頭豬去慰勞皇軍,把姥爺給換了回來。我媽說,姥爺文化沒爺爺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堅定,被皇軍一嚇,膽就破了,甘願做純粹的農民。在戰爭年代,膽小自然做不了幹部。
家族就這種傳統,所以,雖然根正苗紅,父母也就是做老實工人的命。我也老實,子弟校畢業,分配到燕化後勤,學廚子。年輕人不樂意,但我爸說啦,組織叫幹啥就幹啥,不准鬧情緒。到了1989年,我剛19歲,在餐廳工作了兩年,還沒轉正。
那時我迷上油畫,專門拜了個老師;我每天瘋狂地學習,連炒菜也琢磨著繪畫,聯想著梵谷、高更、畢卡索。我不知道學潮怎麼開的頭,我對政治氣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沒幾天,我搭公車進城,去中國美術館看一個畫展。出來後逛大街,發現有許多學生在遊行,抬著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邊看了一會兒,還捐了一塊錢呢。
老威:此刻你還是一個旁觀者。
武文建:許多所謂的暴徒這時都在旁觀,也沒想到自己日後會捲進去。老 威:你具體投入是什麼時候?武文建:我一個小人物,像一顆芝麻粒掉進湯鍋,所以談不上「投入」。當時天安門還沒多少人,熱鬧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帶。而我自從做了畫家夢,就不愛上班了,只要沒事兒,就喜歡往城裡跑,豎起耳朵到處聽新鮮唄。
直到5月20號,李鵬傻屄發佈戒嚴令,部隊分幾路準備進城了,北京市民才開始起來,聲援學生。燕化也在那天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我們先在火車站集中。當時從長安街到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比國慶典禮還喧鬧,我跟在隊伍裡,很激昂,卻沒任何政治動機。許多人和我一樣頭腦單純:就是愛國,聲援學生。
老威:你參加過幾次遊行?
武文建:大概四次吧。天安門熱鬧起來後,我莫名興奮,有時進了城,就整宿在草坪上露營。5月20號遊完行後,有人說:「我們工人階級能否幫這些學生做點什麼事?」於是大夥就派我去天安門指揮部接受任務。
我是楞頭青,一挽袖子就上了。當時設了六、七道卡,可真夠嚴的。我口袋裡揣著《工作證》,一被擋住,就掏出來,哇啦哇啦解釋。好不容易進到最後一道卡,見到的所謂「指揮部」就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臺階底下,一些學生領袖裹著灰不溜秋的破衣裳,鬍子拉碴的。我當時就立在那兒,衣領歪斜,也不認識誰是誰,就大聲說:「我們是燕化工人,你們需要幫忙嗎?我們有一大幫人。」學生們把我圍在中間,上下打量好一陣兒,其中一個說:「讓我們研究一下。」
我等了幾分鐘,剛要出去,一張紙條還真遞過來了,內容是:「請你們去天安門東北角維持秩序。」署名為「高自聯常委遙遠」。
於是燕化的一百多人就去東北角維持了一宿的秩序。當時的廣場可真夠亂的,因為李鵬的戒嚴令下達後,各種謠傳蜂起,北京的市民們非但沒叫嚇唬住,反而被激發了,拿老毛的話說:「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
老威:廣場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數得清?我幾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種人性突然之間的昇華所觸動。許多老百姓自願到天安門,送水送東西。有個七十多歲的老大爺,由他兒媳婦領著,擠過來,遞上兩大包。他媳婦嚷著解釋:「我們不讓老爺子過來,他偏過來給你們送吃的,家裡攔不住啊!」
我都感動得掉淚了,那種人性的純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門了?
武文建:沒有,撐了一兩天,燕化的人還是回去了。在之後的十幾天,我只進過一次城,我待在家裡畫畫。直到6月3號晚上,我邊看電視邊畫畫,突然螢幕換了,並且宣佈「不許市民上街,不許什麼的,要採取行動什麼的。我急壞了,一夜沒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進城去。
老威:你可真夠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經作好死的準備。我打小被共產黨洗腦,相信「軍民魚水情」,所以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殺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門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車在天橋停,我下去,沿著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門,地上全是一灘灘的血。我有一張畫,就塗的這些情景,一塊血,一個圓圈—我十幾年的紅色教育就這樣全被顛覆了。
老威:還能走得通嗎?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亂。這一灘血,那一灘破爛,槍聲稀稀拉拉的。當靠近前門底下,我突然望見一大片解放軍,人人手裡都握著齊眉的棍子,就迎著跑過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個和平主義者,別看我只有19歲,卻反感扔磚頭、砸瓶子一類的過激行動。我還是願意相信解放軍—只要不被激怒,他們還是不會喪失理性。所以我就迎過去。可這時,有市民蹦出來,從我身後向當兵的扔磚頭。我急忙揮手叫道:「別打!別打!別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磚頭的轉眼跑了,我沒甩磚頭,就理直氣壯地站在原地。可說時遲,那時快,驀地從斜對面爆出一聲吼:「就這小子鬧的!就這小子嚷嚷得歡!!」我本能的扭頭,哎呀!綠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舉過頭頂,直撲過來,我渾身一麻,蹭地就竄開了。
老威:你還能進到廣場?
武文建:坦克和部隊都扎在裡面清場,進不去,只遠遠望見在冒煙。
老威:當兵的訓練有素,你能跑掉嗎?
武文建:農村兵普遍腿短,再訓練,先天不足,也跑不過我這腿長的。加上這是奔命呀,一大片綠追一個螞蚱,有一刻腿軟了,棍子頭估計是鐵的,擦著我的背樑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竄了兩米多遠,真瘋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進了一條胡同,當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塊傷,黑紫色,半個多月也沒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飛了,還記得數?估計有好幾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趕鴨子,我感覺前後左右都有人在逃。一個小伙子,只比我慢了兩三步,就被一棍兒給撂翻了,接著叫綠色蓋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發悶。我估計鐵器砸肉體都這種聲兒。
老威:你在逃,怎麼能看見呢?
武文建:我已竄入老北京火車站旁邊的胡同,見當兵的回頭,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過去了。後來當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車站裡的幾個人,才敢出來救護。我抱起那人的腦袋,與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條挺長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醫院。
老威:那人是誰?還活著嗎?
武文建:當時還有氣兒。可那腦袋已經變形,這出來一大塊,那出來一大塊。
老威:爛了?
武文建:沒爛,也沒血,可腦袋已經不是腦袋了,脹大了一倍。像有個外國畫家,專畫變形腦袋的,叫,叫培根,對,培根的作品。我摟著他,邊跑邊問:「你是哪兒的?」他還應了聲:「首鋼。」後來我們截了輛三輪板車,一路狂奔,進了同仁醫院。但見那過道上,一溜,全躺著傷員。我們把人交給兩個身上沾滿血跡的護士,就退了出來。滿腔悲憤,腦子亂極了。
老威:醫院裡躺著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過道的門口,護士就過來接人,不讓進。我繞樓一圈,感覺所有的房間都是滿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淚還嘩嘩地掉,天晚了。六月四號凌晨,銘心刻骨,我在街頭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問題,國家怎麼辦?我怎麼辦?
老威:你睡在哪兒?
武文建:前門附近的五路公車站,尋了輛公汽就上去了。車內有十幾個落難者,學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夥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麼呢?
武文建:除了罵大街,沒別的。還提到拿槍幹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車,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於熱血還在胸中蕩漾,我就找了件T恤衫,用毛筆寫上:「還我民主!還我自由!」後背還是國父孫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穿著這抗議衫在燕化廠區遊走,逢人便說城裡的情況。廠區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職工,把路都堵斷了,公共汽車開不動,連乘客也下了。大夥兒推舉我講話,根本不由我分說,許多手就又推又舉,把我弄上一輛130貨車;還嫌矮,就把我弄上轉盤旁邊的架子樓……
老威:你演講了一番?
武文建:我一乳臭未乾的小子,哪有口才?不過呼了一陣兒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罷工!罷市!」「反對鎮壓!」我還推磨一樣旋轉著,讓大家看身上的字—後來這些舉動都上了《起訴書》。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連石頭都扔不遠。
北京
坦克人︱王維林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政權調集二十多萬解放軍,挺進並合圍首都北京,製造了讓全世界為之震驚的特大慘案。可死亡人數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以至眾說紛紜。官方發言人袁木在6月6日宣稱:經「初步統計」,死亡不超過300人。而中國紅十字會及學運組織對當時北京一百多所醫院的調查結果,計有2,600-3,000人遇難;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10,454人遇難,40,000人受傷;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至少10,000名平民遇難。
幾十個城市、幾千萬民眾捲入的幾百次街頭示威轉眼作鳥獸散。通緝令鋪天...
作者序
評論
我看見子彈在你們的骨頭裡舞蹈◎余杰
認知這不堪的環境,是一種痛苦,但認知痛苦又是一種恩典。—赫塔‧穆勒
廖亦武說:「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魚翅、魚腹、微塵裡進行。」大屠殺不是6月4日那一天就結束了,大屠殺仍在進行之中,而且變得更加隱蔽和殘忍,殺人不見血,殺人如草不聞聲。廖亦武的《子彈鴉片》一書,寫的是6月4日之後,每時每刻都在「微塵」之中發生的屠殺,它不僅屠殺人的肉體,也試圖摧毀人的靈魂。對於死難者來說,「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不再苟活於這個善惡顛倒的世界,或許是一種解脫;而對於那些僥倖活下來的所謂「六四暴徒」而言,漫長的牢獄之災、酷刑、歧視與遺忘,是一個傷口不斷潰爛、痛不欲生的過程—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活著,還是死去」的疑問,有了一個答案,那就是:生不如死。
中文著述,向來是只有天下,沒有蒼生。《史記》之偉大,不是有帝王之「本紀」和將相之「世家」,而是有《遊俠列傳》這樣的篇目。《子彈鴉片》是「六四暴徒列傳」,是可以跟《遊俠列傳》相媲美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廖亦武本人是「六四囚徒」之一員,傷痕累累、噩夢連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赫塔‧米勒如此評價其人其文:「被投入集中營和監獄裡那樣擁擠而噁心的環境裡,這種近乎固執成癖的觀察習性,能讓痛苦更為錐心,每個細節都浸入了個人的色彩,把支撐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這種觀察癖也是一種恩賜,因為它包涵著人性,並支撐甚至拯救了人性。」是的,廖亦武通過為這群命運比自己更悽慘的難友作傳,拯救了歷史、拯救了人性、拯救了記憶,也為這片土地蒐尋到最後一群義人。
八九不僅是學運,更是人民革命
過去,人們通常把八九民主運動等同於學運,其實捲入八九民主運動的人群絕不僅僅是學生。
自古以來,在中國主流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士大夫居於「士農工商」四大群體之首,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詡。士大夫階層的忠順或疏離,對天下興亡的影響僅次於皇帝的賢明或昏庸。由士大夫承載「道統」的思路,左右著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從五四到六四的70年間尤其如此。五四被視為學生運動,其實五四廣泛動員了社會各階層的參與,上海新興工商階級的罷工和罷市,對北京政府的壓力遠遠大於以北京大學為主體的學生們的罷課和遊行。六四也被視為學生運動,其實數百萬上街喊出心聲的民眾,很多都是有家有口、有工作且不愁溫飽的普通民眾,學生只占其中很小的一個比例—但是,學生和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掌握了話語權,他們的聲音被傾聽、被放大。
《子彈鴉片》提供了進入那個歷史事件的另外一個視角:八九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更是一場「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是一個充滿左翼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彙,雖然我個人並不喜歡,但可以暫時借用過來:因為,從那時直到今日,中國仍未形成成熟的公民社會,廣義的中國人還不是「公民」,姑且用「人民」來概括之。
據許多親歷者回憶,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最後時刻的數千人當中,普通市民比學生更多,普通學生比學生領袖更多—大多數學生領袖都有「內線」,獲知軍隊即將開槍清場的消息,遂一走了之。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在北京開槍鎮壓之後繼續反抗的也多半是普通市民。此後,大規模的鎮壓和清洗來臨,這些普通市民大都落入羅網、無法出聲。所以,即便在反對派的敘述中,這個群體也靜默無聲。廖亦武是第一個用一本書來寫他們的作家—廖亦武本人屬於自我放逐的「邊緣知識分子」,正是這種邊緣性,讓他將目光轉向那些比他更邊緣的被鎮壓者、被凌辱者和被蔑視者。
對於學生來說,那是一次公車上書—他們選出的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前面的台階前,希望李鵬出來接受他們的上書;對於人民來說,那是一場夭折的革命—來自湖南的三個普通市民用油漆污染毛澤東像,那是六四前後將徹底的反暴政思想付諸行動的最為壯烈的一次行動。在與中共瘋狂的殺人機器對峙的那一兩天,人們忍無可忍,「忘其身以及其親」。既然中共殺人了,中共就成了人民公敵。民眾明明知道,手無寸鐵不可能打敗使用重型武器的中共軍隊,仍然決定放手一搏,不惜迎面走向死亡。廖亦武記述了若干抗暴者的回憶,硝煙、火光、血肉模糊、屍體狼藉,不忍卒讀。當過黑豹敢死隊隊長的胡中喜講述說:「『唆』的一顆子彈就擦我嘴角過去。⋯⋯我撒開腳丫子就跑,邊跑,那子彈邊『唆唆』地追我,腦袋、胳膊、腰,一陣陣『唆唆』,一陣陣麻,子彈頭射著周圍的地磚,炸起一道道火星。我的褲襠熱了,估計是出小便了。幸虧我個兒不高,目標小,撿回一命。旁邊亂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噗地噴一股,接著是一灘、兩灘、無數灘。大約有十幾個橫在地下吧,那哭那慘叫,已經不是人的聲音了。」
這樣的場景,讓我聯想到一部描述華沙人民反抗納粹的大起義的電影,中共對本族民眾的血腥屠殺,不亞於納粹對波蘭人的屠殺。中共政權是納粹的升級版,這將是對中共最為精準的歷史定位。然而,在西方,這種類比對於那些跑到中國「發大財」的政客和商人來說,是莫大的冒犯。德國是西方對中共政權最友善的國家,德國只反省作為「德國問題」的納粹屠殺,卻對作為「中國問題」的六四屠殺熟視無睹,這是怎樣一種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轉型正義」呢?
「六四暴徒」群體比學運領袖更值得關注與尊重
那些以血肉之軀與全副武裝的軍隊抗爭的,大都是單純、勇敢、熱情的年輕工人和市民,廖亦武採訪到的「六四暴徒」,當時大都只有20歲上下。幾個小時乃至幾分鐘的反抗,就改變了他們的一生。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呢?
首先,這個長期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也被海外民運有意無意地淡忘的「六四暴徒」群體,大都身家清白,遵紀守法,並非中共官方媒體所說的「一貫如此的打砸搶分子」。他們因為將反抗付諸於行動,被中共認定為「罪大惡極」,多半被判處重刑,有一部分人已經被槍殺,廖亦武採訪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緩,有的被判無期,有的被判20年,大多數坐了接近20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長刑期。比如,順手接過旁人遞過來的打火機、點燃一台熄火的裝甲車的王岩,被判無期徒刑,實際坐了16年牢;點燃一輛軍用卡車、阻止軍隊前進的張茂盛,被判死緩,坐了17年牢;從軍車上趁亂拿走兩顆子彈和一顆煙霧彈的李紅旗,被以流氓、搶劫、奪取武器罪,數罪併罰判刑20年⋯⋯與之相比,在被捕的學生領袖和普通學生當中,很少有人被判處如此之重的刑期。
其次,為無名小卒的「六四暴徒」在獄中所受之虐待,與有國際知名度的人物所受之優待,宛如天淵之別。劉曉波曾說過,他不寫六四後的獄中生活,因為他的境況不具有代表性,寫出來有可能誤導讀者,以為中共的監獄還不錯。而在《子彈鴉片》一書中,「六四暴徒」們向廖亦武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北京市第二監獄強迫囚犯生產一種出口到美國的乳膠手套,關押在此的一位名叫石學之的「六四縱火暴徒」,寫了許多揭露真相的英文紙條,塞進手套。監獄當局發現之後,石學之鐐銬披掛,之間還鎖一副土銬,被扔進兩米見方的狗洞,三個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其間,獄方多次緊急集合,強迫大夥觀摩酷刑。難友王岩看到此一場景:「這條五十多歲的漢子被一幫警察踩倒,扒光,輪番電擊。五、六根電棒齊上陣,這根卡住換那根,腋窩、脖子、頭臉、肚臍、胯下、腳心,翻來覆去過電。陰毛散發出焦臭,石學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來了。他企圖掙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地淌一地。可他沒有求饒,始終沒有求饒。」當年我在北京的家,離第二監獄只有一箭之遙。也許因為附近有監獄的「負面因素」,房價相對便宜。我卻不曾料到,就在這所「模範監獄」裡,每天都在發生這樣的慘劇。這就是中國監獄中血淋淋的真相。
再其次,最讓人欽佩的是,這批受盡折磨、劫後餘生的「六四暴徒」,即便深受虛無主義的折磨,始終沒有後悔當年挺身反抗暴政的舉動,也沒有背叛青年時代的理想。比如,當過市民糾察隊隊長的劉儀,坐了16年牢,出獄後一邊擺小攤謀生活,一邊寫文章為公義吶喊。他宣佈說:「我要像昨天那樣,站起來呼籲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們,醒醒吧,認清我們活在一個豬狗不如的麻木今天。」結果,他被警察設了圈套,本來去菜市場討要兩千元欠款,卻被以盜竊罪判刑4年。出獄後繼續販賣蔬菜水果,勉強維持生活。與之相比,那麼多身處自由世界的學生領袖,卻以背叛來營造風光與成功。比如,名字出現在通緝令上的學生領袖李錄,當年號召他人拋頭顱、灑熱血,自己卻鞋底抹油先開溜;當中共變臉成笑容可掬的權貴資本主義之後,他立即以股神巴菲特助手的身分榮歸故里,與狼共舞,不亦悅乎。
沒有多少西方媒體報導這些「六四暴徒」的事蹟,沒有多少西方人權組織幫助他們,甚至有人流亡到西方之後,因為拿不出多少收迫害的「證據」來,而在申請政治庇護的時候遭到刁難和拒絕。與此同時,那些加害者的子女,中共的紅二代和官二代,反倒輕而易舉地在西方實現了「投資移民」。
「六四暴徒」不是暴徒,乃是這個國族的脊樑。他們理應得到關注、尊重和幫助。
把英雄當小丑的人民和最幽暗、最殘酷的人性
《子彈鴉片》中最感人的部分,是這些「六四暴徒」經過漫長的刑期之後,卻發現外面的世界變化太快,他們無法適應日異月新的社會。他們感到,出了小監獄,又進入了大監獄,他們的理想成為他人嘲諷的對象。尤其是家人的冷酷與遺棄,對他們心靈的折磨,尤甚於獄中的酷刑。
劉儀第二次出獄後,來到哥嫂家,剛開始吃飯,哥哥就說他回來的不是時候,嫂子在廚房摔鍋打碗。媽媽說,要跟小兒子走,走了乾淨。嫂子說,要走,馬上走。劉儀說:「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我兩進兩出監獄,身無分文,還一把年紀。你們是怕我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賴在這屋,混吃混住,當著街坊鄰里,也掃了你們的面子。蒼天可鑑,我來此只為看一眼媽,她老人家安穩,我哪怕時運不濟,路死路埋,心裡也安穩。」結果,嫂子說,既然你們母子連心,就一起走。母子倆不得已,離開哥嫂家,再到妹妹、妹夫家。結果,妹夫說,像你這種不識時務的人,誰沾上誰倒霉。母子倆差一點流落在寒冬臘月的北京街頭。
劉儀講述的這一段讓人唏噓不已的「親人的無情」,是人性中最幽暗、最殘酷的部分。人性從來如此,「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趨利避害,嫌貧愛富。在這個信奉「成王敗寇」價值觀的國家裡,失敗者沒有任何榮譽可言。當年,數百萬走上街頭的人們,一夜之間如烏合之眾般灰飛煙滅。人們的是非善惡觀只存在於一時,而不能堅持到永遠。短短幾天之後,當這些「六四暴徒」被捕時,就有親朋告密,就有鄰里幸災樂禍地圍觀,就有警察瘋狂地拷打和凌虐以顯示對黨的忠心—這些人,在幾天之前,還是跟「六四暴徒」站在一邊的義憤填膺者。極權主義之可怕,就在於讓人民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其「共犯結構」之中。
所以,我們不能對人性抱有過於樂觀的期待。這是一個從來不會疼惜英雄的國族。反之,英雄的存在,讓庸人手腳無措、坐立不安。於是,他們樂於接受官方賦予英雄的「暴徒」這一頂「荊冠」,唯有把英雄全都小丑化、罪犯化、賤民化,這些良民和順民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當下的生活,甚至可以在這群小丑、罪犯和賤民面前展示自己的優越感。
在採訪的最後,劉儀擲地有聲地說:「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發家致富』,我不後悔。雖然我已50出頭,但身體零件都還齊全。我堅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位長期繫獄的「六四暴徒」,廖亦武採訪到的人物,只是冰山一角。但願他們不至於像孤立的水滴一樣消失在沙漠裡,但願他們都能等到轉型正義和國家賠償實現的那一天。
六四屠殺之後30年,記載這場屠殺的文學作品依然屈指可數。這是一個禁忌,更是一個傷口—誰願意不斷地用指甲將剛要癒合的傷痕摳開,讓傷口繼續流血呢?人們更希望傷口早日癒合,完好如初,然後進入新一輪的「歲月靜好」、天下太平。廖亦武戳穿了這個虛妄的假相,他的書寫構成了當代中國真正的悲劇文學。
在這個意義上,廖亦武是一名中歐人或東歐人—一點也不奇怪,他流亡德國之後最好的朋友是來自羅馬尼亞的赫塔‧米勒、來自東德的沃爾夫‧比爾曼。他們有相同的傷痛,他們有相通的心靈。廖亦武的作品,跟中國的文學傳統是脫節的,若是放在中歐和東歐的偉大的文學傳統中,反倒能夠熠熠生輝—在那裡,有卡夫卡、哈維爾、米沃什、米奇尼克、凱爾泰斯們。最有精神活力的歐洲,不在被消費主義和相對主義宰制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憐憫心」(阿倫特,臺譯:漢娜‧鄂蘭)的西歐,而在努力「將苦難轉化成精神資源」的中歐和東歐。
正是將廖亦武放置在這一思想脈絡中,廖亦武的意義和價值才得以彰顯。前匈牙利反對派哲學家諾斯‧基斯在1985至1986年間寫道:「因為人的尊嚴受到侵犯,應當抗議,不反抗將損害我們自身的尊嚴。應當抗議,這是為了將這種損害尊嚴的行為公之於世,我們能夠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不歸功於國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擁有人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力。」
法國思想史學家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在《歐洲精神》一書中記載到,在今天的匈牙利,有兩所高中以共產黨時代長期被監禁的哲學家伊斯特萬‧畢波的名字命名。在學校的牆上貼著這位思想家在上世紀三○年代末寫的一篇文章—〈熱愛自由者的十誡〉。其中第五條是這樣寫的:「永遠不要忘記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唯一的且不可分割的。」畢波在這裡用另一種方式提醒歐洲人:歐洲首先是一種責任感,而非一種命運。而廖亦武用他的書回報接納他的德國,也在用他的方式提醒歐洲人和全世界的人:對中國的暴政閉上眼睛的綏靖主義,終將反噬並且毒化你的靈魂。
評論
我看見子彈在你們的骨頭裡舞蹈◎余杰
認知這不堪的環境,是一種痛苦,但認知痛苦又是一種恩典。—赫塔‧穆勒
廖亦武說:「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魚翅、魚腹、微塵裡進行。」大屠殺不是6月4日那一天就結束了,大屠殺仍在進行之中,而且變得更加隱蔽和殘忍,殺人不見血,殺人如草不聞聲。廖亦武的《子彈鴉片》一書,寫的是6月4日之後,每時每刻都在「微塵」之中發生的屠殺,它不僅屠殺人的肉體,也試圖摧毀人的靈魂。對於死難者來說,「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不再苟活於這個善惡顛倒的世界,或許是一種解脫;而對於那些僥...
目錄
卷首詩:二次屠殺
英文版序言:永遠的激勵—Ian Johnson(張彥)
德文版導讀:無聲者的聲音—Sabine Pamperrien
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橋
北京
坦克人王維林
六四畫家武文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7 年)
街頭勇士王岩(縱火罪,無期徒刑)
行為藝術家余志堅(反革命破壞、宣傳煽動罪,無期徒刑,2017 年 在流亡中病逝)
死刑犯張茂盛(縱火罪,死緩)
死刑犯董盛坤(縱火罪,死緩)
六四父親吳定富(兒子吳國鋒被虐殺於北京街頭) 市民糾察隊長劉儀(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兩次判刑,共 14 年)
黑豹敢死隊長胡中喜(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刑 10 年)
街頭勇士李紅旗(流氓、搶劫、奪取武器,數罪並罰,判刑 20 年)
街頭勇士王連會(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無期徒刑)
良心犯李海(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 9 年)
最後的六四囚徒苗德順(縱火罪,死緩)
四川
同案犯李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 7 個月)
獄友蒲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10 年,2002 年病逝)
獄友許萬平(反革命組織罪,三次判刑坐牢,共 23 年)
獄友楊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3 年)
獄友雷鳳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12 年)
獄友侯多蜀(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8 年)
馴獸師陳雲飛(尋釁滋事罪,判刑 4 年)
良心犯佘萬寶(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次判刑,共 16 年)
詩人李必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次判刑坐牢,共 22 年)
詩人廖亦武(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4 年)
後記
劉曉波的最後時刻
瓦茨拉夫‧哈維爾圖書基金會 2018 年「打破沉默」作家獎頒獎辭
為台灣民主基金會「紀念劉曉波」的活動致辭
附錄
二○五位大屠殺死難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群體蒐集
四十九位大屠殺傷殘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群體蒐集
真相說明書—丁子霖、蔣培坤
歲末尋訪—丁子霖、蔣培坤
蔣捷連蒙難記—丁子霖、蔣培坤
送別兒子—丁子霖、蔣培坤
送別丈夫—丁子霖
2011:六四抗暴者還在獄中—孫立勇
出獄一百天—劉賢斌
評論
我看見子彈在你們的骨頭裡舞蹈—余杰
卷首詩:二次屠殺
英文版序言:永遠的激勵—Ian Johnson(張彥)
德文版導讀:無聲者的聲音—Sabine Pamperrien
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橋
北京
坦克人王維林
六四畫家武文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7 年)
街頭勇士王岩(縱火罪,無期徒刑)
行為藝術家余志堅(反革命破壞、宣傳煽動罪,無期徒刑,2017 年 在流亡中病逝)
死刑犯張茂盛(縱火罪,死緩)
死刑犯董盛坤(縱火罪,死緩)
六四父親吳定富(兒子吳國鋒被虐殺於北京街頭) 市民糾察隊長劉儀(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兩次判刑,共 14 年)
黑豹敢死隊長胡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