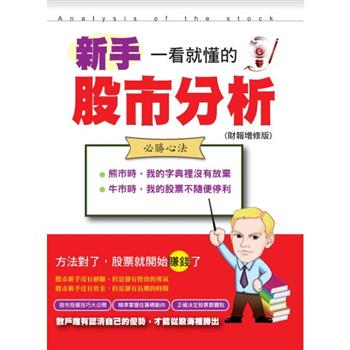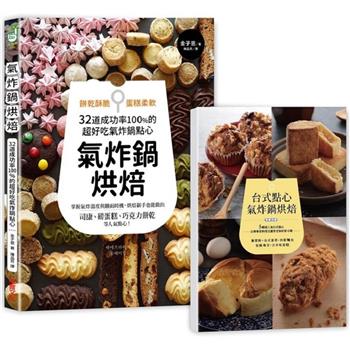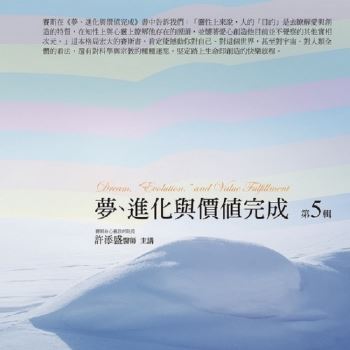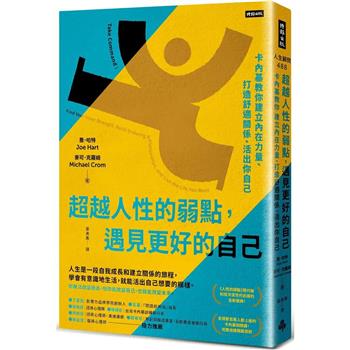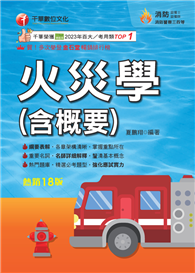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眺望時間的盡頭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眺望時間的盡頭 作者:布萊恩.葛林|Brian Greene|蔡承志 出版社:鷹出版 出版日期:2021-03-31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455 |
物理\化學 |
$ 514 |
宇宙/天體 |
$ 514 |
物理學 |
$ 514 |
NatureScience & Mathy |
$ 514 |
NatureScience & Mathy |
$ 572 |
中文書 |
$ 585 |
科學‧科普 |
$ 585 |
讀書共和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甫出版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世界知名物理學家暨暢銷書《優雅的宇宙》作者
再次推出扣人心弦著述,探索悠遠的時光以及人類對目的的追尋。
很少有人能像葛林這樣同時精擅最新宇宙科學及散文書寫。
——《紐約時報》(2020年度精選好書)
《眺望時間的盡頭》是布萊恩•葛林新推出的宇宙壯麗探索紀實,論述我們面對這片無垠浩瀚如何投身追尋意義。
葛林按照宇宙生成的時間軸,探索是什麼樣的自然原理,在這處注定衰敗的宇宙中,催生出了從恆星和星系,再到生命和意識等種種有序結構:從大霹靂起到物質生成,從物質生成到生命出現,從生命到意識萌現,直到宗教、科學、藝術、創造力、想像力的湧現,到最終包括意識在內一切歸於無有,終至消逝,宇宙回歸寂靜冷清的原子游離狀態……
葛林以高度清晰的文字,溫柔熨貼地梳理古往今來哲人、詩人、科學家,針對每一個過程想要理解的嘗試,書中含括各種理論和視角,揉捏成宇宙科學大歷史的高明書寫。從粒子到行星,從意識到創造力,從物質到意義,葛林讓我們所有人都能掌握並品賞我們在宇宙中轉瞬即逝,卻也精緻之極的須臾時光。
全書以物理定律貫穿,差別地對待所有原子、分子、生命和你與我。第三人稱的外部科學觀察,加上第一人稱的內在思索,將個人歷程、科學理念、概念與事實交織匯集。作者論述時大量運用類比和隱喻,以非技術用語來解釋所有必要的觀點,特別艱澀的概念以簡短摘述代之,讓只具最粗淺背景的讀者都能一路跟隨不致迷途。
這是一趟以科學為動力的旅程,路途上由人性賦予重要意義,也成為一次充滿生機的豐富冒險的源頭。人類身為宇宙中唯一有意識的生物,得以超脫必須身處當下的束縛,將自己視為在過去未來的開展歷程的一部分。知道生命有限,這生存的領悟讓我們必須應付死亡帶來的張力,讓我們在有限時光中碰撞出最激烈的生命火花,希望探知生存為何重要、價值和意義問題,這就是這本書給予宇宙、萬物、人類這些須臾存在的最高禮贈。
作者簡介
布萊恩•葛林(BRIAN GREENE)
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暨數學教授,擔任該校理論物理學研究中心主任,並以超弦論開創性發現著稱。他的著作包括《優雅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宇宙的構造》(The Fabric of the Cosmos)以及《隱遁的現實》(The Hidden Reality),三本書都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累計達六十五週,全球銷售量超過兩百萬本。他還主持了兩個根據他所寫書籍拍攝的NOVA迷你影集,並分別贏得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與艾美獎(Emmy Award)。葛林和製作人崔希•戴(Tracy Day)協同創辦了世界科學節(World Science Festival)。目前住在紐約。
譯者簡介
蔡承志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碩士,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得主。1994年起業餘投入科普書翻譯,1999年轉任全職迄今,期間也從事Discovery頻道字幕翻譯三年。累計作品八十餘本,包括:《星際效應》、《好奇號帶你上火星》、《無中生有的宇宙》、《時空旅行的夢想家:史蒂芬.霍金》、《大人的物理學:從自然哲學到暗物質之謎》、《詩性的宇宙》、《大轉折:百年科學匯流史》、《伊波拉浩劫》、《下一場人類大瘟疫》和《最後一個知識人》等。
| |||
| |||
|
|

 2022/01/07
2022/01/07 2021/09/15
202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