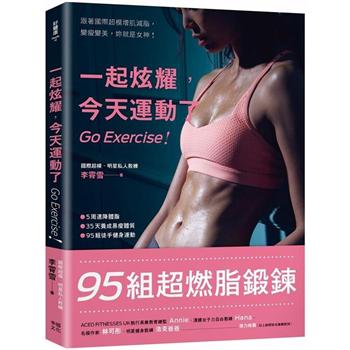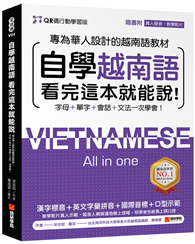圖書名稱:克蘇魯神話 II:瘋狂
原版全系列銷售突破100萬冊!PTT鄉民熱烈討論!
隨手翻開一個故事,喚起你內心深處未知的恐懼
20世紀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恐怖小說體系
眾多恐怖電影、遊戲、文學作品永不枯竭的靈感根源
史蒂芬‧金、尼爾‧蓋曼、伊藤潤二、虛淵玄……多位大師皆是克蘇魯的信徒!
《怪奇物語》、《魔獸世界》、《異形》、《星際爭霸》、《蝙蝠俠》、《Fate/Zero》、
《神鬼奇航》、《異塵餘生》、《沙耶之歌》、《血源詛咒》、《Dota》、《詭屋》、
《鋼之煉金術士》、《爐石傳說》、《襲來!美少女邪神》……
全體排隊向克蘇魯致敬!
【本書特色】
★ 超豪華繁體中文精裝版,精選美術紙及書名華麗燙金,華麗大器,經典必收!
★ 《魔獸世界》官網認證插畫師親手繪製絕美書衣插畫!
★以《死靈之書》概念打造,輔以各式資料圖像、崇拜符號、召喚咒語等超豐富克蘇魯元素!
★ 克蘇魯資深信徒姚向輝精心翻譯,淺顯易懂,台灣書市最流暢最易讀版本!
★克蘇魯神話體系最佳入門、進階全解鎖首選!
本書收錄口碑最好、呼聲最高的4部經典中短篇小說,克蘇魯神話體系入門最優起點!
〈瘋狂山脈〉:米斯卡托尼克大學教授領軍考察隊前往南極洲進行科學研究,就在一支探勘小隊挖掘出怪異的「軀幹頂端淺灰色膨大頸部,帶有類似魚鰓構造,頸部支撐著黃色五角海星形狀頭部,其上覆蓋色彩繽紛的堅韌纖毛」古代生物遺骸後,小隊成員便全數消失。教授與飛行員只好趕赴調查,卻意外發現一座充滿詭異氣息的魔山,其中有古老遺跡,還有潛藏於瘋狂山脈另一側的不可名狀的終極恐怖……
本篇故事劇情影響諸多科幻電影,如《異形》、《突變第三型》。
〈瘋狂山脈〉更是《水底情深》(第90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羊男的迷宮》、《環太平洋》等片的金獎導演吉勒摩.戴托羅多年來想拍成電影的夢幻之作。
〈牆中之鼠〉:艾克漢姆隱修院坐落在一座史前神廟的遺址上,下層地窖裡從依然清晰的銘紋中能辨認出羅馬時代嚴禁的大母神(Magna Mater)的文字符號,相傳此地是舉辦無可名狀的祭典之處。繼承祖傳凶宅的主角按照中世紀風格重建隱修院,內部結構重新建造和購置煥然一新,卻保留了原先的牆壁。有一天僕人抱怨說家裡所有的貓都躁動不安,但卻沒聽到任何其他聲響。當天晚上主角由老黑貓陪伴下睡著,半夜黑貓猛然驚起,繃緊身體,目光灼灼地盯著窗戶以西牆上的一個壁毯位置,然後他聽見從壁毯後傳來老鼠飛跑的細微而獨特的聲響……
1995年電影《衰落的城堡》是依據這篇〈牆中之鼠〉和另一篇作品〈異鄉人〉製作的。
〈印斯茅斯小鎮的陰霾〉:主角為慶祝成年,進行一趟觀光、訪古和追溯家族譜系之旅,從古老的紐伯里波特前往阿卡姆,途經對被陰霾籠罩的印斯茅斯小鎮一探究竟,卻發現所有街道上都見不到任何活物,貓狗徹底絕跡,鎮民們到一定年紀會開始出現「印斯茅斯臉」特徵——向外突出的水汪汪大眼睛,頸部兩側很深皺紋,鼻樑扁平,前額和下巴向後縮,耳朵特別滯後,長而厚的嘴唇和毛孔粗糙的暗灰面頰上幾乎沒有鬍鬚,臉像皮膚病般的脫落表皮——再加上當地的惡魔崇拜傳聞興起的大袞密教,夜晚怪聲破門以及怪型人影匯集河流出海口的魔鬼礁,邪惡陰霾籠罩、充斥死亡和瀆神怪物的海港……
本篇劇情曾被改編為2001年西班牙電影《人魚禁區/異魔禁區/達貢》(英語:Dagon;西班牙語:Dagon: La Secta del Mar)。
〈超越時間之影〉: 1908年5月14日上午10時20分,奇特的遺忘症降臨在一位教授身上。當時他正向學生教授政治經濟學,眼前出現怪異形狀,彷如置身奇特房間,然後癱坐昏迷不醒。時間過去五年四個月十三天他才醒來,卻遺忘從前身分換了一個人以『第二人格』生活,花大量時間重新學習使用手腳和身體,如饑似渴地汲取各種各樣在歷史、科學、藝術、語言和民間傳說上的資訊,直到一天有個瘦削黝黑的外國人來到他家後,隔天他恢復到原本教授的記憶卻完全忘記『第二人格』的記憶——就像被切開大腦拿走似的,而類似的遺忘症在這世上並非只有他一個……
美國知名克蘇魯神話創作者、研究者林‧卡特更將本篇〈超越時間之影〉譽為洛夫克萊夫特「小說中最偉大的成就」,他說:「宇宙驚人的浩瀚範圍和宏大感,打開的時間峽谷,以及敘事的巨幅鋪陳」。
*
假設你的腳邊有一隻螞蟻在爬,你不會在意有沒有踩死牠,因為牠太渺小了,是死還是活,對你來說沒有分毫影響。在「克蘇魯神話」中描述的遠古邪神的眼中,人類就是那隻螞蟻。
洛夫克萊夫特所宣導的「宇宙主義」,即人類遠非世界的主宰者,在尚未探索的未知宇宙中,隱藏著超乎想像、不可名狀的恐怖真相,只是見上一眼就能讓人陷入瘋狂或者死亡。正如作者本人所述:「人類最古老、最強烈的情感是恐懼;而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是對未知的恐懼」。
「待在瘋狂山脈背風的陰影之中,你必須管好自己的想像力。」
繁星已經抵達特定的位置,舊日支配者即將重現人間。
**作者簡介
霍華‧菲力普‧洛夫克萊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H.P.Lovecraft)
(1890—1937)
1890年出生於普羅維登斯安格爾街194號。
3歲時父親因精神崩潰被送進醫院,5年後去世。
14歲時祖父去世,家道中落,他一度打算自殺。
18歲時深受精神崩潰的折磨,未及畢業便退學。
29歲時母親也精神失常,2年後死於手術。
34歲時結婚,但婚後生活並不幸福。妻子的帽子商店破產,身體健康惡化。他因此陷入痛苦與孤獨,5年後離婚。
一貧如洗的他回到家鄉普羅維登斯,將所有精力傾注於寫作。然而直到46歲被診斷出腸癌,他的60篇中短篇小說終究因為內容過於超前,未能為他帶來名利回報。次年,他在疼痛與孤獨的陰影中死去。
今天,洛夫克萊夫特和他筆下的克蘇魯神話,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古典恐怖小說體系,業已成為無數恐怖電影、遊戲、文學作品的根源。
譯者簡介
姚向輝
又名BY,克蘇魯資深信徒,四處「發糖」。譯作有《教父》、《七殺簡史》、《漫長的告別》、《馬耳他之鷹》、《克蘇魯神話I ~ III》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