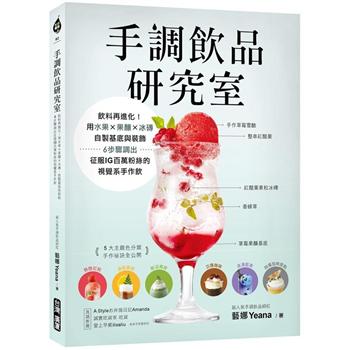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羊道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80 |
散文 |
$ 280 |
文學作品 |
$ 300 |
現代散文 |
$ 316 |
現代散文 |
$ 316 |
散文 |
$ 316 |
Books |
$ 316 |
中文現代文學 |
$ 352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羊道
暢銷作家李娟雋永清靈的游牧紀事
從南面的荒野沙漠到北面的森林草原,綿延千里的跋涉,比世上任何一種生存方式都更深入大地,依從自然的呼吸韻律,憑恃著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
作家 陳雪、凌性傑
資深媒體人 陳浩
真情推薦
暢銷作家李娟最膾炙人口的《羊道》三部曲──《春牧場》、《前山夏牧場》、《深山夏牧場》──第二部作品,記錄李娟與哈薩克牧民共同生活,踏上牧羊古道的真實紀事。
哈薩克牧民是世界上最後一支純正的游牧民族,他們騎在馬背上,領著駝隊,趕著羊群,沿著世代傳承的古道,逐水草而居,度過大自然與人生的四季。
李娟隨同哈薩克族的扎克拜媽媽一家,展開游牧生活,歷經寒暑,遷徙流轉於戈壁沙漠與阿爾泰山區,深刻體會這支古老民族面對大自然殘酷考驗所展現的恬淡堅韌。
在羊道上,世界很大,時間很長,而人很渺小。
「我們這顛簸在牧道上的家,任由生活的重負如鏈軌車呼啦啦輾過,毫不留情地輾碎一切脆弱與單薄。剩下來的,便不只是堅固耐用的物事,更是一顆顆忍耐踏實的心。」──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