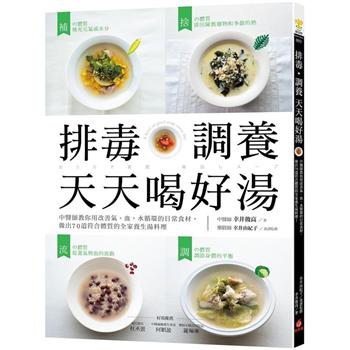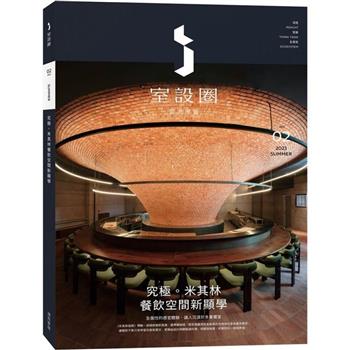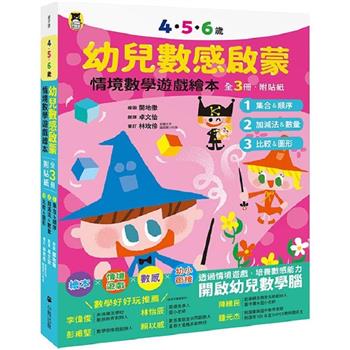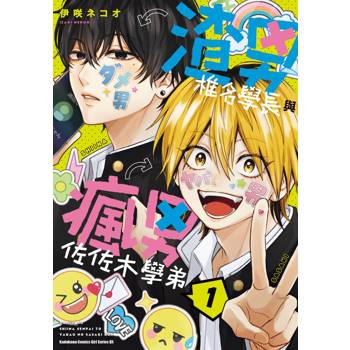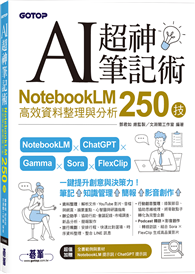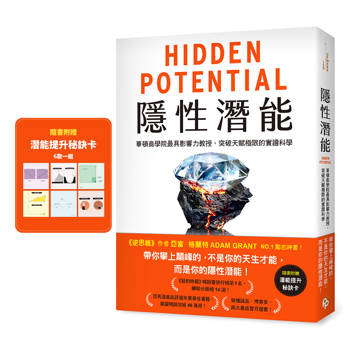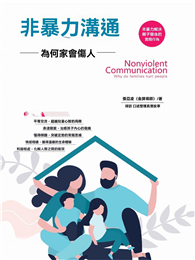誰駭怕寫作
我知道要是不一直寫我就會死,因為寫作就是冒險,而唯有藉由冒險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活著。
加拿大作家愛特伍(M. Atwood)語
寫作,對許多人來說,就像面臨突然掉落眼前的一塊燙手山芋,除了自己不敢承接,還會想辦法推給別人,讓對方去為它傷腦筋。
情況不就是內部要編刊物了,稿子卻遲遲出不來,一問才知道連倡議的人也在逃避責任。他總是說:「我出點子,你們去寫呀!」至於鼓吹大家到外面投稿,那就會看見有人提早把門關上,免得你闖進來逼他動筆寫東西。因此,上引愛特伍的話,就顯得戲謔成分濃厚,畢竟世上絕大多數人都是當寫作比死還痛苦,他們才不要冒這種險。
那麼大家為什麼會駭怕寫作?這說來包括常寫作的人在內也不能免俗,一樣有恐懼的時候。好比德國作家曼(T. Mann)和法國詩人范樂希(P. Valéry)所分別說過的「作家就是比別人更覺得寫作很難的人」和「我,假如被人強制寫作,寧願自殺」,前者不啻是在暗示當了作家才曉得寫作不容易;而後者也無異是在警告他人別妄想迫使詩人一定要量產。可見駭怕寫作或駭怕無止盡寫作,是大家共同的心理,不能單獨責怪某些人缺乏一寫的勇氣。於是「為什麼會駭怕寫作」這個問題,就得轉成「怎樣才不會駭怕寫作」,方有「指出向上一路」的積極意義。
換個角度看,「駭怕寫作」是根本性的問題,而「不駭怕寫作」則是克服「駭怕寫作」的恐懼後始出現的,已經晉升到了另一個層次。以至還是要回到初次而一窺大家駭怕寫作的原因,才能進一步對比找到不駭怕寫作的良方。
這不妨以飲食作類比。我們知道,人通常不會無緣無故吃東西,倘若不是為了生理需求,就是為了修補機能或健體美容,總是有理由才把食物送進肚子裏。但這到了絕食或自我禁食該一特殊狀況,為某種原因而進食卻成了不可思議的事。也就是說,無法吞嚥或修行辟穀的人,他們是無所謂進食,甚至會駭怕進食。這不就像極了寫作?如果你不知道「為誰而寫」,那怎麼可能激起寫作的欲望,終而還會樂此不疲的深愛上寫作?
由此可知,大家所以會駭怕寫作,就是還沒體認或找到寫作的目的,彷彿船隻在茫茫大海中失去方向,恐懼心理自然會油然而生!反過來,有了「所為寫」的對象,那筆底必定有源源不絕的東西跑出來。試想一個提筆就皺眉頭的學生,在遇到應罰寫悔過書的時候,他會不會窮盡所能寫對自己最有利的話?而一個點逗文字始終有困難的人,心血來潮寫信要向朋友討錢,他可不可能突然筆底生花似的儘想些好聽的詞語?這些都是在了解為誰寫作後,剎那間忘了自己不再駭怕寫東西。同樣的道理,任何人想從作文的挫折或頹敗中奮起,在首關上也得確立或搞清楚到底要為誰寫作。
當寫作不再造成心中的鬱結後,第二級序的問題就是「要寫些什麼」。這最具臨場性,也是考驗一個人能否持續寫下去的一大關鍵。換句話說,駭怕寫作的恐懼化解了以後,接下來就是等著自己從百無聊賴中反身喜歡上寫作一途,而這就得熟悉「有什麼東西可寫」。
有什麼東西可寫,基本上不可能憑空設想,它還得從經歷生活、勤快閱讀和精鍊研思等途徑來擷取資源,那一枝「彩筆在握」的事實才可能成真。所謂「成功沒有捷徑」和「我們透過寫作,發現自己的想法」等為美國作家哈瑞爾(L. Harrel)及蒂蒂安(J. Didion)所說的話,就是在不同層次上證成這一說法。後者是說,當你有了東西可寫後,寫作就會像滾雪球那樣越來越可觀,也越來越欲罷不能,因為你每寫一次就誘引出新的靈感,而讓你寫到手軟也停不下來。
在經歷生活、勤快閱讀和精鍊研思中,勤快閱讀於理上是居優先地位的。由於一般人所能經歷的生活有限,而想精鍊式的研思也多半要在題材出現後才會跟著到位,致使勤快去閱讀以獲得各種資訊也就變成最見迫切的需求。因此,閱讀就不只像德國作家布呂因(G. de Bruyn)所說的是為了「能夠過別人的生活」而已,它更重要的是可以成就法國作家沙特(J.P. Startre)所說的「一場自由的夢」,從而恣肆醞釀無限的創造力。
顯然在一個人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足以充實寫作的內容時,他原先駭怕寫作的感覺仍會急速翻湧上來。而向來傳言的所謂「詞窮」或「文思枯竭」一類困境,就是指事到臨頭才發現詞不達意或手感欠佳,以至於寫不到終了。俗話說「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在寫作一事上更容易得著證實。
說實在的,胸無半點墨的人,很難想像他在寫作路上有能耐盡情的馳騁。而這也形同是在提醒大家:你不多讀些書,即使搞清楚了要為誰寫作,也會因為腹笥窘澀而不得不戞然中斷,導致最後無法避免要以「終究不能成篇」的更深遺憾收場!
能寫就是王道
暴君並不怕嘮叨的哲學家宣揚自由的思想,他只怕一個醉酒的詩人說了一則笑話,吸引了全民的注意力。
美國作家懷特(E. B. White)語
有了明確為誰寫作的概念後,駭怕寫作的恐懼指數固然會減少;而經由廣泛閱讀的途徑,實際採取行動去寫作的機率也會大增,但這些都還沒有觸及一個更優位的前提,就是「有什麼理由要去寫作」。
世上儘管有人全年不休的在文字海裏泅泳,也產出了數量或質量可觀的作品,但仍有更多人還在岸上徘徊。他們不是觀望不前,就是淺嚐後又縮手,馴致在此空有勸人寫作的好意。這又是什麼緣故?換句話說,為何明知寫作的心理機制可以啟動了,卻又猶豫不決,甚至依舊要望寫作而興嘆?究竟是那種障礙尚未排除,或者還有什麼心結沒有打開?
這很有可能是基於「經驗法則」。正如一名天文學家在看一支兩百英吋長的望遠鏡,突然驚呼快下雨了。他的助理問說:「你怎麼看出來的?」天文學家回答:「因為我的雞眼痛。」只要你直覺寫作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有可能像該天文學家那樣懶怠於精確探測下雨的原因,而草率的把寫作一事拋在腦後。
此外,不覺得寫作有高度價值的人,也會提不起勁向寫作大業進軍。所謂「在守財奴眼中,金幣比樹還美麗」,英國詩人布雷克(W. Blake)說的這句話,恰巧可以藉來想像不寫作的人心中也還有更為迷戀的東西,如果傾向寫作,他就得犧牲其他能夠立即見效的物事追求。
除了經驗法則,就當數有關寫作的「先天理則」被嚴重的忽視。這是說人類的文化所以能夠創造累積,幾乎是靠寫作完成的,而在一個人還懵懂於這一道理或短少於自我啟蒙,他就不了解寫作可以「終身許之」或「戮力以赴」的深刻意義。
德國詩人賀德林(F. Hölderlin)說:「活著,就是在捍衛一種形式。」這形式的認定,或許會因人而異(如把它視為是競爭權勢或富足的物質生活或追求愛情),但總不及透過寫作來建構知識或創發文學那般值得人叨念;一旦錯過了親身去體驗的時機,就只好看著別人風光過一生。
也許有人會舉出其他事業有成的例子,而不相信這套說詞。但我們也得知道,倘若沒有寫手為那些名人撰稿傳播,或者他們自己委託作家替他們立傳,那麼他們想將「經營之神」或「政績卓著」一類的美聲宏揚於外,就機會渺茫了。因此,回返源頭,把寫作一事擺在最高位置,而孜矻且不懼折騰的迎向前去,也就可以使此生了無遺憾!因為寫作就是來人間走一遭天理所許的最大任務;而能寫作的人,就是王道。
相對於霸道,王道是一條不必瞻前顧後的康莊街衢。它儘管大膽或坦蕩蕩的去釋放魅力,而毋須像前者那般想出頭還得遮遮掩掩一番。大家知道,有錢有勢的人,常常會目中無人。他們不是以威權凌駕別人,就是不願跟凡眾為伍,心中橫梗著古來勢利人所見那種不討喜的邪辟觀念,隨時在伺機出動而巧變奪取多餘的利益。而這在以寫作為生的人那邊,縱使偶爾也會歧出去唆使讀者或誅伐貽誤他人,但大多時候他只能敞開文字世界迎接各種納拒的考驗。而從能夠恆久製造驚奇或供人掘發嘆賞一點來看,寫作就真的是可以榮耀加被的王者事業。
哲學家笛卡兒(R. Descartes)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這經過調整後將它改成「我寫,故我在」,就更貼切了。因為「我思」還在腦海塑形階段,只有到「我寫」後才有完整成品,而足夠用來確立自己的存在樣貌。在這種情況下,寫作而展現另個哲學家柏拉圖(Plato)所意示的「會說故事的人,將統治社會」那一形貌,那麼一個王者氣象的獨造成就不就儼然成形了?
再說,如果把「王道」從前面的名詞性換作動詞性,那麼這又會激起我們在寫作路上鍥而不捨且一直精進的勇氣和毅力。誠如一則阿拉伯諺語所說的「如果不想做,會找到一個藉口;如果想做,自然會找到一個方法」,這「自然會找到一個方法」,對寫作者來說就是只要上路了,沿途自有無窮盡的風景會展露給你看;而你前去汲取所需要的偌多對策,也有如美國詩人威廉斯(T. Williams)說的「點子就在萬事萬物中」,而不勞你苦思冥想就水到渠成了。
這樣你也就可以藉著凜於王道的驅動,不斷地自我惕勵寫出更多更精采的作品。屆時要像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 P. Baudelaire)所期許的「把你的汙泥給我,我將它鑄成黃金」那樣,縱使遇到腐朽的題材也能把它化為神奇的作品;或者接收類似雨果(V. Hugo)對荷馬(Homer)的讚美「世界誕生,荷馬高歌,他是迎來這曙光的鳥」而無所愧作,畢竟你也已經創新自勉而寫作有成了。因此,原先「誰駭怕寫作」的模稜句,到了此刻你就大可將它翻轉過來變成反詰句,語氣就像這樣:「開玩笑,誰駭怕寫作!」即使有加強性的驚嘆號存在,也撓動不了你堅持寫下去的意志了。
其實,有能力寫作,一向是令人羨慕有加的。古語所謂「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這就是特許給能文者的讚譽。當你手中的彩筆善於運轉,武士就會屏息在旁邊觀看你起草檄文,而美人也會腋下挾瑟急著來請你題詩。至於上引懷特語中該一影響隱喻,那就更證明寫作所具有的潛在莫大效應。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寫作新解方的圖書 |
| |
寫作新解方:寫作一路發 出版日期:2021-08-0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Books |
$ 221 |
寫作 |
$ 228 |
中文書 |
$ 229 |
中文 |
$ 234 |
寫作 |
$ 234 |
中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寫作新解方
寫作新解方(寫作一路發)
全書規畫有起步篇、衝刺篇和抵達篇等三部分,共三十章,分別談論寫作的基本觀念、會遭遇的各類問題,以及實際完成作品所需的技藝等。
論述旨意,則是要提供大家可以寫作一路發的方便管道。當中涵義有三:
第一,在學者應付各種作文,看了本書,可保一路暢順;
第二,一般人要以寫作為志業,參究本書,立刻知道進境所在;
第三,教師家長要指導孩子寫文章,仿照本書所示,一切都會有著落。
不敢說這概括了盡了寫作指引的能事,但至少所點出的要項及其有效的舉證等,已遠非坊間同類型泛論且視野拘限的著作所能相比。
也許有人認為從看理論書到實際寫作會有一段距離,這樣有沒有理論書就不關緊要。但依我的經驗,寫作進展不了,不是緣於理論書抽象或難以派上用場,而是自己對理論書鑽研不夠深入所導致的。因此,那類說詞,只合歸在有欠精準的俗見或短見範圍,而不宜再拿來搬弄,以免誤導人心。
反觀我這本仍以理論鋪展為基底而加案例證成的中小型書,能夠在大家進益寫作的路程中起作用,也得先受到類似的對待,有心人不妨試試看。
作者簡介:
周慶華
文學博士,曾任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現已退休。
出版有《佛學新視野》、《走訪哲學後花園》、《文化治療》,《後宗教學》、《死亡學》、《靈異學》、《後佛學》、《生態災難與靈療》、《身體權力學》、《反全球化的新語境》、《新時代的宗教》等六十多種。
章節試閱
誰駭怕寫作
我知道要是不一直寫我就會死,因為寫作就是冒險,而唯有藉由冒險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活著。
加拿大作家愛特伍(M. Atwood)語
寫作,對許多人來說,就像面臨突然掉落眼前的一塊燙手山芋,除了自己不敢承接,還會想辦法推給別人,讓對方去為它傷腦筋。
情況不就是內部要編刊物了,稿子卻遲遲出不來,一問才知道連倡議的人也在逃避責任。他總是說:「我出點子,你們去寫呀!」至於鼓吹大家到外面投稿,那就會看見有人提早把門關上,免得你闖進來逼他動筆寫東西。因此,上引愛特伍的話,就顯得戲謔成分濃厚,畢竟世上絕大多數...
我知道要是不一直寫我就會死,因為寫作就是冒險,而唯有藉由冒險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活著。
加拿大作家愛特伍(M. Atwood)語
寫作,對許多人來說,就像面臨突然掉落眼前的一塊燙手山芋,除了自己不敢承接,還會想辦法推給別人,讓對方去為它傷腦筋。
情況不就是內部要編刊物了,稿子卻遲遲出不來,一問才知道連倡議的人也在逃避責任。他總是說:「我出點子,你們去寫呀!」至於鼓吹大家到外面投稿,那就會看見有人提早把門關上,免得你闖進來逼他動筆寫東西。因此,上引愛特伍的話,就顯得戲謔成分濃厚,畢竟世上絕大多數...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寫作一路發
小時候,還沒著迷上文字世界以前,所有的空閒,我幾乎都是在盡情玩樂中渡過。由於住在鄉下,家裏又窮,買不起玩具,也沒地方可買玩具,所以就自己動手製作,如陀螺、木劍、滾車輪、燈籠和竹製手槍等,不知道在我手裏成形和玩壞的有多少;甚至還學大人編織、燻製釣竿和蓋茅屋等來自我過癮!當中所蓋的一間茅屋,自己獨坐在裏頭,酷似個山大王,得意到完全忘記工作期間的辛苦。後來只因缺少一名壓寨夫人,覺得無趣就把它毀掉了。至今還在遺憾:如果當時繼續研發,說不定我會擁有一幢自己設計的房子,也不必儘是呆在別人蓋好而...
小時候,還沒著迷上文字世界以前,所有的空閒,我幾乎都是在盡情玩樂中渡過。由於住在鄉下,家裏又窮,買不起玩具,也沒地方可買玩具,所以就自己動手製作,如陀螺、木劍、滾車輪、燈籠和竹製手槍等,不知道在我手裏成形和玩壞的有多少;甚至還學大人編織、燻製釣竿和蓋茅屋等來自我過癮!當中所蓋的一間茅屋,自己獨坐在裏頭,酷似個山大王,得意到完全忘記工作期間的辛苦。後來只因缺少一名壓寨夫人,覺得無趣就把它毀掉了。至今還在遺憾:如果當時繼續研發,說不定我會擁有一幢自己設計的房子,也不必儘是呆在別人蓋好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次
後全球化思潮叢書企畫/5
序:寫作一路發/9
起步篇/17
誰駭怕寫作/19
能寫就是王道/24
從起點到終點的塑形/29
許一個創新的夢/34
伴隨路程可能的各種驚奇/39
衝刺篇/45
確定寫給誰看/47
寫給誰看後的寫作策略/52
選擇題材的相應性/57
文體文類得一併配置/62
布局還有形式技巧風格要考量/67
字詞辨正重點在有無創意/72
美感要求決定標點符號的運用/77
段落篇章彈性處理/83
開頭最好具備暗示性/89
結尾要有力收網/94
抵達篇/99
呵氣看完篇/101
文章成形的檢視準則/106
體裁規範的遵守和...
後全球化思潮叢書企畫/5
序:寫作一路發/9
起步篇/17
誰駭怕寫作/19
能寫就是王道/24
從起點到終點的塑形/29
許一個創新的夢/34
伴隨路程可能的各種驚奇/39
衝刺篇/45
確定寫給誰看/47
寫給誰看後的寫作策略/52
選擇題材的相應性/57
文體文類得一併配置/62
布局還有形式技巧風格要考量/67
字詞辨正重點在有無創意/72
美感要求決定標點符號的運用/77
段落篇章彈性處理/83
開頭最好具備暗示性/89
結尾要有力收網/94
抵達篇/99
呵氣看完篇/101
文章成形的檢視準則/106
體裁規範的遵守和...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