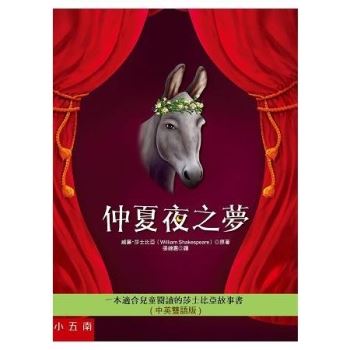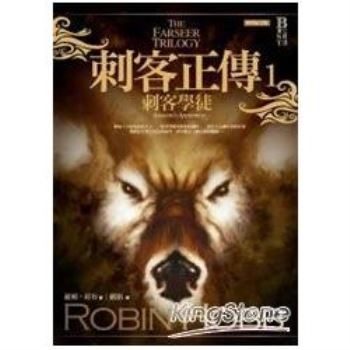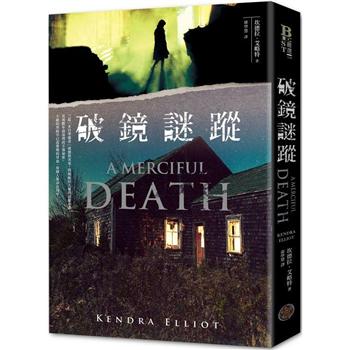【第一章】 傳聞小侯爺身懷琰王血脈
嘉平元年,冬月,朔日。
汴梁,御史臺。
雪是昨夜停的,凜風捲著嘯了半宿,將京城白茫茫壓了一層。
御史臺人來人往,已經忙碌了整整一個早上。
「卷宗,案冊。」御史中丞親自帶人安排,忙得焦頭爛額,「都要齊備,不准錯漏一樣!囚車鐐銬用新的……沒有就去找!」
尋常犯人不入天牢,進了御史臺獄的,不是位高權重,就是罪大惡極。
御史臺送走了不知多少囚車,出了門走北街,不出一刻就到鬧市法場。今天這等陣仗,還是頭一回。
從半月前人被綁得嚴嚴實實,連夜押進來,侍御史也是頭一次見著這位傳聞中「極端凶惡、殺人如麻」的悍犯。
看年紀不過二十來歲,眉目生得英氣疏朗,身上只套了件單薄的囚衣,漿洗得格外乾淨。
絲毫看不出剛提了要在囚車上插花的過分要求,犯人剛揉著耳朵,不甚在意地安撫了中丞大人,正無所事事地倚著乾草堆打哈欠。
「這是什麼人物?」自己辛辛苦苦翻曬了三天的乾草,侍御史一眼就認了出來,瞪圓了眼睛,「將死之人,如何還這等做派?」
「這幾年才來京城吧?」老文吏放下卷宗,「那是雲小侯爺。」
侍御史不解,「誰?」
老文吏嘆了一聲,「知道鎮遠侯嗎?」
當年鎮遠侯謀逆兵變、構陷皇子性命,滿門抄斬,侯府也從那時起就跟著荒置了下來。
一晃五年,門上的封條早已破敗不堪,分封的王爺諸侯換過一茬,這座侯府也依然沒能易主。
「當年有人誣陷端王謀逆,害得端王歿在了天牢。」這是天大的事,侍御史自然記得,「先帝震怒。徹查之下,才知道原來是這個鎮遠侯膽大包天,妄圖謀逆,又構陷皇子。」
老文吏點頭,「鎮遠侯是皇后親侄,卻闖下這等滔天大禍。皇后陡聞這等變故,連驚帶痛,沒多久就也薨了。」
侍御史心驚肉跳,「果然是抄家滅族的大罪……」
「不錯。」老文吏點點頭,「鎮遠侯府,正是雲府。」
侍御史愣住,「那這位雲小侯爺……」
「那年冬月初一,先帝親自下旨,將鎮遠侯府滿門抄斬。」老文吏道:「封城十日,殿前司將整個京城翻了一遍,盡斬雲府上下五十餘口。天羅地網,唯獨跑了一個。」老文吏:「便是雲府的長子嫡孫。」
「……」侍御史聽得撼然怔忡,抬頭望過去。
雲琅打好了哈欠,撣了撣囚車上的浮雪,把手塞回木枷。
「雲小侯爺。」御史中丞自打接了這個燙手山芋,已經不錯眼盯了他半月,一雙眼盯得通紅,「御史臺不曾虧待你。」
雲琅拱一拱手,「是。」
「酒杯是琉璃的。」御史中丞:「菜蔬和肉縱然平常,也都十足新鮮,一片隔夜的筍尖也沒有。」
雲琅誠誠懇懇,「有勞。」
御史中丞:「一共三罈竹葉青,大理寺上元時送的,一滴不剩。」
「酒其實不好……」雲琅低嘆一聲,迎上中丞陰森森視線,改口:「破費。」
御史中丞:「仁至義盡。」
雲琅心服口服:「確實。」
「只剩一個時辰。」御史中丞:「閣下若越獄,下官一頭撞死在這囚車上。」
雲琅:「……」
時辰未到,御史中丞一屁股坐在地上,牢牢盯著他。
鎮遠侯府滿門抄斬是五年前的事,雲小侯爺逃了五年,也不是一次都沒被抓到過。
五年間,地方郡、縣圍剿十餘次,京城殿前司封城三次,千里追襲七次,一無所獲。
雲琅身手超絕,又長年提兵征戰,在北疆邊境滾出一身生死之間的恐怖直覺,哪怕一時被擒住了,稍有疏忽便能藉機脫身。這些年來,因著雲府一案被罷官免職的官員已不下五指之數。
御史臺接了人,御史中丞就沒完整闔眼過一宿,予取予求,務求伺候得雲小侯爺不再跑一次。
御史中丞親自交接,扶著囚車送出御史臺。
****************
罪臣伏法,當街問斬。
囚車繞到菜市口,已至午時二刻。
菜市口人頭擠擠挨挨,一早就開始熱鬧,過了午時,已支起了幾個茶攤。
御史中丞搶上幾步,趕在兵士前,伸手扶住車轅。
雲琅掃一眼那幾個兵士手中的殺威棒,低頭笑笑,不以為意,戴了枷鎖走下囚車。
雲琅向人群裡大致一掃,正要上法場,被御史中丞按捺不住攔下,「少侯爺——」
雲琅朝他囫圇抱拳,「酒真的不好。」
御史中丞定定望著他,張了下嘴,沒能出聲。
雲琅自覺不是挑事的人,想了想,誠懇奉告:「大理寺送的是假酒。」
御史中丞:「……」
法場是臨時搭的,難免草率,階下還是一片雜草磚石,刮著囚衣格外粗糲單薄的布料。
雲琅振落牽衣蓬草,舉步踏上石階。
臺上人高高坐著,眼皮也不抬,「犯臣何人,犯下何罪?」
御史中丞尚未及開口,侍衛司騎兵都指揮使高繼勳已上前一步,抱拳俯身,「回老太師,犯臣是雲府餘孽雲琅,犯的是抄家滅族的滔天大罪。」
監斬的是當朝國丈、太師龐甘。
三朝老臣,頭髮鬍子都白透了,拄著御賜的龍頭拐,顫巍巍路都走不穩。整個人倒還老而彌堅地捧著詔書,念得抑揚頓挫:「天生民,而立之以君。夫君者,奉天養民者也……」
雲琅向來對這些之乎者也頗感頭痛,找準一根木柱,跪坐下來靠著,閉目養神了一陣。
龐甘不緊不慢念了一炷香,終於念到最後:「聖上繼位,感天承運,奉先帝之遺詔大赦天下……然,謀反大逆、罪大惡極者,皆不在此列!」
不少人被懾了一跳,本能抬頭。
「雲府之罪,罪無可恕!」龐甘放下聖旨,沉聲道:「雲琅,你可知罪?」
雲琅起身,「知道。」
龐甘語氣愈沉了幾分:「隱匿之後,你逃去了什麼地方?」
雲琅想也不想,「天大地大,四海為家。」
龐甘追問:「都做了什麼?」
雲琅笑笑,「亡命之徒,自然是逃命。」
龐甘緊迫不捨,「何人助你脫身?」
「眾叛親離。」雲琅嘆道:「孤家寡人。」
案問到此處,便再也問不下去。
龐甘仍不甘心,拄著拐杖緩步上前,近身低聲:「雲琅,你如今已命懸一線,該說些什麼,心中總該有數……」
雲琅笑一笑,在刑臺前盤膝坐定。
龐甘再要說話,一旁監斬官低聲道:「大人,時辰……」
龐甘臉色沉了沉,拂袖回了高臺。
「老太師。」監斬官低聲稟道:「時辰已至,監斬大臣只剩琰王告病未到。」
龐甘神色冷峻,「開斬。」
「是否不妥?」監斬官猶豫,「琰王畢竟奉命監斬,可要派人去請一請?」
雲琅原本闔眸盤膝靜坐著,不知聽見哪一句,睜開眼睛。
「琰王蕭朔?」侍御史在刑臺下,悄聲問老文吏:「可是端王那個……」
老文吏沉聲:「噤聲。」
侍御史臉色也跟著變了變,低下頭閉緊了嘴。
「雲氏餘孽。」龐甘看向刑臺,「謀逆作亂、殘害忠良,滿門抄斬,並脫逃之罪,今認罪伏法……」
雲琅出聲:「且慢。」
龐甘臉色驟沉,又當他臨死嚇得改了念頭,打算供出別人來保命,壓著脾氣等他說。
雲琅好奇,「你們說的那位琰王,便不來了嗎?」
「放肆!」龐甘怒火沖頂,厲聲叱道:「來與不來,與你何干!?」
已經看出雲琅打定了主意不配合,龐甘再不由他打岔,寒聲道:「開斬——」
雲琅:「與我有干。」
他嗓音清冽明朗,壓著龐甘蒼老渾濁的嗓音,吐字格外清晰篤定。
龐甘臉幾乎氣成了豬肝色,死死瞪著他。
雲琅被人按著,躺在鍘刀底下,神色誠懇,「此事說來話長,尚得慢慢理順。老太師若有閒暇,還請飲一杯涼茶敗敗心火,尋個僻靜之處坐穩當,摒退閒雜人等……」
「雲公子。」監斬官小心打斷:「時辰緊迫,長話短說。」
雲琅:「我懷了琰王的兒子。」
整個法場都跟著靜了靜。
監斬官扶得慢了半步,老太師眼睛瞪得溜圓,沒能坐穩,險些一頭栽下了監斬臺。
御史中丞張口結舌,看著雲琅,「小、小侯爺……」
二十三年前,先帝佑和十年秋。司天監報西方白虎異象,參下三星動,臨昴畢、伐天街。
第二天,內監來報,鎮遠侯府得了長子嫡孫。
此事傳得極廣,京城沒人不知道,雲小侯爺是星動而生,命犯白虎、不同常人。
街口專給人看相算命的先生還說,這白虎命格是剋身大凶,主血光橫死,災煞怕克,福少禍連綿。
但先生沒講,白虎命格還有些別的特異能耐。
比如懷孩子。
還是琰王的孩子。
刑臺之下,百姓路人議論紛紛。
「荒謬……荒謬!」侍衛司奉命護衛法場,高繼勳聽著眾人議論,怒聲呵斥:「胡言亂語,妖言惑眾!」
雲琅枕著鍘刀底座,仰頭見他氣得面紅耳赤,好心關懷,「高大人飲一杯涼茶,敗敗心火……」
「住口!」高繼勳上前一步,「時辰已至!老太師不必聽他妄言,儘快行刑……」
雲琅抬了抬手,拿木枷卡住鍘刀,「且慢。」
高繼勳喘著粗氣,死死盯著雲琅。
「雲氏一族,滔天大罪。知罪逃亡罪加一等,合該當街處斬,以儆效尤。」雲琅嘆息一聲:「然,稚子何辜。」
御史中丞站在法場邊上,深吸口氣,用力按了按額頭。
「這段話有些文雅。」雲琅怕侍衛司的高大人不懂,卡著鍘刀,好心解釋:「意思就是說,雖然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我肚子裡的孩子是沒有罪的。」
「我聽得懂!」高繼勳幾乎惱羞成怒,「少在這故弄玄虛!就算你身懷異數,也不過是個雜種餘孽……」
雲琅奇道:「莫非高大人認為,昔日冤案雖然早已平反多年,琰王卻還有罪不成?」
高繼勳正要呵斥,話到嘴邊,忽然不自覺打了個激靈。
五年前那一場冤案,正是聖上死穴,朝野上下至今卻仍然諱莫如深。
滿朝文武都知道,聖上和端王兄弟情深,卻因為人微言輕,只能眼睜睜看著端王獲罪入獄。後來端王平反、鎮遠侯獲罪,如今的聖上那時尚是六皇子,監斬時尚且一度哀痛過甚,吐血昏厥。
沒能救下端王,皇上始終心懷愧疚,對端王遺子的厚待已到了不論規制、不講道理的地步。
平日裡私下說說便也算了,此時眾目睽睽,若是真被雲琅繞進去、順著話頭說了,難免要惹皇上雷霆之怒。
高繼勳驚出一身冷汗,閉了閉眼定定心神,沉聲道:「琰王……自然無罪。」
「這就是了。」雲琅嘆息一聲,「孩子是他的,自然也是無罪的。」
「縱然我有心伏法,卻不該牽連無辜。」
「若是孩子已經足月,我捨了這條命,剖腹取子,也算對得起琰王。」雲琅慨嘆,「偏偏他尚不足月,卻要隨我一屍兩命,幼子何辜。可憐端王血脈飄搖,竟自此斷絕……」
鍘刀懸在半道,被木枷卡著落不下來。刑臺上下聽著雲琅唏噓慨嘆表完了心跡,一時都有些茫然怔忡。
老太師龐甘忽然出聲:「且慢。」
監斬官愣了下,轉過頭。
「雲琅。」龐甘扶著拐杖上前,一雙蒼老渾濁的眼睛緊盯住他,「依你所說,你與琰王……關係匪淺?」
雲琅點頭,「自然。」
龐甘看著雲琅,心中一喜。
他始終欲從雲琅口中逼問出同黨,不想雲琅此刻竟自己露了馬腳,當下不動聲色,緩聲追問:「是何關係?」
雲琅有些莫名,「老太師不知道?」
「我與琰王。」雲琅幫他總結,「生死血仇。」
雲琅沒再往下說,抬頭向雲邊看出去。
天色陰沉,眼見著還要落雪,厚重雲層一疊接一疊蔓到山頭。
隱約可見一線天光。
御史中丞定定看著雲琅,心口跟著一緊,背後冷汗涔涔透出來。
「黃口小兒,謊也編不圓!」龐甘臉色變了又變,半晌坐回監斬臺,冷笑,「既然血海深仇,你又如何能與他攪在一起?還不是矢口狡辯!」
「這有何難。」雲琅失笑,「這種事,無非灌灌酒下下藥。我對他傾心已久,潛進他府裡,尋個月黑風高良辰日,趁他半醉半醒神混沌時……」
御史中丞天翻地覆咳嗽起來。
雲琅沒能說完,有點惋惜,「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御史中丞:「……」
人群尚在愣怔,鴉雀無聲。
御史中丞站了半晌,實在不忍再看下去,按著額頭往角落退了退。
「斯文掃地……斯文掃地!」老太師龐甘氣得鬍鬚打顫,抖著手指他,「天子腳下,豈容此等惡行!」
監斬官聽雲琅說得信誓旦旦,雲裡霧裡間竟已不知不覺信了七八分,猶豫勸道:「老太師,畢竟稚子……」
「何來稚子?分明孽種!」龐甘厲叱一句,抄起斬簽,劈手摔下監斬臺,「荒唐至極!午時三刻已至,速速行刑!」
亡命牌落地,鍘刀必須見血。劊子手屏息凝神,咬牙正要行刑,忽然聽見清脆蹄聲。
兩匹飛馬破開人群,人立嘶鳴,剛好到了監斬臺下。
勁風擦身而過,亡命牌被墨羽箭當中射穿,死死釘在木柱上。
馬上是兩個身形驃悍的黑衣人,其中一個手中弓弦仍在輕震,神色漠然,沉默立馬。
人群一陣騷動,有見識過的,忍不住低呼出聲:「玄鐵衛!琰王府的人……」
龐甘臉色變了數變,落在那兩個冷硬如鐵的黑衣護衛身上。
玄鐵衛是端王留下的親兵,朔方軍裡的精銳,飲血無數殺人如麻,沒一個是好惹的。
皇上憐惜琰王少年失怙,特准玄鐵衛在京城內持刀縱馬。縱然是當朝大臣權貴,也沒人願意同這些只知道護主奉命的殺胚對上。
「本朝律例,從無死囚赦免一說。」龐甘勉強壓下怒火,上前道:「琰王既然告病,法場便該由監斬大臣處置……」
「我家王爺養病,聽聞有子嗣流落府外。」其中一人冷冰冰道:「遣我二人前來尋回。」
「子虛烏有,不過垂死掙扎、胡編亂造罷了!」龐甘:「琰王何必當真……」
「我家王爺說,端王一脈,子嗣艱難,血脈凋零。」另一人道:「不能放過一個。」
龐甘一時被噎住,還要再說,那人已下了馬,至鍘刀下將躺得溜扁的雲琅提起來,扛下了刑臺。
「我家王爺吩咐,琰王府借去十月,驗看血脈。」先前說話的玄鐵衛探向懷中,摸出一方生鐵權杖,拋在刑臺之上,「十月之後,要殺要剮,把人剁成幾段,隨你們就是了。」
雲琅從鍘刀下被扛出來,囫圇塞進了馬車。
玄鐵衛漠然沉肅,護持著馬車緩緩出了鬧市。
雲琅還想矜持,拿腦袋把簾子頂開一小半,看著越來越遠的刑臺,「諸位稍待……」
為首的玄鐵衛稍勒馬韁,看了他一眼。
雲琅不太好意思,清了下嗓子,「能再回去一趟,讓他們幫我把枷鎖摘下來嗎?」
「不是為我。」雲琅有理有據,很客氣,「枷鎖刑具五行屬金,是大凶之物,主肅殺,對養胎不利。」
玄鐵衛並不理他,扶著身側長刀,催馬前行。
****************
端王過世後,先帝讓端王幼子蕭朔襲爵,爵位分例供享一律不變,唯獨改了封號。
王府被下旨重新精心修繕過,向外擴了一條街,圍牆高聳,比以前氣派了不少。
雲琅自覺套上了木枷,被押下馬車,站定抬頭看了看。
雲琅站在府門前,多看了幾眼,視線被玄鐵衛牢牢擋住。
雲琅抬頭,朝他笑笑。
為首的玄鐵衛姓連,叫連勝,端王給起的名字。
玄鐵衛都是端王親兵,從朔方軍時就跟著端王。後來端王從朔北回京,連勝也跟著回來,進了禁軍殿前司,做過三年的殿前指揮使。
雲琅老往端王府跑那些年,沒少被老御史暴跳如雷地堵門,多半都是靠連勝替他瞞天過海、蒙混過關。
「正門不能走。」玄鐵衛凝注他半晌,側開頭,向旁邊一指,「西門入。」
雲琅點點頭,朝西門走過去。
西門的僕從去稟報王爺,玄鐵衛停在門外,沉默良久,霍然出刀。
雲琅不閃不避,凌厲刀風劈面掠下,狠狠颳過眉心,臂間緊跟著微微一沉。
木枷應聲碎開。
僕從從府裡小跑出來,將門敞開。玄鐵衛收刀還鞘,揮手領屬下牽過馬車,進了王府。
雲琅被人領著,穿過大半個王府,帶到了一處格外不起眼的偏殿。
「王爺說,他還有棋局未了,脫不開身。」下人引他入門,在殿中坐下,「請雲公子在此稍待。」
室內暖意融融,大概是燒了地龍取暖。雲琅順手換了個暖爐抱著,正在研究太師椅的木料,聞言抬頭,「什麼局?」
下人一板一眼,「棋局。」
「打攪一下,你這裡真是琰王府?」雲琅撐著桌沿,向窗外看了看,「琰王蕭朔。從玉,炎聲,琰琬的琰,意思是美玉的那個……」
「不是。」下人道:「琰圭的琰。」
雲琅微頓,收回視線。
下人朝他一拱手,出了門。
故人往事,依稀還在眼前。雲琅唏噓一陣,往囚衣夾層裡摸了摸,翻出個從御史臺搜刮的栗子,正要捏開拋進嘴裡,房門忽然被人推開。
雲琅捏著栗子,張著嘴,愣了下。
門外,甲兵衛士漠然森嚴。
天已黑透了,掌了燈,光從廊間投過來,在屋內落下分明人影。
一別經年,琰王身形軒峻,墨衣壓著層疊金線,血紅內襯映在燈燭下,翻出一片黑巒一片血海。
蕭朔背著光立在門口,眉目陰鷙,視線冷冷落在他身上。
雲琅手一鬆。
栗子掉在地上,滾了兩滾,落進暗影裡。
雲琅回神,把暖爐往懷裡揣了揣。揉了揉手腕,放下暖爐,撈住腕間墜著的鐐銬鎖鏈,撐起身。
蕭朔天賦異稟,不知道吃什麼長大的,十來歲時就比他高出半個頭,眼下看只怕也沒差出多少。
單論相貌,變化也並不大。
輪廓更鋒利了,氣息更薄涼了,無波無瀾的視線落在他身上,茫茫一片凍雪苔原。
雲琅在凍雪苔原裡站了一會兒,往後挪了挪,有點想把那個剛放下的暖爐摸回來。
手一動,玄鐵衛長刀霍然出鞘,厲聲:「不准動!」
雲琅收回手。
玄鐵衛身手了得,不容他喘息,刀風凌厲,燭影跟著一晃。
薄薄血刃泛著寒意,已經抵在了頸間。
雲琅舉起雙手,苦笑,「我還戴著鐐。」
「世人都知道。」蕭朔站在門前,凝注他良久,緩聲開口:「雲小侯爺身手絕倫,暗器功夫了得。」
雲琅有點不好意思,抱拳客氣,「世人謬讚……」
蕭朔合攏密函,放在桌上,「雲琅。」
雲琅怔了下,抬頭看他。
「你這些年的蹤跡,禁軍、皇上清楚的,我知道。」蕭朔緩聲:「禁軍、皇上不清楚的,我也知道得十之八九。」
「你猜。」蕭朔傾肩,冷戾眉眼沒進燭影裡,「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些?」
小王爺話音輕緩,殺意像是日暮薄雪,隨著暗影悄然覆落下來。
食肉寢皮,挫骨揚灰。
雲琅看著他,輕扯了下嘴角。
他動了下唇,要說話,神色忽然微變,驟然抬手襲向蕭朔胸肩。
電光石火。
玄鐵衛尚且來不及反應,雲琅已將蕭朔縱身撲倒。
幾支暗箭破窗而入,狠狠扎在了兩人方才站的位置。
「什麼人!」玄鐵衛厲聲呵斥,拔刀破窗而出,「防衛,有刺客!」
窗外有人快速跑動,夜色寂靜,兵器碰撞聲格外響亮。
雲琅很識時務,沒站起來當靶子,還在窗戶底下溜扁趴著。
這一下砸得太結實,哪怕底下有蕭朔墊著,也撞得金星直冒。
雲琅眼前一陣一陣地起霧,晃了晃腦袋,緩過口氣,才來得及告罪,「事急從權,冒犯王爺……」
蕭朔抬眸,視線落在他身上。
雲琅被他一看,也覺得自己趴在王爺身上告罪確實不大合適,用力撐著翻了個身,坐在地上。
蕭朔起身。
「不用謝,舉手之勞。」雲琅長話短說:「王爺若是方便,不如幫我把鐐銬解開。」
「雲琅。」蕭朔撣淨衣襬塵土,「經年不見。」
「是。」雲琅點點頭,幫他算,「六、七年了。」
蕭朔:「你還是這樣恬不知恥。」
雲琅:「……」
蕭朔走過去,將那幾支箭逐一拔起,看了看。
箭從窗外進來,雖然扎在兩人立處,要取的卻顯然只是雲琅性命。
雲琅不躲,在窗口擋著,傷不到蕭朔。
雲琅要躲,往哪裡撲都一樣,偏偏戴著十幾斤的鐐銬結結實實把蕭朔一塊兒砸在了地上。
雲琅摸摸鼻子,張了下嘴,輕咳一聲,「差不多……」
「我原本以為,日日恨不得殺你的只有我一個。」蕭朔走過去,將刺破的那一扇窗戶推開,「現在看來,你找死的本事也不比當年差。」
「我想知道。」蕭朔並不理會他,在桌邊坐下,拿起暖爐把玩,「要你性命的人,是血海深仇,還是因為別的什麼。」
「是血海深仇。」雲琅盯著他的暖爐,試圖插話:「王爺,能不能……」
「比如。」蕭朔:「因為當年舊事,或是一些見不得人的祕辛。」
蕭朔揭開暖爐看了看,將只剩餘溫的冷炭潑在窗外,「想滅你的口。」
雲琅:「……」
「雲琅。」蕭朔隨手扔下空暖爐,「你究竟還知道什麼?」
「我知道的不比小王爺多。」雲琅苦笑,「我有些冷,勞駕小王爺幫我再添個暖爐,好歹……」
蕭朔:「好歹你懷了我的孩子?」
雲琅張了張嘴,戛然而止。
蕭朔坐在燈燭下,偏了偏頭,視線落在雲琅身上。
他神色平淡,這樣微微歪頭,幾乎將那一身冷戾殺意盡數粉飾乾淨,隱約透出些極具誤導的舊時神色。
雲琅看著他,不自覺怔了下。
大約是冷糊塗了,他腦海裡一瞬恍惚,又騰起來蕭朔少年時的樣子。
粉雕玉琢的小皇孫長到少年,厚積薄發後來居上,學問做得好了不少,可依然一點也沒有端王風範。提兵戰陣不必說,被端王往手裡塞了把匕首,連兔子都不敢殺。
還割破了自己的手。
玄鐵衛將刺客盡數絞殺,入門回稟。
雲琅撐著地,使了幾次力氣起身,讓到一旁。
他方才撲過去的時候,蕭朔的袖箭也在瞬息間破窗而出。
其中一個刺客,喉間釘著的正是那支精鐵袖箭。
「雲琅。」蕭朔並不看他,「你想逃去北疆,是不是?」
雲琅正打算摸口茶喝,手一頓,停在杯沿。
「你若越獄,會牽連御史臺。刑場劫囚,朔方軍危在旦夕。」蕭朔淡聲道:「從我這裡走,無論琰王府如何分辯,外人都會以為所謂逃走不過是個幌子。我將你接入府中養胎是假,對外說你脫逃,其實早已為了洩憤將你凌虐打殺、挫骨揚灰。」
「後幾個不大方便。」雲琅人在屋簷下,乾咳一聲,適當退讓,「小王爺實在生氣,凌一凌虐倒也……」
「當年。」蕭朔道:「鎮遠侯構陷謀逆、戕害栽贓時,你的思慮也是這般周全嗎?」
雲琅頓了頓。
蕭朔身後,玄鐵衛原本垂手肅立,聞言倏而抬頭,冰冷視線牢牢釘在他身上。
雲琅靜了半晌,低頭笑笑。
「打殺——」雲琅拂袖,「也可。」
雲琅抬頭,閉上眼睛,「麻煩王爺,留個全屍。」
玄鐵衛眸光驟然冷冽,上前一步,被蕭朔抬手止住。
屋內靜了半晌,蕭朔忽然笑了一聲。
雲琅背後隱約發涼,睜開半隻眼睛,悄悄瞄了瞄。
「好歹。」蕭朔將那封密函拾起,隨手撕碎,拋進火盆,「小侯爺懷了我的孩子。」
玄鐵衛:「……」
雲琅:「……」
玄鐵衛低頭,「是。」
「收拾了罷。」蕭朔掃了一眼那幾具刺客屍首,吩咐:「去拿個暖爐。」
玄鐵衛應聲,正要出門,又被蕭朔叫住:「還有。」
玄鐵衛回身,候著他吩咐。
「找間上房。」蕭朔抬眸,看向雲琅,「撥下人丫鬟,為小侯爺延醫用藥。」
雲琅不好意思,剛要客氣,「倒也不必……」
蕭朔:「讓他生。」
雲琅:「……」
屋裡屋外都跟著靜了靜。
雲琅張了下嘴,清清喉嚨,欲言又止。
……小王爺盛情難卻。
王府的下人動作很快,說話間,新的暖爐已經填好獸金炭,重新送了上來。
雲琅眼睛一亮,把話暫且嚥回去,伸手去接,「謝王爺……」
蕭朔饒有興致,「謝?」
雲琅抬頭。
「你最好生得出來。」蕭朔看了他半晌,忽然笑了下,「雲琅。」
雲琅抱著暖爐,目光落在蕭朔身上。
六年不見,如今的蕭朔和當初相比,當然已經很多地方都不一樣。
但一笑起來,就變得更多。
平時尚能掩飾,冰冷笑意掠過眼底,翻騰戾意就沾著血,壓不住地溢出來。
「懷胎十月,我會等足。」蕭朔起身,語氣不帶半點溫度,落在雲琅耳中,「十月之後……」蕭朔:「任選,一屍兩命。」
雲琅:「……」
小王爺文采斐然。
同門七年,講文章的師傅換了八個,沒見有這麼用的。
任選。
要麼他生個兒子兩命。
要麼他自己一個人屍。
雲琅揣著有點燙手的暖爐,算了算十個月自己能恢復到什麼地步,有點猶豫要不要現在就跟蕭朔改口,說自己懷了個哪吒。
沒等他下定決心,玄鐵衛已推門而入,同蕭朔低聲說了幾句話。
聲音極低,雲琅心裡惦著哪吒的事,隱約聽了個大概。大抵是查過了那些刺客的屍首,發現些特異處,要蕭朔親自辨認。
刺客是朝著自己來的,雲琅有心幫個忙,撐著桌沿起身。
玄鐵衛時刻提防他,雲琅一動,立時有刀跟著出鞘。
蕭朔交代到一半,抬眸看過來。
雲琅扶著桌沿,被刀抵在頸間。
燭火下,雲琅臉色隱隱泛白,微闔著眼睛晃了晃,勉強站穩。
為首的玄鐵衛怕雲琅又有什麼伎倆,正要上前,被蕭朔舉手止住。
雲琅驅散眼前黑霧,緩了口氣,皺起眉。
情形不對。
雖說從法場下來,他就自覺有些畏寒不適,可也該沒多嚴重。
當年京城慘變,一年沙場五年逃亡。幾次命懸一線,病得只剩一口氣,嚼嚼草藥就爬起來了,也沒這麼風一吹就倒,更不要說站都站不穩。
雲琅靠著桌子,警惕抬頭,「暖爐裡下了毒?」
蕭朔淡聲道:「獸金炭。」
雲琅找了一圈,「茶水?」
蕭朔:「龍井茶。」
雲琅仍覺得手腳頗發沉,呼出的氣也灼燙,心頭越發不安,「那只怕是小產,中了紅花,孩子要保不住了……」
蕭朔耐心徹底耗盡,打斷:「雲琅。」
雲琅還在愁,憂心忡忡抬頭。
蕭朔看著他。
屋內茶香氤氳,燭火輕躍,玄鐵衛漠然肅立。
「六年前。」蕭朔走到窗前,「也是今日。」
雲琅手輕輕一頓,無聲攥實。
蕭朔背對著他,窗外呼嘯風雪。
雲琅胸口起伏了兩下,將咳意憋回去,慢慢撐著站直。
「這六年,每到今日給父親上香,我都會將一卷密函也燒掉。」蕭朔緩聲:「告訴他,我還在找你。」
雲琅閉了閉眼睛,低頭笑笑。
「這些年來,每每想起過往。」蕭朔道:「我最後悔的,就是以你為友。」
「我甚至還將你帶回了王府。」蕭朔轉回身,視線落在雲琅身上,「我父親教你騎射輕甲,教你提兵戰陣。」
「母親每次置辦點心衣物,無論何等精細,都有你一份。」
「府上管家下人,都與你熟識,任你來去自如。」
風雪凜冽,屋內靜得懾人。
蕭朔逐字逐句,聲音冰冷:「是我告訴了你,禁軍虎符放在什麼地方。」
雲琅屏住呼吸。
他撐著桌沿,肩胛繃了繃,喉間漫開一片血腥氣。
「我若要你的命。」蕭朔緩聲:「絕不會是下毒這麼舒服。」
雲琅靜立半晌,抬起頭,輕抬了下嘴角。
蕭朔不再與他浪費時間,拋下柄鑰匙,帶玄鐵衛出了門。
****************
不出半炷香,屋內已徹底清淨下來。
雲琅扶著桌沿,盡力想要站直,胸口卻依然疼得眼前一陣陣泛黑。
他抬起手,攥住衣料緩了緩,每喘一口氣卻都如同千斤重錘,高高舉起,結結實實砸下來。
雲琅有些昏沉,撐著慢慢滑坐在地上。
視野被冷汗沁著,看什麼都是模模糊糊。雲琅靠著牆,閉著眼緩了一會兒,低聲開口:「刀疤。」
窗戶被猛地推開,一道身影躍進來。
風雪盤旋半宿,也總算尋到機會,跟著打著旋往窗戶裡灌。
黑衣人想去扶雲琅,又怕他著了冷風,手忙腳亂去關窗戶,被雲琅叫住,「透透氣。」
刀疤咬牙,半跪下來。
雲琅咳了兩聲,不甚在意地抹了抹唇角,拭淨了殷紅血色。
刀疤再忍不住,愴聲:「少將軍!」
「死不了。」雲琅深吸了口氣,一點點呼出來,「刺客是哪裡來的?」
刀疤跪在地上,沉默半晌,摸出一塊沾血的侍衛司腰牌,放在他面前。
雲琅了然,點點頭,「怪不得。」
他才到了蕭朔府上,就有人急哄哄來滅口,無疑是怕他說些不該說的話、做些不該做的事。
當初一場慘變,盤根錯節、牽扯太廣。
為了滅他這最後一個活口,已經上天入地折騰了五年。
刀疤雙目通紅,跪了片刻,又去使蠻力掰雲琅腕間手銬。
雲琅試著挪了下胳膊,實在沒力氣,「不必費事……」
刀疤啞聲:「少將軍若再逞強,勿怪屬下魯莽,動了少將軍胎氣。」
雲琅一陣頭疼,「你怎麼也……」
刀疤皺緊眉抬頭。
「……算了。」雲琅指指桌邊,「鑰匙。」
刀疤愣了愣,撲過去拾起那把鑰匙,替雲琅開了鎖。
自從進了御史臺,雲琅被釘了大半個月的鐐銬終於拿下來,手腳陡輕,忍不住鬆了口氣。
雲琅活動著手腕,察覺到刀疤神色,啞然:「這就要哭了,沙場上受的傷不比這個重得多?」
「沙場殺敵,豈是這般折辱!」刀疤壓不下激切,「少將軍,難道就任由他們這樣對你?!那個琰王……」
雲琅睜開眼睛。
刀疤被他淡淡一掃,懾得呼吸微屏,本能閉上嘴,埋頭跪回去。
「當年之事。」雲琅輕聲:「於他而言,我該挫骨揚灰。」
當年端王被投入獄中,禁軍察覺有異,一度幾乎按捺不住,想要去聖前請命、闖御史臺救人。
雲琅拿了兵符,死令禁軍不准妄動,叫朔方軍水洩不通圍了陳橋大營。
風雪刺骨,雲琅深吸口氣,又一點點呼出來。
雲琅咳了幾聲,隨手抹淨唇角血痕,「去,幫我做件事。」
刀疤埋頭跪在地上,一聲不吭。
雲琅有些頭疼,撐著坐直,緩了些語氣:「好事。」
刀疤悶聲:「自從少將軍回來,沒一件好事。」
「……」雲琅近來越發糊弄不了他們,想抬腿踹人,實在沒力氣,「幫我去買些棉花,棉布也要。」
刀疤愣了愣,「做什麼?」
雲琅看了看自己的肚子,有些犯愁,「保胎。」
刀疤:「……」
「叫你去你就去,哪兒那麼多廢話。」雲琅沒了耐性,擺擺手,「去吧,你們幾個都給我藏好,少來王府晃悠。」
少將軍脾氣向來大,刀疤不敢反駁。低聲應了是,關嚴窗戶,又小心扶著雲琅起身,坐回椅子裡。
雲琅算算時間,估計上房丫鬟應當都備得差不多了,往外轟人,「快走,看著就頭疼。」
「少將軍什麼時候回了朔北。」刀疤小心抱過絨毯,替他蓋上,「我們天天讓少將軍頭疼。」
雲琅失笑,抬腿虛踹。
刀疤不閃不避,由著他踹了一下,「少將軍。」
雲琅抬頭。
「當初的事……」刀疤沉默半晌,「為什麼不跟琰王說實話?」
雲琅呼吸輕滯,靜靜坐了半晌,低頭一笑。
他垂了視線,將暖爐揣在懷裡,往椅子裡靠了靠。
刀疤知道他脾性,沒再追問,悄悄翻出窗戶,沒進風雪裡。
隔了良久,雲琅終於睜開眼睛。
歇了這一會兒,他也攢了些力氣,撐起身,從香爐中取了三枝香。
雲琅把香拿在手裡,輕輕攥了攥。
屋內空蕩,風雪呼嘯。
雲琅回憶著來時路徑,找了找方位,朝舊時端王府的祠堂跪伏在地,無聲拜了三拜。
雪夜寂靜,雲琅額頭滾燙,用力抵在地上,閉緊眼睛。
*************************
京城的雪下了一整夜。
雪霽天明,御史中丞奉聖旨,一早就匆匆趕到了琰王府。
「琰王。」御史中丞雙手奉著聖旨,在門前站滿了一炷香,終於再忍不住,「聖上有旨——」
蕭朔點點頭,「放下吧。」
御史中丞看得詫異,還要說話,被邊上的傳旨太監笑呵呵拉了一把。
太監接過聖旨,朝蕭朔恭敬俯身,呈到了桌案上。
御史臺奉命監察官員行止,御史中丞晾在一旁,眼睜睜看著違禮破例的條目一條一條往上加,不由皺眉,「公公……」
「大人頭一回來這琰王府,不明白裡面的規矩。」傳旨太監笑笑,「皇上對琰王寵愛有加,這些小事,一律都是不管的。」
太監不再多說,笑吟吟告了罪,由府內下人領著出了殿門。
蕭朔打完了一副棋譜,落下最後一枚黑子,拂亂棋局。
那封聖旨被晾在桌旁,蕭朔看了看,隨手擱在一旁,「中丞還有事?」
「下官……」御史中丞定了定神,拱手道:「有些私事。」
蕭朔點點頭,「來人。」
御史中丞看了看兩側玄鐵衛,下意識要再退,又聽見蕭朔出聲:「不必找柱子。」
御史中丞抱著門框,愣愣抬頭。
「原來靠這個辦法,就能困住他不跑。」蕭朔饒有興致,拾了兩枚棋子,「中丞這半個月,撞了幾次?」
御史中丞臉脹得通紅,鬆開手,飛快整理衣冠,「此事與王爺無關!」
「佑和二十六年榜眼。」蕭朔今天難得的好興致,並沒計較他言語冒犯,看著下人分揀棋子,「你是那個剛賜了瓊林宴,族中就有人觸法抄斬,被他保下來的?」
蕭朔言語間已提了兩次「他」,御史中丞來不及裝聽不懂,咬牙低頭,「是。」
「王爺。」御史中丞牢牢攥著白子,胸口起伏,「王爺同小侯爺究竟有何恩怨,下官確實不知。可下官還是要說……」
御史中丞將那枚白子落在角星,抬起頭,「進御史臺獄的第一日,小侯爺同下官要了三樣東西。」
蕭朔:「飛虎爪、夜行衣、蒙面巾?」
御史中丞:「……」
「這是三日後才要的!」御史中丞連氣帶惱,拂袖沉聲:「小侯爺整整三天,都沒說要逃!」
蕭朔不知道這種事有什麼可自豪的,看了御史中丞半晌,稍一頷首,又落了一子。
他與雲琅實在太熟,幾乎不用細想,便能猜出十之八九,「太師椅、龍井茶、獸金炭?」
御史中丞:「這是七日後才要的!王爺……」
蕭朔按住棋盤,笑了笑,「說罷。」
面前琰王實在陰晴不定,不知碰上了哪句話,眼下竟又似和緩了幾分。
御史中丞警惕看了他半晌,摸起枚白子,放在棋盤上。
「人是大理寺獄連夜送來的。」御史中丞道:「送來的時候,鐵鎖重鐐,一身病傷。」
蕭朔神色不動,又拾了枚棋子。
「當夜,侍衛司並太師府提審三次。」御史中丞:「太師府主審,侍衛司動刑。一問端王當年暗中行止,二問……昔日脫逃同謀。」
蕭朔看著棋局,手中棋子輕頓,敲了下桌面。
「胡言亂語!」一旁玄鐵衛怒喝,「端王之事,分明已早有定論……」
「兩夜一日,手段用盡。」御史中丞:「小侯爺只要說了同謀,就能免去一死。只要揭發端王……」
玄鐵衛再聽不下去,又要出刀,被蕭朔抬手止住。
御史中丞定定看著蕭朔,臉色煞白。
「揭發端王。」蕭朔道:「如何?」
御史中丞:「下官不知道。」
蕭朔放下棋子,視線落在他身上。
「問到第二日。」御史中丞道:「小侯爺和下官要了三樣東西。」
蕭朔:「什麼?」
御史中丞:「毒酒,寶劍,三尺白綾。」
燭火一跳,屋內靜了靜。
玄鐵衛立在窗前,胸口起伏目眥欲裂。
「下官常恨登科太晚,入朝之時,同戎狄和談已畢,戰火已熄。」御史中丞抬手,又落了一子,「那一日,下官終見少將軍風姿。」
「小侯爺寫了封血書。」御史中丞深吸口氣,「與下官說……他若真死在牢中,就叫下官去殿前撞柱死諫。」
室內愈靜,落針可聞。
蕭朔拈著棋子,視線落在窗外。
幾個玄鐵衛沉默對視,又垂下視線,一人上前,替御史中丞看了座。
「京城安寧久了,禁軍多年沒打過仗。」御史中丞斂衣落坐,「那些人是暗中來的,怕聖上知道,怕犯人身死交不了差,又心虛膽怯……」
蕭朔靜坐良久,忽然出聲,「哪隻手?」
御史中丞愣了愣,「什麼?」
蕭朔看他半晌,笑了一聲。
昔日對弈,雲琅棋力便遠勝於他,行事向來步步縝密。他已足夠提防,卻沒想到雲琅能布局到這麼遠。
困在府中,還能叫御史中丞來編故事求情。
若是不多此一舉,連寫血書這等故事都編出來,說不定當真能唬弄過他。
「他寫血書。」
蕭朔昨夜看得清楚,除了腕間血痕,並沒見雲琅手上有傷,不動聲色落了一子,「哪隻手?」
御史中丞:「下官的手。」
蕭朔:「……」
御史中丞正氣凜然,昂首抬頭。
蕭朔放下棋子,按了按額角。「他用你的手。」蕭朔道:「寫了血書。」
御史中丞坦坦蕩蕩,「是。」
蕭朔:「讓你去殿前撞柱死諫。」
御史中丞問心無愧,「是。」
蕭朔坐了一陣,「來人。」
王府主簿就在門外候著,小跑進來,跪下聽命。
「今日起,繼續探聽朝野消息。」蕭朔道:「近幾年入朝為官的,身分來路,多查一查……」
蕭朔抬頭,「神智。」
御史中丞不料他這等事竟也做得毫不避人,愣愣聽到最後,不由怒從心中起,「下官神清智明!王爺……」
「送客。」蕭朔道:「這副棋子,送給中丞。」
「小侯爺受侍衛司私刑,傷在臟腑。御史臺盡力調理,眾目睽睽,收效甚微!」
御史中丞還想求見雲琅,被連人帶棋往門外推搡,奮力掙扎,「下官受小侯爺大恩,冒死一言,別無他意!王爺不必忌憚下官立場……」
蕭朔原本也並不在意他立場,「病因不清,本王怕傳上。」
「……」御史中丞氣得手腳發抖,來不及說話,已被人請出了門。
文人一怒,禰衡擊鼓。人已被拖得遠了,還能聽見遙遙傳來的捶柱怒斥聲。
王府不見人不迎客,老主簿這些年不曾見過此等陣仗,有些遲疑,「王爺……」
蕭朔起身,走到窗前。
老主簿小心跟上去,「王爺……可還要探查百官?」
「雲琅心思,遠比你們縝密得多。」蕭朔道:「留他在府裡,是為了弄清他身後的人。」
老主簿有心相勸,瞄見蕭朔神色,嚥回去,「是。」
「御史中丞來說不動,他會再想別的手段。」蕭朔神色平淡,「裝病耍賴喊委屈,都是他用慣了的,無非要人要東西,不必心軟。」
老主簿低聲:「是。」
「日夜著人把守,圍牆上嵌一層釘板,尖頭朝上。」蕭朔:「門口多放幾個獵戶用的獸夾。尋個能容人的竹籠,吊在門上,有人推門就掉下來。」
「……」老主簿:「是。」
王爺心思同樣縝密,老主簿不敢再說,低聲告退,快步出門。
走到門口,又聽見蕭朔出聲:「還有。」
老主簿停在門前,屏息凝神等王爺吩咐,還要再怎麼對付雲小侯爺。
「城西醫館。」蕭朔:「有個致仕的太醫。」
老主簿等了半晌,小心翼翼,「叫來拿針扎雲公子嗎?」
「……」蕭朔深吸口氣,閉了閉眼。
老主簿猜錯了,不敢說話,守在一旁。
「叫他來,就說有人胎氣不穩,要他來對症下藥,調理身子。」蕭朔拂開窗前雪色,將剩餘穀粒盡數撒下去,拭淨掌心,「鬧得盡人皆知些,琰王府月前有喜,為保血脈,闔府閉門不出、精心調理……」
「偏在半月前,去御史臺喝茶,叫侍衛司的人打了。」蕭朔眸色冷了冷,淡聲道:「不給說法,御前說話。」
(此為精采節錄,更多內容請見《殿下讓我還他清譽1》)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殿下讓我還他清譽(1)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華文 |
$ 284 |
Books |
$ 284 |
Books |
$ 324 |
中文書 |
$ 324 |
大眾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殿下讓我還他清譽(1)
鎮遠侯府滿門抄斬,小侯爺雲琅逃了五年,一著不慎,落在暗衛手中。
雲琅跪在法場,對著寒光閃閃的鍘刀,情急之下,脫口而出。
「且慢!我懷了琰王的兒子。」
據傳,琰王蕭朔父母早逝,性情殘暴嗜血,手上不知多少冤魂人命,更與鎮遠侯府有不世血仇。
雲琅胡言亂語死裡逃生,從刑場被扛回了琰王府。
燭光下,蕭朔神色陰鷙,眉目冰冷吩咐:「找間上房,撥下人丫鬟,為小侯爺延醫用藥。」
雲琅不好意思,剛要跟他客氣,冷不防聽見最後一句。
蕭朔:「讓他生。」
雲琅張了嘴,欲言又止。
……小王爺的盛情難卻啊!
蕭朔:「那日你將我灌醉後,做了什麼?」
雲琅:「沒有那天晚上!都是編的!」
老主簿:「那您就編啊!隨便編一個不就完了嗎!」
蕭朔:「記下來。」
老主簿:「什麼?」
蕭朔:「《雲公子夜探琰王府》。那晚月色正好,雲公子見琰王月下獨酌,蹲在牆頭上,見色起意。尋了個機會,將酒動過手腳。待琰王喝到半醉,便……」
雲琅此時吐血暈倒在他肩上,氣力已竭,意識昏沉,一隻手拽著他的衣袖。
蕭朔曲臂,虛護了下,靜靜站了一陣。
蕭朔:「投懷送抱,入我懷中。」
商品特色
要麼生、要麼死
少年俠氣。死生同,一諾千金重
血海深仇下是被掩蓋多年的皇權政爭,及兩個少年至死不渝的真心
★口是心非的冰山小王爺X正經不超過五秒的俠氣少年
★晉江積分3.3億、6.4萬書評、11萬收藏、VIP強推古風耽美文,看過都按讚
★書衣封面的窗戶能左右打開,便能看到在王府裡重修舊好的蕭朔和雲琅
★開窗書衣設計概念:
書中常出現「窗戶」這個元素,不論是雲瑯常一言不和就跳窗逃走,或年少時喜歡翻窗進書房找蕭朔玩,或是府外雪虐風饕、府內燈燭安穩。以此為概念,封面畫出王府裡兩人漸漸解開心結後,開始抽絲剝繭調查當年的血案,聯手面對書衣窗外的風雪及王府外來自皇上的猜忌和朝堂陰謀,呈現出王府裡與王府外的兩個世界。
★隨書好禮大方送:
第一重:隨書贈送精美留言卡
第二重:作者獨冢專訪-1,分享創作二三事
第三重:首刷加送開窗書衣,且看王府內的兩人要如何化解往日恩怨,聯手面對王府外詭譎的朝堂局勢
第四重:書衣上有燙金的作者簽名
作者簡介:
三千大夢敘平生
專職做夢,副業寫作,睡眠重度困難戶。
熱愛漫長的行走,熱愛觀察和記錄,理想是成為一個能把故事講好的人。
有三千場夢,三千段講不完的故事,和三千顆不同味道的水果糖。
【封面繪圖】
蓮花落
繪手一枚,喜歡古風,尤其鍾愛武俠,武俠是初心也是白月光。
因為太懶無法走萬里路,所以讓想像縱馬於江湖之間,可以自由持一竹杖任行逍遙。
希望某天筆能長大到畫出喜歡的花草鳥獸和各種好看瀟灑男人,但筆往往不受控是最大的煩惱。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傳聞小侯爺身懷琰王血脈
嘉平元年,冬月,朔日。
汴梁,御史臺。
雪是昨夜停的,凜風捲著嘯了半宿,將京城白茫茫壓了一層。
御史臺人來人往,已經忙碌了整整一個早上。
「卷宗,案冊。」御史中丞親自帶人安排,忙得焦頭爛額,「都要齊備,不准錯漏一樣!囚車鐐銬用新的……沒有就去找!」
尋常犯人不入天牢,進了御史臺獄的,不是位高權重,就是罪大惡極。
御史臺送走了不知多少囚車,出了門走北街,不出一刻就到鬧市法場。今天這等陣仗,還是頭一回。
從半月前人被綁得嚴嚴實實,連夜押進來,侍御史也是頭一次見著這...
嘉平元年,冬月,朔日。
汴梁,御史臺。
雪是昨夜停的,凜風捲著嘯了半宿,將京城白茫茫壓了一層。
御史臺人來人往,已經忙碌了整整一個早上。
「卷宗,案冊。」御史中丞親自帶人安排,忙得焦頭爛額,「都要齊備,不准錯漏一樣!囚車鐐銬用新的……沒有就去找!」
尋常犯人不入天牢,進了御史臺獄的,不是位高權重,就是罪大惡極。
御史臺送走了不知多少囚車,出了門走北街,不出一刻就到鬧市法場。今天這等陣仗,還是頭一回。
從半月前人被綁得嚴嚴實實,連夜押進來,侍御史也是頭一次見著這...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傳聞小侯爺身懷琰王血脈
【第二章】叫太醫來,就說有人胎氣不穩
【第三章】去見小王爺,給他講那月色正好的故事
【第四章】年紀輕輕,既當爹又當娘的少將軍
【第五章】君子報仇,十來年不晚
【第六章】我活著,你就永遠別想著我會把你扔下
【第七章】小王爺,我委屈,抱我一會兒吧
【第八章】沒戲弄你,我想看那本寫了吹參湯的話本
【第九章】小王爺怒氣攻心,硬生生吐了口血出來
【第十章】他這些年,胸中積了不知多少鬱氣
【特別收錄】作者紙上訪談第一彈,分享創作二三事
【第二章】叫太醫來,就說有人胎氣不穩
【第三章】去見小王爺,給他講那月色正好的故事
【第四章】年紀輕輕,既當爹又當娘的少將軍
【第五章】君子報仇,十來年不晚
【第六章】我活著,你就永遠別想著我會把你扔下
【第七章】小王爺,我委屈,抱我一會兒吧
【第八章】沒戲弄你,我想看那本寫了吹參湯的話本
【第九章】小王爺怒氣攻心,硬生生吐了口血出來
【第十章】他這些年,胸中積了不知多少鬱氣
【特別收錄】作者紙上訪談第一彈,分享創作二三事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22/04/17
202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