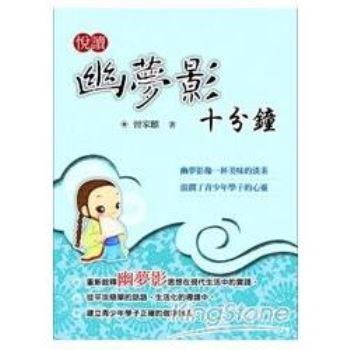金風玉露
這裡,幽靜和閉塞同處一隅。冗長的時日像倒入了甜甜的果漿,即使沉悶也不覺得索然無味
也許是四季如春的氣候,新鮮的空氣成了天然的潤膚乳液,滋潤著從大江南北聚集在這𥚃的人們的面孔。
有一所技術學院,虎落平陽般,聚集著獻了青春又獻終生的一代建設者的子弟。
父輩們的知識和技能似乎在以往的生活中打了水漂,生命只起到響應和服從的作用,理想在現實中坍方。
就在父輩想要把他們貢獻在草徑連四野處時,冰封的黑土地上出現了回暖的跡象,正常的意識在甦醒。高考制度恢愎了,無數囚入平庸和絕望中的心靈正在解鎖。
教育,在對傳統進行了一大輪人為地大批判大掃蕩大割除後,又考慮要在四野荒蕪中恢復生機了。但錄取的門檻及障礙壘得比人還要高。許多考生因為出身、因為血統問題,面前仍竪立著歷史遺留的柵欄,被隔離在正常求學和就業之大門外。
大人們忙著在子女身上重新下注,美名曰:尋找失落了的世界,即使徒勞,也手忙腳亂個不停,找朋友,托關係,把後門敲得砰砰作響,時不時來點預告,各自的美夢想方設法往四面八方延伸。
想盡辦法,能走的就東西南北地去飛,走不了的伺機而動。
這所學院像是一鍋大雜燴,初中生,高中生,社會青年,全部放在一起編班。學生們的年紀參差不齊地擠在一起,純真和庸俗也一股腦地擰在一塊兒。
來這裡的學生誰也沒有太在意是學工程技術,還是機械操作,圖的是走進這裡便有了沾沾自喜的本錢,為未來打了一個端鐵飯碗的長期包票。
子女們不願被上輩人貢獻在這裡,如同在不大的生活之網中撲騰的小魚,心很活躍,見洞就鑽,不能地空雙馳,那就水陸兩棲,做好隨時回歸城市、逃離此地的心理準備。
好在內心自然而然地演奏著靑澀的戀歌,不然枯燥的日子不知該如何過校園生活無聊極了。
教室,實習車間,寢室,每天的生活都在三點一線上周而復始地循環。好在還有一個週末可以回家,可是,茵茵不想看到把愁苦擠在眉宇間的母親的臉。母親總抱怨是父親讓她遠離了城市,可是她忘記了她的「反動階級」出身,只有來到偏遠地區才可以找到活下去的出路,那就是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茵茵想不到要學的專業和自己的理想遙距十萬八千里。她在毫無選擇中學起了鉗工。
第一次的實習,茵茵墊腳站在工作臺前,憋紅了秀氣的面頰,怎麼也端不平一把銼刀。班上,屬她的年紀最小,似乎周身的力氣還未長足。一種挫敗感滲出委屈,令她眼中的淚影不時浮現。想到自己高考中的中文成績是整個地區的第一名,卻落得今後一雙細手可能越挫越粗的後果,難免有些憋屈。但想到同班的楊子昊考上了名牌大學卻被人調包,想到同寢室的小玉考入了一所音樂學院不知是因為逾齡還是外型沒過關而未被錄取,環顧四周,生活中潛伏著諸多不公平、不如意,大家都習以為常地在生活,於是重新端起銼刀,淚水在眼眶中打了幾個轉後,自動回收了。
「我來幫你。」隨聲一個男生上前,幫她把工件在鉗臺上夾牢固,然後端起銼刀推拉起來,鐵屑紛紛落下。
「看到一個本該拿繡花針的手去端銼刀,讓人忍不住想幫幫。」他看一眼周圍都在各自做各自的工件的同學,找了一個幫助茵茵的理由。
「沒有掄大錘,算是走運。」她小聲回應道,很怕周圍其他同學的眼光聚焦在他倆身上。她從中學課本上一早就學到了孔乙己的精神勝利法。
這個男生就是楊子昊,不知被誰首先叫成了昊子,於是茵茵也用昊子來稱呼他。他體魄強健,是校藍球隊的隊員,三步跨欄、矯健如飛的動作,讓場上加油的女生喊啞了嗓音。同寢室的四個女生,除了茵茵,其他三個都是他的啦啦隊員,不知為他拍疼了多少次手掌。茵茵還看過他和老師對奕,舉棋深度思考的樣子,成了他留給她的最佳印象。
她和昊子曾做過小學的同校同學。
「我記得你跟人打過架。」茵茵說時認真,像是在幫昊子喚起回憶。那年他五年級,而她三年級。
「那麼久遠的記憶,你都記得。」
「因為難忘。」
那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有一處垃圾站,經常能看到三個人影在那裡出現:一個精神病患者,另一個四季穿著灰色長袍、剃光的頭頂上有明顯的九個香疤的尼姑,還有一個被人罵作地主狗崽子的小男孩。不知道在那些家家戶戶都倒不出什麼剩飯殘食的垃圾堆裡,他們用木棍能刨出一些什麼有用的東西來。
那天,放學路上,有男生罵撿垃圾的小男孩:地主崽,垃圾鬼。昊子看不過去,上前阻止,打起架來。他的拳頭出擊強硬,打得對方流鼻血。校方亮出強硬的處理方案,給了他一個記過處分,這一下,壞了他的聲譽。
後來昊子隨父母工作調動,換了學校。
以後,茵茵開始留意到那個撿垃圾的和她同齡的小男孩,左臉頰有一粒紅豆大小的肉色胎記,如果擦浄臉上抹花了的泥指印,是一個五官周正的漂亮小男孩。那時,他用力倒吸著可能是因鼻炎引起的總是流不淨的兩條鼻涕,明顯的營養不良,令他看上去比同齡人身型纖薄。
茵茵沒想到和昊子事隔七年又在這裡相遇。在她成長的歲月中,生活的車輪在雜亂無章中緩慢而笨拙地滾動向前。她遇到的人和事就如盤中紅白黃綠幾樣菜色,不同的人品搭配出百般花樣,既簡單又複雜。
她沒有告訴昊子是因為受到他的影響,幾次走近那個撿垃圾的小男孩,把一些讀過的書籍,放在他的炸了邊的竹筐裡。還把一本少年英雄在菜地裡勇鬥偷菜的地主婆的小人書送給他,過後,又有些後悔,不知道裡面講述的內容,那個小男孩看後會是什麼感受?
她無法預知不公平的命運會跟蹤這個小男孩多久?
昊子的父親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因為受到海外關係的牽連而一生鬱鬱不得志。昊子也因伯父在台灣,兩次考上大學都走不進校門,一次政審不合格,遭遇了「不宜錄取」;再次是名額被人頂替了,只能忍氣吞聲。他學會了認命,不去和別人爭高低。體弱多病的母親臨終前拉著他的手,說:「孩子,永遠不要服輸和絕望,要相信自己。」
茵茵知道他的故事後,由衷為他鳴不平。他卻安慰她說:「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要學會在適應中求改變。」
他只是比她大兩歲,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令他在她心中也有了一種份量。她忍不住對著他的側影連看了幾眼,在想:如果那古銅色的肌膚是曬黑的就好了。
可是這種膚色同寢室的小玉喜歡,說這是健康膚色,並美名曰:「男生色。」
那日,昊子把一本線裝本的書遞給她,說是父親的藏書,他只借給她看。書頁已泛黃,倒著翻,竪著看,是繁體字。書頁中有黑白插圖,都是些戴著圍巾,身著長袍馬褂的書生人物。讀完全本,她記得最清楚的是書中最後的一段文字:
來時歡樂去時悲, 空到人間走一回。
不如不來也不去,不如不歡也不悲。
不知是否她從小過早吸入了人世間無情的畫面,抑或是與生俱來就屬於悲天憫人的那類人,從那本線裝書中,她讀出了人間悲情,可昊子說他看出了佛理。
書中,茵茵翻看到昊子寫給她的詩:
我希望你每天都是這樣,
像清晨的露珠,晶瑩透亮。
嘴上有歌聲,歌聲中有歡笑,
歡笑裡灑滿陽光。
「這是寫給你的詩,全詩共三段。」還書時,昊子告訴她。
「第二段呢?」她問得有些漫不經心。
「下次……」昊子的回覆帶省略號,有些餘音繚繞。
「可以告訴我詩名嗎?」
「夢你。」
「太直白了,一點都不含蓄。」
「但很真。」
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從一個男生的眼中讀到了明眸清澈如水。
生活在一起三伏中向前,人心不變才是反常
學校生活疲軟得像一個充氣不足的皮球,即使每天費力地踢,也踢不出一個叫好的歡呼聲,好在有夢想。
女生宿舍,每四人一室。
茵茵這一室,彼此一熟稔,便嘻嬉哈哈個沒完。茵茵發現,同室女生的名字有楓,有玉,有姓陸,有姓金,四個人的名和姓的諧音,可組成「金風玉露」。這一發現,真像是捏麵團一樣把四人合在一起捏出一個親熱來,就差點演繹出女版的桃園四結義了。
剛開始,大家親如姐妹,甚至衣服換著穿。小玉胖,無論穿誰的衣服都像是把一塊平整的布料綁在了身上,沒有寛鬆的餘地,除了招來笑聲,便是加大了她對自己身材的不自信。
只是,不久,大家又各懷心事,更多的時候,陸靑蘋喜歡和徐小玉一同出入,而金茵茵和高楓紅在一起時相談甚歡。
無論是楓紅的羞赧,還是小玉的囈語,靑蘋都微笑以對,似乎在笑彼此不在同一個層次上。每人都可以在她帶笑的神情中,領會出各自解讀出來的意思。
女生生性敏感,使得她們各自都能夠從所妒嫉的女生身上意識到自己某方面的缺陷。漂亮的女生相互之間喜歡暗暗較勁,若和相貌平平的女生在一起,便不容易產生衣服撞色般的無措和窘態。
茵茵和靑頻誰都可以一眼認出來,可班主任卻說茵茵和靑蘋長得像,原本根據成績定奪正副班長,結果把屬於茵茵的副班長職務給了靑蘋,說是認錯人了。茵茵知道,靑蘋有惹人注目的身分——校長的女兒。儘管靑蘋成績不怎麼好,但人情風一來,花香似乎都飄向了她那裡。
茵茵和靑蘋有過一次倆人在一起的時候,是靑蘋叫上她一起上街去買酒,買的是茅台,擺在普通的貨架上。「六塊錢!」酒價貴得令茵茵乍舌。靑蘋只是笑笑,說:「我爸的生日,需要孝敬的。」然後,又笑笑說:「我媽給的錢,走形式。」不過,靑蘋就是消息靈通,她靠近茵茵的耳邊,神秘地說:「妳知道這酒的歷史嗎?我爸說他喜歡喝的是歷史。」見茵茵好奇地想多聽,於是說下去:「這酒廠的老闆是你的同鄉,你不知道吧?三十多年前,因反對公私合營,拔棵草般地說槍斃就把他槍斃了。」靑蘋說她的一個表叔就在這家酒廠工作,說完了這酒的故事,又補充一句:「誰叫他是資本主義的孝子賢孫,肯定要拔除的。」
這冷冷的一席話,聽得茵茵打冷顫,不由地想:歷史中藏著多少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呀!
靑蘋的家離學校很近,不知為什麼她還要選擇住校。她喜歡收集同學們的車票,無意中透露說是可以用來報銷。靑蘋每週都會回家,總會帶來一些吃喝玩樂方面的驚喜。大家都喜歡她做的水果拔絲。她的食物鏈與眾不同,不能吃肉,閉上眼睛都能從食物中嗅得出肉味來,一見肉就作嘔狀,喜歡用各種水果做菜。這次又帶回一玻璃瓶的色彩鮮艷的食物,說:這是沙律。這些新穎的食物名稱令同寢室中的其他三人感到很新鮮。寢室中靑蘋最先使用摩絲髮膠,也最早穿絲光襪。
靑蘋的身上貼滿了南風吹來的時代感。誰都知道靑蘋的母親是閩南人,從那邊隨便帶來一件小物品都會帶來一種新時尚。
茵茵也模仿過一次靑蘋那樣的收集工作,是幫小玉做的,幫忙收集十八歲以上同學的身分證,說是去濱海買股票開戶需要,借用一下,很快就會歸還。那時的股票市場興起不久,正在乘風破浪按照暴發戶的新思路挺進。小玉的叔叔去了沿海地區做貿易生意,收到的新資訊帶動著小玉的頭腦靈活。
面對靑蘋,茵茵有不少自卑。靑蘋烏溜溜的眼睛烏溜溜的頭髮,是歌中唱的那種典型的美少女,而自己的頭髮卻帶棕色,鄰居的奶奶說這是因為缺少太陽中的鈣,於是她拼命去曬太陽,曬得臉都黑紅色了,髮絲依然幼細,始終沒有黑起來。
可同室的小玉不這樣看,很真誠地告訴茵茵:靑蘋沒有你好看,她是運動型,你是文藝型,你比她靈秀。
茵茵不明白班上的雁鳴那麼喜歡靑蘋,靑蘋卻可以無動於衷。只是,她還不知道,靑蘋也有和她類似的疑問:班上那個生龍活虎的陽光男生昊子,為什麼眼光總追逐著茵茵在蹓躂?
內心不斷躁動的時節,靑春就像飄流瓶。
還在成長中的她們,讀了幾句哲理,就以為自己也可以超年齡地高深起來
她們四人在一起時不時還會討論一下有關命運的話題,在烏托邦的世界裡領會著烏托邦。
茵茵發現,自己有時生活在錯覺中,那時說命運有點像是在說巢中羽翼未豐的鳥兒,有些尚早,有點像舉起沒有香檳的酒杯碰出響聲來,只圖聽到一聲清脆的「乾杯」來證明自己的歡喜,自己的存在。
「我喜歡心靈美。」楓紅最先開口,毫不費力地用了一句最流行的教條。小玉笑說這是現實主義。
「訂婚戒指,教堂,婚紗。」靑蘋經常喜歡說這三個詞彙,說時,眸中閃現出耀眼的光亮。小玉說這是理想主義。
「你呢?」茵茵搶先問小玉。
「我?印象主義,崇拜好看的男生。」小玉回答後,轉頭看向在紙上塗鴉的茵茵,說:「你就不用說了,喜歡寫詩,還有人為你寫詩,典型的浪漫主義。」
茵茵聽著,昊子和雁鳴的面容在自己的腦海中輪流浮現。她發現同室四人當中,只有自己的心思還在左右晃蕩,還不能確定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類型的男生。
小玉長得扁鼻子小眼的,一副蔑視世界的樣子。高興時,她會湊在茵茵的耳邊說聲:「靑蘋沒有你漂亮。」不過一個轉身,又跑去學校食堂幫靑蘋打水買飯去了。靑蘋每週回家帶來的酒心巧克力,對小玉不能說沒有誘惑力,在靑蘋身邊多少可以蹭一點嘴中的實惠。
四人也曾一起喝香檳,沒有高腳酒杯,陶瓷碗塑料杯也能碰出歡快的響聲。小玉最初想學茵茵,輕輕優雅地搖晃著花瓷碗中的橙黃色液體,只是碗一放到她唇邊便把優雅打撒,使起從父母那裡遺傳來的東北人豪爽的性子來,一連兩大口,再嘖嘖兩聲:「這葡萄酒像水,不夠勁兒。」
成長中的生命,對未知的事物充滿著好奇。四人有時也會對生辰八字中的命重命輕的運程感興趣。
小玉一邊說著不迷信,一邊翻開從地攤上買來的生辰八字算命書,給大家算起命來。
「靑蘋的命重,四點八兩,富貴命。茵茵命輕了點,三點二兩,會移花接木,欸,移花接木是什麼意思?」小玉的小眼睛在一行文字中聚焦起來,聲調突然間艱澀地滑行:「我怎麼這麼可憐,才二點一兩?而且早年駁雜多端,兄弟少力,哎呀,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呀!」
大家分不清小玉在看命數還是自說自話在演戲,而且說哭還真的流出了一滴眼淚,情緒導入悲傷的系統,整合出一齣微型哭鬧劇。這種戲劇性的變化,令寢室內其他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說什麼是好。
只有當話題轉向男生時,四人的臉上都難以掩飾從興奮中滲出的羞赧,和眸中的好奇一起迸射出幾抹奪目的光彩。哪個少女不懷春?每個人的心中各揣著一個夢想中的男生。
「今天去公共澡堂洗澡,有男生爬梯子從天窗上看過來。」楓紅在鏡前,梳著還未乾透的頭髮,心有餘悸地述說。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夢裡不知是牽手—偏偏錯過的人是你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夢裡不知是牽手—偏偏錯過的人是你
作者簡介:
露西(香港)
原名 左川華(Lucy)
祖籍江南水鄉,在大陸的東南西北不同的地區留下過成長中的足跡,於今工作並生活在香港,是繁華都市中的繁忙一族。原本所學專業工商管理,卻涉足教育領域。長袖善舞於三尺講臺,津津樂道於歷史典故。一直喜歡讀書,有過讀博士的願望,卻放棄了垂手可讀碩士的機會。人生在七拐八彎中走著,總想說點什麼,於是執筆書寫。
章節試閱
金風玉露
這裡,幽靜和閉塞同處一隅。冗長的時日像倒入了甜甜的果漿,即使沉悶也不覺得索然無味
也許是四季如春的氣候,新鮮的空氣成了天然的潤膚乳液,滋潤著從大江南北聚集在這𥚃的人們的面孔。
有一所技術學院,虎落平陽般,聚集著獻了青春又獻終生的一代建設者的子弟。
父輩們的知識和技能似乎在以往的生活中打了水漂,生命只起到響應和服從的作用,理想在現實中坍方。
就在父輩想要把他們貢獻在草徑連四野處時,冰封的黑土地上出現了回暖的跡象,正常的意識在甦醒。高考制度恢愎了,無數囚入平庸和絕望中的心靈正在解鎖。
...
這裡,幽靜和閉塞同處一隅。冗長的時日像倒入了甜甜的果漿,即使沉悶也不覺得索然無味
也許是四季如春的氣候,新鮮的空氣成了天然的潤膚乳液,滋潤著從大江南北聚集在這𥚃的人們的面孔。
有一所技術學院,虎落平陽般,聚集著獻了青春又獻終生的一代建設者的子弟。
父輩們的知識和技能似乎在以往的生活中打了水漂,生命只起到響應和服從的作用,理想在現實中坍方。
就在父輩想要把他們貢獻在草徑連四野處時,冰封的黑土地上出現了回暖的跡象,正常的意識在甦醒。高考制度恢愎了,無數囚入平庸和絕望中的心靈正在解鎖。
...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這裡,幽靜和閉塞同處一隅。冗長的時日像倒入了甜甜的果漿,即使沉悶也不覺得索然無味……
目錄
第一章 金風玉露 8
第二章 各奔西東 40
第三章 城中花絮 59
第四章 同衾為遠 97
第五章 自己買花 123
第六章 繞指情牽 156
第七章 許我淚眼 191
第八章 解鎖生前 221
第九章 玉蘭香散 246
第二章 各奔西東 40
第三章 城中花絮 59
第四章 同衾為遠 97
第五章 自己買花 123
第六章 繞指情牽 156
第七章 許我淚眼 191
第八章 解鎖生前 221
第九章 玉蘭香散 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