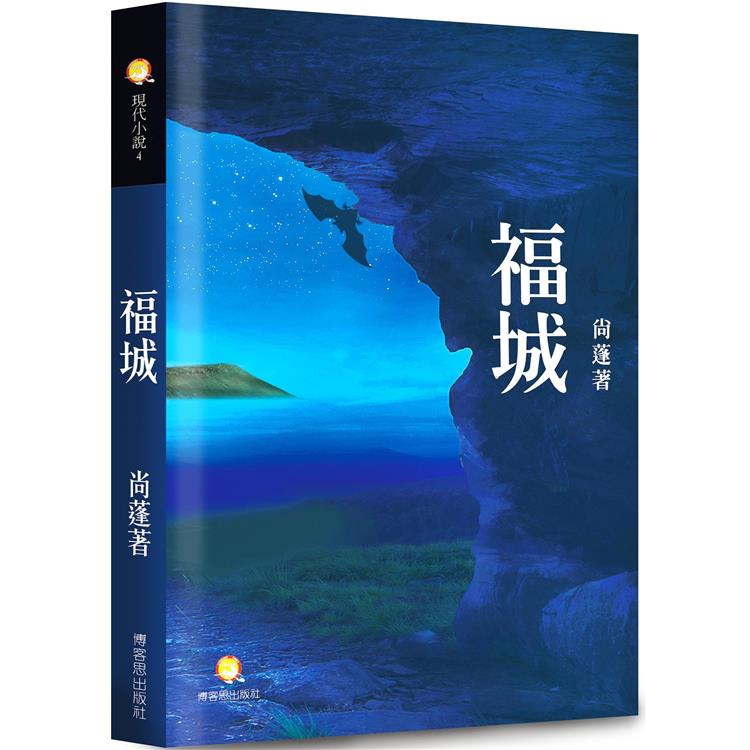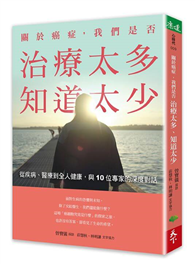蝙蝠選擇一座城,人選擇一種生活。當全球疫情開始,蝠疫捲土重來,封城犧牲一部分關係,成就另一部分關係。人該怎樣活著:承擔責任?追逐自由?做有用的人?為愛情和文學革命?…………
海上,信號飄忽不定,人和人的關係在科技文明下,說散就散。一串不再聯繫的號碼,無意棄置在手機簿上。遺忘,說到底,不過幾個數字。
人走了,想念或懊悔,那都是時間之後的事了。
「什麼叫『永遠地離開』?」福靖打開窗,雪從高處飄落。
人們的目光習慣向上看,忘了底下才最重要。
晚上沒有陽光。明天,雪自己會化。
「我們刻意把自己活成了書裡的樣子,明知幻想會破滅……」麋洋希望野治幸福,那麼她的知難而退就很值得,「拙劣的模仿是不需要負責的。」
「還能怎樣?」麋洋從學校門口往下繞,沿著山路走向大海,「讀了那麼多書又能怎樣?」
大海只不過是人類美好的嚮往。到了那裡,同樣存在生物鏈。島上的階層分化不比城市弱:歧視、垃圾、犯罪、強姦、病毒……所有城市有的毛病,島嶼和大海一樣都不會少。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福城:福城,疫情下的世界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福城:福城,疫情下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