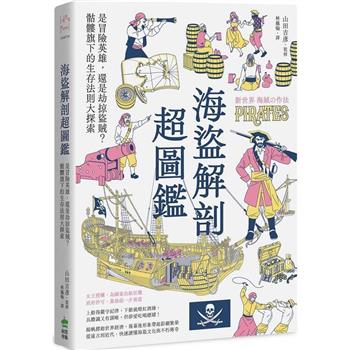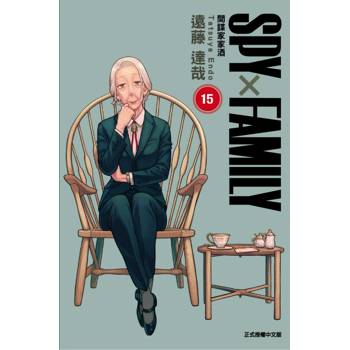一代名伶李香蘭的戰爭、電影與歌
傳奇背後的少女歌手,她的親情、友情與愛情
山口淑子揮別童年玩伴,舉家從撫順遷往奉天。此時沒有人知道,這位日籍工程師的次女,將一步步成為那個為人熟知的傳奇,李香蘭。
李香蘭這個名字,來自將她收為義女的滿籍將軍。她的天籟歌聲,習自友伴介紹的俄籍聲樂家。在一場音樂會嶄露頭角之後,她成為奉天廣播女歌手,又被新京滿映網羅為女演員,與日本東寶、松竹合作拍片,主演多部電影。她數度赴日舉辦演唱會,轟動一時。之後轉籍上海華影,在大光明大戲院開演唱會,亦是盛況空前。
她曾與貴公子松岡謙一郎熱戀。又於24歲辭離滿映之際,與護衛兒玉英水死別前夕擦出戀花。
戰後,年方25歲的她,歷經漢奸審判,一度面臨死刑威脅,幸得舊友協助取得戶籍謄本,方獲判無罪。在那場可以說是時代造就的審判之後,她被迫搭上客輪,揮別這片她生長、熟悉的土地。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亂世麗人李香蘭(壹)鶯啼春曉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亂世麗人李香蘭(壹)鶯啼春曉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大荒
本名林國隆,苗栗縣頭份客家人,1951年生,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學國文教師、工廠作業員、報社、出版社校對、編輯,現任職《客家》雜誌。早年以筆名雪眸寫作,著有短篇小說集《明天》、《有情》、《擱淺在君懷》、《離愁》和長篇小說《惡淵荒渡》、《悲劇台灣》、《坦克車下》等書,另以本名譯有《手相開運術》一書。停筆20年後,2014年春開始蒐集《亂世麗人李香蘭》資料,2014年3月動筆,2022年4月文稿底定,決以新筆名「大荒」發表。
大荒
本名林國隆,苗栗縣頭份客家人,1951年生,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學國文教師、工廠作業員、報社、出版社校對、編輯,現任職《客家》雜誌。早年以筆名雪眸寫作,著有短篇小說集《明天》、《有情》、《擱淺在君懷》、《離愁》和長篇小說《惡淵荒渡》、《悲劇台灣》、《坦克車下》等書,另以本名譯有《手相開運術》一書。停筆20年後,2014年春開始蒐集《亂世麗人李香蘭》資料,2014年3月動筆,2022年4月文稿底定,決以新筆名「大荒」發表。
目錄
1931 年
1. 遙想礦難 觀露天採 14
2. 日軍入侵 小遊奉天 23
1932 年
3. 柳芭來信 闔家歌舞 34
4. 夜來騷亂 母子驚魂 41
5. 文雄被押 飭回失業 50
6. 家移奉天 將軍宴迎 57
7. 喜見柳芭 山家來訪 64
8. 父戀詩酒 女讀三國 74
1933 年
9. 淑子認親 名李香蘭 84
10. 奉天影院 連番見識 92
11. 肺病住院 幼妹誕生 102
12. 柳芭帶路 擺脫謠曲 111
13. 俄女授課 苦學聲樂 120
14. 巧遇淡谷 午茶歡暢 131
15. 淑子試衣 樂會開嗓 140
16. 受邀錄唱 父有意見 150
17. 電臺試聲 友家遭難 161
1934 年
18. 新春誌趣 揮別父親 172
19. 風雨列車 飄搖過河 183
20. 親炙古都 住進潘家 194
21. 胡同賞景 初學騎馬 204
1935 年
22. 騎遊三海 闔家外浴 216
23. 豐臺事件 山家關心 225
24. 明公造訪 初遊太廟 233
25. 訪客驚魂 反日潮起 242
26. 宅院偷閒 街頭熱戰 251
1936 年
27. 寒假逍遙 校園蕩漾 264
28. 瀛臺茶會 內心呼喚 270
1937 年
29. 中日交戰 愛澤來訪 282
30. 北平陷落 總裁開示 292
31. 陪父赴津 邂逅川島 299
32. 潘家低調 窗誼續敘 306
1938 年
33. 潘掌天津 愛澤示警 314
34. 共餐山家 聆辦報事 320
35. 再會山家 無所不談 328
36. 遊頤和園 聽晚清事 336
37. 會見川島 夜遊累癱 345
38. 再會山家 說川島事 356
39. 女校遭炸 初識李明 364
40. 逐夜奢靡 義父譴返 372
41. 滿映有請 揮別潘家 383
42. 搭車赴都 長官熱迎 393
43. 被騙試鏡 主角上身 403
44. 練主題曲 訪訓練所 413
45. 行車拍片 頻頻叫停 421
46. 潘府敘舊 雙親探班 431
47. 親子車遊 京城明媚 442
48. 同仁互動 初識曉君 454
49. 李明找碴 香蘭重訓 464
50. 風塵僕僕 訪日風光 473
51. 倉惶登臺 四處拜會 479
52. 四處演出 回程憶思 487
53. 談影世家 驚憶地震 496
54. 雙李結怨 蘭展氣度 503
1939 年
55. 獻機義演 李明回歸 514
56. 雙姝雙寶 遠征阪神 522
57. 躍上寶塚 新戲開拍 530
58. 勤練學能 初識久米 537
59. 作家赴宴 香蘭醉酒 545
60. 車站送別 不實宣傳 555
61. 暢遊大廟 交心一夫 563
62. 初識岩崎 續拍順利 575
63. 香蘭探訪 稔嗆甘粕 584
64. 訪泰次郎 遊園上野 596
1. 遙想礦難 觀露天採 14
2. 日軍入侵 小遊奉天 23
1932 年
3. 柳芭來信 闔家歌舞 34
4. 夜來騷亂 母子驚魂 41
5. 文雄被押 飭回失業 50
6. 家移奉天 將軍宴迎 57
7. 喜見柳芭 山家來訪 64
8. 父戀詩酒 女讀三國 74
1933 年
9. 淑子認親 名李香蘭 84
10. 奉天影院 連番見識 92
11. 肺病住院 幼妹誕生 102
12. 柳芭帶路 擺脫謠曲 111
13. 俄女授課 苦學聲樂 120
14. 巧遇淡谷 午茶歡暢 131
15. 淑子試衣 樂會開嗓 140
16. 受邀錄唱 父有意見 150
17. 電臺試聲 友家遭難 161
1934 年
18. 新春誌趣 揮別父親 172
19. 風雨列車 飄搖過河 183
20. 親炙古都 住進潘家 194
21. 胡同賞景 初學騎馬 204
1935 年
22. 騎遊三海 闔家外浴 216
23. 豐臺事件 山家關心 225
24. 明公造訪 初遊太廟 233
25. 訪客驚魂 反日潮起 242
26. 宅院偷閒 街頭熱戰 251
1936 年
27. 寒假逍遙 校園蕩漾 264
28. 瀛臺茶會 內心呼喚 270
1937 年
29. 中日交戰 愛澤來訪 282
30. 北平陷落 總裁開示 292
31. 陪父赴津 邂逅川島 299
32. 潘家低調 窗誼續敘 306
1938 年
33. 潘掌天津 愛澤示警 314
34. 共餐山家 聆辦報事 320
35. 再會山家 無所不談 328
36. 遊頤和園 聽晚清事 336
37. 會見川島 夜遊累癱 345
38. 再會山家 說川島事 356
39. 女校遭炸 初識李明 364
40. 逐夜奢靡 義父譴返 372
41. 滿映有請 揮別潘家 383
42. 搭車赴都 長官熱迎 393
43. 被騙試鏡 主角上身 403
44. 練主題曲 訪訓練所 413
45. 行車拍片 頻頻叫停 421
46. 潘府敘舊 雙親探班 431
47. 親子車遊 京城明媚 442
48. 同仁互動 初識曉君 454
49. 李明找碴 香蘭重訓 464
50. 風塵僕僕 訪日風光 473
51. 倉惶登臺 四處拜會 479
52. 四處演出 回程憶思 487
53. 談影世家 驚憶地震 496
54. 雙李結怨 蘭展氣度 503
1939 年
55. 獻機義演 李明回歸 514
56. 雙姝雙寶 遠征阪神 522
57. 躍上寶塚 新戲開拍 530
58. 勤練學能 初識久米 537
59. 作家赴宴 香蘭醉酒 545
60. 車站送別 不實宣傳 555
61. 暢遊大廟 交心一夫 563
62. 初識岩崎 續拍順利 575
63. 香蘭探訪 稔嗆甘粕 584
64. 訪泰次郎 遊園上野 596
序
自序
嘔心瀝血 九轉丹成
記得1995年寫完最後一篇小說,第二年在上班的報社副刊發表後,迄今沒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中年娶了陸妻後,際遇如故,寒酸生活一直未見起色,陸妻失望之餘,對我的寫作提不起興味,兩子陸續誕生長大,在去中體系的教育下,除了不依我的調教,偏離雍容和穆,加上上班的報社,工作環境不是很友善,動輒得咎,工作壓力特大,動了一二十年的筆,就此擱下,說不寫就不寫。
2013年12月飲食、服藥失當,致血壓驟降,鬼門前走一遭,出院後身心難免恍然,不太專心,工作時在網上點了一首李香蘭的歌,忘了是〈支那之夜〉還是〈紅色的睡蓮〉。細如游絲的歌聲立馬扣緊我的心弦。李香蘭,我大學時就聽聞過,也知道她是日本人,但沒聽過她的歌。就像過往尋覓胡琴音帶、光碟一樣,我對美聲的追尋往往會熱一陣子。想到過往漫長歲月對她的「漠視」,除了她的歌,網上有關她的報導、故事,是越看越感興趣,待看過日本影星上戶彩和澤口靖子主演的她的影片後,寫她故事的願念油然而生。
這時李香蘭,或者說山口淑子還在世,但已93高齡,為了寫她,開始尋找資料,網上關於她的資料是越查越多,光是《李香蘭和支那之夜~名曲・蘇州夜曲之謎的解讀~》(《李香蘭支那夜~名曲・蘇州夜曲謎解~》,以下簡稱《李謎》。此作似乎只存在於網路,隨著時日的推移,不斷增生新的內容,表現新的內容時又把以前用過的資料拿來襯托,在網路不斷有機生長,應該不會印成紙本)大部頭作,我就下載到手軟。我將檔案巨大的《李謎》系列文章分成四夾,約有150萬字,但也僅為近八九年收集的龐雜資料的一小部份。此巨著文圖除了討論她在《支那之夜》暨多部代表作的演出,兼及生平種種,內容博雜,迭有重複,但也不難看出她在日本的人氣。全面下載李香蘭資料的結果,2014年就蒐集了逾10G的量,以後七八年陸續加載,購買影音檔。最後,以她為中心的人事物文字、影音資料達25G。
關於她的書或自傳,我儘量找來看。實體書,臺灣商務印書的《李香蘭自傳 戰爭、和平與歌》(以下簡稱《自傳》)看來平淡,上海文化出版的《此生名為李香蘭》(以下簡稱《此生》)帶有一些秘辛,臺灣書房的《李香蘭的戀人 電影與戰爭》(以下簡稱《李戀》)一書,作者田村志津枝對李香蘭成見甚深,讀來甚是不悅,相反的,北京團結出版社的《那時的寂寞 一代名伶李香蘭》一書,作者蕭菲甚是喜歡香蘭,書的內容多從李香蘭的傳記擷取改寫,參考性不高,但讀來賞心悅目。
當然拙作最重要的參考書物還是李香蘭本人和藤原作彌合寫的《李香蘭 私半生》(商周出版,以下簡稱《李傳》)。此書從她童年寫到她二戰後離開上海,與拙作《亂世麗人.李香蘭》(以下簡稱《亂世麗人》)對李香蘭敘事的時間範疇若符合節。至於網路小說〈滿映影星〉,情節恣意誇大,有些固然精彩,合情合理,但稗官野史,不敢引以為參考。
2014年春節過後開始蒐集資料,並加以整理分類,第二年春節過後,按捺不住寫作的心,懷著停筆20年後開工誌慶的心情開始動筆,起初摸擬東京電視播放的《李香蘭》劇的情節書寫,大概一兩個禮拜過後,開始以《李傳》一書提供的情節布局,邊寫邊揚棄先前寫的文字,將辛苦蒐集的資料依序融入,開始形成自己的敘事方式。《亂世麗人》和《李傳》、一般李香蘭的影片一樣,從她918事變前夕的童年寫到她1946年3月被遣送回日本為止。這期間,她藝人生涯七年多一點,其中在滿映就佔去六年一季。本序言提到的李香蘭基本上就是這時期的青年李香蘭。
鋪陳的情節屬虛構,但有所本,主要以《李傳》為藍本,再參酌其他書本、影音、文字資料開展故事。情節展開的過程,把《李傳》或其他傳記中的一兩句她或相關人物講的話語或敘述,巧妙地織進人物的對話或敘事裡頭。
上戶彩和澤口靖子主演的李香蘭電影,分別是《李香蘭》和《(再見)李香蘭》。當然,它們情節有的很迷人,但若不符《李傳》所載,或過於誇飾,個人還是不予採用。兩片中,李香蘭聞知護衛兒玉英水被徵召赴菲律賓前線,一時都非常激動,突然衝破謹守三四年的工作理智線,撲倒在兒玉懷裡。事實上,《李傳》、《自傳》和《此生》三本傳記都未書及此,若真有此情節,為了加深她對兒玉的懷念,李香蘭應該不會保留。她僅在《李傳》中透露出一點她和兒玉僅有的一點親密:兒玉送她回家途中,見她跌倒,順手把她扶起時,牽起她的手。這時她才滋生浪漫的情愫。這種文學性的輕描淡寫確實不若戲劇性的演出,但問題是,牽完手的第二天一早,兩人在車站死別。這場永別,香蘭著墨甚少。顯然在層層管制下,只是看著他搭上火車,沒有悱惻的話別場景,只是揮手看著他隨著車子逐漸遠去。這種在戲劇上的貧乏,在人情上的憾恨,反而留給文學綿綿的憶思,內心無盡的纏綿。
寫作《亂世麗人》,雖然以《李傳》(為了敘述方便,此處的《李傳》視同李香蘭)為圭臬,但還是有些微地方違拗了她,因為根據資料和推論,她應該記錯了。
《李傳》91-93頁,對當年日本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作家群和獨立作家久米正雄訪問滿映,同時接受酒宴招待一事有些描述。懇話會成立於1939年2或3月,久米正雄和田村泰次郎年譜所載,他們隨懇話會赴新京時在1939年6月,我最初執筆時描述這一段時,定時1939年6月。所以宴後第二天清晨「我還是冒著零下15度的大雪,用厚圍巾包住整張臉,穿著大外套……」(《李傳》93頁)這種冬晨車站送行的情節,我就沒採用。設若懇話會2月或3月剛成立,田村等人即隨團來新京,那時李香蘭連《東遊記》都還沒拍,怎可能和作家久米正雄討論《白蘭之歌》的拍攝事宜。
警方辦案,發現新的事證會重啟調查,我寫這一段文字時也一樣。重看久米年譜時發現《白蘭之歌》編劇木村千依男當年隨久米來訪新京,拙作據以修正時乃用久米口頭敘述的方式把木村輕輕帶入,且言明木村提前返日。稿子動了一點小手術過了關,不久再看《李戀》一書102頁,木村和久米都赴滿映宴,也看了宣詔節晚會,對香蘭演唱有印象深刻的描述,再翻閱以前參考過的〈三重大學人文學部紀要〉,幾經考慮決採用大陸開拓懇話會第一次視察旅行「1939年4月25日從東京出發,5月1日到新京,2日參加國民大會,夜宿中央飯店,然後再往哈爾濱進發這一時間序來鋪寫中央飯店的滿映宴。作家宴從6月變5月,改寫時,木村如實寫入,寫完後,又覺得有違《李傳》、《李戀》兩書書明懇話會作家是從哈爾濱回來,返日回程順道訪滿映的說法,和木村、久米年譜表明的6月和李香蘭會面也不合。決定再改寫,情節的鋪陳變成懇話會和久米5、6月都去了滿映,5月的輕描淡寫,6月份回程前往拜會後的洗塵宴,自然詳細鋪寫,同時用回想的方式帶出木村對李香蘭在5月1日宣詔晚會唱歌的印象,符合《李傳》、《李戀》兩書所述,懇話會作家回程途中順訪滿映,木村和久米兩作家年譜6月會香蘭的紀錄。
不管怎樣改寫,滿映給作家的洗塵宴和車站送別的時間點都勾不到冬雪的天氣。前文提及,宴會當時也在討論電影《白蘭之歌》。作家群接受滿映酒宴時,木村、久米的劇本和原作,都寫得差不多,原作1939年8月3日東京日日新聞連載到40年1月9日,久米6月宴後返日,將小說收尾交報社刊行,時間吻合。如依《李傳》所寫,香蘭在雪晨送別作家,當年11月到第二年2或3月,久米的小說可能已經連載或連載結束,和《李傳》所說的書「尚未寫成」也相矛盾。值得一提的是,《李傳》說到該酒宴的章節時說:「我對那未曾謀面的祖國產生深深憧憬,並且決定無論如何,非到日本走走看看不可。」事實上,酒宴當時她已去過日本兩趟,期間都很長。想來香蘭書寫《李傳》時,部份依據印象式的記憶,未作嚴格考證。行文至此。想說的是,寫作《亂世麗人》對《李傳》依賴甚深,但對其中有些印象式、不夠精確的描述,還是持保留態度。
為了寫李香蘭,除了網上的文字和一般書面資料、影音,尤其是電影,能找到就看。寫作的八九年期間,共下載了十部她演出的電影,計2.83G,17部電影片段,計0.47G。寫作的中後期,網上下載的《莎韻之鐘》的日語對話聽來吃力,網查後,透過亞馬遜日本買了(koalabooks)的《莎韻之鐘》DVD,但無論怎麼放,還是讀不到中文字幕,影片分成好幾部,畫質跟下載的差不多,但沒多久,畫面變模糊。《亂世麗人》寫到後段,李香蘭演出《戰鬥的大街》、《誓言的合唱》和《野戰軍樂隊》時,取得的文字資料甚少,遑論網上的影音資料,好不容易在網路廣告看到販售《野戰軍樂隊》的廣告,向龍騰影音多媒體買了影片,結果發現李香蘭在整部67分鐘的電影裡頭只出現3分8秒的一次,唱了一首歌。一開始有些失望,但想想這個特色依舊可以營造一些情節,還是如獲至寶。蓋1944年3月,斷斷續續拍了一年四個月的《我的夜鶯》殺青後,直到1945年6月大光明大戲院的「李香蘭歌唱會」,女主角這16個月的演藝歲月,若沒有《野戰軍樂隊》軋一腳,會變得很貧乏,有了這部電影,故事後段的推進多了一個支點,情節的蠕動多了一股推力。書寫至此才發現,這兩部買來的影片檔案都很大,每一部超過3.5G,遠遠超過我下載李香蘭大小影片的總和,兩者加起來7.2G。印象中,寫作期間資料蒐集總量維持好幾年10幾G,最近檢視,總量已達25G,想來主要是這兩部電影作祟。
李香蘭演出的所有電影,都是在籍滿映的六年一季的時間內,她是滿映人,所以我對滿映資料的蒐集一直很費力。寫作本作前,筆者透過網路、影片對滿映有些了解,寫作途中,對網上古市雅子寫的《「滿映」電影研究》多所參考。此作對於滿映各階段的行事風格、人事變遷著墨甚多。大概寫到第二三遍時,也在網上發現了滿映演員張奕編著的《滿映始末》。這本書每節敘述一個小故事,從滿映創始寫到長春電影製片廠,也就是從作者少年寫到他退休的70幾歲,前半段章節,透露出來的滿映和李香蘭的秘辛很多,採用後也將李香蘭形塑得更生動,有情味。
香蘭演了許多電影,筆者無可避免地常把她演出的過程帶進情節。要如此書寫,除了要看過她演出的電影外,也得關注相關的文件資料,寫《支那之夜》時,得助於《李謎》裡頭的文章不少,寫《我的夜鶯》時,網上渡邊直紀的《滿映哈爾濱表象-李香蘭主演《我的夜鶯》論》(《満映映画表象-李香蘭主演『私鶯』論》)針對那部電影給了很多深入的解讀。《亂世麗人》從頭到尾,校寫了五遍,大概寫到第三遍時,才在網路發現這本小冊子,囫圇吞棗,急於書寫,全書第五遍校寫完畢,整理這篇序言時,才發覺資料引用不確實,拙作在《我的夜鶯》這一敘述段,只好開刀式的刪修,加了蘇聯紅軍追捕白俄流亡劇人的戲碼。此外,《我的夜鶯》這部戲還有兩處戲中戲,電影裡頭的大小角色在片中演出歌劇,戲中劇劇情的敘述和詠唱,大大得力於〈古諾:浮士德/名曲如繁星的大歌劇〉和〈THE QUEEN OF SPADES〉(〈黑桃皇后〉)兩文。寫作當時想:日俄籍演員混編的劇組呈現《我的夜鶯》的攝錄已經很困難了,何況是戲中劇,這兩篇文章的出現讓戲中劇的書寫有了脈絡可循,心裡的大石終於放下一些。
李香蘭從影的七年當中,南下中國電影中心滬蘇一帶拍片共五次,第五次轉籍上海華影時,戰局吃緊,片子拍不成,第三次來滬時寄籍華影前身的中聯,拍了《萬世流芳》。拍《萬世流芳》的過程,除了電影本身和《李謎》內相關報導外,《湮沒的悲歌 「中聯」、「華影」電影初探》一書也起了很大的參考作用。此書圖文並茂,對於中聯、華影相互傳承,兩公司組織、製作的電影,和演員相互間,演員、官長之間的互動,詮釋甚多,尤其在日本侵華的大環境下,華日電影交流對電影製作和演員的衝擊,更有深刻的探討,故本作描述1942年秋香蘭在上海拍攝《萬世流芳》的那一段時日,多了一些內察中聯內部活動,仰視時代氛圍的視角。這些元素在1945年香蘭正式入籍華影時還是適用。
香蘭南下拍片,除了滬蘇行外,到臺灣算是另類的一次。當時旅滿日人鮮少有機會來臺灣,她一人就來過兩次,且滯留相當長時間。看過電影《莎韻之鐘》後,對她當時拍攝該片時的住居環境、生活情況有了概略性的了解,再參考《李謎》內系列文章、其他零星資料,以拍攝該片為中心的動態場景大體完成,整部小說大概書寫第三遍時,買了《流轉家族 泰雅公主媽媽和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一書。這本書對於當時霧社一帶泰雅各部落間,官警、部落間的互動有著脈絡分明的描述,揉進了這層基底,當時霧社小社會的結構就更扎實了。此書作者下山一,與香蘭同一世代,未被筆者寫入本作中,但他妹夫佐塚昌男(原日混血)一家悉數入列。書中提到佐塚昌男接受徵召前往南洋,香蘭和劇組人員特地到臺中農改所歡送。獲訊喜出望外,當即另闢一小節書寫歡送會。
青年李香蘭的職業是演員,所以她事蹟的鋪陳,拍片是主軸,但形成她藝術顛峰的還是歌唱。當時她最重要的演唱會有四場:初出道,在東京高島屋百貨舉行的亞洲資源博覽會和日本劇場演唱會,《李謎》系列文章:〈昭和13年李香蘭「満州資源博覧会」前後篇〉、〈李香蘭初來日〉、〈初來日印象〉……著墨甚多,兩三年後的日本劇場演唱造成騷亂,《李謎》內的〈再考 日劇七周半(七圈半)事件〉系列文章,也把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影響寫得很清楚。有了第一手資料,這兩場以日本劇場為主的演唱會,個人寫來自然深入,且得心應手。同樣《李謎》裡頭〈臺灣李香蘭〉一文、《李戀》一書相關章節和其他文章,也將李香蘭1941年元月來臺巡迴演唱理出了時間軸,方便了系列場景的鋪敘。1945年6月上海大光明大戲院的「李香蘭女士歌唱會」,除了《李傳》,京都大學〈從中國音樂史上消失的流行歌:再一場夜來香狂想曲〉(〈中国音楽史から消えた流行歌:もう一つの「夜来香ラプソディー」〉)一文也給了我一點養份,演唱會得以順利呈現。
依佛家觀點,李香蘭乃因緣和合而生,個人才具配合大環境,因緣俱足,才會有波瀾壯闊的一生,青年李香蘭尤然。如今因消緣散,美人已遠。同理,個人才具不足,經過一番構思,編織文字,同時把前輩、先賢的相關資料摶成《亂世麗人》,也是一番因緣和合的過程和結果。書寫該作時,由於急於動筆,資料引述不確實,開刀式重寫的部份難以勝數。整部作品書寫了五六遍,第一到第四遍,逐字校對,根據新的資料修繕、增補,寫第五遍時,作重點式的修校。書成,整理序言時,發覺很多資料引用瑕疵,只好忍痛剖文修補。如今序就書成,八九年的夜長夢多落幕,欣然迎向另一階段的試煉。
嘔心瀝血 九轉丹成
記得1995年寫完最後一篇小說,第二年在上班的報社副刊發表後,迄今沒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中年娶了陸妻後,際遇如故,寒酸生活一直未見起色,陸妻失望之餘,對我的寫作提不起興味,兩子陸續誕生長大,在去中體系的教育下,除了不依我的調教,偏離雍容和穆,加上上班的報社,工作環境不是很友善,動輒得咎,工作壓力特大,動了一二十年的筆,就此擱下,說不寫就不寫。
2013年12月飲食、服藥失當,致血壓驟降,鬼門前走一遭,出院後身心難免恍然,不太專心,工作時在網上點了一首李香蘭的歌,忘了是〈支那之夜〉還是〈紅色的睡蓮〉。細如游絲的歌聲立馬扣緊我的心弦。李香蘭,我大學時就聽聞過,也知道她是日本人,但沒聽過她的歌。就像過往尋覓胡琴音帶、光碟一樣,我對美聲的追尋往往會熱一陣子。想到過往漫長歲月對她的「漠視」,除了她的歌,網上有關她的報導、故事,是越看越感興趣,待看過日本影星上戶彩和澤口靖子主演的她的影片後,寫她故事的願念油然而生。
這時李香蘭,或者說山口淑子還在世,但已93高齡,為了寫她,開始尋找資料,網上關於她的資料是越查越多,光是《李香蘭和支那之夜~名曲・蘇州夜曲之謎的解讀~》(《李香蘭支那夜~名曲・蘇州夜曲謎解~》,以下簡稱《李謎》。此作似乎只存在於網路,隨著時日的推移,不斷增生新的內容,表現新的內容時又把以前用過的資料拿來襯托,在網路不斷有機生長,應該不會印成紙本)大部頭作,我就下載到手軟。我將檔案巨大的《李謎》系列文章分成四夾,約有150萬字,但也僅為近八九年收集的龐雜資料的一小部份。此巨著文圖除了討論她在《支那之夜》暨多部代表作的演出,兼及生平種種,內容博雜,迭有重複,但也不難看出她在日本的人氣。全面下載李香蘭資料的結果,2014年就蒐集了逾10G的量,以後七八年陸續加載,購買影音檔。最後,以她為中心的人事物文字、影音資料達25G。
關於她的書或自傳,我儘量找來看。實體書,臺灣商務印書的《李香蘭自傳 戰爭、和平與歌》(以下簡稱《自傳》)看來平淡,上海文化出版的《此生名為李香蘭》(以下簡稱《此生》)帶有一些秘辛,臺灣書房的《李香蘭的戀人 電影與戰爭》(以下簡稱《李戀》)一書,作者田村志津枝對李香蘭成見甚深,讀來甚是不悅,相反的,北京團結出版社的《那時的寂寞 一代名伶李香蘭》一書,作者蕭菲甚是喜歡香蘭,書的內容多從李香蘭的傳記擷取改寫,參考性不高,但讀來賞心悅目。
當然拙作最重要的參考書物還是李香蘭本人和藤原作彌合寫的《李香蘭 私半生》(商周出版,以下簡稱《李傳》)。此書從她童年寫到她二戰後離開上海,與拙作《亂世麗人.李香蘭》(以下簡稱《亂世麗人》)對李香蘭敘事的時間範疇若符合節。至於網路小說〈滿映影星〉,情節恣意誇大,有些固然精彩,合情合理,但稗官野史,不敢引以為參考。
2014年春節過後開始蒐集資料,並加以整理分類,第二年春節過後,按捺不住寫作的心,懷著停筆20年後開工誌慶的心情開始動筆,起初摸擬東京電視播放的《李香蘭》劇的情節書寫,大概一兩個禮拜過後,開始以《李傳》一書提供的情節布局,邊寫邊揚棄先前寫的文字,將辛苦蒐集的資料依序融入,開始形成自己的敘事方式。《亂世麗人》和《李傳》、一般李香蘭的影片一樣,從她918事變前夕的童年寫到她1946年3月被遣送回日本為止。這期間,她藝人生涯七年多一點,其中在滿映就佔去六年一季。本序言提到的李香蘭基本上就是這時期的青年李香蘭。
鋪陳的情節屬虛構,但有所本,主要以《李傳》為藍本,再參酌其他書本、影音、文字資料開展故事。情節展開的過程,把《李傳》或其他傳記中的一兩句她或相關人物講的話語或敘述,巧妙地織進人物的對話或敘事裡頭。
上戶彩和澤口靖子主演的李香蘭電影,分別是《李香蘭》和《(再見)李香蘭》。當然,它們情節有的很迷人,但若不符《李傳》所載,或過於誇飾,個人還是不予採用。兩片中,李香蘭聞知護衛兒玉英水被徵召赴菲律賓前線,一時都非常激動,突然衝破謹守三四年的工作理智線,撲倒在兒玉懷裡。事實上,《李傳》、《自傳》和《此生》三本傳記都未書及此,若真有此情節,為了加深她對兒玉的懷念,李香蘭應該不會保留。她僅在《李傳》中透露出一點她和兒玉僅有的一點親密:兒玉送她回家途中,見她跌倒,順手把她扶起時,牽起她的手。這時她才滋生浪漫的情愫。這種文學性的輕描淡寫確實不若戲劇性的演出,但問題是,牽完手的第二天一早,兩人在車站死別。這場永別,香蘭著墨甚少。顯然在層層管制下,只是看著他搭上火車,沒有悱惻的話別場景,只是揮手看著他隨著車子逐漸遠去。這種在戲劇上的貧乏,在人情上的憾恨,反而留給文學綿綿的憶思,內心無盡的纏綿。
寫作《亂世麗人》,雖然以《李傳》(為了敘述方便,此處的《李傳》視同李香蘭)為圭臬,但還是有些微地方違拗了她,因為根據資料和推論,她應該記錯了。
《李傳》91-93頁,對當年日本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作家群和獨立作家久米正雄訪問滿映,同時接受酒宴招待一事有些描述。懇話會成立於1939年2或3月,久米正雄和田村泰次郎年譜所載,他們隨懇話會赴新京時在1939年6月,我最初執筆時描述這一段時,定時1939年6月。所以宴後第二天清晨「我還是冒著零下15度的大雪,用厚圍巾包住整張臉,穿著大外套……」(《李傳》93頁)這種冬晨車站送行的情節,我就沒採用。設若懇話會2月或3月剛成立,田村等人即隨團來新京,那時李香蘭連《東遊記》都還沒拍,怎可能和作家久米正雄討論《白蘭之歌》的拍攝事宜。
警方辦案,發現新的事證會重啟調查,我寫這一段文字時也一樣。重看久米年譜時發現《白蘭之歌》編劇木村千依男當年隨久米來訪新京,拙作據以修正時乃用久米口頭敘述的方式把木村輕輕帶入,且言明木村提前返日。稿子動了一點小手術過了關,不久再看《李戀》一書102頁,木村和久米都赴滿映宴,也看了宣詔節晚會,對香蘭演唱有印象深刻的描述,再翻閱以前參考過的〈三重大學人文學部紀要〉,幾經考慮決採用大陸開拓懇話會第一次視察旅行「1939年4月25日從東京出發,5月1日到新京,2日參加國民大會,夜宿中央飯店,然後再往哈爾濱進發這一時間序來鋪寫中央飯店的滿映宴。作家宴從6月變5月,改寫時,木村如實寫入,寫完後,又覺得有違《李傳》、《李戀》兩書書明懇話會作家是從哈爾濱回來,返日回程順道訪滿映的說法,和木村、久米年譜表明的6月和李香蘭會面也不合。決定再改寫,情節的鋪陳變成懇話會和久米5、6月都去了滿映,5月的輕描淡寫,6月份回程前往拜會後的洗塵宴,自然詳細鋪寫,同時用回想的方式帶出木村對李香蘭在5月1日宣詔晚會唱歌的印象,符合《李傳》、《李戀》兩書所述,懇話會作家回程途中順訪滿映,木村和久米兩作家年譜6月會香蘭的紀錄。
不管怎樣改寫,滿映給作家的洗塵宴和車站送別的時間點都勾不到冬雪的天氣。前文提及,宴會當時也在討論電影《白蘭之歌》。作家群接受滿映酒宴時,木村、久米的劇本和原作,都寫得差不多,原作1939年8月3日東京日日新聞連載到40年1月9日,久米6月宴後返日,將小說收尾交報社刊行,時間吻合。如依《李傳》所寫,香蘭在雪晨送別作家,當年11月到第二年2或3月,久米的小說可能已經連載或連載結束,和《李傳》所說的書「尚未寫成」也相矛盾。值得一提的是,《李傳》說到該酒宴的章節時說:「我對那未曾謀面的祖國產生深深憧憬,並且決定無論如何,非到日本走走看看不可。」事實上,酒宴當時她已去過日本兩趟,期間都很長。想來香蘭書寫《李傳》時,部份依據印象式的記憶,未作嚴格考證。行文至此。想說的是,寫作《亂世麗人》對《李傳》依賴甚深,但對其中有些印象式、不夠精確的描述,還是持保留態度。
為了寫李香蘭,除了網上的文字和一般書面資料、影音,尤其是電影,能找到就看。寫作的八九年期間,共下載了十部她演出的電影,計2.83G,17部電影片段,計0.47G。寫作的中後期,網上下載的《莎韻之鐘》的日語對話聽來吃力,網查後,透過亞馬遜日本買了(koalabooks)的《莎韻之鐘》DVD,但無論怎麼放,還是讀不到中文字幕,影片分成好幾部,畫質跟下載的差不多,但沒多久,畫面變模糊。《亂世麗人》寫到後段,李香蘭演出《戰鬥的大街》、《誓言的合唱》和《野戰軍樂隊》時,取得的文字資料甚少,遑論網上的影音資料,好不容易在網路廣告看到販售《野戰軍樂隊》的廣告,向龍騰影音多媒體買了影片,結果發現李香蘭在整部67分鐘的電影裡頭只出現3分8秒的一次,唱了一首歌。一開始有些失望,但想想這個特色依舊可以營造一些情節,還是如獲至寶。蓋1944年3月,斷斷續續拍了一年四個月的《我的夜鶯》殺青後,直到1945年6月大光明大戲院的「李香蘭歌唱會」,女主角這16個月的演藝歲月,若沒有《野戰軍樂隊》軋一腳,會變得很貧乏,有了這部電影,故事後段的推進多了一個支點,情節的蠕動多了一股推力。書寫至此才發現,這兩部買來的影片檔案都很大,每一部超過3.5G,遠遠超過我下載李香蘭大小影片的總和,兩者加起來7.2G。印象中,寫作期間資料蒐集總量維持好幾年10幾G,最近檢視,總量已達25G,想來主要是這兩部電影作祟。
李香蘭演出的所有電影,都是在籍滿映的六年一季的時間內,她是滿映人,所以我對滿映資料的蒐集一直很費力。寫作本作前,筆者透過網路、影片對滿映有些了解,寫作途中,對網上古市雅子寫的《「滿映」電影研究》多所參考。此作對於滿映各階段的行事風格、人事變遷著墨甚多。大概寫到第二三遍時,也在網上發現了滿映演員張奕編著的《滿映始末》。這本書每節敘述一個小故事,從滿映創始寫到長春電影製片廠,也就是從作者少年寫到他退休的70幾歲,前半段章節,透露出來的滿映和李香蘭的秘辛很多,採用後也將李香蘭形塑得更生動,有情味。
香蘭演了許多電影,筆者無可避免地常把她演出的過程帶進情節。要如此書寫,除了要看過她演出的電影外,也得關注相關的文件資料,寫《支那之夜》時,得助於《李謎》裡頭的文章不少,寫《我的夜鶯》時,網上渡邊直紀的《滿映哈爾濱表象-李香蘭主演《我的夜鶯》論》(《満映映画表象-李香蘭主演『私鶯』論》)針對那部電影給了很多深入的解讀。《亂世麗人》從頭到尾,校寫了五遍,大概寫到第三遍時,才在網路發現這本小冊子,囫圇吞棗,急於書寫,全書第五遍校寫完畢,整理這篇序言時,才發覺資料引用不確實,拙作在《我的夜鶯》這一敘述段,只好開刀式的刪修,加了蘇聯紅軍追捕白俄流亡劇人的戲碼。此外,《我的夜鶯》這部戲還有兩處戲中戲,電影裡頭的大小角色在片中演出歌劇,戲中劇劇情的敘述和詠唱,大大得力於〈古諾:浮士德/名曲如繁星的大歌劇〉和〈THE QUEEN OF SPADES〉(〈黑桃皇后〉)兩文。寫作當時想:日俄籍演員混編的劇組呈現《我的夜鶯》的攝錄已經很困難了,何況是戲中劇,這兩篇文章的出現讓戲中劇的書寫有了脈絡可循,心裡的大石終於放下一些。
李香蘭從影的七年當中,南下中國電影中心滬蘇一帶拍片共五次,第五次轉籍上海華影時,戰局吃緊,片子拍不成,第三次來滬時寄籍華影前身的中聯,拍了《萬世流芳》。拍《萬世流芳》的過程,除了電影本身和《李謎》內相關報導外,《湮沒的悲歌 「中聯」、「華影」電影初探》一書也起了很大的參考作用。此書圖文並茂,對於中聯、華影相互傳承,兩公司組織、製作的電影,和演員相互間,演員、官長之間的互動,詮釋甚多,尤其在日本侵華的大環境下,華日電影交流對電影製作和演員的衝擊,更有深刻的探討,故本作描述1942年秋香蘭在上海拍攝《萬世流芳》的那一段時日,多了一些內察中聯內部活動,仰視時代氛圍的視角。這些元素在1945年香蘭正式入籍華影時還是適用。
香蘭南下拍片,除了滬蘇行外,到臺灣算是另類的一次。當時旅滿日人鮮少有機會來臺灣,她一人就來過兩次,且滯留相當長時間。看過電影《莎韻之鐘》後,對她當時拍攝該片時的住居環境、生活情況有了概略性的了解,再參考《李謎》內系列文章、其他零星資料,以拍攝該片為中心的動態場景大體完成,整部小說大概書寫第三遍時,買了《流轉家族 泰雅公主媽媽和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一書。這本書對於當時霧社一帶泰雅各部落間,官警、部落間的互動有著脈絡分明的描述,揉進了這層基底,當時霧社小社會的結構就更扎實了。此書作者下山一,與香蘭同一世代,未被筆者寫入本作中,但他妹夫佐塚昌男(原日混血)一家悉數入列。書中提到佐塚昌男接受徵召前往南洋,香蘭和劇組人員特地到臺中農改所歡送。獲訊喜出望外,當即另闢一小節書寫歡送會。
青年李香蘭的職業是演員,所以她事蹟的鋪陳,拍片是主軸,但形成她藝術顛峰的還是歌唱。當時她最重要的演唱會有四場:初出道,在東京高島屋百貨舉行的亞洲資源博覽會和日本劇場演唱會,《李謎》系列文章:〈昭和13年李香蘭「満州資源博覧会」前後篇〉、〈李香蘭初來日〉、〈初來日印象〉……著墨甚多,兩三年後的日本劇場演唱造成騷亂,《李謎》內的〈再考 日劇七周半(七圈半)事件〉系列文章,也把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影響寫得很清楚。有了第一手資料,這兩場以日本劇場為主的演唱會,個人寫來自然深入,且得心應手。同樣《李謎》裡頭〈臺灣李香蘭〉一文、《李戀》一書相關章節和其他文章,也將李香蘭1941年元月來臺巡迴演唱理出了時間軸,方便了系列場景的鋪敘。1945年6月上海大光明大戲院的「李香蘭女士歌唱會」,除了《李傳》,京都大學〈從中國音樂史上消失的流行歌:再一場夜來香狂想曲〉(〈中国音楽史から消えた流行歌:もう一つの「夜来香ラプソディー」〉)一文也給了我一點養份,演唱會得以順利呈現。
依佛家觀點,李香蘭乃因緣和合而生,個人才具配合大環境,因緣俱足,才會有波瀾壯闊的一生,青年李香蘭尤然。如今因消緣散,美人已遠。同理,個人才具不足,經過一番構思,編織文字,同時把前輩、先賢的相關資料摶成《亂世麗人》,也是一番因緣和合的過程和結果。書寫該作時,由於急於動筆,資料引述不確實,開刀式重寫的部份難以勝數。整部作品書寫了五六遍,第一到第四遍,逐字校對,根據新的資料修繕、增補,寫第五遍時,作重點式的修校。書成,整理序言時,發覺很多資料引用瑕疵,只好忍痛剖文修補。如今序就書成,八九年的夜長夢多落幕,欣然迎向另一階段的試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