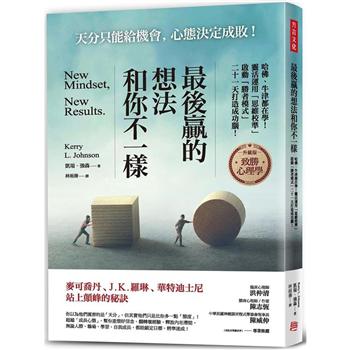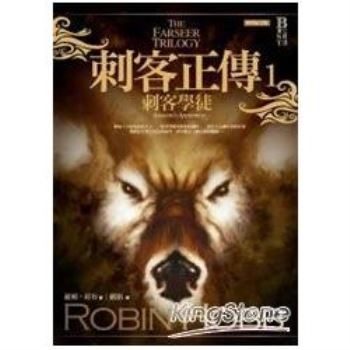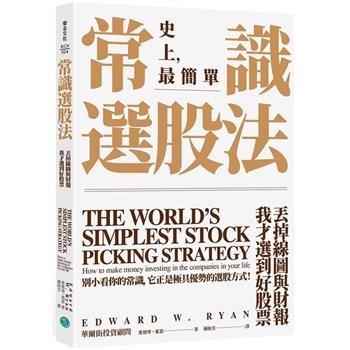第一章
十七歲那年的十月二十三號,我背著黑色旅行袋從綠穀戒毒所走出來,透過玻璃門就見他一邊踱步一邊朝這邊張望。聽到門響,他停下來,一見是我立刻把手從西褲口袋裡抽出來,張開雙臂迎上來。看著迎上來的他,我也想有所表示,或者說點什麼,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喉嚨堵得出奇,張不開口,腳下開始猶豫,後來乾脆停了下來。見我停下,他也放慢腳步,在空中舉著的雙臂定格,然後慢慢地垂了下去,臉上期待的表情漸漸消散,代之以難以描述的欲言又止。他似乎完全理解了我的停頓,這幫我做了決定。我把頭一低,繞過他直接走到車後,打開後備箱,把行李扔了進去。
他站在原地沒動,目光追隨著我,過了一會兒低下了頭。我知道他明白了,我沒好,他太聰明了,他是名律師,什麼也逃不過他的眼睛。我們默不作聲地在原地站了一會,「吃飯了嗎?」他問。我還是沒說話,腳卻開始移動,低著頭走到車旁,坐進駕駛座後面的座位。
Blue Dreams,「海之夢」,他又帶我來到這個波城最貴的餐廳,他總是以為只要對我好我就不恨他了,他錯了,我恨他,我十五歲就開始恨他,現在還恨。
他,是我的爸爸,家中我最親近的人,我叫他Daddy Jay,爸爸傑恩。可是在我十五歲那年事情變了樣,一切都變了,面目全非。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叫過他爸爸,我對他的稱呼變成了一串省略號。
我和他默不作聲地吃著各自的晚餐。我們的沉默影響到了周邊餐桌,他們本來熱烈的談話漸漸靜了下來。黑色的桌布!太靜了,靜得讓我覺得不堪承受,我挪動身體換了個姿勢,一抬頭正看到血色夕陽映照下他閃光的金髮。還是那樣梳得一絲不苟,金燦燦地發亮!我這樣想著,突然感到一陣無端的煩躁。
「我要一杯血瑪麗。」我說。
他抬起頭,看了我一會兒,喚來服務生。
「兩杯血瑪麗。」他說。
我想哭,反而笑了。我伸手把服務生放在他面前的血瑪麗拿了一杯過來,倒入我剩下的蔓越莓汁,然後端起杯子晃了晃開始喝了起來。我一邊喝一邊笑。他一味地寵我,我要什麼他給我什麼,從來不說NO,而我卻恨他。一切都是他的錯,是的,一切都是他的錯,包括他對我這種近乎縱容的溺愛。世上有這樣的父親嗎?我剛從戒毒所出來,就把手又伸給魔鬼,他在一邊看著,什麼也不說,還托了我一把。我一口喝乾了杯子裡的混有蔓越莓汁的血瑪麗。我親生父親一定不會這樣!我心想。
我把空杯推過桌面,放到他面前,又把他的那杯挪到自己面前。我呷了一口,發覺原來那種辛辣乾烈的酒精味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甘酸甜如飴的味道。
真好喝!我想著,端起酒杯又開始喝,一口接一口,像是快乾死的莊稼遇到甘露。
周圍的一切變得美好起來,「血瑪麗」,多麼漂亮的名字!黑色的桌布像騎士的披風飄了起來……
黑、紅、金,我看到這三個顏色大塊大塊地在我眼前飄過:「啊,多麼昂貴的色彩組合!」他後來告訴我這是當晚我唯一說過的一句話。
第二天醒來我感到頭痛欲裂,口乾舌燥。我使勁睜開眼睛想弄明白自己在哪兒,一抬頭正對著窗外射進來的一縷陽光,眼睛被閃得生痛。我掙扎著爬起來,看到身上穿的還是昨天那身衣服,環顧四周,想起昨天從戒毒所出來的事,想起血瑪麗,想起飄起來的黑桌布……
床頭櫃上的手機閃著綠光,我伸手去拿,卻被一陣湧上來的噁心改變了前驅的方向,我衝進廁所,大口大口地吐起來,吐完感覺好點,頭卻更痛了,咚咚咚,像是要炸開。我扶著櫃子站起來,嘴巴對著水管開始喝,咕嘟咕嘟……我聽見喝水的聲音,有點恍惚,是本在喝水嗎?我看到他的喉結在上下滑動。本,我們今天晚上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屋子裡回蕩,我清醒了一些。沒有本,我還在自己的臥室。我搖搖頭,想努力找回自己的意識。嗯,沒有本,只有咚咚的頭痛。我按著太陽穴挪回床邊。
手機還在閃著綠光,像是幽靈在跟我打招呼。我坐在床邊喘勻氣,拿起手機,點開螢幕,看到電已經充滿。我知道是爸爸傑恩幫我充的電,他思維縝密,做事周到。我拔下接線頭,看到手機桌面提示有六個新短訊,我試圖解碼,可是手抖得太厲害,劃了幾次都沒成功。咚咚咚,小錘子還在堅韌不拔地敲著我的神經。我用左手握住右手手腕又劃了一次,這次解開了。點開短信,一個是DJ,我爸爸,Daddy Jay的。我現在跟他說話時沒有稱謂,別人提起他時我管他叫DJ,Daddy Jay的首寫字母。他告訴我他今天要上法庭去為一個客戶辯護,讓我照顧好自己,冰箱裡有買好的食物……一個是艾瑪姨的留言,說是歡迎我回來,要約我吃飯;其它四個都是本發給我的,沒說什麼就問我好,說他想我。
都挺好,除了我的頭要炸裂開,其他都挺好!這麼大的房間,漂亮的傢俱……頭太痛了,我把自己摔回床上,手機好像是掉在了地上,隨它去,我只想知道如何趕走那頑固的咚咚咚的敲擊聲。
等我再次醒來時天色已暗。我聽到樓下有動靜,一定是爸爸傑恩回來了。幾點了?我找到掉在地下的手機,看了看時間,七點十五分,這麼晚了!我翻身起來,衝進浴室。洗完澡頭不痛了,空空的,但是不痛了。我在衣帽間清一色的黑色服飾裡找到那條本喜歡的吊帶長裙,穿上以後在鏡子前打量自己。還可以,挺有個性的!我用本的標準給自己打了分,然後畫了一個淡妝來到樓下。
餐桌上放著剛買來的冒著香氣的BBQ烤肉和剛烤好的新鮮麵包,爸爸傑恩穿著圍裙在擺桌子,聽見我下樓的聲音抬起頭:「狄娜,親愛的,休息得怎麼樣?」他問我,一臉的熱切。
「嗨,」我冷冷地打了個招呼,沒說話。
「嗯,過來,吃晚飯吧,我拌了生菜沙拉。」他臉上的熱切消失了,聲調還是討好地歡快。
「對不起,我要出去,不吃了。」我避開他的眼睛,望向別處。
他好像被人堵住了嘴,突然沒了話。我頓了一下就朝大門走去,在掛車鑰匙的地方,我的手碰到了走廊櫃子上的鮮花,粉粉的一大捧。我知道那是他買的,為我買的。粉色是我兒時最喜歡的顏色,可是現在的我,我看看自己的黑裙子跟腳上的黑靴子。還買粉色花!我心想,但什麼也沒說。我知道,說也沒用,他跟我一樣有的地方特別固執。我用手劃過那飽滿的花瓣,手與花瓣的接觸就像手被眾多的花瓣親吻。「花吻」,是我小時候給這個動作起的名字,每次家裡買了鮮花,我都湊上手臉,感受那芬芳的吻。我現在早已沒了這份心境,只是一個習慣動作而已。門關了一半,我聽到他在後面喊:「別忘了給我發短信。」
「別忘了給我發短信。」坐在車裡,我腦子裡迴響著這句話。發短信是我必須遵守的底線,他不問我去哪,卻堅持讓我給他發短信。他需要知道我在哪裡。
「在你十八歲之前,我是你的法定監護人,如果找不到你我就報警!」上次把我從警察局接回來時,他看著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對我這樣說。我記住了,從那以後我就記住了,因為我不想讓警察再介入我的生活。
我給本發出一條短訊,告訴他我一會兒就到。
街邊的灌木快速閃過,街景變得熟悉起來。一想到本,他那對碧藍的眼睛就在我眼前晃。它們大而憂傷,看著醉人。在戒毒所裡沒有一天我不擔心他,可是他總是說一切都好,關於他的生活細節不肯多說一句。
爸爸傑恩不問我去哪兒,他知道我是去找本,不問是他無聲的抗議,爸爸傑恩不願意我跟本在一起,他覺得本會把我帶壞。
把我帶壞?本是那種螞蟻都不願傷害的人!上次爸爸傑恩對我說出他的擔心,我跟他急了眼。誰帶壞誰還不知道呢!他只知道本用藥,還以為自己女兒是個天使。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為愛無需道歉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為愛無需道歉
執念於自己的人,從一己情緒角度看問題,看不到愛的真諦,愛是什麼?
愛原來也可以是離開,而這樣的離開是情願委屈 自己,也不強迫接受,是做出犧牲而不求報答,甚至不求理解!
寬厚包容面對周遭不在規範上的不得已,世間的 缺憾多仰賴默默使愛的人填補彌平,本書從一個殘疾 棄嬰被收養的視角,解讀棄養、母愛、青春期迷途、 吸毒輟學、同婚收養的問題。 真愛平凡卻支撐了整個 世界,真愛了不起卻潤物細無聲。
作者簡介:
瑞菲女士是旅美業餘作家,曾出版過《我當美國政府官員》一書。平時常在《僑報》等北美中文報刊上發表記錄生活的各種短文。
2013-2014年,瑞菲女士任美國佛蒙特州國際學校(VIA)的中國區總校長,負責VIA在中國五個校區的日常運營。
2006-2012年,她擔任美國麻薩諸塞州外經貿廳大中國部主任,負責處理麻薩諸塞州與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之間的所有相關事務。
瑞菲女士在生物製藥行業有16年科研經驗,並在哈佛醫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所以及多家生物製藥公司任職。她還是波士頓兩所中文學校的校長和創始人之一。
瑞菲女士擁有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分校的教育碩士,尼亞加拉大學的生物碩士和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系的學士學位。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十七歲那年的十月二十三號,我背著黑色旅行袋從綠穀戒毒所走出來,透過玻璃門就見他一邊踱步一邊朝這邊張望。聽到門響,他停下來,一見是我立刻把手從西褲口袋裡抽出來,張開雙臂迎上來。看著迎上來的他,我也想有所表示,或者說點什麼,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喉嚨堵得出奇,張不開口,腳下開始猶豫,後來乾脆停了下來。見我停下,他也放慢腳步,在空中舉著的雙臂定格,然後慢慢地垂了下去,臉上期待的表情漸漸消散,代之以難以描述的欲言又止。他似乎完全理解了我的停頓,這幫我做了決定。我把頭一低,繞過他直接走到車後,打開後備箱...
十七歲那年的十月二十三號,我背著黑色旅行袋從綠穀戒毒所走出來,透過玻璃門就見他一邊踱步一邊朝這邊張望。聽到門響,他停下來,一見是我立刻把手從西褲口袋裡抽出來,張開雙臂迎上來。看著迎上來的他,我也想有所表示,或者說點什麼,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喉嚨堵得出奇,張不開口,腳下開始猶豫,後來乾脆停了下來。見我停下,他也放慢腳步,在空中舉著的雙臂定格,然後慢慢地垂了下去,臉上期待的表情漸漸消散,代之以難以描述的欲言又止。他似乎完全理解了我的停頓,這幫我做了決定。我把頭一低,繞過他直接走到車後,打開後備箱...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3
第四章 031
第五章 037
第六章 041
第七章 045
第八章 065
第九章 072
第十章 076
第十一章 079
第十二章 087
第十三章 095
第十四章 098
第十五章 102
第十六章 115
第十七章 122
第十八章 133
第十九章 140
第二十章 144
第二十一章 151
第二十二章 154
第二十三章 165
第二十四章 1...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3
第四章 031
第五章 037
第六章 041
第七章 045
第八章 065
第九章 072
第十章 076
第十一章 079
第十二章 087
第十三章 095
第十四章 098
第十五章 102
第十六章 115
第十七章 122
第十八章 133
第十九章 140
第二十章 144
第二十一章 151
第二十二章 154
第二十三章 165
第二十四章 1...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