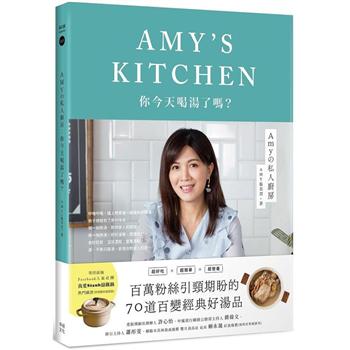1.當代英語文學圈不可不讀的女性作家,被譽為年輕世代的魯西迪
2.英國青年一代作家代表,歐巴馬也是書迷
3.24歲出版第一本作品,震驚文壇,橫掃各大獎項
這些姓和名不協調的孩子,他們的名字裡藏著移民潮。
這是一本會咬人的小說。――英國作家魯西迪
尖銳諷刺、節奏鮮明、語彙豐富、文風新穎。這是莎娣.史密斯震驚文壇的出道作――《白牙》。
英國白人阿奇娶了小他二十八歲的黑皮膚女子,他一生怯懦膽小,就連自殺都只敢交給拋硬幣決定;山曼德是個孟加拉裔服務生,沉醉在祖父是戰爭英雄的過往威名,本身卻意志不堅、出軌偷吃,和老婆打架屢屢敗下陣。
兩人因二次世界大戰相識,再因進入苦悶家庭生活成為摯友,並在下一代自我認同危機中相互扶持――阿奇的女兒愛瑞滿頭狂野鬈髮、豐腴有肉,卻渴望著白人的直髮,深信消瘦身材才好看;山曼德有一對雙胞胎,他卻認為英國習慣腐蝕了家族優良傳統,於是挑了一個兒子送回祖國(因為錢不夠),衷心期望就算父親本人意志不堅,兒子(之一)也要當個好回教徒。然而,就像人無法擺脫自己的影子,傳承也非自身能選擇或排除。傳承在血液之中,在愛瑞的鬈頭髮上,在雙胞胎的基因裡,讓他們無論走到何處,永遠感到格格不入,彷彿時時刻刻都得遷徙,世世代代都是外來者。
莎娣.史密斯於二十四歲推出重磅鉅作《白牙》,雖是新人作家之姿,文字卻洗鍊而技巧純熟。她在接下來十年皆有作品發表,無不獲得文壇一致推崇。書中描述兩個混種家庭的兩代離散;一代是物理上,一代是心理上。她更以某種宿命論口吻做為開頭,再以此串接整篇故事。然而能佐證命運的不只是超自然信仰,諸如遺傳學、基因、DNA都能成為論述根據。可見史密斯想用以舉證的多元範例已非兩兩對照,而像散落面前的抓周物品,任憑抓取、各自表述。這便是當代英國社會――或任何身分認同已太難定義的社會――之困境。「我是誰」再也不是選擇題形式,而是長文申論仍不能說清的大哉問。
§莎娣.史密斯作品集§
《白牙》White Teeth
《簽名買賣人》The Autograph Man
《論美》On Beauty
《搖擺時代》Swing Time
《西北》NW
名家推薦
臺北大學應用外語系 王景智教授 專文導讀
作家 張惠菁 專文推薦
小說家 王聰威、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江淑琳、作家 吳曉樂、瑯嬛書屋店長 張之維、逗點文創結社總編輯 陳夏民、浮光書店、春秋書店創辦人陳正菁、作家 陳思宏、作家 黃崇凱、陽明交通大學外文系終身講座教授/國家講座主持人 馮品佳――推薦
榮獲獎項
《衛報》首作獎
惠布瑞特首作獎
不列顛國協作家新作獎
艾瑪獎的最佳小說和最佳女新人獎
《週日郵報》青年作家獎、柑橘獎、作家協會小說首作獎決選名單
媒體讚譽
舉重若輕之筆,嘲謔寫日常生活各種失落與在失落中寄望遙遠夢土的人們,刨根倫敦多元族裔龐雜的文化認同問題。
――張之維,瑯嬛書屋店長
莎娣.史密斯大學時期寫就的作品,已可看出她往後作品的輪廓。從巨觀社會結構到微觀人際互動,在她筆下,自然浮現、潺潺流動。――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江淑琳
天賦異秉到不可思議的新人作家。文字精明,博學多聞,更帶了些撒潑世故的口吻。
――角谷美智子,《紐約時報》
這本出道作談種族與認同,卻生氣勃勃、輕快活潑……莎娣帶刺的慧黠文字不但親切,更稱得上辛辣無比。
――《時人雜誌》
了不起的出道作……令人想到魯西迪與約翰.厄文。《白牙》走喜劇風格,處處顯露精明不羈,並由作者的精巧文學手法編織成冊。
――《娛樂週刊》
《白牙》就像倫敦的寫照,是各種聲音、語調和本質持續混和而成的產物。
――《紐約時報》書評
作者簡介:
莎娣‧史密斯 Zadie Smith
1975年出生於北倫敦,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牙買加人。她就讀劍橋大學英文系,1997年畢業。
她備受讚譽的第一本小說《白牙》(White Teeth)是一幅現代倫敦多元文化的生動寫照,闡述三個不同族裔家庭的故事。該書獲得諸多獎項,包括《衛報》首作獎,惠布瑞特首作獎和不列顛國協作家新作獎等;同時也奪得艾瑪獎的最佳小說和最佳女新人獎,進入《週日郵報》青年作家獎和百利女性小說獎以及作家協會小說首作獎的決選名單。這本書讓她從藉藉無名之士一躍而為眾所矚目的文壇新星,不少評論家將之譽為年輕世代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或者古雷西(Hanif Kureishi)。
莎娣‧史密斯的第二本小說《簽名買賣人》(The Autograph Man)是一個關於失落、執迷和聲名本質的故事。在書中,她以戲謔的方式檢視聲名的虛浮與不可靠。同時,她也透過鮮活的言詞,將好萊塢電影元素融入書中人物的日常對話,顯示出與她同一世代的人,在生活中,如何受到好萊塢的影響。該書贏得2003年《猶太季刊》文學獎,同年亦被英國權威文學雜誌Granta選為二十位年輕世代最佳作家之一。
2005年,她的第三本作品《論美》(On Beauty)入圍英國曼布克文學獎決選,並在2006年獲得百利女性小說獎。莎娣‧史密斯,絕對是這個世紀值得期待的重要作家。
譯者簡介:
梁耘塘
東吳大學英國文學系,美國夏威夷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譯有《小婦人》、《男人獵豔書》、《視覺藝術與認知》、《白牙》等。
穆卓芸(審定)
文字手工業者,譯有《尋找松露的人》和《愛情的謎底》等書。
章節試閱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三點。兩兄弟經過八年的隔閡,在一個空房間(終於)見面了,並發現預言他們未來的基因,竟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米列特對他們的差異大吃一驚。鼻子、下顎的輪廓、眼睛和頭髮。他哥哥對他來說根本就是陌生人,而他也老實地這樣跟他說。
「是你希望我變成陌生人吧,」馬吉德面露狡猾說。
但米列特就是直言不諱,根本沒興趣在那邊打啞謎,簡單一句自問自答說出他掛心的問題。「所以你們是篤定要舉行了是吧,啊?」
馬吉德聳聳肩。「停止或開始都不是我能決定的,兄弟。不過是的,我打算盡我所能予以協助。那是個偉大的計畫。」
「那是件令人憎惡的事,」(傳單:創造的神聖性)
米列特從桌下拉出一把椅子,面朝椅背坐了下來,活像困住的螃蟹,手腳攤在兩旁。
「我倒認為比較像是矯正造物主的錯誤。」
「造物主不會犯錯。」
「所以你的意思也是要繼續囉?」
「你他媽說得沒錯。」
「我也一樣。」
「好,很好,就是這樣了,是不是?結果已經出來了。KEVIN會採取一切必要行為阻止你和你們這種人。事情他媽的結果就是這樣。」
但跟米列特的了解正好相反,這不是演電影,不會有他媽的結果,就好像沒有他媽的開始一樣。於是兩兄弟開始爭論,而爭論又在片刻間逐步擴大,他們讓「中立地方」的美意變成了笑話;相反的,他們讓整個房間充滿了歷史――過去的歷史、現在的歷史和未來的歷史(因為真的有這種事)――他們就像容易興奮、愛拉大便的小孩,把原本空白的地方用過去的臭屎尿搞得汙穢不堪。他們用他們的每個牢騷、每個早年的記憶、每個爭論的原則、和每個激辯的信念,覆蓋了這個中立的房間。
米列特以椅子排列,證明可蘭經中清楚闡明的太陽系,遠遠存在於西方科學好幾世紀以前(傳單:可蘭經與宇宙);馬吉德在黑板上畫出潘達的閱兵場,以及子彈可能經過的詳細路線,然後在另一個黑板描繪出限制酵素犀利穿透一系列核甘酸的圖解;米列特用電腦當作電視,板擦當作「馬吉德和羊」那張照片,然後獨自模仿那一年到家裡來的每位父親、曾姑媽和表哥的會計師,淚眼婆娑做出那種膜拜偶像的不敬行為;馬吉德利用投影機投射出他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一點一點引導他弟了解他的論點,捍衛基因改造有機體的專利權;米列特用檔案櫃影射另一個他憎惡的檔案櫃,裡面塞滿來自猶太科學家和失去信仰的回教徒彼此交換的想像文字;馬吉德把三把椅子放在一塊,打開萬向燈,有兩個兄弟一起縮在車裡發抖,幾分鐘後就被永遠拆散,然後是一架紙做的飛機起飛……
就這樣一直一直下去。
一直到證明了人們一提到移民者就常說的一句話:他們很有腦筋;無事不達。就是會在任何機會善用任何工具。
我們常覺得移民者就是常常在遷移,沒有束縛,隨時可以改變路線,而且能在每個變化中運用他們傳奇性的機智。我們都聽過德國沙特的足智多謀,或印度阿三的不受束縛,他們航行到愛莉絲島,或多佛港,或加來地區,像個過去空白的人踏進這塊異地,沒有任何行囊,很高興也很樂意將他們的差異留在碼頭,進入這個新地方碰碰運氣,一統在這個「沛綠悅人且受自由意志主義者所支持的自由大地」之下。
不管眼前是怎樣的路,他們都會走,就算是來到死胡同也無妨,德國沙特和印度阿三會愉快地下定決心,迂迴進入這個多文化的快樂地。很好,恭喜他們。但馬吉德和米列特卻做不到。他們離開這個中立的房間就像當初進來時一樣:頹喪、沉重、無法動搖他們的路線,也改變不了他們各自危險的軌道。他們似乎就是沒有任何進展,悲觀的人來看,可能會說他們連動都沒動一下――馬吉德和米列特是季諾 兩隻惱人的飛矢,占據了與其等長的空間。更可怕的是,這空間也與蒙格.潘達和山曼德.伊格伯的等長。兩兄弟困在短暫的「當下」,也破壞了所有想為這個事件標上日期、追蹤主角、提出時間和日數的企圖心,因為,現在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也不會有這麼一段「過程」。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移動,沒有任何東西改變。他們只在原地奔跑。這就是季諾的弔詭。
但季諾打的是什麼算盤(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算盤),他的角度又是什麼?有些人聲稱他的弔詭論是更普遍的靈性計畫的一部分。為了
(1) 先證明多樣性,就是「多」,是一種錯覺,然後
(2) 證明真實是沒有縫隙、平滑流暢的一體。一個單獨的、不可分割的「一」。
因為當你可以把真實無窮分割成許多小部分時,就會像這對兄弟在那房間做的事一樣,結果是無法忍受的弔詭。你會一直在原地踏步,到不了任何地方,絲毫沒有進展。
但多樣性不是錯覺。就跟燉煮的鍋子正以某種速度朝沸騰邁進,而這速度也非錯覺一樣。撇開弔詭不說,他們的確在跑,就像阿奇基里斯在跑一樣。而且他們會領先那些仍在一眛否認的人,就像阿奇基里斯一定會讓烏龜望塵莫及一般。沒錯,季諾有他的角度,他想要「一」,但這個世界是「多」。然而,這個弔詭還是很吸引人。阿奇基里斯越想追上烏龜,烏龜就更奮力表現牠的優勢。同樣地,兩兄弟比賽衝向未來,只是徒勞發現他們更奮力陳述過去,就是他們剛剛經過的地方。這正好帶出了關於移民者(難民、流民、旅客)的另一件事:就像一個人無法擺脫自己的影子一樣,他們也無法忘掉自己的過去。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三點。兩兄弟經過八年的隔閡,在一個空房間(終於)見面了,並發現預言他們未來的基因,竟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米列特對他們的差異大吃一驚。鼻子、下顎的輪廓、眼睛和頭髮。他哥哥對他來說根本就是陌生人,而他也老實地這樣跟他說。
「是你希望我變成陌生人吧,」馬吉德面露狡猾說。
但米列特就是直言不諱,根本沒興趣在那邊打啞謎,簡單一句自問自答說出他掛心的問題。「所以你們是篤定要舉行了是吧,啊?」
馬吉德聳聳肩。「停止或開始都不是我能決定的,兄弟。不過是的,我打算盡我所能予以協助。那是個偉大的...
作者序
【導讀】
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
――國立台北大學 應用外語系教授 王景智
如何估算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莎娣‧史密斯(1975-)塑造的倫敦人提供了一個丈量的標準。在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和古雷西(Hanif Kureishi; 1954-)之後,史密斯以她北倫敦人細膩的觀察力、笑中帶淚的幽默以及冷靜客觀的批判,瀟灑走出前人的陰影,在白人土地上勾勒少數族裔的彩色人生。
母親為牙買加移民,父親為英國白人,這對老夫少妻帶著混血女兒落腳倫敦西北郊區,也因此倫敦西北的地景與族裔群像在莎娣‧史密斯筆下都成了――套句《白牙》牙買加移民後裔愛瑞的台詞――「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陌生人的無所不在,讓生命的不堪無所遁形,他們的突擊總迫使我們得直視難解的生命課題,也因此讓我們理解到原來和陌生人的距離又遠又近。史密斯的《西北》故事就是由陌生人莎爾的造訪揭開序幕。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四月天莎爾突然現身主角黎亞家門口急促地按著門鈴,鈴響前一刻黎亞才在驗孕棒上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藍色加號,雖然事後證明莎爾不過只是拿母親生病住院急需用錢當幌子來誆騙黎亞,但陌生人莎爾訛詐錢財的伎倆卻讓黎亞驚覺,她竟如此抗拒成為母親。一如莎爾,《簽名買賣人》艾力克斯─李‧坦登是站在年老色衰好萊塢女星姬蒂‧亞歷山大紐約住所門口按電鈴的陌生人。艾力克斯亦出身北倫敦,他的膚色比牙買加愛瑞淺,但卻比愛爾蘭黎亞深,因為他是華裔猶太人,在孕育他成長的土地上,總有些尷尬時刻讓他覺得格格不入。即使如此,買賣簽名的這項工作一直驅策他追尋滿足欲求的方法,其中包括自行偽造,以假亂真。然而就在他得到夢寐以求的姬蒂‧亞歷山大真跡並因此聲名大噪、一夕致富後,艾力克斯發現,那張一鎊紙鈔上父親的簽名才是他這輩子最珍貴的蒐藏,因為那不是一個陌生人的簽名。
《西北》的莎爾和《簽名買賣人》艾力克斯都是不請自來的陌生人,《論美》的傑羅姆‧貝爾西卻是享受東道主悅納異己的陌生人。傑羅姆從美國布朗大學去英國當交換生,不僅擔任父親事業勁敵蒙提‧吉普斯的私人研究助理,還接受蒙提的邀請搬進他在北倫敦基爾本(Kilburn)的住所,蒙提刻意拉近與傑羅姆之間距離的結果,就是舉家遷往波士頓與傑羅姆的父親霍華‧貝爾西正面交鋒。至於《搖擺時代》裡無名的敘事者,是至親好友身邊最熟悉的陌生人。七歲時在基爾本,流著牙買加母親和白人父親血液的小女孩牽著母親的手走進踢踏舞教室,認識了同為棕色皮膚的崔西;三十三歲時,在倫敦西北區的聖約翰伍德(St. John’s Wood),她收到崔西寫給她的電郵:「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妳的真面目了。」不論是摯友崔西或親密工作夥伴艾咪,其實「我們根本不了解彼此」。她靠著空中大學函授課程取得學位的女性主義母親也同樣覺得,那個抑鬱深沉且「缺乏抱負」的女兒很陌生,而敘事者酣醉攬鏡自照時也發現,鏡中女子是一個回視她的陌生人。
史密斯對種族主義的批判與基本教義派的嘲諷也像一面鏡子,除了反射前輩族裔作家古雷西和魯西迪的身份認同政治,也與他們的族裔書寫相互輝映。《白牙》裡的一對雙胞胎兄弟馬吉德和米列特,父母皆為從破落倫敦東區搬到生活條件相對單純的倫敦西北區的孟加拉移民。父親山曼德二戰時為英國政府效命卻擔心兒子如果繼續待在倫敦會數典忘祖,甚至背棄阿拉真主,決定將兒子送回故鄉接受「道德調整」。無奈二戰遭斷臂的老兵服務生小費有限,薪水微薄,即使抵押了房產也只夠支付一人的返鄉旅費,進退兩難之際,印度總理甘地遺孀因「藍星任務」遭錫克教徒報復,在新德里自家花園遇刺身亡,這個發生在印度的暴動事件讓遠在倫敦的山曼德決定送早兩分鐘出生的馬吉德回孟加拉,因為他「腦筋好、脾氣穩、學語言也快」,更重要的是,一九八四年的英國「只會讓我們撕裂」。八年後,離開英國的馬吉德「比英國人還英國」,留下的米列特則成為比穆斯林還穆斯林的KEVIN (Keepers of the Eternal and Victorious Islamic Nation) 激進組織成員。史密斯以小人物視角介入國家歷史的書寫方式與魯西迪改寫印度分裂與獨立建國史的幾部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以再現歷史盲點的手法來凸顯官方敘事的排他性與唯我獨尊。
至於米列特從青少年足協「幾十年來僅見最好的前鋒」變成自家製造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變形記,則會讓人想起古雷西於一九九四發表的短篇故事〈我兒狂熱〉(My Son the Fanatic)。巴基斯坦裔的計程車司機對模範生兒子丕變的生活態度感到不解與擔憂,原以為兒子染上毒癮,但在看到兒子蓄鬍並一天朝聖地麥加祈禱五次,父親恍然大悟,兒子已加入穆斯林基本教義組織成了聖戰士。古雷西的巴基斯坦移民父親極力想將兒子拉回西方物質文明世界卻苦無對策,所以在兒子禱告時衝進房間飽以老拳,除了洩憤,更冀望能因此將兒子打醒,但漠然的兒子僅淡淡地回了一句:「現在誰才是〔失去理性〕的狂熱份子」? 相較之下,史密斯的孟加拉移民父親似乎對兒子的宗教狂熱多了些同理心,因為「他知道那種乾旱,他嘗過那種人在異地才會有的乾渴――令人害怕又揮之不去――一種持續一輩子的乾渴」。古雷西的故事似乎預示了那對父子日後將形同陌路,而恪守教規的伊斯蘭聖戰士恐怕也不會還俗了,但史密斯的馬吉德和米列特或許在數百小時的社區服務後,能學會不要把生命浪費在讓他們生活太複雜的事務上,並重新與和他們有相同身份特質的人產生連結,然後在英國這塊土地上打造一座屬於他們自己的「千禧花園」。
在呼應古雷西冷峻的批判之外,史密斯和魯西迪一樣,都慣以笑中帶淚的敘事手法直指偏執狂的荒謬行徑帶給個人及群體的傷害。收錄在魯西迪《東方,西方》短篇故事集裡的〈先知的頭髮〉,就是壓垮文明與理性的那根稻草。某日清晨開設錢莊賺取高利的父親正準備出門收帳,在停放私人小船的岸邊撈起了一個精緻的小玻璃瓶,裡面裝著一根頭髮,他立刻得知那是遭竊的先知的頭髮。擁有聖物的父親搖身一變成為虔誠的穆斯林,旋即在晚餐桌上如數家珍地列出家中每位成員違反教義的行為,並用刑鞭打一對回嘴的子女。憤怒的兒子知道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那個裝有先知穆罕默德頭髮的小瓶子,只要把它放回清真寺一切就可船過無痕,所以他潛入父親書房,順利找到聖物後隨手放進長褲口袋,孰不知褲袋竟破了個洞,這是母親在家務上從未發生過的疏忽,興許是她被丈夫主動吐實的婚外情以及連串的家暴事件給嚇得分心了,就在兒子準備跨步上船去物歸原主時,那裝著先知頭髮的瓶子竟從破洞掉出落入水裡,兒子毫無察覺地乘船離去,瓶子則被尾隨的父親發現從水中撈起;寶物再度落入父親手中,其代價就是家毀人亡。先知的頭髮最終由警方歸還清真寺繼續供信徒膜拜,然而錢莊主的家庭悲劇就像是腐壞的白牙,「沒有回頭的機會了」。
無獨有偶,史密斯作品中也有類似的笑中帶淚情節。在《白牙》的〈臼齒〉部分,愛瑞、馬吉德和米列特因參加收穫節社區活動去拜訪二戰白人老兵漢彌頓先生。他牙口不好,三個年輕人準備的蘋果、雞豆和炸薯片對他而言都太硬了,唯一能送入嘴裡的就只有椰子裡的椰漿。接著漢彌頓先生當起潔牙大使,提醒三人牙齒保健的重要,畢竟哺乳動物一生只有兩次換牙的機會,不過打仗時「把牙齒刷得雪白」絕非明智之舉。漢彌頓在「黑得跟雞寮一樣」的非洲剛果打仗時,辨識被德軍徵召入伍的那些「黑鬼」的唯一方式就是他們「雪白的牙齒」,只要看到一道白光從眼前閃過就「碰」地開槍,一個「可憐的狗雜種」就「開膛破肚」地躺在漢彌頓腳下,這就是槍火下的優勝劣敗。漢彌頓告訴三個年輕人的「白牙」故事乍聽之下荒誕可笑,但種族極端主義者的傲慢反彰顯了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價值的重要,不論是史密斯故事裡「外黑內白的椰子人」、外黃內白的香蕉人、或是「跟撲克牌黑桃一樣黑」的人,但凡生為人,無論人種膚色牙齒都是白色。種族主義者漢彌頓也知道這個道理,但他卻以此警告馬吉德不要吹噓自己父親是二戰英雄,因為說謊會爛牙,一旦細菌開始腐蝕牙齒就「沒有回頭的機會了」;一旦極端主義開始侵蝕人類的普世價值並任由其孳長,我們就回不去了。
莎娣‧史密斯筆下的移民大多來自前殖民地,宗教信仰也非常多元,這群異鄉客共同紮根在熟悉又陌生的西北倫敦努力追求想要的幸福,於此同時也嘗試更進一步認識那一直住在心裡的陌生人。閱讀莎娣‧史密斯的倫敦書寫不僅拉近讀者與作家的距離,在一個有意義的程度上,也讓我們重新思索人與人的距離。拿她筆下的陌生人故事做為丈量標準,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大約是三十五公分――閱讀時的最佳護眼距離。
【導讀】
導讀 理想人生黑幫電影
作家 張惠菁
有時候,讀一本幽默的小說像是在看角色們作一些我們自己會做的蠢事,只是加倍蠢、放大蠢。看小說家把一件蠢事像籃球轉播慢動作解析那樣,停格,重來,一個跨腿一個阻擋一個跳躍地仔細講解過後,我們覺得獲得了對那愚蠢精闢入裡的認識。以至於下次自己在幹同樣的蠢事時,幾乎可以沾沾自喜起來。
為什麼只能沾沾自喜,而不能從此戒絕不犯呢?既然都已經知道那是蠢事了。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蠢事――尤其是其中最蠢的那些,跟你心目中執迷地珍視為理想或人生目標的東西是那麼地接近,以至於到頭來很難區分理想和愚蠢,很難痛下那割除腫瘤的一刀,而不把整個肝臟一起切了。
對於小說《白牙》中,孟加拉移民第一代的父親山曼德而言,那是另一塊母土。比起他千里迢迢移民過來的這個地方,故鄉母土顯得美好而值得懷念:信仰總是純粹的,生活是杜絕了汙染的,沒有電動玩具或是婚前性行為。以至於他身在倫敦,卻要不斷地想像故鄉,虛構故鄉。虛構到他開始相信,應該要把兒子送回去,來一趟反移民,才能得到最完美神聖的教育成果。
對第二代的大兒子馬吉德而言(他就是那個被父親送回巴基斯坦的兒子),他想去的是科學許諾的未來,生物都用基因工程修補過,身體瑕疵當作一個寫錯的鉛筆字那樣擦掉,皮膚上的痤瘡都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
至於小兒子米列特呢,那是黑幫電影。最好像個教父那樣坐在高背椅裡,一半臉孔隱在暗影中。一動手指就有人幫你掏槍轟掉坐在艙聽吃義大利麵的那些小嘍囉,搞得滿地番茄醬。
黑幫電影?沒錯。如果我們把這本小說中,各個角色深藏在內心中的渴望條列出來,則故鄉基本上等同於一部黑幫電影。說穿了,身為移民第一代的父親山曼德,他全心相信與渴望、不惜把兒子送回去接受純粹宗教教育的故鄉,其實和小兒子米列特迷戀的黑幫電影,或是荷坦絲相信的世界末日福音,甚至可憐的愛瑞那無望的愛情,都是同樣的作用。――這些角色暗地渴望著另一個世界,期待在那裡分配到比他們真實身分更稱頭些的角色。他們強調自己是革命者後裔,再不然就想像自己是教父(或上帝的選民、滿頭自然捲變成滑順直髮的大美人……)雖然,表面上,前者是一個失根的移民第一代對家族記憶的嚴肅追想,後者是一個青少年看太多好萊塢暴力電影引致的不良後果,但不知為何,這一切在《白牙》裡都荒謬地像是同一回事……
實際上,他們是住在倫敦近郊的一群小人物。但似乎都期待著一個更崇高、更有力量些的自我。他們住在倫敦有點像是諸神走錯路來到了人間,只好在這兒吵個不停。而他們想像的那種崇高與力量,只有在一個不是「現在」、不是「這裡」的非凡的異世界(戰爭、革命的大時代,或是電影裡的黑社會)才可能發生。
可惜二十世紀末的倫敦遠非那樣的神奇世界。戰爭早就結束了,那時沒搭上英雄列車的人,現在想補票也沒機會了。結果是,為了接近那個想像的世界,只得用一些「替選方案」來代替。熱愛黑幫電影的米列特,沒有幫派可混,只好去加入宗教狂熱組織。自命為科學家、光榮退役軍人的山曼德,現實生活裡是個餐廳服務生,只能對著客人嘮叨他的科學知識,在家長會發表宗教使命宣言,或是到酒館裡對著酒保講那個已講過上百次的曾祖父起義抗英史……
好像人人都沒法過上那個夢想的生活,只剩下一點替代品。或者,是因為那個異世界的存在,才使得現實裡的一切一無例外地都成了替代品呢?從光榮的歷史來到平庸的現在,渴望為個什麼崇高的理想流血獻身,可最後唯一能貢獻熱血的對象,也不過是一隻貪得無厭的蚊子罷了。
莎娣.史密斯似乎急著拆穿這一切。有時你真要想,在她嘻笑幽默的底層,其實是隱藏著憤怒,憤怒於角色們的虛假裝飾,憤怒於他們將軟弱偽裝成崇高的理念,並藉以振振有詞。憤怒與荒謬總是比鄰的。因為憤怒所以戳破世界的荒謬。你幾乎要想,這部小說很接近愛瑞在公車上那場精采的情緒爆發。接近小說的末尾,愛瑞終於對這些環繞在她身邊吵個不停的爸爸媽媽伯伯阿姨們爆發了。但那憤怒的爆發其實是一次最無助的展示。她其實是無計可施的,大人們那些毫無根據的信念、那些理想人生替選方案、甚至連替選方案都實現不了的挫敗感,這一切洶湧而來,把她的人生弄得吵雜逼仄。而她無力屏擋。她渴望的東西其實很簡單,不過就是一點安靜,怎麼竟那麼難。在這群人人有話要說,有怨要抱,有理念要貫徹,有世界要改造的迷途諸神中尋找安靜,彷彿在泥濁洶湧的恆河裡撈取一顆失落的碎鑽石那樣難。
只是莎娣.史密斯比愛瑞更尖銳冷靜。她試著收起火氣,以揭露這些信念的愚蠢與荒誕,一層一層地拆開著那些替代品,愛情,宗教,科學,教育……直拆到空無的核心。連故鄉,連愛情,連宗教……都不過等同於一部黑幫電影。
【導讀】
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
――國立台北大學 應用外語系教授 王景智
如何估算我們與陌生人的距離?莎娣‧史密斯(1975-)塑造的倫敦人提供了一個丈量的標準。在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和古雷西(Hanif Kureishi; 1954-)之後,史密斯以她北倫敦人細膩的觀察力、笑中帶淚的幽默以及冷靜客觀的批判,瀟灑走出前人的陰影,在白人土地上勾勒少數族裔的彩色人生。
母親為牙買加移民,父親為英國白人,這對老夫少妻帶著混血女兒落腳倫敦西北郊區,也因此倫敦西北的地景與族裔群像在莎娣‧史密斯筆下都成了――套句《白牙》牙買加移民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