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民偶像作家,廣播、電視劇腳本天后向田邦子登峰造極代表作
揉合辛辣與纖細、哀切且溫柔,電影版由森田芳光執導,大竹忍、黑木瞳、深津繪里、深田恭子主演
棲居在名為「女人」這可憐又可愛的容器裡,其實是甚為可怖的阿修羅!
她們並不委曲求全,只是明眼淡看一切謊言!
阿修羅,古印度神話中的惡神。猜疑心重、易怒、喜道人是非,滿口仁義禮智信,看似為正義公平而戰,事實上,內心卻潛藏著忌妒、嗔怒、怨恨等情感……
平日不苟言笑的年邁老父竟然有情婦!四姊妹使出渾身解數,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她們也都有各自的難題:守寡的大姊與有婦之夫發生婚外情;婚姻看似幸福美滿的二姊懷疑先生出軌;三姊因芳心寂寞而致性格扭曲;渴求家人認同的小妹則與尚未出道的拳擊手同居;而恬靜溫柔的母親看似一無所知,實則……
當全心的信任換來背叛,無盡的猜疑如影隨形,自以為是的幸福岌岌可危,存在的價值隨之瓦解。
外遇發生時,殘酷的人性試煉就此展開……
作者簡介:
「大和民族的張愛玲」─向田邦子Mukoda Kuniko
一九二九年生於東京市。童年時期隨著父親的職務異動,搬遷各地留學。實踐女子專科學校畢業,曾任職電影雜誌編輯等工作,之後成為廣播、電視劇作家,代表作有《寺內貫太郎一家》、《森繁的高級主管課本》等。因為乳癌病發,開始寫作隨筆散文。作家山本夏彥激賞地表示:「向田邦子猛然乍現,便成了名人。」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以〈花的名字〉、〈水獺〉、〈狗屋〉獲直木獎,值得一提的是,以正在小說雜誌上刊載的短篇小說獲得提名,實屬日本文壇難得一見的特例。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八月,在台灣旅遊途中因空難猝逝。著有《父親的道歉信》、《回憶.撲克牌》、《隔壁女子》、《女兒的道歉信》、《午夜的玫瑰》等書。
向田邦子是日本的重要作家,逝世後大學為她設立研究所、電視台每年為她推出年度大戲、出版社為她設立電視劇本獎。二十餘年後,經典劇本仍一再重拍、相關著作不斷推陳出新,堪稱大和民族的張愛玲。
譯者簡介:
王蘊潔
樂在文字中打滾十餘年仍欲罷不能的專職譯者,曾詮釋《博士熱愛的算式》、《不毛地帶》、《洗錢》等眾多日本重量級作家的作品。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宛如阿修羅》推薦序:小事的魅力
文╱林婉瑜
二○○三年,日本大導森田芳光將《宛如阿修羅》拍成電影。
一開場就是阿修羅神的圖騰,旁白說道:「阿修羅是印度古神之一,看似為公平正義而戰,事實上,內心卻潛藏嫉妒、憤怒、怨恨等情感,像紛爭不斷的人世。」
原著小說裡,鷹男則是對著四姊妹的背影感嘆:「簡直就像阿修羅。」甚至四姊妹的母親藤,在發現丈夫口袋藏有外遇對象的孩子的玩具時,「有那麼一剎那的時間,藤的臉變成了阿修羅」。
在這個四姊妹發現父親外遇,同時努力處理自身感情風暴的故事裡,阿修羅隱喻了女人溫柔卻恆定的力量,與機心。
現實生活中,向田邦子來自育有三姊妹的家庭;她的作品,無論散文或小說,時常描寫家庭生活與姊妹間細膩的情感。
那是我很熟悉的。
父親只有我與妹妹兩個女兒,我在小女生的環境長大;現在,自己也生養兩個女兒。那種纖細與幽微我懂得,有時也想像,家中有個男孩會有所不同嗎?
向田的文筆是這樣,讓人想到自身。
小說裡,三女瀧子、四女咲子從小便處於競爭比較的關係。
我與妹妹亦是如此。從小,若母親只有一塊橡皮擦,她會私下拿給妹妹;若同樣請母親接送,我經常等上半個小時,妹妹不用等,母親會早於約定時間許多出現在妹妹眼前。為什麼一起逛街時,母親的手搭在妹妹肩上,而我總是落單?與她相處,沒有時優時劣的緊張情勢,只有經常性處於劣勢。
也許不算競爭者吧,自始都沒贏過的。
單純內向的瀧子,最終為了保護咲子,鼓足勇氣把恐嚇咲子的人約出來狠狠教訓一頓,這是瀧子與咲子的和解。而我與妹妹的和解似乎還懸在未來某一時間點,無到來的跡象。
閱讀向田,那些家庭情境、手足相處,像某種概括影射,與你我生活總有某些重複與疊合;那些看似無謂的零件什物,同樣也散落在我們周遭。所以儘管那是將近半世紀前的文字,它們無視時空阻礙輕易地召喚,溶解我們。或說,是我們自動走入向田描繪的場景,而與之悲歡。
小說中有許多細節,是電影裡看不到的。
電影裡,為了變成植物人的丈夫鎮日傷心的咲子(深田恭子飾),是因一時失神偷了東西,被店員恐嚇威脅;小說中,哀傷的咲子是「對溫柔太飢渴」,事後被一夜情對象宅間威脅。
又如勝又(中村獅童飾)對瀧子(深津繪理飾)這段表白,實在非常可愛,電影裡沒有,小說中才得以讀見:
瀧子驚訝地回頭,勝又急忙從口袋裡拿出大張的便條紙,用簽字筆匆匆寫了幾個字,貼在玻璃上。便條紙上用稚拙的字寫著:「沒有大學學歷不行嗎?」
瀧子瞪大眼睛。
勝又撕了那張便條紙,又重新寫了大大的「欣賞」兩個字,然後,又重新寫了「喜歡」這兩個字,最後又想了一下,寫了「愛」這個字,「啪」一聲貼在玻璃上。
瀧子倒抽了一口氣,勝又懦弱的雙眼溼潤,好像隨時都會哭出來。
阿修羅也有軟弱的時刻。
小說中的女主角們,對愛的信仰成為一種執念。
所以儘管咲子提早下班撞見了陣內的背叛,還傻呼呼地說:「因為我不應該提早下班,突然回家……所以,我可以當作沒有發生。」儘管綱子想要了斷與有婦之夫貞治的關係,還是在與其他男人相親後忍不住打電話給貞治:「是我,我想馬上見你。」而四姊妹的母親藤,則是站在丈夫外遇對象家門外,痴痴地看著那棟建築。
向田不直言愛,不直陳遺憾,她給予一個又一個情境,一些相處的對話或片段。散文中小說中都是如此。
幫助構成這些情境的無所不在的「小事」,充滿魅力:勞作課被踐踏的紙鳶(《女兒的道歉信》)、語氣疏淡的父親的家書(《父親的道歉信》)、裂痕像母親後腳跟的鏡餅(《宛如阿修羅》)、讓筷子休息以便細嘗食物真滋味的筷枕(《午夜的玫瑰》)……枝微末節,向田把注視轉向那個物件,物件就成了人生況味的指涉,有溫暖的氣味。
這是小事的魅力。
如小說家童偉格所述:「所謂『完整』總也是假象,當我們嘗試從她的一個零餘舉措中,歸納完整的她是什麼,我們很可能是對自己過於輕饒,對他者過於盲目。」
不要錯過小事。
無法四捨五入的零碎。
這樣的小事可以像「雨水滴落的聲音/輕輕將世界擊碎」(陳雋弘詩句);可以是一杯沸騰的茶「一個溫暖的夢為何此狂暴/雪巴茶知道」(鴻鴻詩句);可以是「擱在懷裡的檸檬啤酒/輻射出與你等量的暈眩」(孫梓評詩句)。
懂得這些小事的同時,你我似瞬間走入充滿音樂的房間,瞬間鬆開了,原本要揮向整個世界的拳頭。
讀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這則新聞:「編號B-2603波音737型的遠航客機,於台北飛往高雄途中空中解體,墜毀在苗栗三義,機內上百名乘客全數罹難,其中包括一名日籍女性作家向田邦子。」我嘴巴微張無聲地喟嘆。
照片底,秀氣、醞有種種風情的邦子故去,已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
《宛如阿修羅》和她的諸種著作是昭和時代的作品;但這些文字與你我無隔閡,彷彿時間不存在,文化切分不存在。
這種直指人心的力量,我相信二十年後翻讀還是一樣。
不刻意追求傳奇,向田邦子獨特的凝望與堅持,和實踐在生活裡的品味,終究,成了一則傳奇。
【本文作者簡介】林婉瑜:詩人,著有《索愛練習》、《剛剛發生的事》。
名人推薦:《宛如阿修羅》推薦序:小事的魅力
文╱林婉瑜
二○○三年,日本大導森田芳光將《宛如阿修羅》拍成電影。
一開場就是阿修羅神的圖騰,旁白說道:「阿修羅是印度古神之一,看似為公平正義而戰,事實上,內心卻潛藏嫉妒、憤怒、怨恨等情感,像紛爭不斷的人世。」
原著小說裡,鷹男則是對著四姊妹的背影感嘆:「簡直就像阿修羅。」甚至四姊妹的母親藤,在發現丈夫口袋藏有外遇對象的孩子的玩具時,「有那麼一剎那的時間,藤的臉變成了阿修羅」。
在這個四姊妹發現父親外遇,同時努力處理自身感情風暴的故事裡,阿修羅隱喻了女...
章節試閱
〈女正月〉
這天早晨,瀧子的心情宛如冬天凍結的天空般充滿肅殺。
話說回來,鮮有令她興奮雀躍的早晨。瀧子總是挽著髮髻,脂粉不施,戴著眼鏡;打扮古板樸素的她表裡如一,個性也很陰沉,從來不曾放聲大笑。
竹澤瀧子,三十歲,單身,目前在區立圖書館擔任圖書館員。那家圖書館已經舊得連招牌上的字都模糊了,冷清的建築物宛如讓人不屑一顧的老處女。
瀧子每天早晨都是第一個到圖書館,打開暖氣後立刻投入工作。然而,這天早晨,瀧子在埋頭工作前,拿起閱覽室的紅色公用電話打電話給姊姊卷子。
「姊姊,是我,瀧子。嗯,身體馬馬虎虎啦。嗯,嗯,我有點事想跟你談談。」暖氣的蒸氣在玻璃窗上形成一層白霧,瀧子邊以手指在玻璃上寫著「父」這個字,邊說:「才不是這麼輕鬆的事。」
姊姊里見卷子今年四十一歲,與丈夫鷹男、十七歲的兒子宏男、十五歲的女兒洋子一家四口住在郊區的透天厝。卷子皮膚白晳,是個美女,和瀧子不同,性格溫順。
接到妹妹電話時,卷子正在吃早餐。她咬著嘴裡的食物說:「你在說什麼啊,結婚的事哪裡輕鬆了?也不想想你今年幾歲了。」
「是小咲嗎?」丈夫看著報紙問,卷子應了一聲「是瀧子」,而後對著電話說:「我告訴你,女人年過三十,身價就會暴跌,你不要再猶豫了。」
「我不是說了嗎?跟這件事無關。」
「那是什麼事?你倒是說啊。」
「你們姊妹不要在電話裡吵架,一大早的,是在幹什麼嘛?」鷹男插嘴說。
「喂,喂……」
「我要說的事──等四個人到齊了再說。」
「四個人?你是說我們四姊妹嗎?你要幹什麼?」
最後一句話並不是對瀧子說的。宏男出門上學前衝進客廳,在卷子面前伸出手。
「我昨天不是說過了嗎,要買書嘛。」
「什麼書!」
「同樣的話到底要我說幾遍啦。」宏男嘟著嘴,一口氣說出英文書的名字。
「媽媽哪懂英文,用日文說一遍。」
洋子在一旁插嘴說:「咦?哥哥,這本書你上次不是買過了嗎?」
「白痴,你在亂說什麼?上次買的是……」
「我不是說了嗎?用日文說一遍。」
「這種事為什麼不在昨晚處理好?」
鷹男皺著眉頭。卷子放下電話,從小抽屜裡拿出錢給宏男。
「記得拿收據回來。出門時,連說一句『我走了』都不會嗎?喂,洋子,你的裙子太短了。」
送兒女出門後,卷子回到餐桌旁,伸手拿了土司。
「真是的,每次叫他用功讀書,他就說要買書,還說什麼沒有參考書就讀不好書……」
「喂!」
「嗯?喔,瀧子……」卷子跑過去拿起電話,邊吃東西邊說:「對不起,你剛才說什麼?」
瀧子不禁火冒三丈。在等待期間,窗戶上的字她描了又描,變得好不巨大。
「卷子姊,雖說我們是姊妹,既然要我等,至少也該打聲招呼說『等我一下』吧?」
「我不是向你道歉了嗎?」
「你連我剛才在說什麼都忘了。」
「誰叫你偏偏在我最忙的時候打電話來……」
瀧子打斷了姊姊的話。「今天晚上到你家會合,到時候我會告訴大家。」
「喂!」
「我會聯絡大姊和小咲,啊,我會吃完晚餐再去。」
「何必在外面吃,我叫外賣的壽司……」
卷子的話還沒說完,瀧子就「咔嚓」一聲掛了電話。
「真是一點都不可愛。」卷子忿忿地看著電話,嘆了一口氣。「女人還是不適合在圖書館工作。」
「只要她交了男朋友,就會變可愛了。」
卷子追上邊繫領帶邊走向玄關的丈夫。「今天晚上也要開會嗎?」
鷹男沒答腔,坐在門檻上穿鞋子。
「你說今天要去國立,是去辦什麼事嗎?」
「國立」指的是卷子的娘家,父親恆太郎和母親藤這對老夫妻住在那裡。
「我媽的私房錢到期了,她當初填的是這裡的地址。」
「她為什麼不寫自己家裡?」
「如果我爸知道了,不就沒有工作的動力了嗎?我媽希望他再工作幾年……」
「男人不管到了幾歲都很辛苦啊。」
「女人才辛苦。」
妻子的語氣中隱約帶著嘲諷。鷹男沒搭理,伸手開了玄關的門。「代我向你爸問好。」
「只問候我爸嗎?」
「又不是『桃太郎』,說到老爺爺,就要提一下老婆婆。」
鷹男出門了。送走丈夫後,卷子聳了聳肩,露出苦笑。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偏僻的小村子裡,住著一對老夫婦。老爺爺去山裡砍柴,老婆婆到河邊洗衣服。
走在車站前的大馬路上,卷子想起這個故事,忍不住笑了起來。行道樹的葉子紛紛掉落,露出光禿禿的樹枝,但今日天氣和煦,從國立車站到娘家二十分鐘的腳程成了絕佳的散步路線。
她在雜貨店兼小蔬果店買了大蘋果當伴手禮,剛好是和母親同名的富士蘋果。
老婆婆在河邊洗衣服時,河裡撲通撲通漂來一顆大桃子。
竹澤家的透天厝位在國立的偏僻區域,走進掛著門牌的大門,有一扇通往巴掌大後院的木門。一走進木門,恆太郎健壯的背影立刻映入卷子的眼簾。恆太郎正在修剪院子裡的樹木,藤則在一旁的晒衣架上晾衣服,眼前的情景讓卷子忍不住笑出聲來。
「這不是卷子嗎?」
「有什麼好笑的?」
他們驚訝地轉頭問道。
「因為……老爺爺在院子裡劈柴,老婆婆在院子裡洗衣服啊。」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如果剛好有桃子出現就完美無缺了。」
「這個季節怎麼會有桃子?」
「媽,剛好有和你同名的品種,所以就順便買了幾個。」
卷子笑著從手提袋裡拿出紅通通的蘋果。
「啊,『富士』……」藤拉著女兒在簷廊坐了下來。「哪有人回娘家買這麼貴的東西,真是個傻孩子。」
「和我家裡平時買的相比,已經算便宜的了。」
「這麼大的蘋果,我們兩個人怎麼吃得完?」
「我會幫忙吃。爸,來吃蘋果!」
「我不吃。差不多該出門了,今天要去公司。」
「還是每週兩天班嗎?」
「週二和週四。」
「原來是火木人……」
恆太郎正要走回屋內,見到半乾的衣物掉在乾枯的草皮上。他彎腰撿了起來,拍了拍灰塵,用夾子夾在晒衣架上,默默地進屋。恆太郎向來沉默寡言,今年六十八歲的他已經退休了,但每週去朋友的公司幫忙兩天,日子過得悠然自在,卻似乎無意和老妻共同享受晚年生活。他從不說笑,也不會放聲大笑,儼然是嚴謹頑固的一家之長。
卷子將目光從父親的背影移到方才撿起的衣服上,那是一件鬆緊帶已經鬆馳的駝色大內褲。
「媽,那不是你的嗎?」卷子看到藤嘴角浮起羞澀的笑容。「爸以前不會做這種事。」
「喂,衣服掉地上了!」
母女兩人同時模仿恆太郎的口吻,不約而同笑了起來。
「爸也老了。」
「他現在也會幫忙關遮雨窗了。」
「爸會關遮雨窗?」卷子瞪圓了眼睛。幾個女兒還住在家裡的時候,恆太郎向來就是個老太爺。
「會不會是來日不多了?」
藤嘆著氣說,卷子笑了起來。
「他知道以前讓你吃了太多苦,所以現在彌補一下。」
「為錢發愁或是被他罵幾句不算是吃苦。」
「對女人來說,這也算是一種幸福吧。」
母女兩人突然沉默下來。
「……你們夫妻沒有問題吧?」
「目前是沒問題啦。」卷子發覺話題轉到自己身上,慌忙從皮包裡拿出存摺。「媽,你打算怎麼處理?銀行的人說希望你續存。」
「好哇。」
「啊,對了,瀧子有沒有打電話來說什麼?」
「她什麼都沒說……發生什麼事了嗎?」
「她說有重要的事,要等四姊妹到齊才能說。」
「到底是什麼事?」
「她說今晚要來我家,我以為她有跟你說什麼。」
「她是不是找到對象了?」
「她說不是這件事。對了,到底該怎麼辦?」
「嗯……」藤瞥向存摺時,恆太郎走了過來。藤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存摺藏到腿下。
「喂,賣豆腐的來了,你不用買嗎?」
「昨晚才吃過豆腐。」
「喔,對喔。」
恆太郎轉身離開後,卷子吃吃笑了起來。「爸現在居然會說這種話。」
藤一臉溫和地微笑點點頭,把存摺塞進和服腰帶,起身走向手拿大衣準備出門的丈夫,為他整了整衣服。
三田村綱子正在料亭「【枡】川」的大廳插花。
綱子今年四十五歲,是竹澤家四姊妹中的長女。婚後育有一子,丈夫英年早逝,她當插花老師維持生計。兒子派駐仙台工作,她獨自住在東京下城區的一間小房子。
「老師,茶泡好了。」
領班民子來喚她,綱子停下手。
「我之前不是說過,不要叫我老師。」
「哎呀,插花的老師當然也是老師啊。」
綱子微微點頭,民子便離開了。她看著插好的花,伸出一隻手正想調整一下花的位置,背後傳來【枡】川老闆貞治的聲音。
「辛苦了。」
綱子沒回頭,很恭敬地回了一禮。
貞治假裝欣賞著剛插好的花,很快竊聲說了一句:「明天,一點鐘。」
綱子面無表情地微微欠身。
貞治剛離開,民子立刻探頭進來說:「老師,電話,你妹妹打來的。」
綱子偏著頭納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匆匆走去帳房,向正在記帳的老闆娘豐子欠了欠身,有所顧慮地拿起了電話。
「喂,喔,是瀧子……」
「我有重要的事跟大家說,今天晚上在阿佐谷集合。」
電話中傳來瀧子慣有的淡漠語氣。
綱子皺了皺眉頭:「這麼突然,有什麼事嗎?」
「見面再說。」
「我也有我的時間安排,你突然打電話,就說晚上要見面……」
綱子正在說這句話時……
「這個月的……」豐子驟然把一個信封遞到她面前,不知道是否想阻止她聊太久。不過,這種作法未免太小心眼了。
「幾點?時間。什麼?咲子也要去嗎?」
「她也會到。八點,你不要遲到。」瀧子淡淡說完後,傳來掛電話的聲音。綱子嘆了一口氣,向盛氣凌人的老闆娘打了聲招呼,回到了玄關。
咲子今年二十五歲,是四姊妹中的老么,幾個姊姊覺得她一事無成,總是把她當成小孩子。她離家住在出租公寓,在一家叫作「小丑」的咖啡店當服務生。
這天晚上,瀧子下班後來到「小丑」,坐在最裡面的包廂座位。
「到底有什麼事要說?」咲子顧慮到有其他服務生和酒保在場,遞上菜單時,小聲地問姊姊。
「四個人到齊時我就會說。」
「大家都很忙,你就不要裝模作樣了,有話就趕快說嘛。」
瀧子不理會妹妹的抱怨,頻頻回頭看著門口。
「而且,你也不問別人有沒有空,就說晚上八點要集合,太以自我為中心了。」
「如果你告訴我你住在哪裡,我就能提早通知你……」
「我最近要搬家。反正要搬家了,就算說了也沒用。」
「難道有什麼不方便嗎?」
「你別胡思亂想了,因為我住的地方沒電話,所以才說有事打電話到店裡來。」
她們每次一見面就起爭執。咲子氣鼓鼓地抗議說:「這裡九點才打烊,我趕不及。」
「你就說家裡長輩生病了。」
瀧子若無其事地說這句話時,入口的門開了,一個身穿邋遢風衣、看起來很懦弱的男人走了進來。他是在徵信社上班的勝又靜雄,比瀧子大兩歲,今年三十二歲。
勝又直接走向瀧子的座位旁,向她鞠了一躬說:「你好。」
「兩杯咖啡。」瀧子說著,把咲子打發走了。
等勝又有所顧忌地在瀧子對面坐下來後,瀧子看著他手上的牛皮紙信封。
「我拜託你的……」
勝又拍了拍信封,點點頭。瀧子做了一個拍照的手勢,問:「沒問題嗎?」
「嗯,算是……」
「好。」瀧子伸出手,但勝又有點遲疑。瀧子皺起眉頭。
「是不是沒拍到?」
「不,拍是拍到了,只是拍得不太清楚……」
「既然這樣……」瀧子伸出一隻手。勝又正要把信封遞給她,又縮了手,翻眼看著瀧子,「你……真的想看嗎?」
〈女正月〉
這天早晨,瀧子的心情宛如冬天凍結的天空般充滿肅殺。
話說回來,鮮有令她興奮雀躍的早晨。瀧子總是挽著髮髻,脂粉不施,戴著眼鏡;打扮古板樸素的她表裡如一,個性也很陰沉,從來不曾放聲大笑。
竹澤瀧子,三十歲,單身,目前在區立圖書館擔任圖書館員。那家圖書館已經舊得連招牌上的字都模糊了,冷清的建築物宛如讓人不屑一顧的老處女。
瀧子每天早晨都是第一個到圖書館,打開暖氣後立刻投入工作。然而,這天早晨,瀧子在埋頭工作前,拿起閱覽室的紅色公用電話打電話給姊姊卷子。
「姊姊,是我,瀧子。嗯,身體馬馬虎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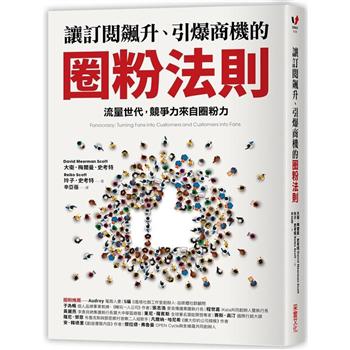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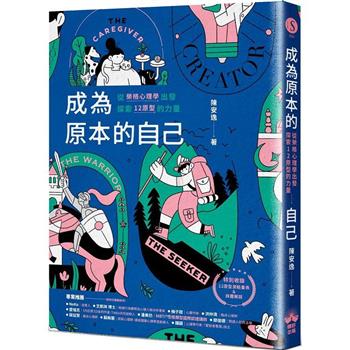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編號B-2603波音737型的遠航客機,於台北飛往高雄途中空中解體,墜毀在苗栗三義,機內上百名乘客全數罹難,其中包括一名日籍女性作家向田邦子。無可諱言地,此一不幸的空難事件,讓台灣成為向田邦子讀者的傷心地,至今仍難以從某些日本人的記憶中抹滅。然而,這場空難卻也意外地讓許\多台灣民眾開始注意到這位曾活躍於日本廣播界及電視界的著名劇本作家及文壇女作家,甚而成為她的忠實讀者。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閱\讀向田邦子的長篇小說,向田邦子的作品幾乎圍繞在家庭與家人上頭,父母子女之間、夫妻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她擅長運用尋常題材,以一種隨手捻來的靈感的態度去闡述故事,讀她的書一定要有顆靜下人的心,因為她的作品中沒有太多起承轉合的鋪陳,不會有盪漾不已的重度回甘,習慣於日式推理作品的節奏感或西方作品中的「失落-救贖」的起伏的讀者,肯定會不習慣於向田邦子這種含蓄、簡單與緩慢的散文,向田邦子的散文之美,美在「點到為止」,她不把故事的發展與看法寫出來,就像本書的故事重心-外遇,向田邦子不刻意去詆毀醜化外遇,甚至根本沒讓外遇的故事發展出所謂的結局。 讀每本書之前,我喜歡不作任何預設立場,讓自己投入如同書中主角,咀嚼、體驗種種喜怒哀樂,宛如做一場又一場人生冒險,閱\讀本書對我而言有些吃力,吃力的不是這本書有什麼深度文學秘碼,也非蘊涵著層層堆疊的哲學底蘊,而是本書的主角-四個姐妹之間的那種平凡的、家居的互動,不喜歡這種家庭瑣事互動的人會認為本書有點類似無聊的八點檔連續劇(坦白講,我覺得有點類似),姐妹之間的相依、較勁,生活下的苦悶或小確幸,構成了這本書的骨幹。 故事從四姐妹的七十歲老爸竟然發生外遇開始,四個姐妹四種不同的故事圍繞在旁,一個七十歲老男人,其出軌的理由是為了什麼?他又只剩下什麼?既然出軌本身不能被接受,為什麼世上仍有這麼多人樂此不疲?除卻愛情,性的本身還剩下什麼?一種契合?還是僅止於一種滿足?七十歲早已到了不惑之年,甚至也應該不受性慾的約制,為何還會臨老入花叢呢?向田邦子很含蓄地用了「被需要」這三個字隱誨不明的答案。 四個姐妹與媽媽各有五種愛情觀,除了探討女性對愛情的追求之外,向田邦子成功\地塑造了女人對愛情的堅強態度,四姐妹對愛情的態度都是義無反顧,愛情一旦遭到威脅,就會起身而戰捍衛自己的感情主權,宛如阿修羅,阿修羅是古印度神話中的惡神。猜疑心重、易怒、喜道人是非,滿口仁義禮智信,看似為正義公平而戰,事實上,內心卻潛藏著忌妒、嗔怒、怨恨等情感。向田邦子用阿修羅來形容筆下的幾個女人,真是夠狠毒,誰說「女人不該為難女人」的,能掀開女人的底與真面目的往往都是女人。 本書與作者其他作品不一樣,在其他作品中,「女人,妳要的到底是什麼?」是故事的重心,而本書「宛如阿修羅」的故事卻完全不同,向田邦子在這本書中說出了「女人,要的就是愛情!」,透過生活瑣碎的紀事、酸甜苦辣的真實人生,沒有太多的辛辣情節,卻使人像品味一杯茗茶、一杯好酒般,低迴再三又不經意間,輕輕嘆息。 但本書讓我比較感興趣的並非在女人對愛情的觀點與作法,而是姐妹之間的那種互動,這是身為大男人的我所無法從生活體會的,原來女人心是如此細膩,細膩到一個表情一個動作都會蘊藏著多種情緒,原來女人間的互動是如此經過算計,算計到人際之間的每一斤倆每一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