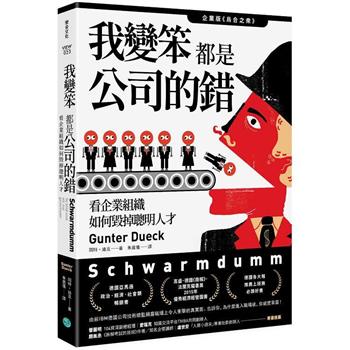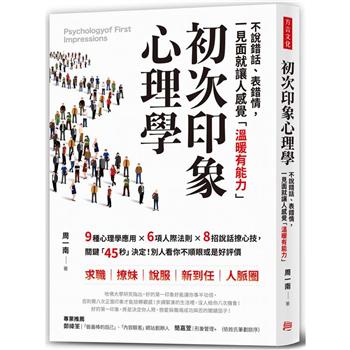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俗世哲學家: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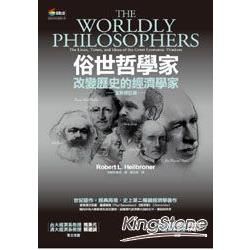 |
俗世哲學家: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 作者:海爾布魯諾(Robert L. Heilbroner) / 譯者:唐欣偉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0-11-1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84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2 |
財經/企管/經濟 |
二手書 |
$ 280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商業財經 |
$ 316 |
哲學 |
$ 352 |
中文書 |
$ 400 |
經濟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本書要介紹一小群名聲特異的人士。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根據低年級歷史教科書的標準,這些人根本無足輕重。其中有幾位頗負盛名,但沒有一個人是民族英雄。有幾位曾遭到痛罵,但沒有一人成為全民公敵。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政治家的行動,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的將領吆喝聲更具震撼力;比國王與立法者的敕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凶禍福。
能夠爭取人心的人,力量勝過刀劍權杖。這些人主要是以學者身分默默工作,不太關心世人對他們的評價。從他們的行列中流傳下來的觀念,在世界各大洲造成了爆炸性的影響,足以決定國家政權的興亡。他們讓階級與階級,甚至國家與國家彼此對抗。他們的觀念就是具有令人驚訝的力量。
他們是誰?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
大經濟學家們從事的研究,能夠激動人心,卻也危險重重。他們所處理的觀念和大哲學家們的觀念不同,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會造成直接的影響。他們所極力策動的實驗,也不同於隔絕在實驗室裡的科學實驗。大經濟學家們的想法曾震撼世界,其錯誤則遺患無窮。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家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他們的國籍、生活和性情各不相同。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不是他們的人格、生涯、偏見,也不是他們的觀念,而是他們共有的好奇心。這個世界十分複雜而又看似混亂無序;在虛假的虔誠之下隱藏著殘酷,卻又有著不為人知的成功之處。這些在在都讓他們目眩神迷。他們都很關注同胞們如何創造物質財富,以及如何仿效旁人,以賺取自己的那一份財富。
所以,他們可以被稱為「俗世哲學家」。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 — 賺錢的欲望。
或許這不是最優雅的哲學,但卻是讓人最感興趣、最重要的一種哲學。誰會在一戶窮人家,以及一個屏息等待某個可以進場撿便宜的投機商人之間,尋找「秩序」和「計畫」;或是在一群遊街的亂民,以及一位笑臉迎接顧客的賣菜小販之間,尋找「一致的法則和原理」呢?然而大經濟學家們就是相信,這些看似不相干的線條,能夠織成一張掛毯。只要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觀看,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就會呈現出井然有序的進程,喧囂的雜音也會變得和諧。
對社會史的秩序與意義之探尋,正是經濟學的核心。因此,它也是本書的主旨。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又一個的原理原則,而是一連串塑造歷史的觀念。我們不僅會看到喜歡賣弄學問的教師,還會遇到許多窮人、投機商人(有的破產倒閉,有的大發橫財)、亂民,甚至某個賣菜的小販。我們應當回到大經濟學家們所察覺到的社會模式起伏中,重新發現我們社會的根源。
《俗世哲學家》是一部永恆經典,不僅讓我們能更深入地瞭解自己的歷史,也令我們能更清楚地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
作者簡介:
海爾布魯諾(1919-2005)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與經濟思想史學家,不僅在學術界享有盛名,其著作也廣受一般讀者歡迎,總銷量高達一千萬冊。寫於一九五三年博士班就讀期間的《俗世哲學家》,為其最受讚譽的作品。 海爾布魯諾自一九三六年在哈佛大學接觸到大經濟學家的思想時起,就一直深研這個主題。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還是斐陶斐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的成員。畢業後,他在政府部門與銀行業實踐所學,隨後於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取得博士學位。他的第一本著作《俗世哲學家》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時便一炮而紅,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成為史上第二暢銷的經濟學著作,且是各大學經濟學系的必讀書籍。晚近《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m)與《未來的願景》(Visions of the Future)兩書,在學界與一般大眾之間,也都廣為流傳。 海爾布魯諾曾擔任社會研究新學院諾曼.托馬斯經濟學講座教授(Norman Thomas Professor),對許多企業、政府與大學聽眾演講,獲得了許多榮銜,包括獲選為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並由紐約州人文學科會議提名為年度學者。二零零五年,海爾布魯諾於紐約逝世。
譯者簡介:
臺大政治系國關組學士、政研所碩士;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研究碩士、政治與政策系博士。現任佛光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 作者: 海爾布魯諾 譯者: 唐欣偉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0-11-09 ISBN/ISSN:978986120398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經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