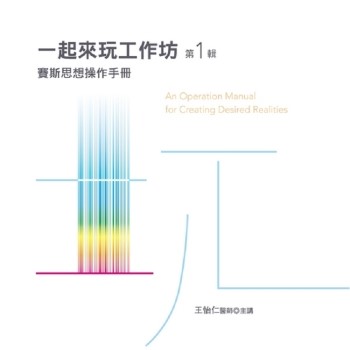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一顆蘋果的距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79 |
網路\原創小說 |
電子書 |
$ 79 |
愛情小說 |
電子書 |
$ 79 |
文學小說 |
$ 158 |
網路愛情小說 |
$ 158 |
大眾文學 |
$ 158 |
愛情小說 |
$ 176 |
中文書 |
$ 180 |
愛情小說 |
$ 180 |
文學作品 |
$ 22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 我們總希望初戀是最後一次戀愛,也覺得最後一次的戀愛如同初戀。++
曾有一段回憶,有一個人,從我們的生命裡走過,留下一道傷口。
每當輕輕觸碰,心就痛得要掉下淚來。
而那一切,明明是最重要的事,曾幾何時,卻被我們遺忘在遙遠的記憶中。
看著眼前這個似曾相識的臉孔,我總想起我談過一場戀愛,很安靜,很溫暖,心跳得很快。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她一個人就給足了所有我需要的愛。我在她身邊成長,她是陪伴在我身邊的人。
即使長大後談了幾次大人的戀愛,但我知道,再也不會有任何一段感情讓我如此放不下了。
本書特色
—每個人都曾經為了曖昧不明的感情受委屈。這個故事,將愛情開始前曖昧迂迴的情懷忠實地呈現。
—除了人物內心的描繪細膩,幽默而令人會心一笑的對話及情節,更讓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在故事架構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能自然而流暢地鋪陳,不刻意造作煽情,作品讀來清新愉快。
作者簡介
新生代青春小說偶像 青庭
200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手裡的溫柔》後,短短兩年時間,青庭已累積出版七部作品,並成為網路小說新一代作家中,詢問度最高、最受期待的作者。
她的筆,寫著青澀歲月中的美滿。細膩的呢喃,吟詠著你我共同的心事。故事中時而幽默的對話,也每每令人開懷一笑。每一次的新作品,都帶給我們更多、更飽滿的感動與共鳴,令我們在笑與淚中回味青春的點滴。
不是昆蟲的青庭出生在日頭赤炎炎的夏日,喜歡看灑進走廊的陽光,喜歡看舊教室的斑駁老窗,喜歡和同學促膝坐在大禮堂,喜歡走過午休時的靜謐穿堂,喜歡在太陽斜射的午后跨坐在單車上,喜歡制服襯衫曬在金色太陽下。
那年畢業了,於是喜歡寫校園故事就這麼開始了,希望在闔上書以後,能讓讀者看見還穿著制服的那年夏天。
已出版作品:
《手裡的溫柔》、《藏在抽屜的夏天》、《追求》、《第三個不能說的願望》、《愛,拐幾個彎才來》、《六月的畢業情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