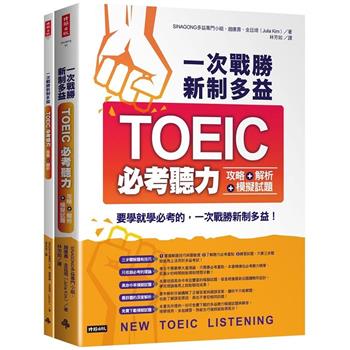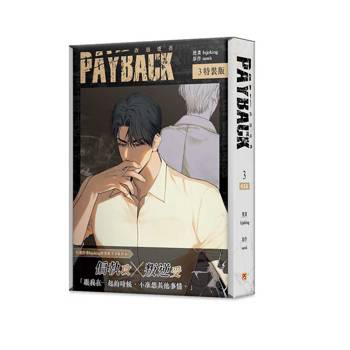★美國《科學人》雜誌、《出版人週刊》專業書評讚譽推薦
從畢氏定理到海森堡測不準原理,十個偉大方程式的發現之旅
當諾貝爾獎得主費曼說,為今日電子時代奠定基礎的馬克士威方程式是19世紀意義最重大的事件時,他在開玩笑嗎?
牛頓的重力定律如何影響了年輕的革命分子?
背叛、精神失常和自殺在熱力學第二定律中扮演什麼角色?
為什麼有人說尤拉的方程式是「上帝的方程式」?
方程式的發現過程不僅精采絕倫,
也訴說了發現這些方程式的天才個人經歷的波瀾掙扎。
多數人學到的第一個方程式非常簡單:1+1=2。如此基本,但意義卻如此重大!它說明了加法的基本定義:一個單位加上一個單位,等於兩個單位。1+1=2是數學的童話故事,是展現人類心智具備改變真實世界的神奇力量的第一個算式。學習方程式就像經歷一場奇妙的旅程。本書便要引領讀者經歷這些旅程。
從畢氏定理到海森堡測不準原理,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克里斯告訴我們歷史上十個偉大方程式背後的故事,揭示它們如何作為那個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成為如同偉大藝術作品的創作。
作者帶領我們見證蘇格拉底如何誘導一名奴隸男孩證明畢氏定理;領略熱力學第二定律背後如莎士比亞名劇般的故事情節;閱覽薛丁格與海森堡兩人關於波動力學情緒澎湃的手稿片段。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科學家不僅傳承了解世界的方式,還接續了許多問題和不滿,驅使他們追求更精微複雜的概念,讓人類的知識繼續發揚光大。因此之故,我們對這個世界才有了了解,而我們對世界的意義的理解也隨之改變。
方程式是人類共同的成就,也是世世代代的研究成果淬鍊而成的精華。一如書中稱頌的方程式,本書證明了科學的意義不是僅局限於實驗室和教科書,它也出現在我們出於困惑、沮喪、驚奇和敬畏,而對這個世界產生的了解當中。這場對歷史上最偉大的方程式所做的導覽,為我們揭露科學發現的全貌。
作者簡介:
羅伯•克里斯(Robert P. Crease)
紐約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哲學系系主任,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史學家。
《物理世界》雜誌(Physics World)「臨界點」專欄(Critical Point)作家,著有多本科學和哲學著作,包括《史上最美的十項科學實驗》(The Prism and the Pendulum)等書。
譯者簡介:
張淑芳
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美國麻州大學企管碩士,譯作包括《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信念與財富》、《一個計量金融大師在華爾街》、《巴菲特親自幫我上的一堂課》等。
吳玉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職於出版社,譯作包括《創新的兩難》、《馬斯洛人性管理經典》、《小,是我故意的》、《衝業績一定有效的10種態度》、《答案,在你心中》、《論自然與語言》、《100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對本書的讚譽】
「本書幽默揶揄、深入探究又饒富哲學寓意,帶領讀者漫遊探訪十個偉大的方程式,也就是在我們人類努力想了解自身所處的世界的漫長過程中十項最重要的勝利。如同陶邁斯(Lewis Thomas)和古爾德(Steven Jay Gould)對生物學的貢獻,克里斯在這些探討物理學的篇章中,揭示了推理與令人狂喜的創造力的精采融合,這正是人類心智最非凡的特性。」――曼恩(Charles C. Mann),《1491》一書作者
「這不只是一本頌揚偉大方程式的書。克里斯運用自己兼為科學史家和哲學家的跨學科技巧,闡明沒有方程式是某個天才靈光乍現的結果,而是數年、數十年或甚至數世紀文化發展的頂點極致。他也說明方程式如何不只影響了科學和數學,也改變全人類的思維。」――泰雷西(Dick Teresi),《消逝的發現》(Lost Discoveries)一書作者
名人推薦:【對本書的讚譽】
「本書幽默揶揄、深入探究又饒富哲學寓意,帶領讀者漫遊探訪十個偉大的方程式,也就是在我們人類努力想了解自身所處的世界的漫長過程中十項最重要的勝利。如同陶邁斯(Lewis Thomas)和古爾德(Steven Jay Gould)對生物學的貢獻,克里斯在這些探討物理學的篇章中,揭示了推理與令人狂喜的創造力的精采融合,這正是人類心智最非凡的特性。」――曼恩(Charles C. Mann),《1491》一書作者
「這不只是一本頌揚偉大方程式的書。克里斯運用自己兼為科學史家和哲學家的跨學科技巧,闡明沒有方程式是某個天才靈光乍...
章節試閱
第1章 「文明的基礎」:畢氏定理
c2=a2+b2
說明:一直角三角形斜邊長的平方等於兩股長平方之和。
發現者:不詳
時間:不詳
直到今天,畢氏定理仍是整個數學界最重要的單一一項定理。
――布羅諾斯基(J. Bronowski),《文明的躍升》(The Ascent of Man)
畢氏定理的起源永遠是歷史之謎。但是講授畢氏定理的人和自行重新認識這項定理的人,給了我們無數重新發現畢氏定理的故事。有些故事訴說的經驗如此震撼人心,幾乎改變故事主角的人生和事業。畢氏定理的魔力和神奇之處在於,儘管這項定理非常複雜,剛開始解答並非顯而易見,證明過程卻很精簡,本身就是一項經驗。
某個人的一生因為畢氏定理而改變,這個人便是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四十歲之前,霍布斯是一位有天分卻少有創見的學者。他精通人文,卻覺得自己不夠博學。他最重要的成就是翻譯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文字優美,卻偶有錯誤。他在科學界相當低調,儘管當時刻卜勒(Johannes Kepler)、伽利略和其他科學家紛紛發表令人振奮的突破性發現,顛覆了科學界。
一天,經過友人的書房時,霍布斯看見桌上放著一本歐幾里得(Euclid)所寫的《幾何原本》(Elements)。這種情形沒什麼稀奇:一位擁有如《聖經》這類精緻的昂貴重要藏書的紳士,不會把書束之高閣,而是顯眼地展示給訪客看,通常會翻開到一段著名的篇章或一首著名的讚美詩。
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的確就像《聖經》。這本書以公理(axiom)和公設(postulate),闡明了許多當時的數學智慧;自從這本書在約西元前300年出版後,學者便開始分析這部著作;書中的知識至今依然適用。除了《聖經》之外,當時沒有其他著作像《幾何原本》一樣,不斷再版或一再被研讀。霍布斯那天看到的詳細確切章節是:第一卷,命題47,畢氏定理。
霍布斯看了一下那項聲稱:一直角三角形斜邊上的正方形面積,等於另兩邊上的正方形面積之和。他大為震驚,甚至口出穢言,他的友人,也是第一位為他作傳的奧布雷(John Aubrey),不願拼寫出這個字。「他╳╳,」霍布斯咒罵道:「這是不可能的!」
好奇的霍布斯繼續讀下去。論證的過程把他導引到書中其他命題:命題46、14、4和41。這些命題又導引出其他命題。霍布斯看完這些命題,很快確信這項令人震驚的定理是真的。
「從此他愛上了幾何學。」奧布雷寫道,還說霍布斯自此變了一個人。他開始著魔似地在他的床單、甚至大腿上,畫下幾何圖形,寫出計算。他開始投入所有精力研究數學,而他也有那麼一點天分,雖然仍舊能力平庸,而且讓自己陷入具爭議又毫無希望的長期數學研究,為霍布斯作傳的作者和支持者至今都覺得困窘。這些故事並不特別引人入勝。重要的是,這項定理改變了霍布斯本人和他的學術生涯。正如一位評論者對霍布斯初遇畢氏定理的描述:「因為這次發現,過去他所思所寫的一切都被改正。」
霍布斯開始指責當時的道德和政治哲學家不夠嚴謹,對先哲卻景仰不已。他不公平地拿那些學者來與數學家做比較,認為數學家從人人都理解和接受的「低下而謙卑的原則」開始,緩慢卻篤定地開展數學原理。霍布斯開始在著作中以類似數學家的方式重新建構政治哲學,首先釐清術語的定義,然後以一種有次序的方式說明其中的意涵,例如《巨靈論》(Leviathan)一書便是如此。畢氏定理教導他一種新的說理方式,讓他以看來必然且放諸四海皆準的作法,有說服力地表達他的推論成果。
畢氏定理:規則
大家熟知的「畢氏定理」這個術語指兩件不同的事:一是規則,一是證明。規則陳述的是一項事實,指直角三角形邊長之間的相等關係:直角三角形斜邊長的平方(c2)等於另兩邊邊長平方之和(a2+b2)。這項規則有實用的價值:舉例來說,若我們知道兩邊的長度,就能計算出斜邊的長度。證明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論證如何知道這項事實是正確的。
同一個措辭指涉兩件事物,這點令人困擾。問題在於「theorem」(定理)這個字。它代表被證明(或假設被證明)的結果。這個字源自希臘文,意思是「檢視」或「深思」,和「theater」(劇場)是同一個字根。當像霍布斯這樣的人看到畢氏定理時,會注意到兩件非常不同的事:一是結果、規則或被證明的事(斜邊的規則),一是過程、證明本身或確認規則的方式。
畢氏定理的規則非常重要,對我們描述周遭空間是不可或缺的。對大小營建案的木匠、建築師和測量員來說,這項規則是無價之寶。這就是共濟會(Freemasons)以畢氏定理作為他們的象徵符號的原因,據說這個祕密組織源自中世紀的石匠行會。一份共濟會的文獻記載,畢氏定理「含括或表述了共濟會賴以建立的真理,也是文明本身的基礎」,而共濟會聚會所的地毯上常裝飾著歐幾里得的證明中所用的一個簡化圖示,稱為古典式(Classic Form)。這項規則也說明了天體空間的特性,因此對導航和天文學是不可或缺的。
早在歐幾里得或甚至畢達哥拉斯之前,這項規則便已眾所周知。特定長度的邊,如3、4、5單位或6、8、10單位,會產生一個由兩個較短的邊形成直角的「三角板」,古代工匠從經驗中發現了這項事實。這樣的三數字組稱為「畢氏三元數組」(Pythagorean triplet),由於這項規則簡單明瞭又切實可行,不同地方各自發現了這項規則並不令人意外。古代另一個關於這類三元數組的發現,似乎是c2=a2+b2這項規則。一塊名為普林頓322(Plimpton 322)、約西元前1800年的巴比倫楔形泥版,記載著一個十五行畢氏三元數組的列表,目前和其他文物一起存放在哥倫比亞大學。這塊泥板顯然是一種三角函數表或畢氏定理規則的教具,以便算出直角三角形的斜邊長。泥板上沒有任何變項(variable),但似乎是要透過一些範例來說明畢氏定理的規則。
古印度也知道這項規則。《繩法經》(Sulbasùtras)記載了這項規則的應用,這些伴隨經書或佛陀的「神聖之學」(sacred teaching)出現的文本,似乎是在西元前500年至西元前100年寫成,但傳遞的顯然是更古老的知識。這本書以相當豐富的幾何知識,說明如何建構儀式區,不過描述太簡略又不夠嚴謹,也沒有提供太多解釋」。
現存最早的中國探討天文學和數學的古籍《周髀算經》(書中某些文章的寫作日期可回溯至西元前1世紀,但據說那些內容早在數世紀前就存在),同樣說明了這項規則。其中一項應用是計算太陽與地球之間的距離。推論過程利用一個竹筒和竹筒的影子,並假設地球是平的;這本書廣獲科學史家推崇為「唯一根據理性且全然數學的觀點,說明一個平的地球的宇宙」。現存最早的版本包含一個經常被引用、背景像棋盤一樣的圖示,我們可以從這個圖示輕易看出,根據斜邊邊長畫出的正方形面積,等於根據另兩邊邊長畫出的正方形面積之和;但幾乎可以確定這項說明出自3世紀,遠在歐幾里得之後。
巴比倫的泥版、印度的《繩法經》和中國的《周髀算經》都說明了這項規則,將這項數學知識應用到其他某種用途:普林頓322楔形泥版用於教育,《繩法經》用於宗教,《周髀算經》用於天文研究。這些文物和其他提到這項規則的古代文獻並未清晰解釋規則,主要是用來計算距離和檢驗結果,不過偶有比較正式的說明。
的確,在數學的里程碑中,畢氏定理無疑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其數千年的歷史中,這項定理出現各種各樣多采多姿、從平凡無奇到饒富詩意的實際例證,包括田野、運河、曬衣繩、小徑、道路和水渠的尺度。一份埃及的手稿記載:「一個10腕尺(cubit,1腕尺約52公分)的梯子,其底部距離牆面6腕尺;它可以到達多高的地方?」一份中世紀的義大利手稿提到:「一支長20英尺的矛斜靠著高塔。若把它的末端往外移12英尺,這支矛可以觸及塔多高的位置?」一份印度文稿要讀者計算一個有著紅雁游動的池塘深度,若一朵蓮花的花苞頂端在水面上方約9英寸的位置,但遭強風吹拂沒入水面下約40英寸的地方,花莖固定在池塘底部。這類練習讓數學趣味十足!
這項定理的規則已經成為知識的模範,了解這項規則往往象徵著擁有智識。在電影《綠野仙蹤》(Wizard of the Oz)片尾,稻草人為了證明它真的有腦袋,提出一個拙劣拼湊版:「一等腰三角形任兩邊邊長的平方根之和,等於第三邊邊長的平方根。」這種無厘頭的說法很完美,因為它讓觀眾不需要真正去思考這個說法是否正確,把劇情留在童話世界裡。
畢氏定理:證明
然而,證明一項規則,和只是知道它,兩者大不相同。證明是指根據一些基本原理,論證一項結果的普遍有效性,純粹如此而已,無關實際的目的,而且重點不在結果本身,而是如何得出這個結果,以及我們之所以相信它的箇中過程。證明講述的是我們了解一個方程式的旅程。因此,要證明一項規則,需要用不同的觀點來思考數學,不僅止是說明那項規則。因為證明不是宣示權威,而是對智識民主的肯定。它不只是傳遞先人的片段智慧,只是一種智力的傑作,神來一筆。它不是在宣稱「這就是事實!」或「天才告訴我們該這麼做」。相反地,證明一項結果是指,根據我們已經擁有的一些數學定義和概念的基礎,任何人都可以進行這樣的旅程,至少原則上如此。因此,實際上證明是說:「按照這種方式,那麼你會發現,我們早就知道要得到那個結果的所有步驟!」所以證明一項規則這種作法建立了一個里程碑,只要循著指示的路徑,任何人都可以到達那個里程碑,進一步探索未知的領域時,還可以放心地據此為自己確認方向。證明重要的方程式,就像立起了里程碑,把數學從複雜的地域轉化成一片勝地。數學的其他部分仍然存在,只是已隱身成為背景。
雖然傳統上認為,第一個提出這項直角三角形斜邊規則證明的人是畢達哥拉斯,但最早宣稱畢達哥拉斯最先提出證明的說法,卻要到半個世紀後才出現,而這幾乎可以確定這種說法並不正確。「證明」的概念似乎源自古希臘,歷時數百年發展過程。這項概念在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中趨於完備,該書完全以清晰且正規的證明來說明數學知識。畢氏定理的證明是該書第一卷的倒數第二項證明。一直角三角形中,直角對邊上的正方形面積,等於另兩邊上的正方形面積之和。命題48,也就是第一卷的最後一項證明,是畢氏定理的逆命題:若一三角形一邊上的正方形面積,等於另兩邊上的正方形面積之和,則該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證明如下:在一直角三角形的每一邊上各畫出一個正方形。從直角的頂點畫一條線,與三角形斜邊垂直,一直到斜邊上的正方形的另一邊。這樣會把那個大正方形分成兩個矩形。結果兩個矩形的面積分別與另外兩個正方形之一相等:因此,兩個較小的正方形面積之和,等於斜邊上的正方形面積。有趣的是,歐幾里得的證明與這些線條創造出來的獨特圖像有關,由於這些線條讓人聯想到一些奇特的圖像,這項證明也被稱為風車證明、孔雀證明或新娘椅證明。
每一個偉大的發現似乎都讓人忍不住想要徹底搜尋紀錄,看看是不是有人更早發現它,發現了卻沒有寫下來,或是觸及這個議題但沒有發現它。畢氏定理,我們似乎永遠注定要這麼稱呼它,也不例外。對史學家來說,說明一個民族多麼接近成功證明畢氏定理,似乎是一種試圖顯示該文明先進程度的方式,並根據普林頓322楔形泥版、《繩法經》、《周髀算經》和其他文本,聲稱巴比倫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發現了畢氏定理。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容易混淆或忽略了經由經驗而認定的畢氏定理的規則,與畢氏定理這個方程式的證明,兩者之間的差異。
新的證明
人類偶爾會自行踏上發現之旅,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情況下發現畢氏定理。法國數學家和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便是一例。帕斯卡的父親禁止在家中討論任何數學問題,擔心這些討論會讓他的孩子分心,妨礙學習最重要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但是少年帕斯卡開始利用一塊木炭來探索幾何學,過程中發現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中編纂的許多證明,包括畢氏定理。
提出畢氏定理新的證明也是可能的。因為如果形形色色的應用和範例讓這項定理在數學里程碑中顯得獨一無二,那麼各種各樣的證明方式也增添了它的獨特性。多數證明是根據相同的公理,但以不同的過程來完成。許多證明是利用幾何學,特別是早期的證明,如蘇格拉底的證明、歐幾里得的證明,以及後來中國的《周髀算經》,其中的a、b和c指圖形的各邊長,證明的方式則是利用這些圖形,說明它們的面積的某些特性。其他證明是利用代數,或根據更複雜的數學來完成,其中的數字是指抽象的概念,甚至談到向量。然而,有些所謂證明所認定的結果,已經被畢氏定理證明,所以其實是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代數的證明方式,也就是巴比倫人了解的方式,便是導引出c2=a2+b2這項規則的證明。
4世紀時,希臘幾何學者帕普斯(Pappus of Alexandria)發現一項自歐幾里得的定理延伸而來的定理。幾世紀後,在巴格達工作的阿拉伯數學家庫拉(Thãbit Ibn Qurra)提出幾項新的證明,修訂了一部早期的《幾何原本》阿拉伯文譯本。兩百五十年後,印度數學家巴斯卡拉(Bhaskara)十分醉心於《周髀算經》視覺上簡單明瞭的證明方式,再行設計了一張簡圖。他沒有提供解釋,只寫下一個詞作為說明:「觀察」。
之後,義大利藝術家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荷蘭科學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都提出新的證明。1876年,美國國會議員加菲爾德(James Garfield)也提出證明,後來他成為第二十屆美國總統。的確,歷史上已經出版過十多部關於畢氏定理的證明的文集:1778年,在巴黎刊行的出版品列出三十八種證明;1880年,德國出版的一部專論中提出四十六種證明;1914年,荷蘭出版了有九十六種證明的著作。美國第一本針對一般大眾的數學雜誌《美國數學月刊》(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從1894年起的最早幾期刊物便開始刊載畢氏定理的證明。該雜誌有些高傲地表示,解題屬於應用範圍且不具科學價值,「是最低等的數學研究之一」。然而,該雜誌承諾會提供「適當的版面探討解題」,例如畢氏定理的問題,以達到教育的目的。「它〔解題〕是將心智提升到更高的原創研究和探索範疇的階梯。許多蟄伏的心智藉由精通某個問題,恢復了活力。」1901年,發表了約一百種證明後,該雜誌的編輯放棄了這項努力,宣布「證明的方式無窮無盡――我們不得不放棄」。
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教師,也是該雜誌訂閱者的路明思(Elisha S. Loomis)不願放棄,他是共濟會會員,曾在該雜誌發表一些證明。路明思持續收集畢氏定理的證明,其中許多是由其他老師提供,這些老師班上的資優生知道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1927年,(時為大學教授的)路明思出版了《畢達哥拉斯命題》(The Pythagorean Proposition),書中含括兩百三十種證明;1940年,八十七歲的路明思出版了第二版,蒐羅三百七十種證明。他將這兩本書都獻給他所屬的共濟會分會。路明思將這些證明分為幾何的、代數的、動態的和四元式。多數證明是幾何的:證明31是惠更斯的證明;證明33是歐幾里得的證明;證明46是達文西的證明;證明225是巴斯卡拉的證明;證明231是加菲爾德的證明;證明243是《周髀算經》的證明。代數的證明中,萊布尼茲的證明列在證明53。路明思贊同提出新證明的這種挑戰可以檢驗學生的奮戰精神,他顯然被證明的過程吸引,喜歡指出有趣的證明和提出證明的有趣人物,或是稱讚提出證明的年輕人。他責難那些在他看來輕蔑這個主題的人。他批評一些刪除歐幾里得證明的美國幾何學教科書,那些教科書可能是想展示「原創性或獨立性」,並挖苦地說:「省略歐幾里得的證明,就像在哈姆雷特一劇中省略哈姆雷特一樣。」他在《畢達哥拉斯命題》第二版的最後一句話是:「而這尚無止境。」
路明思說得沒錯;的確沒有止境。在金氏世界紀錄網站的「最多畢氏定理證明」項目,最近宣稱一個希臘人已經發現五百二十種證明。當你讀到這段話的時候,一定又出現了更多證明。
第1章 「文明的基礎」:畢氏定理
c2=a2+b2
說明:一直角三角形斜邊長的平方等於兩股長平方之和。
發現者:不詳
時間:不詳
直到今天,畢氏定理仍是整個數學界最重要的單一一項定理。
――布羅諾斯基(J. Bronowski),《文明的躍升》(The Ascent of Man)
畢氏定理的起源永遠是歷史之謎。但是講授畢氏定理的人和自行重新認識這項定理的人,給了我們無數重新發現畢氏定理的故事。有些故事訴說的經驗如此震撼人心,幾乎改變故事主角的人生和事業。畢氏定理的魔力和神奇之處在於,儘管這項定理非常複雜,剛開始解答並非顯而易見,證...
作者序
前言
多數人學到的第一個方程式非常簡單:
1+1=2
如此基本,但意義卻如此重大!它說明了加法的基本定義:一個單位加上一個單位,等於兩個單位。它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它展示了其他所有方程式的格式:包括算術、數學整體、物理學,以及其他科學分支。這些項(term)的排列方式,顯示了它們彼此之間一種特殊的關係。這個簡短卻基本的方程式就像一根魔法棒,開啟了許多道門。它就像是通往知識的入口――這第一小步,是後續無數步伐每一步的基礎。加拿大卡加立皇家山學院(Mount Royal College)英文教師,也是詩人的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曾經寫信給我,談到這個意義深遠的算式:
1+1=2是數學的童話故事,這是我教我兒子的第一個方程式,也是展現人類心智具備改變真實世界的神奇力量的第一個算式。我還記得我兒子在學這個算式的時候,他伸出兩手的食指,也就是用來比「1」的手指,當他看到被自己整個身體隔開的這兩根手指,可以在他的腦海中用一個單一的概念合而為一,那個神奇的時刻,或許是他第一個真正的哲學驚奇……當我看到兒子心智大開,知道「1+1」不僅是「1+1」的時候,了解到那個小小的方程式就像一把鑰匙,它帶領我兒子領悟的並非外在世界的驚奇,而是他自己與我們所有人內心的奇妙世界。
哈里森的描述提醒我們,學習一個方程式,至少像1+1=2如此基本的方程式,實際上就像一趟旅程。這趟旅程有三個階段。一開始我們對那個方程式一無所知。之後我們經由學校教育,或由於偶然因素,或出於好奇,或刻意安排,理解了那個方程式,過程中經常伴隨著不滿和挫折。最後,學習方程式的經驗轉變了我們體驗世界的方式,讓我們自然而然地,即便只是片刻瞬間,滿是驚奇。
本書探討的就是那些旅程。
最早的人類生活沒有方程式存在,他們也不需要方程式。伊甸園裡沒有方程式,智慧樹上也沒有方程式。蘇美人的天堂迪爾姆(Dilmun)沒有方程式,中國人信仰的盤古開天的宇宙蛋(cosmic egg)裡沒有方程式,所有其他各種神話的人類起源地也沒有方程式。當時的人類甚至沒有方程式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人類發明的,是我們試圖了解這個世界而創造的。即便如此,人類並不是某天醒來,突然決定要發明方程式。隨著時間演進,人類有了這樣的需求,於是科學化的方程式概念到了非常近期的人類歷史上才首次出現。
拉丁文的aequare這個字,意思是變得平坦或平均。許多現代的英文單字源於這個字根,包括adequate(適當的)、equanimity(鎮靜)、equality(同等)、equilibrium(均衡)、egalitarian(平等主義的)、equivalence(等義)、equivocation(雙關性)。「equation」這個字原先只是指分割成相等的群體。舉例來說,「equator」(赤道)是地理學家想像的一條線,把地球對分成大約均等的兩個區域。中世紀的占星家用「equation」這個字,代表他們自行把太陽與行星的運行軌道劃分成相等區域的過程,每一個區域據稱都由一個不同的星群管轄。
在此同時,數字和計算成為人類生活重要的一環。商人用數字來記帳、處理財務、編列預算;宗教權威利用數字來記錄年分、季節,以及如出生、死亡和結婚等特殊事件;政府官員則利用數字來進行人口統計、普查和課稅。因此開始需要發展符號,以標示數字和量。西元前3世紀,希臘數學家丟番圖(Diophantus)更進一步,利用符號代表未知的量,並建立關於這些量的運算規則,包括減法和加法。他不僅說明了如何利用符號來描述一個未知數,以便從一些已知數求得這個未知數(所謂行列式方程式〔determinate equation〕),也說明了這些符號可以藉由一個無限集合的解法來計算數字(丟番圖方程〔Diophantine equation〕或不定方程〔indeterminate equation〕)。這些離現代的方程式概念還有一大段距離。即使是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和牛頓(Isaac Newton),也都是用文字以比(ratio)的形式來表述他們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伽利略的落體定律和牛頓的運動定律,而不是用研究科學的學生熟悉的方程式。直到18世紀,自然科學家才習慣以今日我們所知的方程式形式,表述他們的研究結論。
因此,即使只是撰寫最簡單的方程式,仍需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歷史和概念之旅。1910年,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家中的兩位,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出版了條理分明、體系化的著名教科書《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共有三冊,以一種純邏輯的方式,完整推演出數學的基本原則。1+1=2這個方程式在哪裡第一次出現?就在第一冊的後半部!
拜這段漫長旅程之賜,「方程式」這個詞終於有了科學意義,成為某個特別的結構化語言的一部分,指的是兩個可度量的量,或可度量的量的集合,是相等的(那麼嚴格來說,表述不等式〔inequality〕的陳述不是方程式)。在這個對現代數學和科學不可或缺、如密碼般的結構化語言中,符號代表可以用來進行各種運算(加減乘除是最簡單的例子)的其他工具的集合。
自從發展出這個特別的專門術語,每個方程式都經歷兩種不同類型的發現過程。首先由第一個發現某個方程式的人提出,也就是把那個方程式介紹到人類文化中的人。之後,每一個學習這個方程式的人重新發現它。
某個方程式的發現之旅,有著與其他歷史轉捩點不同的背景因素。方程式的出現,並不是由血腥的戰場或強大政治力量的衝突建構而成。它反而往往出現在悄然寂靜的地方,遠離令人分心的事物和外界的干擾,例如研究室和圖書館。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在他的書房裡,寫下改變世界的方程式;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一座孤島上,開始匯整他的方程式。這樣的環境讓科學家處理他們的不滿,探索令人苦惱的感受,因為他們手邊拼合的作品無法適切整合,需要做某種調整或增添某個新的東西。於是科學家將注意力集中在某個問題上,那個問題往往可能用容易誤導的簡化方式來表達:這個正三角形的邊長是多少?天體之間的作用力有多強?電如何移動?可不可以把兩個看似矛盾的給定理論整合在一起?這合理嗎?
當解答出現的時候,它看起來合乎邏輯,甚至像是必然的結果。寇茲(Roger Cotes)在牛頓的經典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簡稱《原理》)第二版的一篇序言裡寫道,這部作品「獲得普遍接受」。方程式的發現者常常覺得,自己好像偶然發現某個早就存在的東西。因此,方程式就像珍寶,某個眼光獨到的人發現未經琢磨的原石,經過挖掘和檢視,置於雄偉的知識寶庫,代代相傳。方程式如此便於說明科學發現,又如此適用於教科書,可說是知識的尋寶圖。它精簡濃縮了一段艱困的過程,向我們傳達了發現者、時間、地點的訊息,往往還有成因或目的。一個事件或時刻,例如掉下一顆蘋果,成為一種提喻(以部分代表整體),清楚呈現了那段漫長的發現過程。世世代代的學者繼而藉由批評那個模型,並讓它複雜難解,贏得聲名。這個尋寶圖對所有人都有用處!
然而,不管這幅搜尋世界的尋寶圖多麼有用,卻會讓人以為,方程式是這個世界的基本特徵,而不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的確,我們出生在一個已經有了方程式的世界,那些方程式不是「我們」創造的。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方程式看起來好像其實並非出自人類的發明,而是在人類出現很久以前便已存在:上帝在第八天創造了方程式,作為他的工(His work)的藍圖。或者,如伽利略所言,自然之書(Book of Nature)是用數學符號寫成的。
但每一個方程式都出自人類之手。它是某個人在某個特定的地點和時間統合而成,他覺得有必要對手邊的東西不滿,想要了解弄懂事情,或有時只是想讓某件看似極端複雜的事更容易理解。有時候這個創造過程掩藏於古代,就像畢氏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的例子,早在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之前,這項定理的原理就為人知曉。有時候方程式發現者的書信、草稿和筆記,詳細披露了這個創造過程,如牛頓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出的方程式。但在任一例子裡,都不能說方程式是他們個人的成果,因為這些科學家即使獨自進行研究的時候,都在與其他科學家共同研究理解自然的過程中,進行了無數對話。
當英國科學家黑維塞(Oliver Heaviside)將馬克士威的研究成果,重新整理成今日眾所周知的基本形式時,也就是現在所稱的馬克士威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提到他只是想更清晰易懂地了解馬克士威的研究而已。這樣的動機,也就是意識到可以用更好的方式來表述某件已經約略了解的事,可以說是所有方程式發現者的心聲。
當一個人真的針對某個基本議題提出新的方程式之後,當他解決了他的不滿之後,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都將為之改變。因此,這類方程式不僅教導我們如何進行某種計算,為這相同的世界帶來新的工具,如哈里森所言,方程式還可以做「更多」。在學習1+1=2的過程中,他的兒子不只是輸入一個新的數據點,更轉換了思維,對這個世界有了一種新的理解。但這種新的理解,伴隨著新的迷惑和新的不滿。
哈里森的敘述最後提醒我們,方程式可以激發驚奇的感覺。科學不是一種呆板機械式的活動,讓我們漠然地靈活操縱或凝視這個世界,而是有著非常微妙情感層面的生活形式。當然,有了一項新發現或新成就時,想要開香檳慶祝的喜悅之情會油然而生。但如果科學只能激發這種情緒,也就是有了讓人名利雙收的發現而感到雀躍,將會是可悲的行業,因為這樣的時刻寥寥可數。幸運的是,科學引發的情緒更加多樣化,更加深刻。科學研究中的每一個時刻都伴隨著不斷出現的各種情緒,包括迷惘、困惑、好奇、渴望、找出答案的強烈欲望、對毫無成果的厭倦、一事無成的沮喪、方向正確帶來的狂喜。這樣的情緒始終存在,並未深藏,卻經常被忽略,不過只要我們決定留意它們,很容易就察覺到。
當我們第一次學會一個重要的方程式時,我們瞥見的世界結構,比我們猜想的更深層,這種方式顯露出真實世界與我們經驗中的世界兩者之間的深層連結。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反應不會只是:「是啊,那樣有道理」,或甚至常說的「茅塞頓開的一刻」。後者這種簡略的說法,與指引獲取知識的尋寶圖形影相隨,因為它將伴隨發現而產生的情緒簡化並壓縮至一瞬間。這種發自內心的情緒――驚歎――更加微妙、深刻且久遠。
不過即使是科學家,也會因為比較醉心於這個世界和自己的利益,對最初接觸方程式的時刻興趣缺缺,自然不再對方程式心生讚歎。的確,我們會對自己太熟悉的工具或物件,變得不再驚奇。方程式可能變成看起來只是另一套隨處可得的工具,或我們基於義務必須學習的繁重工作。
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一書中寫道,經驗太老道的領航員往往會經歷一段讓人懊悔的轉化過程。當他們對研判河水的水紋愈來愈駕輕就熟,同時似乎也愈來愈無法領略河川的美和詩意。河流的特色,一根浮木、水面上一道歪斜的水痕、一小片漣漪,曾經激起驚奇和讚歎之情,卻愈來愈變得只有在利用儀器進行領航的時候才有意義。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方程式的情況。
但偉大的科學家往往仍會對前人的科學突破,驚歎不已。物理學家威爾切克(Frank Wilczek)曾經撰寫一系列文章,討論表述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一次方程式F=ma,稱這個方程式為「古典力學的靈魂」,表達了極盡而適當的推崇之意。物理學家和宇宙論者錢卓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寫了一部專論,探討牛頓的《原理》一書(牛頓在這本書中提出他的第二運動定律),把這本書比喻為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上的畫作。而聆聽費曼(Richard Feynman)著名的《費曼物理學講義》(Lectures on Physics)的人,會發現費曼對他要教授給學生的方程式充滿毫不靦腆、油然而生的驚歎之情。這三位知識淵博的諾貝爾獎得主,都能不斷對這個世界和方程式感到驚奇,我們則透過方程式了解世界。
本書旨在說明,方程式遠不像看起來那樣只是簡單的工具。就像人類製造出來的其他東西,方程式有社會意義,能夠發揮文化力量。本書檢視了一些偉大的方程式,並簡單說明方程式的發現者、這些發現背後隱藏的不滿,以及那些方程式對我們世界的本質提出哪些看法。
前言
多數人學到的第一個方程式非常簡單:
1+1=2
如此基本,但意義卻如此重大!它說明了加法的基本定義:一個單位加上一個單位,等於兩個單位。它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它展示了其他所有方程式的格式:包括算術、數學整體、物理學,以及其他科學分支。這些項(term)的排列方式,顯示了它們彼此之間一種特殊的關係。這個簡短卻基本的方程式就像一根魔法棒,開啟了許多道門。它就像是通往知識的入口――這第一小步,是後續無數步伐每一步的基礎。加拿大卡加立皇家山學院(Mount Royal College)英文教師,也是詩人的哈里森(Richard Harr...
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文明的基礎:畢氏定理
第二章 古典機械論的靈魂: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第三章 科學革命的高峰:牛頓的重力定律
第四章 數學之美的黃金標準:尤拉方程式
第五章 科學界的莎士比亞:熱力學第二定律
第六章 19世紀最重大的事件:電磁方程式
第七章 名人方程式:E=mc2
第八章 金雞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方程式
第九章 量子理論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
第十章 與不確定共生: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結 語
謝 辭
前 言
第一章 文明的基礎:畢氏定理
第二章 古典機械論的靈魂: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第三章 科學革命的高峰:牛頓的重力定律
第四章 數學之美的黃金標準:尤拉方程式
第五章 科學界的莎士比亞:熱力學第二定律
第六章 19世紀最重大的事件:電磁方程式
第七章 名人方程式:E=mc2
第八章 金雞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方程式
第九章 量子理論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
第十章 與不確定共生: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結 語
謝 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