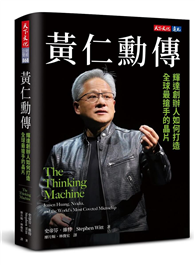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進行最終的大遷徙,
這些落腳城市或是經濟文化繁榮的誕生地,也可能是暴力衝突的發生地。
這些白熱化的人口聚居中心即將重劃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在這本壯闊宏觀的著作裡,得獎作家道格‧桑德斯帶領讀者踏上一場詳盡的旅程,橫跨五大洲的三十座城市與鄉村,見識這些地方的居民和社區——他們的慘痛經歷和成功經驗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他援引學術界最新的發展,進行鉅細靡遺的研究與調查,而他的發現結果將扭轉我們對遷徙、城市、人口成長、外援與政治的看法。
後人對於這個世紀最鮮明的記憶,除了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終階段的大遷徙,徹底從鄉間的農業生活移入城市。目前世界各地都已開始感受到這項遷徙帶來的影響。《落腳城市》帶領我們深入實地觀察此一現象——從馬里蘭州到深圳,從里約的貧民窟到孟買的貧陋社區,從洛杉磯到奈洛比。
道格‧桑德斯引領我們認識那些遷徙人口,透過他們的經歷闡明他們在經濟結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明確指出,城市與國家如果為外來移民賦予公民身分與發展機會,即可隨著移民演變為中產階級而因此獲益;此外,他也說明了漠視移民的地區為何會出現愈來愈多的社會動盪、貧窮與宗教基本教義運動。
融合了細膩的人物描寫與精闢的社會分析,《落腳城市》將改變我們對全球化的看法。
這波最終的都市化涉及的人數史無前例,也許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幾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響。不論就規模或範圍而言,這項移動在人類史上都將是後無來者;家庭生活因此受到的影響——不論是農村的大家庭還是都市的小家庭——也將就此終結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核心發展:亦即人口的持續成長。
鄉村與鄉下地區的人口紛紛打包家當,以大都會為遷徙目標,並且在那裡建造「落腳城市」,也就是鄉村移民在市郊或市中心的隱密地區集中居住的地方。他們在這些地方奮力建構新生活,並且融入當地的社會與經濟體系。他們的目標是建立社群,儲蓄、投資、創造新經濟,然後搬遷出去,把空間讓給下一波的移民。
《落腳城市》指出,這種遷徙的過程正在我們眼前上演於世界各地的城市,包括伊斯坦堡、多倫多、華沙、孟買、奈洛比與深圳,而這項發展也對地方、國家與國際經濟的成功發展帶有深遠的影響。許多落腳城市及其居民都遭到忽略或刻意漠視,甚至被拆除驅離。
正如桑德斯所言,這種做法實是大錯特錯。成功的落腳城市能夠產生富足的中產階級;失敗的落腳城市則會衍生貧窮與社會問題。桑德斯舉實例指出,許多衝突、革命與政治危機都是落腳城市發展失敗的直接產物,早自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鄉下移民因為糧食短缺與貧窮問題而起義抗爭,直到一九七八年德黑蘭的非伊斯蘭教徒移民所掀起的革命,乃至巴黎與柏林市郊心懷不滿的外來移民所發起的暴動或者訴諸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的行為。
桑德斯指出,關鍵就在於我們必須看見這些落腳城市的所帶有的機會。在巴西的聖保羅與西班牙的帕爾拉,地方與國家政府藉著為落腳城市的居民賦予公民身分,讓他們有機會持有房產、獲得教育、享有交通連結與良好的治安,而促使外來移民順利融入當地社會。桑德斯探究這些引人入勝的總體趨勢,更利用他身為記者的敏銳眼光觀察各種人文細節。從達卡到里約乃至柏林與馬里蘭州的市郊地區,我們會見了許多當地的家庭與個人,從他們的故事鮮明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在桑德斯眼中,這些落腳城市絕非我們能夠置之不理的一灘死水,而是交替演變的發生地,是個過渡地點。二十一世紀若干最重要也最驚人的變化,都發生在這些地區。
作者簡介: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
任職《環球郵報》的歐洲中心主任暨海外特派員,並且負責撰寫一個深受歡迎並曾獲得獎項肯定的每週專欄,內容探討的皆是新聞背後的智識觀念與社會發展。
他在亞洲、歐洲、中東與美洲撰寫了許多文章,曾四度獲頒相當於美國普立茲獎的加拿大國家報紙獎。桑德斯現居英國倫敦。
譯者簡介:
陳信宏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目前為專職譯者。譯有《裸女》、《滾滾豬公》、《幸福建築》、《我愛身分地位》、《我可以把妹妹煮來吃嗎?》、《好思辯的印度人》、《幸福的歷史》、《品牌思考很簡單》、《101個兩難的哲學問題》、《猿形畢露》、《66億人的共同繁榮》、《最後的演講》、《只有這本!必讀的西方五大哲學家經典》、《一把鑰匙,走進哲學》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人推薦】
「本書作者桑德斯為了探討這個課題,不僅窮究當代這方面的研究著作,更橫跨五大洲走訪了三十座城市與鄉村,寫成無論從人性,文明史,和當代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各種層面看,都極具時代高度的傑出著作,在我的知識標準裡,它這是與科普對應的社普這個領域的頂級著作,對全世界讀者、學者,甚至於政策制定者都有振聾發聵,讓人的思考能力有煥然一新的喜悅之感。── 南方朔‧知名作家、評論家◎專文推薦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 的新書《落腳城市》(Arrival City) 用了新聞記者最擅長的手法,在全世界30個大小城市與社區裡,以近距離的追訪方式、深入淺出的描述了動人的鄉城遷徙故事。這些人與城市的故事將對我們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看待21世紀全球變遷中的城鄉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劉可強‧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專文推薦
「加拿大記者道格‧桑德斯擅於撰寫生動的報導,也長於提出富有說服力的論證。他為我們的未來寫下了一項迫切需要的論述,不僅深具前瞻性,也充滿樂觀態度……沒有幾本書能夠讓理性主義者對未來感到樂觀又充滿力量,但這本書就有這樣的能耐。」──《衛報》
《落腳城市》:為友善的移民政策呼籲
南方朔(知名作家、評論家)
一九八七年,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裔英國作家奈波爾(V. S. Naipaul)寫了一本有心靈自傳性質的《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寫一個移民作家心靈的憂傷及漂泊。所謂「抵達之謎」乃是義大利超現實主義畫家基利柯(Giorgio de Chirico)一幅作品的名稱,而這個名稱乃是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所取。畫裡有個碼頭,背景露出古船的桅桿,空蕩蕩的街道有兩個人,一個可能是抵達之人,另一個可能是碼頭當地人。畫裡的寓意似乎是說抵達的異鄉人在抵達之地找不到出路而要回鄉,但他趕到碼頭時都發現那古船蹤跡已杳,他已被困在黯淡的時空膠囊裡。在那本著作裡,奈波爾以那種獨特的印度式感傷娓娓的訴說著他的心靈漂泊感,見證了「四海無家處處家」的空曠蒼涼。
我們由奈波爾的自述,已知他是一九五○年代移民潮的時代由千里達赴英留學的,他的確過了很長一段苦日子,尤其他選的是難度最高的寫作生涯,更是歷盡艱辛才進入主流的文藝圈,這使他後來縱使功成名就,但那種自視為陌生人、漂泊者的心情從未改變。他在生活上應該不是悲慘,但卻是那種比較形而上的憂傷。但他那個時代的英國及歐洲移民工人則完全不同了。
今天的人們已知道,近代社會早已在「合理性」下掩護著許多階級的、族群的或文化上的歧視及壓迫。城市的空間建構就是個例證。各統治集團在階級偏見下,總認為土地分區使用,寬廣的街道,整齊清潔而空間宜人的住宅群落、高樓大廈林立的商業區和賣場,這才叫做城市,這才稱之為都市的合理性。至於城市窮人們所居住的地段,那些狹窄的巷弄,湫隘的房舍,由於公共設施低劣而排水不良、垃圾滿地、髒亂不堪的地段,則被認為是「城市之癌」,而任它自生自滅。而人們今天已知道,當人們選擇了讓它自生自滅,那種區域就真的會在自生自滅中沉淪為犯罪的溫床,那個社區的居民就會在被棄感下成為激烈的復仇者。奈波爾那一代歐洲許多移民聚落,他們的父母以移民工人身分進入歐洲,他們無法取得公民的身分,無法享有公民的一切權益,注定只能終其一生做現代式的奴隸工人,等到某一天被用完後拋棄。他們的子女也將面對同樣的命運,於是在一九八○年代初,歐洲許多城市都出現了移民之子們因為活動空間不足而去占用公有廢棄建築物,而和取締的警察對打的「霸屋運動」(squatter movement)以及移民之子們和欺侮他們的光頭幫白人小孩們對打的社區暴力事件。對他們那一代的移民工人們根本沒有「抵達之謎」,只有「抵達之痛」。
而到了今天,終於有了英國記者作家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極費苦心也極具見識的《抵達城市》(Arrival City),在本書它被譯為「落腳城市」。就概念而言,移民到另一個陌生地方是抵達,但從歷程和機制而言,他們到了異地後乃是一長串過程的開始,他們都會有一個起點,那個起點就是「落腳城市」,從這裡他們開始了未可知的前程。「落腳城市」是一切的起點,如果他們在起點就能被當作人看待,那麼他們就會像人一樣,雖然辛苦但卻會在友善的環境裡搏命攀爬,由於經濟性移民自古以來都是最強韌的一群人,他們早晚會在努力下脫貧,而成為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子女也會在接受教育之後有更好的人生機會;如果落腳城市視他們為賤民、為垃圾,他們就真的會在人生旅程上無止境的沉淪以致憤恨下去,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落腳城市就會雙輸。
這本《落腳城市》,乃是本不凡之作,作者桑德斯深刻的認識到現在全世界已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大人口遷移潮的時代,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遷徙流動,因而移民政策和落腳城市也隨之成為當代與氣候變遷同等重要的大問題。移民時代的落腳城市,究竟會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新興生長點?或是反過來成為新的動亂源,何去何從的選擇,正面臨著考驗。本書作者桑德斯為了探討這個課題,不僅窮究當代這方面的研究著作,更橫跨五大洲走訪了三十座城市與鄉村,寫成無論從人性,文明史,和當代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各種層面看,都極具時代高度的傑出著作,在我的知識標準裡,它這是與科普對應的社普這個領域的頂級著作,對全世界讀者、學者,甚至於政策制定者都有振聾發聵,讓人的思考能力有煥然一新的喜悅之感。
由人類的社會經濟史,我們都知道人類由篳路藍縷一步步走來,早期的篳路藍縷經驗早已被後代的資產及中產階級所遺忘,因而理所當然的視後來的中資產階級價值及合理性為應然,而對篳路藍縷祖先輩的經驗再現,則認為是次等不入流,這乃是都市中資產階級看到新興鄉村到都市的移民群落,那種歧視感的起源。人們看著他們居住地點的擁擠湫隘和髒亂,本能性的就排斥之、輕賤之,巴不得他們從眼前消失,如果這種心態的人成為執政者,好的人會出現奇怪的道德感將他們的社區鏟平,蓋起高樓大廈但殊不知這遠遠超過了那些人的經濟能力,只是將他們驅逐到更惡劣的環境,甚或真正的置他們於死地。真正合理也合乎人類歷史經驗的做法,乃是將移民第一個落腳的城市扮演好移民社會友善的迎賓室角色,尊重他們的求生權利和資格,不把都市中資產階級價值觀橫加在他們無力承擔的肩膀上,而是讓他們享有和我們祖先從篳路藍縷中發展的機會。每個移民的聚落都是由生存意志強韌無比的人口所組成,他們刻苦耐勞、奮鬥不懈、認真學習,運氣好的不必一代,平均只要兩代,在友善的環境下就可發展到和我們一樣成為中產階級。然後他們離開這個落腳城市,進入主流社會,他們留下來的地方讓位給更新的移民,如此生生不息,經濟與社會的活力也源源不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狄亞.沈思(Amartya Sen)曾經深刻的指出過,新的移民能力、意志什麼都不缺,他們唯一缺乏的乃是落腳城市由於友善或不友善而造成的缺乏生存的「門路」,他所謂的「門路」不是我們所謂的「鑽門路」,而是一個友善的城市透過體制化的安排,而使他們擁有廣泛的機會。易言之,用當代社會經濟學「社會資本學派」的說法,乃是為他們營造出社會資本異端,有能夠值得努力下去的條件。
當代哈佛大學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學者首創「社會資本」之說,將貨幣、人力等資本之外,將社會本身也視為資本的一種形式,譬如說一個社會的官吏效率良好,即是一種良好的資本。一個社會正式或正式的整個肌理,也都是社會資本的範疇。在一個落腳城市,如果對新移民有偏見,不能取得合法的住民身份,在自由就業貸款或求學上有種種障礙,他們也無法自由開創出適合生存的人際網路,政府也不能在適合他們生存的公共條件上投入資本或任由他們被雇主或不良勢力剝削,那麼這些移民聚落就缺乏了由篳路藍縷到成長的機會和條件,他們的抵達就只會是噩夢又接一個噩夢,他們的生命也只會下沉,不會向上流動。本書也指出,在友善的落腳城市,已出過巴西傑出的總統魯拉,伊斯坦堡市長埃爾多安,洛杉磯市長維拉萊波沙等不平凡的移民人物,這也證明了人們歧視移民的偏見是如何的可怕與錯誤!近年來,我愈來愈相信人的問題沒有爛蘋果,只有爛籃子,落腳城市就是個爛籃子或好籃子的問題。
近年來,全球最大移民潮的中國,移民工人問題日益嚴重,中國的官吏深受俗化的階級偏見影響,再加上官僚主義,他們以戶籍制度限制工人在落腳城市取得居民合法身分,而在中國無身分,即不可能享有受教育、醫療福利一切權益,因此它們的移民勞工只能在工作地點居住在形同監獄的勞工宿舍,賺取微薄的薪水,有家眷的只能每年過年時見一次面。而今物價上漲,縱使調薪也無補實際,因此近一、兩年工人大批過年回鄉後即不再回來,許多雇主已不敢接單,許多產業正因移民工人問題而凋萎,對中國經濟已造成極大的壓力。鴻海的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青年移民勞工不敢結婚生育,這些問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源頭,那就是落腳城市對移民工人缺乏了友善。中國已有學者認為必須解除城市的身分管制,讓貧民窟開放,他們的思維邏輯裡,就是讓移民工人有篳路藍縷成長的早期資本主義及城市成長的機會。這種主張看似突兀,但貧民窟裡可以出總統、市長,重新思考落腳城市的問題,其實已到了時候。
本書理論及故事都豐富動人,而且洋溢著深刻的人性價值的關懷,洵屬極為稀見的社會傑作!
《落腳城市》推薦
劉可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道格.桑德斯的新書《落腳城市》運用了新聞記者最擅長的手法,在全世界三十個大小城市與社區裡,以近距離的追訪方式,深入淺出的描述了動人的鄉城遷徙故事。這些人與城市的故事將對我們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紀全球變遷中的城鄉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在大規模人口遷徙的過程中,落腳城市是一個動態的社會現象。它至少有四個正面的功能:做為一個維繫人際關係及社會網絡的中繼站,做為一個進入城市就業市場的媒介機制,做為一個在城市中可安定立足的平台,以及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社會晉升的管道。在全球城市化的過程中,落腳城市讓大量的鄉城移民可以逐漸去除貧窮,創造資產累積,進而孕育新興中產階級的能量。
桑德斯的細微觀察與宏觀分析並非創先。早在二十世紀中期的後工業城市化過程中,學者專家們即已注意到城市新移民在創造中產階級的社會安定以及財富的累積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熟知的珍.雅各(Jane Jacobs)之《偉大城市的誕生與死亡》外,另有一位很重要的學者李.桑德考克(Leonie Sandercock),她的《世界城市-II》(Cosmopolis II)不只是對於鄉城遷徙的現象與功能有深刻的觀察,更將世界城市的多元文化與其交錯複雜的社會關係形容為一種特殊並關鍵的「雜種」(mongrel)。在她的分析中,財富累積,晉升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創新的根本元素就是多元,複雜,高密度的雜種文化。這個觀點在《落腳城市》中得到具體的印證,高密度,多元複雜的鄉城遷徒提供了創新的機會與能量。
名人推薦:【名人推薦】
「本書作者桑德斯為了探討這個課題,不僅窮究當代這方面的研究著作,更橫跨五大洲走訪了三十座城市與鄉村,寫成無論從人性,文明史,和當代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各種層面看,都極具時代高度的傑出著作,在我的知識標準裡,它這是與科普對應的社普這個領域的頂級著作,對全世界讀者、學者,甚至於政策制定者都有振聾發聵,讓人的思考能力有煥然一新的喜悅之感。── 南方朔‧知名作家、評論家◎專文推薦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 的新書《落腳城市》(Arrival City) 用了新聞記者最擅長的手法,在全世界30個大小城...
章節試閱
六公里,中國
話從一座村莊說起。在外人眼中,這座村莊彷彿定格於時間裡,遺世獨立,安寧靜謐,亙古不變。這座村莊看起來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行經此地,瞥見村裡叢聚的低矮房屋,必然覺得這裡平靜安詳,充滿了細膩而秩序井然的美。在想像當中,這裡顯然有著怡人的生活節奏,不受現代化的束縛。村中為數不多的簡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頂端。畜欄裡有幾隻牲畜來回走動,兒童在一片田地的邊緣奔跑著,炊煙從一間小屋上冉冉升起,一個老人漫步在山丘頂上的樹林裡,背後馱著一只布袋。
這個老人名叫徐欽全,正在找尋治療藥物。他沿著梯田邊緣的古老石徑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這是他的家族成員走了十個世代的道路。在這裡,他可以找到自己兒時就已知曉的各種藥物:莖桿纖細的麻黃,用於發汗去風邪;枝葉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補肝效果。他以小刀割下莖桿,裝進布袋裡,再走回丘頂。爬到頂端之後,他停住腳步,略站了一會兒,望著北方揚起的塵土。在那裡,一群建築工人正在把一條狹窄崎嶇的小徑開發成寬廣平直的大道。往返北邊的重慶原本要一天的路程,不久之後就將縮減至兩個小時以內。徐先生看著遠方的樹木被煙塵染成土黃色。他想著村裡眾人的苦難,想著折磨他們已久的痛苦。這樣的苦難導致他們的兒童送命,使他們數十年來活在缺乏糧食的恐慌裡,接著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單調生活中。那天晚上,在村莊大會上,他提出了一項拯救全村居民的方法。今晚之後,他說,我們將不再是個小村莊。
當時是一九九五年,這座村莊名為「六公里」。這座村莊的外觀、村裡的家族,乃至仍然維持完全人工耕種的小麥和玉米,在幾百年來都幾無改變。這座村莊在緬甸公路興建期間獲得了「六公里」這個名稱,原因是緬甸公路的東方終點就在內陸大城重慶。不過,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數十年之久,「六公里」卻成了個虛幻的名稱,因為原本通往重慶的橋梁遭到炸毀,最近的替代橋梁不僅位於好幾公里之外,更因路況極差,以致繞道前往那座橋梁根本不符成本效益。況且,那道橋梁也遭到了共產黨的封鎖。這座小村莊因此無法與任何城市或市場聯絡,只能自己種植作物維生。由於土壤貧瘠,農具簡陋,村裡生產的糧食一直都不夠餵飽所有人。每隔幾年,天氣與政治的變化就會導致饑荒,造成居民喪生,兒童挨餓。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的可怕時期,這座村莊喪失了一大部分的人口。饑荒在二十年後終於結束,但存活下來的居民也只能依賴政府補助勉強過活。一如世界各地的農村,六公里的村民也沒人認為鄉下生活有任何平靜或自然之處。在他們眼中,鄉下生活乃是一種單調乏味而且又駭人的賭博。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開始擁抱某種型式的資本主義,於是其國內的村莊也就突然獲准為了市場需求而開發非耕地。因此,徐先生在會議上提出他解救村莊的方法之後,現場毫無異議:如此一來,村裡所有的土地都將成為非耕地。自此以後,六公里就不再是鄉村,而是搖身一變成為鄉村居民的遷徙目的地。
十五年後,六公里成了重慶市郊一公里處一個盤桓在一條四線大道旁的幽靈:在密集矗立的公寓大樓之間,突然出現一片閃閃發光的海市蜃樓,只見一望無際的許多灰色與褐色方塊在山坡上流洩而下,形成一團毫無章法的水晶結構,徹底掩蔽了地貌。靠近看,才發現這些水晶原來是房屋與商店,是居民在未經規畫也沒有申請許可的情況下以磚塊與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層樓住家,交疊聳立,以難以置信的角度突出於地表上。在徐先生提出自救方案之後不到十年,他這座原本只有七十人的村落已經增加了超過一萬名居民;十幾年內,這附近的幾座村莊已結合成一片居民多達十二萬人的聚落,其中絕大多數人的戶籍都不在這裡。這裡不再是一座偏遠的村莊,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圍地區,而是重慶市當中頗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慶市的人口多達一千萬左右,摩天高樓四處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都與曼哈頓相仿。重慶市每年增添超過二十萬人口以及四百萬未登記的移入居民,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長速度最快的城市。
這樣的成長主要來自於六公里這類地區的人口增生。像六公里這樣由逃離鄉下的人口自行建構而成的聚落,在中國稱為「都市村莊」,重慶市周圍就出現了好幾百座這樣的村莊,儘管市政府並不承認這些聚落的存在。這些地區的街道與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出處而劃分;居民對於和自己來自同一個鄉間地區的鄰居都稱為「同鄉」。在中國各地,每年至少都有四千萬農民湧入這類都市飛地。不過,這些人口當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許多達半數——最後還是回到鄉間村莊,也許是因為都市生活太過辛苦,也許是因為衣食無著,也有出於個人喜好的選擇。能夠在都市飛地留下來的人口通常具有非常堅定的決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髒亂腐臭的貧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古徑現在已經成了一條繁忙的街道,兩旁滿是雜亂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手機行、肉販,冒著蒸氣、飄散著嗆辣香味的小吃店,還有賣衣服、賣工具、賣高速紡紗線的攤商,熱鬧嘈雜,蜿蜒長達兩公里,深入令人暈頭轉向的雜亂小巷與不知通往何處的階梯,看來就像是把幻覺藝術之父艾薛爾(M.C. Escher)的版畫顛倒了過來一樣。頭頂上滿是電線和有線電視的線路;廢水從水泥地裡湧出,流過房屋周圍,沿著開放的水溝灌入一條臭氣沖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橋梁下。垃圾與廢棄物似乎無所不在,在每一棟房子後面堆積成山。每一條巷道上都壅塞著二輪、三輪、四輪的車輛。所有的空間都擠滿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舉目所及完全看不見綠意。從這個觀點來看,你也許會認為這裡是窮人迫不得已的棲身之地,是這個龐大的國家裡遭到社會摒棄的失敗者最後的容身之處——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過,你一旦從主要道路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徑,即可看出六公里這種地方的真正本質。在每一扇窗戶後方,在每一棟水泥房屋的粗陋門口裡面,都可見到繁忙不休的活動。在山谷頂端,也就是徐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做出重大決定的那個地點附近,你會不禁注意到一棟由渣煤磚蓋成的長方形建築,塞在一個陡峭的角落裡,不斷發出吵鬧的聲響,並且散發著怡人的杉木香味。這裡是王健一家人的工廠兼住家。三十九歲的王先生在四年前從八十公里外的南涌村搬到這裡,身上帶著七百元人民幣(一百零二美元),是他從事兩年木工工作所攢下的積蓄。他租下一個小房間,撿拾了一些廢棄的木料和鐵料,然後開始以手工製作傳統的中式洗澡木桶。這種木桶頗受新興的中產階級喜愛。他花了兩天的時間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後賣了出去,每個木桶賺得五十元人民幣(七點三美元)的利潤。一年後,他賺的錢已夠他買些電動工具和一間比較大的工作室。他把太太、兒子,還有兒子的太太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孫子一起接了過來。他們睡覺、烹飪、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後方一個沒有窗戶的空間裡,只用一張塑膠簾隔開。比起他們當初在鄉村裡勉強居住的小屋子,這個空間不但更擁擠,也更沒有隱私。
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想要回去鄉下:這裡雖然骯髒狹小,生活卻比鄉下好得多。「在這裡,你只要找對了謀生方式,就可以讓你的孫子獲得成功的機會——在村莊裡,你只能努力填飽肚子,」王先生說。他一面用一條鐵帶箍住木桶,一面用連珠砲般的四川方言說著話。「我那個村裡和我一樣離鄉背井的人,我猜有五分之一都是自己創業。而且,村裡幾乎所有人都離開了——只有老人還留在那裡。那裡已經變成一個空村子了。」
王先生和他太太仍然固定會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裡,供養他們仍然建在的兩名退休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買下了同一條路上的一家餐廳讓他兒子經營。王先生的獲利空間很小,因為競爭非常激烈:重慶還有另外十二家洗澡木桶工廠,其中一家同樣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廠產量最高,」他說:「可是不一定是利潤最高的。」因此,他們還得存許多年的錢,並且祈禱洗澡木桶業的熱潮不退,才有能力買下自己的公寓,把孫子送上大學,並且舉家離開六公里。不過,等到他們夢想成真的那麼一天,說不定六公里也已經發展成了他們夢想中的城市。
這整座山谷看起來猶如一幅灰色的立體派畫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築裡藏著許許多多在政府紀錄上並不存在的微小企業。在木桶工廠的同一條街上,可以見到另一個極度吵鬧的地方,共有二十名員工在那裡製造著鐵欄杆;除此之外,更有其他許多工廠,一家生產大型冷藏庫,一家是粉末顏料攪拌廠,一家工廠以五、六部大型機器輸出刺繡圖案,另一家生產電動馬達線圈,還有一個地方酸味刺鼻,只見許多十三、四歲的小小工人彎著腰操作熱封機,製作吹氣海灘玩具。這裡有著各式各樣的家庭工廠,製作櫥窗道具、塑鋼窗戶,射出工業用空調管,生產廉價木質家具、木質裝飾床架、高壓變壓器、電腦車床加工而成的機車零件,以及不鏽鋼餐廳抽油煙機。這些以亞洲各地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工廠全都創立於近十幾年,老闆不是外來的鄉村移民,就是第一波鄉村移民的員工。
在每一棟素面的水泥方塊建築裡,都可以聽到同樣的故事:從外地搬遷而來,努力奮鬥,供養家人,認真儲蓄,規畫未來,仔細盤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還有這個地區的全部十二萬人口,都是一九九五年以來移入的鄉下村民。這裡雖然骯髒、擁擠、生活困苦,而且這些人經常都把子女和家人遺留在鄉下村莊裡,但他們只要在這裡撐得過頭幾個月,就會決定留下來長期奮戰,因為他們認為在這裡才有希望。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自我否定以及極度貧困的生活。幾乎所有人都會寄錢回家供養村裡的家人,再存一點錢準備讓自己的孩子日後到城裡接受教育,而且這些幾乎就佔了他們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斷盤算著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鄉下讓人難以忍受的貧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難以負擔的開支,同時也盼望著有一天能夠時來運轉,得以突破這兩方面的困境。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的主要功能就是做為他們遷徙目的地的門檻。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圍的新興聚落,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這裡不只是個供人居住、工作、睡覺、吃飯、購物的地方,而最主要是個過渡性的地點。在這裡,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種重要活動的目的都在於把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莊帶進都市的世界裡,帶進社會與經濟生活的核心,讓他們得以接受教育和教化,融入主流社會,享有可長可久的繁榮生活。落腳城市不但聚集了處於過渡期的居民——外來人口一旦到了這裡,即可轉變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裡享有可長可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是個處於過渡時期的地區,因為這裡的街道、住宅,還有居住在這裡的家庭,有一天都將成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標的路途中敗下陣來,陷入貧窮的深淵當中,或是遭到搗毀拆除。
落腳城市和其他都會地區有著極為鮮明的差異,不只因為這裡住的都是外來的鄉村人口,也不只因為這裡的市容充滿了臨時拼湊的色彩,又總是變化不休,而是因為這裡的每一條街道、每一間住家和每一個工作場所,都不斷聯繫著兩個方向。一方面,落腳城市與「來源鄉村」保有長久而緊密的聯繫,人員、金錢與知識的往返流動不曾止息,從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遷徙活動得以發生,也讓村裡的老年人口得以獲得照顧、年輕人口得以獲得教育、村莊本身也得以擁有建設發展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落腳城市也和「既有都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聯繫;其政治體制、商業關係、社會網絡與買賣交易都是一個個的立足點,目的在於讓來自鄉村的新進人口能夠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站定腳步——不論這樣的立足點有多麼危顫不穩——從而謀取機會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中心,以求獲得社會的接納,與世界產生連結。六公里生產許多物品、販賣許多物品,也容納了許多人口,但這許許多多令人眼花撩亂的活動,都有著一項核心的目標,一個共同的使命。令公里是一座落腳城市。在都市的這個外圍地區,這裡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六公里,中國
話從一座村莊說起。在外人眼中,這座村莊彷彿定格於時間裡,遺世獨立,安寧靜謐,亙古不變。這座村莊看起來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行經此地,瞥見村裡叢聚的低矮房屋,必然覺得這裡平靜安詳,充滿了細膩而秩序井然的美。在想像當中,這裡顯然有著怡人的生活節奏,不受現代化的束縛。村中為數不多的簡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頂端。畜欄裡有幾隻牲畜來回走動,兒童在一片田地的邊緣奔跑著,炊煙從一間小屋上冉冉升起,一個老人漫步在山丘頂上的樹林裡,背後馱著一只布袋。
這個老人名叫徐欽全,正...
目錄
目次
序:一切事物改變之處
一、城市的邊緣
六公里,中國
塔村(Tower Hamlets),英國倫敦
二、由外而內:新城市的盛衰演變
最初的開端:小移動,大遷徙—寇赫瓦迪(Kolhewadi),印度拉特納吉里市(Ratnagiri)
生產陣痛:落腳城市的成形—坎蘭格查(Kamrangirchar),孟加拉達卡
發展停滯:缺乏立足點的城市—深圳,中國
停滯不前的城市—基貝拉(Kibera),肯亞奈洛比
改革:危立於懸崖上—聖馬塔(Santa Marta),巴西里約熱內盧
三、立足於金字塔的頂端
令人浩嘆的美國落腳城市—洛杉磯,加州
後移民國家的落腳城市
外來移民的郊區化發展—維吉尼亞州赫頓(Herndon)與馬里蘭州惠頓(Wheaton)
四、鄉村的都市化
鄉村陷阱—達塔利(Tatary),波蘭
最後的村莊—水林村,中國四川省
沒有城市的鄉村—朵利(Dorli),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
落腳村莊—畢斯瓦納(Biswanath),孟加拉錫爾赫特
五、第一波人口大遷徙:西方如何形成當今的樣貌
現代世界的醜陋門戶—巴黎
十九世紀的建構過程—倫敦
隱藏的移民—多倫多與芝加哥
六、一座落腳城市的死亡與誕生—伊斯坦堡
外來移民找到了落腳處
都市邊緣的挑釁力量
與舊市區直接衝突的落腳城市
舊市區接管落腳城市
落腳城市的轉變
新移民遇上落腳城市
落腳城市尋得本身的政治立場
落腳城市吸收舊市區
七、起於市郊邊緣的巨變
伊撒聖殿(Emamzadeh ‘Isa),德黑蘭
沙漠中的火花
始於邊緣的內潰
社會悲劇
貝塔瑞(Petare),委內瑞拉卡拉卡斯
穆蘭德(Mulund),孟買
八、新城市與舊世界的衝突
空間的問題—金字塔社區(Les Pyramides),法國埃夫里(Evry)
公民身分的問題—克勞茲堡(Kreuzberg),柏林
空間與公民身分—帕爾拉(Parla),西班牙
九、遷徙的終點:從土壤地板到中產階級
佳丁安潔拉,巴西聖保羅
孟買
十、在都市立足紮根
斯洛特瓦特,阿姆斯特丹
卡拉伊爾,孟加拉達卡
松克里夫公園,多倫多
目次
序:一切事物改變之處
一、城市的邊緣
六公里,中國
塔村(Tower Hamlets),英國倫敦
二、由外而內:新城市的盛衰演變
最初的開端:小移動,大遷徙—寇赫瓦迪(Kolhewadi),印度拉特納吉里市(Ratnagiri)
生產陣痛:落腳城市的成形—坎蘭格查(Kamrangirchar),孟加拉達卡
發展停滯:缺乏立足點的城市—深圳,中國
停滯不前的城市—基貝拉(Kibera),肯亞奈洛比
改革:危立於懸崖上—聖馬塔(Santa Marta),巴西里約熱內盧
三、立足於金字塔的頂端
令人浩嘆的美國落腳城市—洛杉磯,加州
後移民國家的落腳...


 2012/06/15
2012/06/15